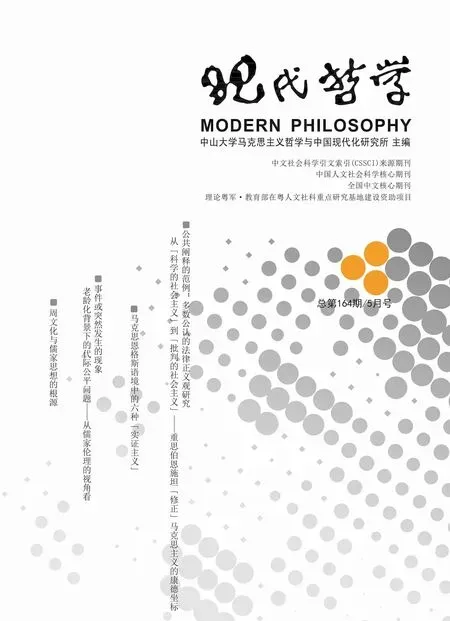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公平问题
——从儒家伦理的视角看
王 珏
一、老龄化与代际公平危机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保障体系改革成为最受重视、最多争议的世界性伦理-政治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场围绕着养老保障领域中“代际公平”(generational equity)的讨论就已经席卷北美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并延续至今,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议程与政策导向。如学者们所达成共识的,“代际公平”问题背后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语境是全球人口结构老龄化[注]Steven K.Wisensale, “Global Ag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Vol. 1, No.1, 2003.。严格说来,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由两个因素构成:低生育率、人均寿命的延长。两者共同作用的直接后果就是养老抚养比的变化:一边是愈加庞大的退休人口,耗费越来越多的退休金和医疗照顾费用;另一边则是急剧减少的劳动人口,未来能转移支付给退休人口的资金也相应减少。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对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提出严峻挑战,更严重的是,它侵蚀了养老制度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代际契约(generational contract)。养老制度本质是一种在经济上活跃的社会成员与已不活跃的成员之间分配资源的政治制度,因而,必然隐含一种代际契约作为伦理前提:当前工作的一代有义务支持退休的一代,同时作为回报,当前工作一代有权利在自己将来退休的时候,从未来工作的一代得到同等水平的支持。然而老龄化趋势展现了一种可能违反契约的不公平前景:当下和未来的工作世代(working generations)将不得不承担越来越高的保险缴费率,但当他们退休的时候得到的资金支持却大为缩水,有研究者将这种前景称为养老金权利危机(the “entitlement” crisis)。不难发现,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同样面临着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代际公平危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正以世界第一的老龄化速度迈向深度老龄社会,并将长期负担着世界上数量最大的老龄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7%,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达到11.4%,接近国际标准14%的深度老龄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低迷,刚刚颁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显示,中国人口的负增长已经势不可挡。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代际公平已经成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迫在眉睫的危机:统计数据显示,基本养老保险的抚养比已经由制度建立之初的5∶1降到2.8∶1,2015年养老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达到6个,并且据相关机构的测算,到2022年半数省份养老基金将收不抵支,其中个别省份累计结余耗尽风险加大[注]王延中主编:《社会保障绿皮书: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9)No. 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5—34页。。

这种价值视野上的差异不应当仅仅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偏好,相反,其中隐藏着解决中国养老领域代际公平问题的重要伦理资源,后者正是本文试图挖掘的主题。事实上,西方持续几十年之久的代际公平讨论与其说提供了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不如说促成了如下认识:代际公平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如何解决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解作为养老保障制度运作基础的代际契约。一方面,只有诉诸于代际契约,才有判定公平与否的标准;另一方面,对代际契约模式的不同理解也制约着追求代际公平目标时所能采取的手段,并最终影响代际公平实现的效果。
代际契约具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这意味着在衡量某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代际公平状况时,必须充分考量文化语境与传统价值信念的影响。换言之,妥善应对中国养老保障领域中的代际公平危机需要回到我们自身的文化根基,寻找能够将传统与现实结合起来的伦理生长点,并通过恰当的制度转化,将之培育为能够在老龄化压力下保护代际团结的屏障。这是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历史性任务,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课题。本文将仅限于从伦理角度探讨此课题中的一个起点性问题:中国传统的养老代际契约及其对代际取予均衡关系的理解,是否仍然是在中国当下历史语境中实现代际公平的重要出发点?如果以之为出发点,它又为实现代际公平贡献了什么样的理论视野和制度资源?
二、 中国语境下的反馈模式与代际契约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著名社会家费孝通就提炼出“反馈模式”,作为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并将之与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严格区分开来。用公式来表示,西方的公式是F1→F2→F3→Fn;中国的公式是F1←→F2←→F3←→Fn(F代表世代,→代表抚育,←代表赡养)[注]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第7页。。两个模式的首要差别在于是否承认子女赡养父母义务,更深层的差别则是对代际契约的不同理解。接力模式预设的是单向的、个人主义导向的契约;而反馈模式则将每个主体(Fn)看作是属于同一个给予与反馈的网络中,平衡世代之间的取予的代际契约也必须依赖于这个网络才能得到确定。这种以儒家孝道为根基的“反馈模式”,不仅是无数中国家庭仍然实践着的日用伦常,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代际关系和养老模式的一个主导视域[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代的社会调查资料都表明家庭养老在中国当代社会仍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虽然也面临种种挑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其次,《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我国《婚姻法》第21条也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就养老是涉及伦理、政治和实践的综合问题而言,它不能不受到所置身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对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家庭价值与孝道。。随着社会文化与家庭结构的变迁,越来越多社会研究与调查注意到养老领域中传统反馈模式的衰落及由此引发的代际不公问题:反馈的逻辑被市场化和理性经济人的交换逻辑或者片面强调父母义务的“恩往下流”所替代,结果是已经为子代付出的父辈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特别是在某些农村地区,老人在失衡的代际关系格局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又受制于历史因素与制度因素而无法得到充分的国家福利支持,以至于晚年生活艰辛。代际失衡所导致的农村养老危机,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和伦理问题[注]参见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基于反馈模式的巨大影响,中国语境下的代际公平议题指向的是包含着两个维度的一场全面危机。从宏观维度(公共生活层次)看,代际冲突的来源是不同世代对福利制度贡献与收益的不平衡,危机的核心表现是国家福利制度能否承受为越来越庞大的老年群体提供退休金和医疗福利的压力。从微观维度(私人生活层次)看,代际危机的来源是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的不平衡,特别表现为一种子代对父代的单方面索取,所谓“恩往下流”的现象。危机的核心表现是主张家庭责任的传统反馈养老模式能否在现代社会行之有效。
需要看到,相较于通常只关注福利制度层次上代际冲突的西方视角,上述中国视角不仅仅在宏观维度之外加上一个微观维度,更重要的是,对代际契约性质的解释发生了一个微妙而深刻的重点转移。我们可以将之标识为一种从代际“竞争模式”到“相互依赖模式”的转变,两者立足于对世代的不同时间经验。如德国现象学家黑尔德(Klaus Held)敏锐指出的,对生命进程有两种不同的时间上的体验方式,一种是度日的经验,另一种是世代生成的整体性经验[注][德]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倪梁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58页。。度日的经验基于日常性,基于我们对时间日复一日的计算。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代际公平理念就是基于上述计算逻辑的概念,将代际冲突理解为不同世代(即先后进入国家福利系统中的不同年龄群组)之间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谓代际公平就是计算出离散的不同年龄群组的公平分配份额。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则系于原发的亲子和家庭经验,通过亲子经验“超过对个别日子的计算,而远眺我的生命整体,将作为生死之间的成长和衰老,自己的衰老至死亡的生命过程置于世代序列”[注]同上,第254页。。换言之,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源生于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及生命深层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事实。传统反馈的养老模式所呼应的正是这一深层的时间经验,其隐含的代际契约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代际相互依赖的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仅仅关注福利制度中世代之间的线性关联,反馈模式的代际契约着眼于从人生的整个历程来衡量社会成员世代间的取予关系,并倾向于超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僵硬划分。两者之间的区别具有深刻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和伦理蕴含。本文将仅限于从伦理角度探讨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如何引导我们超出西方自由主义模式,而趋向于一种体现儒家正义论原则的代际公平理念。
三、 家庭与孝道作为理解代际公平的基础语境
笔者将通过与自由主义契约论模式的对比研究,阐明基于世代生成经验的代际契约对解决代际公平问题的关键意义。本文选择美国生命伦理学家诺曼·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的审慎生命周期理论(prudential lifespan account)作为自由主义契约论模式的代表,是基于如下两个理由:1.丹尼尔斯是将罗尔斯正义论应用到养老保障制度领域的理论先驱,其立场可以说代表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应对养老代际公平危机的一种主导模式;2.丹尼尔斯明确否认孝道可以成为养老资源分配的价值基础,而孝道恰恰是中国传统反馈养老模式的伦理与文化基础。
丹尼尔斯从实际生活和伦理论证两个方面给出了必须排除孝道原则的理由: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的改变,国家福利制度已经代替家庭成为养老责任的首要提供者。重新回到家庭养老模式无异于开历史的倒车;另一方面,仅仅依据父母养育了子女这一事实,无法合理地推出子女孝养父母的义务,或者至少无法无争议地确定子女对父母所负义务的内容。这里,丹尼尔斯的论证可以看作是康德经典论证的一个翻版,其核心论点是亲子关系永远无法达到对等性。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是由他们选择成为父母这一行为所附加的,但子女没有对等的行为(即子女并没有选择成为子女的自由),因而子女并不欠父母任何东西[注]Norman Daniels, Am I My Parents’ Keeper? An Essay on Justice between the Young and the O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9.。在将家庭与孝道排除出可选项范围之后,丹尼尔斯设置了一种罗尔斯式无知之幕,以实现用一种完全公共的方式来确定代际之间公平分配比率的目的。他主张从生命周期出发,将不同年龄群组之间的财富转移理解为同一生命不同阶段之间的转移。如此确立的分配比率是完全以个人为导向的,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代际转移的形式。
从儒家视角出发,丹尼尔斯契约论的理论框架至少在三个方面会遭遇严重的理论困难。第一,孝道责任不能被还原为一种基于对等性的伦理关系。在儒家看来,家庭关系首要的是一种“一体”的关系:“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若草莽之有华实也,若树木之有根心也,虽异处而相通,隐志相及,痛疾相救,忧思相感,生则相欢,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亲。”(《吕氏春秋·精通》)“一体”的比喻不仅意味着家庭成员属于一个共同体,而且凸显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怀救助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的特征在于它的无条件性:比如我母亲生了严重疾病,我不得不承担照料她的责任,虽然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对我构成不公平,因为这恰恰是家庭关系本质的内在要求。换言之,置身于家庭之中意味着被接纳于一个给予与接受的网络中,在其中我最迫切的需要总会得到回应。鉴于人类生存的脆弱性和有限性(即每个人都会有年幼、生病、受伤、残疾以及衰老的时候),这种以家庭为典范的给予与接受之网构成了人生的基本之善,是人类生活繁荣兴旺的一个根本条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网络中给予者与接受者的身份是可互换的、可逆的,造就我们给予者的身份与道德义务的是我们曾经作为接受者所接受的照料。当自由主义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设想为对等的原子式个体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是否认了父母与子女的生命是通过代际演替而深度联结在一起的事实,否认了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与之相反,儒家对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理解已经预设了一个给予与接受的共同体,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道德义务是基于在这一关怀共同体中关怀者角色的交互性,而非对等性。孔子有一段著名评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这可以看作是上述逻辑的直观佐证。而中国传统的反馈模式F1←→F2←→F3则可以看作是上述逻辑的制度化,其中每一个Fn都是一个责任主体,通过交互责任实现代际之间的依赖和团结。总之,在儒家看来,要正确理解代际之间的伦理契约、理解养老秩序,就必须从家庭开始,从肯定代际之间的相互依赖开始。是否承认家庭源初的伦理地位,是儒家与自由主义者在养老问题上争执的第一个关键点。
丹尼尔斯模式会遇到的第二个严重挑战,是关于选择主体的同一性难题。丹尼尔斯模式设定无知之幕(包括对自己年龄无知)之后的个体必然会选择一种最公平的方式,在整个生命周期之内合理分配社会基本善。然而,这样孤零零的、抽象的个人是否能够真实想象自己老龄生活的样子,能够预测自己在衰老的阶段所持的价值观?如果无法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丹尼尔斯模式就会面临“非同一性”问题,从而危及他的核心主张,即生命周期解释应当可以不偏不倚地对待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注]此处关于对审慎生命周期理论的“非同一性”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对Waymack的研究的扩展。(Mark H.Waymack, “Old Age and the Rationing of Scarce Health Care Resources”, Aging and Ethics, Nancy Jecker ed.,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1991.)。为了把生命诸阶段融为一体,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所谓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共同的词汇和实践以把握生命历程的总体意义。对后一个任务而言,显然家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家庭提供了一个重要语境,只有参照它,个体的生命历程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才能具有公共可理解性。
儒家反馈模式的一个理论优势在于它将主体的年龄变化与他在一个给予与接受的共同体中的伦理地位的变化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叙事。并非偶然的,人们在家庭代际中的位置与其在福利制度中的代际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通过将代际之间的正义问题转化为个体不同年龄阶段之间的分配问题,丹尼尔斯实质上割裂代际之间的联系,也遮蔽了福利制度与社会其他机制之间的互动,这使他所设想的那种理想化的代际分配比率难免沦为空中楼阁。
第三点困难可以看作是第一点困难的逻辑延伸。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建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严格区分,并将在社会公共领域中能够充分合作的成年公民之间的关系作为理解正义的主要背景。这解释了丹尼尔斯模式的一个基础性预设,即代际公平只能在社会正义论的一般框架下解决,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孝道不能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但如果上述第一点论证是成立的,即养老道德义务首先基于对依赖性的承认以及对家庭作为一个接受/给予网络的基础地位的认可,那么罗尔斯式社会正义论就不足以应对养老领域中所有合理的、公平的要求。如美国著名社群主义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所指出的,当罗尔斯式正义理论以抽象的社会而非家庭或学校为背景时,它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即家庭成员的需要以及每个人为家庭的共同事业所做的贡献以及随之应得的利益,两者都为分配利益提供根据[注][英]艾里克斯·弗罗伊弗:《道德哲学十一讲》,刘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
此外,维持一个给予/接受的网络所需要的正义标准也与罗尔斯式正义标准完全不同。后者假定人们的基本需求都是稳定和同质的,我们可以理性计算出分配资源的最优化方式,以达到某种帕雷托最优状态。但在一个给予/接受的网络中,所谓“正义的”给予的标准并非是我曾经接受的东西,甚至不是我能合理期望得到的东西,而是需求者的需求本身。简单地说,我欠我父母的就是他们所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且这种责任是无法预先设定预算或加以理性优化,反之亦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无法在家庭的脉络中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相反,家庭成员经常为了改善一位亲人的命运(有时甚至只是为了满足愿望)而接受一些较小的或短期的不利情况,包括为了家庭整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注][美]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候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8页。。家庭生活的正义往往通过这种局部的“不公平”而达到整体网络的、跨时间的公平。与此类似,儒家会认为,丹尼尔斯模式将代际公平问题局限于社会正义理论框架之中是有误导性的。如果关于代际分配公平的探讨仅仅从成熟的理性人开始,那么这种探讨从一开始就忽视了养老问题所代表的人类生活处境(human condition)的一个真实基础,即脆弱与依赖。人生的底色离不开生命两端的依赖状态:从不免于父母之怀的幼儿到年老体衰的老人,人生的整个历程都包裹在交互照料网络之中,年龄的变化也必将表现为照顾与被照顾者角色的变换。只要人类生存还不能免于脆弱性和依赖性,那么这种相互关怀的网络就是处理代际关系与代际公平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因而,在儒家看来,罗尔斯式社会正义理论是不充分的,因后者的探讨方式在起点上就已经越过了代际之间根底上相互依赖的关系。
回到代际公平讨论中最基础的问题,代际之间是否有契约来维持资源的代际转移?如果有契约的话,契约又是依据什么达成的?儒家的回答与自由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儒家坚持认为家庭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语境,代际契约植根于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家庭关系原型,对代际公平问题的回答必须“始于家庭”。相应地,定义“代际公平”的最佳语境并非个体自身,而是个体衰老和世代更替过程中的一些共享的期待和义务。这些共享的期待和义务植根于日常实践着的代际依赖与团结,并且随着社会文化、伦理处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就家庭是实践代际依赖与团结的首要伦理场所而言,它必然在一种“代际公平”理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儒家思想的吸引力很大程度正是来源于它对家庭的本质与作用的深刻洞察。下文就尝试从儒家伦理资源出发,构建一种家庭本位的代际公平分配模式,以应对中国当下养老领域中的代际公平危机。
四、 儒家正义论视域下的代际公平
关于儒家思想的性质,当前学界也是莫衷一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说法有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和宗教儒学三种[注]赵宏宇:《儒家视野下的社会正义观》,《原道》2015年第28辑。。本文采取一个更宽泛的理解,把儒学理解为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生活体系,并以此出发重构儒家分配正义与社会正义理论,以应对来自现代生活的挑战[注]陈祖为:《儒家思想是否具有社会正义观》,《伦理学与公共事务》2008年第2期。。尽管养老领域的代际公平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资源就不再适用。虽然中国需要吸收很多西方因素以完成一个现代化的构建,但对于日常生活世界而言,“儒家式的正义秩序”仍然具有可欲的吸引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维持社会和伦理关系的正常运转。正如本文试图论证的,养老反馈模式不仅给解决中国语境下养老领域代际公平问题开辟了一种超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野,而且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度资源。问题在于如何重构儒家正义论,以使其最基本的特质、最关键的承诺能够切中当代社会现实的脉搏,帮助解决当下生活世界的挑战。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一种儒家正义论至少可以贡献如下三点重要启示。
首先,儒家理想中的正义社会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家庭被看作是一个正义社会的基础和中心。从分配正义的角度看,虽然家庭并不被包括在社会领域中,但家庭被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并为社会领域划定了第一组边界。因而,在分配中首先要确立以家庭为本位的优先原则。即使现代化进程分离了家庭所承担的部分功能(比如生产功能),但这并不改变家庭始终是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分配领域的事实。亲属关系和感情纽带也并未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使家庭成为一个分配正义无法企及的领域,相反,家庭领域有属于自己的正义原则,并将影响力延伸到其他领域,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密切相关[注][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宋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具体到养老秩序,儒家会认为参与代际契约的并不是离散的不同年龄群组,也不仅是单个的个体(这些个体分别属于不同的世代),而是不同的世代通过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代际之间的取予关系。换言之,就维持养老领域中的代际公平而言,家庭并非如自由主义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个无关因素,相反,它是一个关键的行动者,是平衡代际之间取予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中介。不同于罗尔斯式代际契约仅仅考虑单向度、前后相继地通过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同世代之间的平等分配关系,儒家式代际契约的着眼点是代际之间总已经在进行的互助互济:父代通过公私两个渠道转移资源给子代,直到子代工作、自立;子代工作后,自然有义务反馈支持父代,这种支持既包括家庭内的赡养,也包括通过养老福利体制向父代转移收入。换言之,保持和提升代际公平的关键在于维持和加强代际团结的纽带。落实到公共政策,儒家的代际公平观念会更加注重平衡老年福利与儿童福利,并倾向于为家庭留下更大的自主空间。
相应地,世代之间公平分配原则不应仅仅基于个人的权利与应得,或者说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权利与应得,而是我们相互交织的生命与责任。如范瑞平指出的,经典的儒家社会正义论首要关心的是,如何促进和提升仁义这些内在伦理之善的实现;儒家正义观要求的是与他人相关的德性(仁即是典型的例子)的完满实现,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自我的权利或应得[注]Tim Murphy & Ralph Weber, “Ideas of Justice and Reconstructions of Confucianism”, Asian Philosophy, Vol. 26, No.2, 2006, P. 111.。植根于孝的德性,儒家反馈模式事实上支持了家庭内部服务和资源的双向流动,不仅成年子女赡养老年父母,父母也会持续地给成年子女以帮助,包括金钱上的资助。这种传统的代际关系衍生出一种可以称之为“责任伦理”的机制[注]杨善华、贺常梅:《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老年人出于自身的责任感和对子女的关爱,他也会通过降低自身需要、帮助子女照看孙辈、承担家务、直接补贴等方式降低子女的家庭负担。将老年人简单理解为社会负担是一种误导的看法,相反,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双向的交流主导着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这种双向的交流有助于减轻国家福利制度内部代际不公的压力。一方面,从父母向子女的逆向资源流动可以有效平衡子代所负担的养老缴费压力。此外,从父母到成年子女的逆向资助的行为也是对国家福利系统的一种重要补充,因为父母对子女的资助和帮助通常更切合受帮助者的需要,能实现更有效率的资源分配。相关的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已经表明,这种家庭内代际互助的存在使得不同代际的利益冲突有了在微观层次上沟通和调和的可能性,亦即家庭养老可以为福利国家养老金改革提供缓冲空间。如果家庭养老衰落的话,那么养老体系就会陷入对社会保险路径严重依赖,一条腿走路的另一面就是潜藏着的巨大系统性和制度性风险[注]参见刘骥:《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欧洲福利国家养老金政治的比较分析》,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66页。。就此而言,无论从微观维度还是宏观维度看,代际公平关系在深层次上都需要通过家庭这个社会细胞而得到调节和维持。虽然存在着“恩往下流”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家庭养老已经失败了,而只意味着需要在变化了的条件下重新理解孝道。有学者指出,中国家庭正经历着“下行式家庭主义”的重构,这种家庭主义着眼于“代际团结的功能性益处和对孝顺的再定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转变,共同产生代际之间的团结一致”[注]阎云翔:《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第9页。。
最后,虽然儒家认为赡养老人是家庭的首要责任,但这里并不存在对政府责任的“挤出效应”,相反,家庭是否胜任这份责任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儒家仁政思想要求政府帮助家庭完成照料老人的责任,这既包括帮助家庭积累适度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也包括直接提供养老服务和养老支持。孟子曰:“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甚至给出保持家庭充裕的具体标准,以之为仁政的根本,“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假使家庭中人人生活充裕是社会和政府的分配目标,那么很自然那些没有得到家庭给予与接受网络庇护的人应该优先得到政府的适当照顾。一种儒家社会正义论会主张政府资源优先分配给四类人:“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就养老而言,这意味着政府有责任在家庭失灵的情况下起到替代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 儒家所主张的政府与家庭混合责任立场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建构中盛行的“大政府、小家庭”模式有着根本区别。后者是企图用政府责任来替代家庭责任,乃至挤出家庭。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指出的,如果国家只是单纯地取代了父亲的角色,那么福利国家并没有消除家庭破裂的社会成本,而只是将它从缺失的父亲处不公平地转嫁到纳税人身上,甚至反向激励“去家庭化”,进一步削弱社会资本[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唐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1页;易富贤:《从全球视角探求中国人口新政》,《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5期。。同理,片面强调社会养老将使人不能“亲其亲”,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最终侵蚀社会团结纽带。过分倚重“公共儿女”提供资源,不仅在分配上是低效的,而且易于陷入代际冲突的风险。就家庭是代际团结的源泉、也是其传递媒介而言,在老龄化时代,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养老保障制度更加需要守住家庭之根。
综上所述,儒家正义论主张一种超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二元对立的代际公平理念,这种代际公平不能被抽象为某种分配比率,而必须实现于一个植根于世代生成时间体验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相互依赖的关怀网络之中,在其中个人责任、家庭责任与国家责任相辅相成。从这种代际公平的理念出发,在制度层面上,儒家正义论支持构建一种以家庭养老为中心、国家福利制度为主导、社区服务为依托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合理建构的这种养老模式不仅可以延续中国文化伦理传统,而且可以有效沟通养老制度的宏观与微观层面,缓和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澄清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养老制度设计不应该被误解为是让国家退出养老责任,让家庭独自承担绝大部分的养老压力。相反,在儒家社会图景中,家庭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道环围。相应地,一种儒家正义论的视角始终关注如何在家庭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密切互动中为家庭的自主性与功能性留下充足的空间。这种思路对国家责任提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要求,它要求国家不仅承担应负的养老责任,而且要求国家建立维护家庭价值的社会政策体系,将养老资源分配问题嵌入更深层的社会成员相互依赖的网络中,以从源头提升代际和谐,降低养老领域代际冲突的风险。
- 现代哲学的其它文章
- 论自我与他者关系视域下的“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