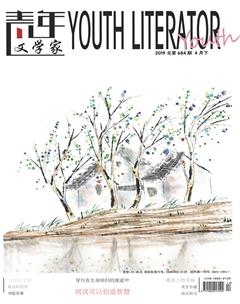论梁秉钧小说的流散书写
摘 要: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流散书写已然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梁秉钧的流散创作与其自身旅美求学以及游历世界各地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长期行旅,跨越不同的地区和国界,游走于不同的文化空间之中,梁秉钧得以拥有独特而多元的视角体察文化之间的差异。藉由文字探寻流散者的身份构建问题,并在流散语境下反观香港的文化身份。
关键词:梁秉钧;流散者;流散策略;文化身份
作者简介:张露(1996-),女,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2-0-02
一
“流散”从由希腊文转译而来,意思是“散播种子或者撒播”。最早使用“流散”的英文单词Diaspora时,首字母D是需要大写。大写的Diaspora专指犹太人的漂泊经历,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了犹太人在埃及受到悲惨的奴役,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埃及,寻找富饶之地迦南乐土。在几个世纪后,犹太人散居到世界各地,因此这种流散包含了犹太人的无根感、漂泊感和疏离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小写的diaspora,“流散”这一术语拥有了更加宽广的视角。人们被迫或者主动离开家园,穿越不同的空间,生活在异地,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生存状态。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流散”现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流散写作这一新的文化创作。“任何文学都必然以某种方式来抒写一种生存体验,现代散居经验的独特性催生了一种特殊的写作类型——流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这种写作引起跨文化的独特视角而具有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并成为当代最有魅力的写作方式之一。”[1]散居者作为跨界生存的特殊群体,他们具有双重或者多重生存体验,由此形成了复合混杂的文化身份。因此,对于文化身份的把握也是流散书写的关键。
梁秉钧在《东西》中说过:“我喜欢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接触不同的文化,但又同时知道跨越文化是不容易的。我既遇见种种不同的东西,有时带着他们跨越边界,有时倒是它们带我跨越了我自己认识的边界。”[2]梁秉钧自身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求学,又多次赴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地讲学,游历上海、澳门、台北、巴黎、纽约、华盛等世界各地。他把自己放置在广阔的世界中,遇見种种的人物,接触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在创作中他藉由文字去探寻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流散者,怎样面对异域文化做出选择。
二
流散意味着跨越不同的地区和国界,远离故国,在异国他乡生活,接触异域的文化。流散者在地域和文化上的越界,使他们必须面临文化身份构建的问题。斯图亚特·霍尔在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中谈到对身份的理解,“我们不能把它想成一个既成的事实,表征新的文化行为,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总是进行中的、永不完结的、总是从内部再现的一种生产行为”。从动态的角度看待文化身份,它是有待于生产、建构的,需要流散者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在当代理论中,它主要围绕个体能否自由地、自主的启动行为,或他们所做之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否能为他们的身份被构建的方式所决定的问题”。[3]
小说《使头发变黑的汤》中,玉珠的母亲婚后嫁给了美国的华侨,所以侨居到美国生活。玉珠的母亲是一位在中国旧式家庭长大的小姐,从未为生活操心劳累过度,来到美国后成为了一个柔弱的家庭主妇,依赖自己的丈夫。丈夫去世后,独自开餐厅拉扯五个子女长大,深切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在美国陌生的文化背景下,玉珠的母亲最终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友善大度的品质,成功地在美国扎根,生存下来。虽然生活在美国,但是她依然坚守中国文化。她潜移默化地教育她的五个子女,对人要彬彬有礼、宽大、不计较,希望别人有宾至如归感,这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待人接物处世之道,是母亲坚守中国文化的具体表现。作为第一代移民,玉珠的母亲一直通过自己的勤劳与质朴适应美国社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但同时,她也有明确并且完整的故国文化观念,即使在异国生活,但是对于故国文化的认同和坚守的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
玉珠作为第二代移民,虽然在美国长大,但是在文化上受到了母亲很深的影响。在母亲的传统文化教育下,玉珠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玉珠认为中国人谦逊宽容,言而有信,而外国人则以自我为中心,斤斤计较,不守信用。她的白人舍友常常不还信用卡欠款,经常把原本属于玉珠的那份菜吃光,大半夜带人回宿舍吵吵闹闹,不顾及别人感受。面对白人舍友的这些行为,玉珠开始是不计较的,用母亲教导的宽容大度,忍让的态度对待她。但是之后,白人舍友越来越过分,玉珠也不知道容忍的限度到底在哪里了。很明显,母亲教导的故国文化观念与玉珠所处的现实生活出现了差异,越是一味的忍让,白人舍友越是得寸进尺。于是,从这个事件上,玉珠开始比较自觉地看待生活其中的世界了,努力尝试在异域文化与故国文化之间寻找一个立足点,思考自己身处双重的文化夹缝之中的困惑。
而同样是作为第二代移民的玉珠的妹妹莉莎,却不再遵循母亲教导的传统礼仪,而是彻底地转变身份认同周围的文化。“社会心理分析认为文化认同即是对文化范畴的认知、确认后对文化价值的肯定。而文化基本范畴首指‘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构成文化身份最易变化的浅层表现”[4]在小说《岛和大陆》中,梁秉钧巧妙地设计了聚餐的情节,通过小小的餐桌窥视不同的文化。餐桌上有煲了八九个钟头的老鸽子汤,冬菇丝、瘦肉丝、芽菜和粉丝拌在一起的凉菜,丝瓜、腰果、肉丁、虾和云耳炒成一碟的热菜,还有鱼以及其他细致的粤菜。这些故国的饮食都是为母亲和玉珠准备的。桌上一大盆的烤鸡和西菜,则是适合莉莎和朋友们的。在餐桌传统礼仪方面,玉珠的母亲热情地招呼大家一起吃,不用等。而莉莎和她的朋友们不一起吃,他们也不打招呼,各自直接拿了菜,回到客厅去看电视,边看边吃。从饮食习惯,餐桌礼仪构成的文化身份变化的最浅层表现上来看,莉莎已经转变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融入到异域的文化中去了。
三
王德威在《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中提出“在行旅所构成的时空坐标点中,更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行旅者如何移动,安顿和重新定义他们的位置,由中心到边缘。由故乡到异乡,由此岸到彼岸,只是有关行旅故事的开端。”[5]作为一名行旅者,梁秉钧不断拓展步履,游走世界,内心却始终保留着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的热爱与深情,就好像在纵横交错的十字路口,不管左转还是右拐,还是会回到原地。他小说中的流散写作不仅为了探讨流散者的身份建构问题,更多的是借此言说“说不尽”的香港文化身份。香港处于历史与现实“夹缝”之中,文化身份始终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状态。由于历史原因,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长发一百五十多年,社会制度、语言习惯、文化教育等都受到了英国根深蒂固的影响。香港人对“身份”产生了迷茫,不是英国人,却受到英国制度统治,不自觉接受英式价值观;作为中国人,却与中国文化产生隔阂,渐行渐远。文化身份的缺失和找寻始终根植在香港人的心中。
梁秉钧作为香港本土文化作家,摆脱了以往作家对香港意识和文化身份建构的模式,用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在越界游走中,探讨与阐述流散语境中香港的文化身份问题。他把自己亲身经历与体验到的文化身份的焦虑转化成小说中跨越地域空间、跨越边界、跨越国界的生活图式。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而且生活在异乡普普通通平凡的人物。九七将近,身份的焦虑与模糊,许多作家想写宏大的时代,构建戏剧性的传奇,塑造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寻找香港文化坐标定位。梁秉钧却没有这样的野心,他只是想从一些比较熟悉的普通人物身上,生活在异乡的香港人身上,看他们是如何承受生活的挫折与苦难、排解烦恼与忧虑,化解尴尬与不顺,在变幻的时代中探索标准与准则,凝聚某些特质。不需要宏达的叙事背景,跌宕起伏的情节,传奇性的人物,只凭借小人物、小背景、小故细腻地讲述香港故事,将平凡大众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习惯放置跨越界限的文化语境中,关照平凡的流散者,借此表达对香港文化身份的思考。
《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中,生活在异乡的W、D、Y或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或是为了追寻心中的梦想而离开香港,在海外漂泊。作为异乡的流散者,他們以“他者”的文化身份介入西方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一方面要追随别人形成的标准,另外一方面又要否定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内心的真实感受,这种矛盾的文化对接使他们陷入到扭曲的文化空间中。经历了长期漂泊之后,他们更加向往一个具有身份归属感的文化空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空间。然而,这种从“他者”到“自我”的文化身份的回归最终也失去依傍。梁秉钧在《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中指出香港本身是一个文化失忆的地方,殖民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割断了香港人与本土历史,中国历史的联系,只学习欧洲历史,属于香港本土的特质被抹去,被歪曲,无法真正地建立香港文化身份,香港人失去精神上的皈依,只能游离在暧昧的边缘地带。所以,《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中出现的流散者当他们以漂浮的状态渴望回归香港文化空间时,也只能陷入迷茫之中。
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梁秉钧用更广阔的视野讲述香港故事,香港文化身份的缺失的思想还未消失,但如果一味地追求本土身份是没有结果的,多元的文化身份才是香港最好的出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设置了三次聚餐来描述作者的好友、女朋友、女朋友的父亲、餐厅经理等自身代表的文化的不同特质,作者借三次饭局表明应该建立多元并存的香港社会。聚餐时,作者的好友、女朋友、女朋友的父亲、餐厅经理等每个人都带来了代表自身文化特征的食物:日本的寿司、中东的蘸酱、西班牙的头盘、葡式鸭饭、夫妻肺片、意大利面、糯米酿猪肠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的食物被摆放在同一个餐桌上,再配合着电视里面播放的民族气节高昂的爱国歌曲晚会,组合成了一次美味而又热闹的聚餐,构建成了香港文化多元并存的语境。对于香港人而言,期待的未来应该是多元,多样化的社会,混合的不同文化可以毫不突兀地结合在同一个地方,才是真正让人心满意足的生活。在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的结尾,作者认为虽然有些人离开,又有一些人新加入,我们对于事物也各持己见,争吵不休,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走在了一起,也许到头来学会互相仁慈。对于香港的文化身份,也许只有兼容并包才是最好的出路。
注释:
[1]王晓路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15.
[2]梁秉钧:《东西》,上海: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57.
[3]周宏亮:《认同的焦虑:<美国情人>的身份认同理论分析》,《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1).
[4]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田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2004(5).
[5]王德威,季进:《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260.
参考文献:
[1]陈公仲.流散与文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2]斯峻.香港小说精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赵稀方.小说香港[M].北京:三联书店,2003.
[4]许翼心.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5]颜敏.“流散”的意义“流散”——兼论我国内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独特理论话语[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