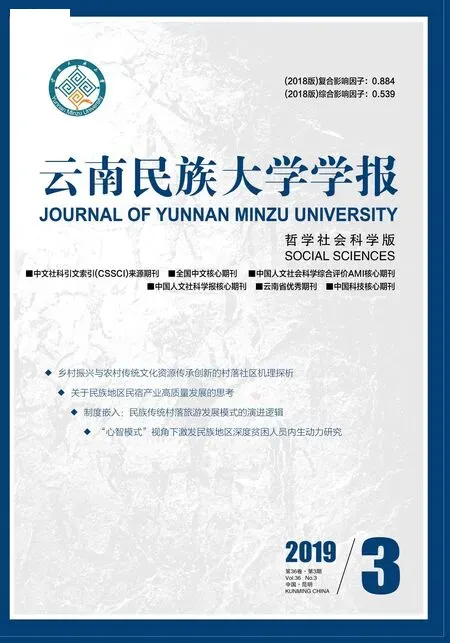蒙古族传统“安代”仪式的指号分析
特日乐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200433)
一、前言
莫尼卡·威尔逊认为仪式是理解人类学社会基本构成所在,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而正因为表达是囿于传统和形式的,所以仪式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维克多·特纳强调仪式是指号的聚合体(aggregation of symbols),①[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和反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他特别关注仪式过程中的各种指号,②指号(sign),拉丁文signum,德文Zeichen,法文signe,意大利文segno。Sign除了指号外,又译为符号、记号、指号和标记。不同的译者或不同的学科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譬如在洛克著《人类理解论》较早的译本中,译者将“sign”译成“标记”,而在莫里斯的《指号、语言和行为》译本(罗兰、周易,1989)中,“sign”则被译为“指号”。李幼蒸先生在《理论符号学导论》中,通篇使用“记号”来对译“sign”,而用“符号”对译“symbol”。国内人类学界,通用用法是“sign”为“符号”。有少部分学者,采用“指号”。认为指号既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也是仪式语境中具有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③[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页。指号的意义与指号形式之间呈现出一个巨大的理解和解释空间,我们可以从仪式指号的隐喻性叙事中发现其文化动力。④彭兆荣:《仪式之翼与阈限之维》,《读书》2018年第12期。
本文通过皮尔士指号学路径,从象似、标指、象征三个维度,阐释和解读蒙古族传统安代仪式中关键指号的多层内涵,从而揭示传统安代仪式复杂的指号体系及其背后的深层结构。19世纪末20世纪初,指号学⑤Semiotics,又译符号学;Sign,又译符号。本文以皮尔士传统的semiotics(指号学)为分析框架。为与索绪尔传统的semiology(符号学)作区分,全文都将采用“指号学”“指号”译法。的理论被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Charles Sanders Peirce)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充分发展。不同于索绪尔符号理论观点,皮尔士将生活的经验和对象纳入意指过程,⑥Pierce,C.S.1995.PhilosophicalWritings of Peirce.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P99.强调了指号的社会属性,将指号的表征、传播和意涵融于一体,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解框架。⑦丁尔苏:《超越本体》,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20世纪80年代后,理查德·帕蒙提厄(Richard Parmentier)⑧Parmentier,Richard J.1994.Signs in Society:Studies in Semiotic Anthrop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罗伊·A·拉帕波特(Roy A.Rappaport)⑨Rappaport,Roy.1999.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韦伯·基恩(Webb Keane)⑩Keane,Webb.2007.Christian Moderns:Freedom and Fetish in the Mission Encounter.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等人类学家先后在仪式领域涉猎皮尔士指号学理论。国内仪式研究的指号学探索,目前较为鲜见。本文尚可称为指号学视角研究仪式的一次粗浅尝试,力图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二、蒙古族传统安代仪式过程
安代流传于内蒙古通辽市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安代仪式一般定于闲暇季节,短则七天,长则二十一天,最长四十天有之。主要为患“安代病”的妇女所举行的驱邪治病仪式。安代仪式的病患:一是由于旧时包办婚姻,无法与相爱的人结婚所患相思病,出现胡言乱语、精神错乱者。二是因不孕,影响家庭和睦及子嗣延续而出现沉默寡言、卧床不起、日益消瘦者。三是由于额勒(鸢)附体,出现摇头晃脑、兴奋狂躁者。整场仪式有1位“博”①一般为当地造诣高深的萨满。、2-4位歌者(安代沁)、1位病人及其他参与者。最为重要的角色为博,他负责仪式流程、人员分配,劝慰病人,制作“乌热查干格尔”及面人,保证整场仪式的顺利进行。以下是安代仪式的大致程式:
(一)筹备:博根据病人及家人所描述症状,初步诊断病情,并与家属商定仪式日期、地点、规模及歌者等具体细节。场地一般为十余丈村庄平坦一隅。翻开场地表层土,用马粪与草芥铺垫约半尺,再用湿土夯实,以仪式参与者舞蹈步伐更富弹性,顿踏间作出声响。②王景志:《中国蒙古族舞蹈艺术论》,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27页。
(二)设坛:在场地中央立一根长杆,蒙古语称“奈吉木”,意为金柱子。病人在家人协助下,洗净头发并将之披散,遮挡面部,被领至场地中央的“奈吉木”旁。病人双手持香跪拜“奈吉木”,后坐在长凳上侯之。闻讯而至的村民以“奈吉木”为轴心,肩并肩自觉围成一大圆圈,静待仪式开始。③《库伦旗旗史纵横(含歌谱)》(内部资料),1993年印刷,第91页。
(三)赞鞭:博着法服,手持铃鞭,道奇④歌手。腰别弯刀或单面鼓隆重登场。先高歌一曲《合珠来》赞歌,大意为博的神鞭威力凶猛,赞其恐吓鬼魂之效用。唱毕,宣布仪式开始。
(四)开解:博和道奇为了开解病人,用一至两晚,以歌舞形式,探询病因。唱词诙谐,旋律柔和,使病人产生强烈共鸣,逐渐使其打开心扉,随博和道奇加入众人挥动手帕,顿足起舞。
(五)赞茶:病人歌舞至大汗淋漓,被搀扶至“奈吉木”旁的椅子歇脚饮茶,众人齐唱《赞茶歌》。
(六)夺安代:稍事休息后,仪式迎来高潮。有时一个场地容不下,便另组一圈。绕场而转的病人,依据歌舞的热烈程度选择圈组。两个圈组争相吸引病人,形成“夺安代”的景况。⑤于平,冯双白,刘青弋等:《传统舞蹈与现代舞蹈》,北京:舞蹈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七)送安代:仪式结束前,博用柳条或秸秆做成蒙古包状模型,蒙古语称“乌热查干格尔”。用五色丝绒网住,并贴上五色额勒剪纸。安代仪式结束当晚,将“乌热查干格尔”搬至安代场地。待安代收场,据当日占卜所预测的不吉方向烧掉之。同时在三叉路口挖一三角坑,将五谷杂粮、“博”所写的符、病人的替身“小面人”一并放入其中。遂唤病人跪在一旁磕头,博念叨: “磕头吧,磕头吧,从此你就脱灾了!”尔后,病人“闭关”三七二十一天。博最后告知病人的家属,鬼魂、灾厄均已消失,病人痊愈。⑥白翠英,邢源,福宝林等:《安代的起源及其发展》,通辽:哲里木盟文化处编印,1983年印刷。至此,整个仪式即告结束。
三、传统安代仪式的指号学阐释
(一)指号学理论观照
按照皮尔士定义,征象(sign/sign vehicle/representamen)是第一性,它和第二性即对象(object),有真实的三维关系,并由此决定了第三性即释象(interpretant)的存在,使释象也与对象保持同样的三维关系。从征象到对象再到释象,构成了指号认知相对完成的过程,即 “指号过程”(semiosis,如图1所示)。譬如:一个人听马头琴音乐。征象是人感知这段音乐;对象是马头琴声;释象则是马头琴由吉他声产生的思乡情绪。


表1 皮尔士指号“小三元”结构的特征
皮尔士的指号学最常用的分类是其“小三元”结构(如图2所示),即对对象(object)的分类。他将对象(object)分为象似(icon)、标指(index)和象征(symbol)。一个象似是与指号客体有相似性(resemblance),即以像类物,如公共厕所男士叼烟,女士穿裙子蹬高跟鞋的图符、心电图、按在纸上的手印、一张熊的照片(照片和真熊之间即构成象似)、及语言中的拟声词、狗的汪汪叫、猫的喵喵叫以及拟态词如磨磨蹭蹭等均属此类;标指(index)是与指号客体之间通过实际或物理或想象的因果关联性(causal connection)的指号。譬如,我们在森林看到熊的脚印,就能推断出熊来过此地。看到沙滩,就会联想到大海。这是因果关系。而象征(symbol)则没有本质的关联和相似性,却有任意性(arbitrariness)或规约性(stipulated convention),且需后天习得。如“熊”,我们后天习得才知“熊”这一汉字代表熊这个动物。再譬如,商品标识(苹果、耐克),红色代表爱情、活力、愤怒,白色代表纯洁、神圣。这些都是约定俗成,且具有任意性。征象(sign)与释象(interpretant)的分类今日较少运用,在此从略。①Marcel Danesi.2004.Messages,Signs and Meanings:A Basic Textbook in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Toronto:Canadian Scholar's Press,pp.28-33.
(二)传统安代仪式的指号分析
传统安代仪式看似奇异怪诞,象征意义并非荒谬而突兀。每个都与其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事物相关联。社会成员通过指号,传承与交流世界观、价值取向、文化精神及其他观念。而人类学学者的工作就是用“本土人的观点”来解释象征体系对人的观念与社会生活的界说,从而理解形成地方性知识的独特世界观、人观与社会观背景。②张实:《医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1.象似第一维:“奈吉木”之拟象
相传很久以前科尔沁草原有父女相依为命。有一天,姑娘突然得了奇怪的病,神经恍惚,举止失常。几经医治,没有好转,父亲用勒勒车拉女儿去蒙古勒津求医。走到蒙古勒津附近是,车轴突然断了,女儿奄奄一息,父亲捶胸顿足,绕车轴踏步。他无计可施,为了安慰女儿,甩起手巾,边舞边唱表达自己内心的无助与无奈。循声而来的牧民们,纷纷加入随老阿爸放声悲歌。不一会儿,姑娘醒来,加入牧民们的队伍手舞足蹈,直至汗如雨注,病愈如初。③张海鹰主编:《阜新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8。车轴被称作“奈吉木”,亦称“金柱子”。传统安代仪式中的“奈吉木”由此而来。
人们为仪式设坛时,在场地中央通常竖立一根车轴。仪式参与者以此为轴心围成圆圈,右手握一块绸巾或扯起蒙古袍下摆,随领唱者边歌边舞。时至今日,牧民们在成吉思汗陵前祭奠成吉思汗时,也要先到陵宫正厅墙外正南百步远的金柱处绕柱三圈,又到距柱八十一弓处向外撒奶。④莫福山主编:《中国民间节日文化辞典》,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有时, “奈吉木”的顶端要系白色手绢、哈达或灯笼。有时还在“奈吉木”底下埋放五谷杂粮的种子。⑤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内蒙古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年版,第66页。蒙古民间认为病人患安代的主要原因是其身体内固有的风马(hiimori)变弱而运气变坏,⑥风马(hiimori)指有飞翔马儿的图案的旗帜。蒙古语中表元气、生命力、吉祥如意等。育龄女子子宫或胎盘里的寒气,导致不孕、流产、胎停。如果患安代病的年轻媳妇们围绕“奈吉木”而歌舞,身体就会康复,继而得到“金子般的贵子”①苏尤格:《安代的文化意识溯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于是在为不孕症年轻妇女举办的安代仪式中,对“奈吉木”的祭拜显得尤为重要。博在劝慰病人的过程中会唱道:
快说!波热
莫尝到铃鞭滋味!
纯白的雏鸟可爱啊哈波热
冠顶是红色的啊哈嗬嗬!
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哈波热
帽顶是红色的啊哈嗬嗬!
从天窗冒出的蒸汽啊哈波热
比锅撑子还要直啊哈嗬嗬!
绕圈而舞的人群中间啊哈波热
金奈吉木柱挺且直啊哈嗬嗬!②那沁双和尔:《安代文化研究》,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
仪式中,博的唱词饱含了对生命的寓意,不乏“波热”(蒙古语:男性生殖器)、“挺且直”等直白的表述。所谓生殖器崇拜,实为原始社会之普遍的信仰。原始社会智识蒙昧,对于宇宙间一切自然力,每每难求得合理解释,而遂加以人格化。③周予同,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的图腾、神话、俗语、传说中,多是以刀、箭、枪、棒状物代表男性生殖器。汉族文化中的石柱、竹子、满族文化中的祖宗杆子、普米族的莫句散也与之类似,皆为生命寓意的表现形式。奈吉木与男性生殖器之间的具象外观的相似性(resemblance),与皮尔士所言的象似定义吻合。强调男性器官,因其最能代表男性特征;再者在草原生产活动中,男性力量起到重要作用,父权制烙印明显。④邹永前:《神祇的印痕:中国竹文化释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生殖崇拜投影于仪式活动与社会行为中,充分寄托了蒙古人民繁衍种裔的渴望。生殖崇拜现象虽具表象性,但其深层含义是人类自身的生产问题,即种的繁衍。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安代仪式的奈吉木下还要埋入五谷杂粮的种子,对生命延续的关切不言而喻。⑤巴·苏和主编:《传奇的库伦文化》,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笔者认为奈吉木的第二层寓意为萨满升天。奈吉木作为一棵树、一根杆、一架梯子、一条绳子的变体,寓意萨满象征性升天,与天神及各种神灵沟通,恳求神灵结束这场疾病。景颇族在仪式中会攀爬一架刀梯,⑥[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殷满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48页。有些阿尔泰萨满会攀爬树上刻着梯阶的白桦树,梯阶代表着萨满在通往天国之巅的癫狂之旅中途径的各级天国。⑦同上,第3页。
除上述两种寓意外,奈吉木作为天柱具顶天立地的意蕴。笔者认为奈吉木所反映的是天、神、人、地的统一观。每一个族群有一个小宇宙,支撑这个族群小宇宙的核心是奈吉木,它所映射的是大宇宙。地与天之间的奈吉木,既是支撑物又是联系物。蒙古语中的“孟克·腾格里” “呼克·腾格里”“迭额列·腾格里”都是指至高无上的“天”。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为“额其格·腾格里”(意即“父天”),与之对应的是“额都根·额和”(意即“地母”),是仅次于腾格里的大地神。⑧那木吉拉:《阿尔泰神话研究回眸》,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上面是“父天”,下面是“地母”,中间的竖线奈吉木,则是沟通天地的精神能量。对奈吉木的崇拜,可以营造一种可以和外部世界具有某种超自然能量者同在,能够在对未来的理想化中感受超自然力量的加持。⑨李学更:《普米族民族艺术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2.标指第二维:病人的信任
依据皮尔士的定义,标指(index)是与指号客体之间通过实际或想象的因果关联性(causal connection)的指号。笔者认为病人的信任与仪式疗效之间有着因果关联性。病人的信任包括对萨满博的信任、对自己的信任、及对仪式参与者的信任。
对萨满博的信任是安代仪式之根本。来参加安代仪式的通常是久病不愈,几经医治均无疗效,最后求助于博的人们。在仪式中,病人选择相信博,来参加安代仪式即标指着对仪式疗效的预期认可。博在取得病人的信任后,很好地利用了其权威和巫术技能,对病人进行积极暗示,让病人相信自己的病能够被治愈。①Koss-Chioino,J.D.1996.The Experience of Spirits:Ritual Healing as Transactions of Emotion(Puerto Rico).In W.Andritzky(Ed.),Yearbook of Cross-culturalMedicine and Psychotherapy,Vol.1993,Ethnopsychotherapy.Berlin,Germany:Verlagfur Wissemschaft und Bildung,pp.251-271.例如,安代歌曲《朝呼尔》中,有一段唱词为:
榆树钱呦
不管结得多么厚
一旦刮起旋风
七零八落掉满地
起来跳舞唱歌啊
恶毒的安代呦
不管来势多凶猛
只要大家把它来封锁
定会将它消灭
起来跳舞唱歌啊②白翠英,邢源,福宝林等:《安代的起源及其发展》,通辽:哲里木盟文化处编印,1983年版,第107页。
博自始至终营造一种安全舒适的氛围,诸如“定会消灭”的积极暗示唱词基本贯穿整个仪式。仪式临近尾声,博还会念叨: “磕头吧,磕头吧,从此你就脱灾了,你的病好了!”博是神灵的使者,神意通过他传达给自己,病人对其心怀敬意,按照其指引,做规定动作,歌之舞之,用一种公开方式传递他人自己即将被治愈之信号的标指。他对病人进行觉醒状态下的良性暗示,及病人的自我暗示,使病人体内紊乱了的能量代谢又重新回到动态平衡状态。
对仪式参与者的信任也在仪式中不可或缺。安代病人的家属一般会回避参加安代仪式,这样便于安代病人在仪式中放松芥蒂,敞开心扉。病人的疾痛经验被参与者所接纳和分享,病人个体与群体间先前弱化的信任感再次在仪式中加强。 “夺安代”中病人被焦点化,使得病人对仪式参与者产生同盟般信任,继而从疾痛的阀限状态交融到以健康的体魄回到群体社会。③Kleinman,Arthur M.1973.Medicine's Symbolic Reality:On a Central Problem in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Inquiry:An Interdisplinary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16,pp.1-4.
罗伊·A·拉帕波特在其《人性建构中的仪式与宗教》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中曾提到一种Kaiko仪式,在Kaiko仪式中跳舞就是宣誓自己是其同盟。若做出此行为,即证明之后将践行同盟承诺,一同参加战斗。现在的舞蹈和未来参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在Kaiko仪式语境中舞蹈就是标指。同样,安代仪式的操演,标指着对安代仪式的认同。故而,病人的信任与安代疗效之间存在因果关联性(causal connection)。笔者认为以上论及的三种信任共同作用与仪式疗效有着因果关联。病人选择相信萨满、自己以及仪式参与者,即内心的积极暗示会使病人的身体发生良性循环。而愈加笃信,在仪式中的参与度也会愈强。例如,愈加全力地配合博作指定动作,抑或更为投入地舞蹈歌唱,从而汗液将体内毒素排出。同时,身体由于运动而产生的胺多酚 (endorphin)又使病人心情愉悦,忘记病痛。安代仪式的操演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状态,标指着这个状态的发生,标指着病人如何被仪式的施为力量 (performative force)所影响是一种自涉(self-referential)的仪式标指信息。
3.象征第三维:“鸢”的善恶双重秉性
整个安代仪式中鸢的影子可谓无处不在。安代的一种——鄂勒安代,更称为“唱鸢”。在赞鞭环节,博用于去除鸢的魂灵使用的法具是鸢鞭。2尺长的细木棍外缠黑疯狗皮做成,鞭头上拴五色长布、绸条,以及五块鸢鸟的头骨,称为五鸢鞭。④乌丙安:《萨满信仰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仪式收尾时所用纸扎房也用鸢鸟装饰。故而,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探讨鸢在安代仪式中的象征寓意。
鸢,又叫老鹰、鹞鹰等,鸟纲,鹰科。蒙古语叫额勒(eliyee),属中型猛禽,体长54—69厘米,体重684~1l15克。虹膜暗褐色,喙黑色,蜡膜和下喙的基部为黄绿色;脚和趾为黄色或黄绿色,爪为黑色。上体为暗褐色,颏部、喉部和颊部污白色,下体为棕褐色,均具有黑褐色的羽干纹,尾羽较长,呈浅叉状:在飞翔时翼下左右各有一块白斑。⑤邵丽鸥主编:《鸟类王国》,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蒙古族有一则关于“鸢和蜜蜂”的传说。从前凤凰唤来鸢和蜜蜂,让他们探清世界上什么肉最美味。回家途中,鸢问蜜蜂:“你觉得什么肉最美味?”蜜蜂答曰: “人肉”。鸢却觉得是蛇肉最美味,两人争论不休,鸢将蜜蜂的舌头揪下。回后禀报凤凰,未等蜜蜂开口,鸢抢先答道:“蛇肉最美味。”由于救了人类一命,牧民们不再猎杀鸢,成为了传说中的神祗鸟。①蒙古学百科全书编委会:《蒙古学百科全书(宗教卷)》,呼和浩特:内蒙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这种神祗属性在安代的治疗仪式中也有所体现。额勒(鸢)安代的治病仪式中,查干额勒(白鸢)成为了女性萨满舞者的神偶。甚至,为了治疗这种病人,出现了叫作白鸢(查干额勒)的女性萨满,也称乌达根。 “查干额勒”是乌达根(巫婆)的神偶。女性萨满舞者在仪式中须装扮成白鸢的样子,着白色长褂,手持白色手绢,效仿白鹰在天空中飞翔或从山上向下俯冲的各种动作,并唱鸢鸟歌曲。效仿和歌唱神祗鸟是保持其神祗属性,使其愉悦而不愿离开的重要方式。②Michael Harner.1980.The way of the shaman:a guide to power and healing,New York:Bantham New Age.乌达根在安代曲子《朝代》 (二)中这样唱道:
你被五只鸢迷住了波热
仰面躺着不行啊 波热
得上了怪病
是病毒进入脏腑的缘故
你被邪恶的仓鸟迷住了
不抡胳膊跳舞不行了
跟着我跑动吧
汗湿脊背吧
唱吧玩耍吧朝呼尔。③白翠英,邢源,福宝林等:《安代的起源及其发展》,通辽:哲里木盟文化处编印,1983年版,第109页。
鸢兼具善恶双重秉性,既是救了人类命运的神祗鸟,也是地狱使者的一种恶灵,它的出现有时预兆着灾厄不幸的降临。在《朝呼尔》歌词中,提到了“五只鸢魂的作祟”,源于安代的起源传说—— “五鸢传说”。很久以前,有五个神通广大鸢鸟公主。第一个叫“白音西呼代”,第二个叫“巴特尔呼代”,第三名叫“阿拉坦斯日古楞”,第四名叫 “乌云塔娜”,第五个名叫 “乌森海拉古尔”。④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每当他们在天空中飞翔,地面上便会掠过她们的影子。而哪个妇人若是被他们的影子掠过,就会招致安代病,出现哼哼唧唧、胡言乱语、夜间兴奋不睡、晃脑袋、进进出出等疯狂性精神错乱症状。鸢魂附体在年轻女孩和媳妇身上作祟,使她们身患安代病。求医吃药无法治好安代病,唯有请博给患者举行驱鬼仪式,唱歌送走鸢魂,才能痊愈。
四、结语
皮尔士指号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符号动态网络,既有总体的“大三元”—征象、对象和释象的互动,也有具体的“小三元”象似、标指和象征的对转。⑤纳日碧力戈:《民族三元观:基于皮尔士理论的比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81页。传统安代仪式中奈吉木之象似,信任之标指,鸢之象征组成一个纽结在一起的复杂指号体系,赋予了安代仪式场域强大的力量。人与神沟通,人与人和谐,秩序、权威和关系在此得以展演。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着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传统安代仪式时至今日,已近乎绝迹。安代作为蒙古族的重要文化遗产,我们尤其有必要捕捉其传统仪式关键要素,通过指号学分析路径,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究其历史文化缩影及文化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