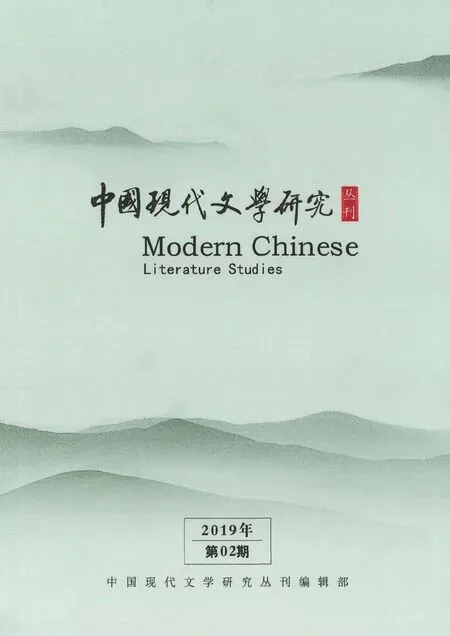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
——评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
王 贺
一 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现况
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发端得相当晚。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虽然颇为复杂,但治学观念的迟滞、无法更新与文献资料长时期难以利用,应负主要责任。也正因此,经过了1980年代的准备,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再度接续学术传统的自觉努力开始奏效。
在现代文学史的编纂与叙述中,首先开始重视图像叙事。杨义、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的《中国新文学图志》(1996)便是这一方面开风气之先的著作,此后出现的诸如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2007)、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2010)等书,固然各擅胜场,但对诸多图像资料的搜集、利用,则是其共同的特色。大约同一时期,较多关注图像资料的文学史研究,也渐次展开,代表性的研究如陈平原、夏晓虹利用晚清画报完成的多篇论文,本文读者早已耳熟能详,此外,他们也编注了《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2014)、《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2014)等资料集,为学界提供了有利的研究条件。
受此一学风影响,专门搜集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并将其汇集整理、付梓刊行一事,在新世纪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其中,搜罗最广、规模最为宏大的,便是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利用馆藏、组织人员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丛书。该丛书先后出版有“书画卷”4辑、“书目卷”2辑(《巴金文库目录》《唐弢藏书·图书总录》)及“期刊卷”“信函卷”“手稿卷”各1辑,“版本卷”2辑。①其中,“期刊卷”“版本卷”的《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上)》(2009)、《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2011)、《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初版本图典》(2015)三种,专事现代文学作品、期刊的初版本图版,并以其收录丰富、齐全见长。但《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不收录在单行集基础上编辑的选集、文集、全集和丛刊性质的多人合集”,理论、批评作品几乎未收,使人扼腕;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初版本图典》虽然收纳合集,却将翻译文学评论、研究(早期不少理论、批评著作,对此均有所涉猎)排除在外,同样给人留下不少遗憾。
这一大规模整理现代文学版本学、文献学基础资料尤其图像资料的工作计划,因为成绩显著,也或多或少掩盖、或是让我们高估了学术界对于这些资料的真实、主流的看法。事实上,迄今为止,学者们对现代文学版本的图像资料的搜集、利用普遍既无浓厚兴趣,也充满了误解、偏见。举例来说,发表、出版的专书和论文,运用到这些版本的图版时,作者和编辑往往就会利用Photoshop、美图秀秀等图像处理软件,对原图进行修改。当然,这一修改有时是出于美观、版面的需要(近似于影印图书时的“修版”,但至少利用修版后的影印古籍所作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其结论便要打折扣)②,有时是为了避免版权的争议,但无论何种情形,都既没有任何交代、说明,取舍也显得相当主观、任意。但是,这样一来,其所谓的“原汁原味”的“原图”,实已变身为“伪文献”“伪史料”,势必带来很多问题。
在这些“原图不原”的图像资料中,公家机关图书馆、资料室的藏书章常常会被修掉。其实,哪怕是被修掉的某一图书馆章,也是很重要的研究线索。近现代的铅印书籍可能暂时还没到讲究、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但对于一本古书来说,其上的藏书章如被修除,姑不论其他,单是对于我们了解它的递藏、流传有序,恐怕就很难着手了。因为这本书在一定时间内很可能其他人都很难看到,只有此研究者一人能够读到。倘若我们又假设那本书只有某地某校图书馆所藏,其他人见此图片,而想要检查、借阅实物,一旦没有了这个标记,便无门径可寻。《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以下简称《图鉴》)的编著者在搜集这些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时,就有过这方面的遭遇。他们发现,即使是在原书保存在公立图书馆的情况下,有时也因编目混乱、收藏不善等,不得不面对有书无目、见非所查的尴尬局面。③这从相反的方向揭示了文献保存、流传这一信息的重要性。
但这仅是初版本在内的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中附加或承载的一个方面的信息、线索。一般研究者无此概念、导致“原图不原”的现况尚可理解,笔者感到担忧的是,一些致力于文献史料整理、研究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时也表现得无甚差别,对文献史料之真伪之区隔漠不关心,然而,其所提供于读者的“原汁原味”的“原图”,许多既已经过处理、修改,又如何让人放心参考、利用?
二 《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的贡献与未竟之业
《图鉴》分上中下三册,由黄开发、李今历时十余年编著而成,于2018年3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全书的一大贡献即在于为读者提供了近千册1920—1950年间的现代文学作品的初版本、珍稀版本的图片。其中诗歌96种,散文163种,小说198种,戏剧67种,创作合集30种,翻译文学101种,理论、批评著作41种,收书数量总计696种、888册。加之由于印制精良、不惜成本,数千张图片能够以大幅、清晰、无损的形式呈现出来,一时通览全书,真可谓洋洋大观、琳琅满目。
再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每一种书,都收入了其封面和版权页,部分也酌情集纳了其题辞页、扉页(上有作者题签)、环衬页、插图等。选录初版本的书影时,编著者更是优中选优,将缺少封面者,封面涂抹、损伤严重、品相不佳者,或缺少封面、版权页者予以剔除,而只遴选了品相佳、封面和版权页等完全来自同一文本的版本,作为入编的对象。历经艰苦的寻访、交涉,他们卒使《缀网劳蛛》《骆驼祥子》《白毛女》《财主底儿女们》上卷等书的初版本书影得见天日,而这也是它们在学术界的首度公开亮相。
所有这些作品的图像资料,不仅对于追溯版本源流、考定版本真伪、比较诸版本之优劣、探究一书之出版发行等专门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不从事这些方面专门研究的学者及普通读者建构了文学史的“原生态”和“现场感”。而编著者对版本学、文献史料的研究和对图像资料的精益求精,正是他们能够圆满完成预期目标的基准和条件。
诚如朱金顺、陈子善诸先生所言,有必要强调以实物为主这一原则,乃是现代文学版本学、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④整理和研究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根本,是从实物出发,根据实物进行拍照(或扫描)、著录、分析、研究,但《图鉴》却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可靠、坚实的图像资料基础,使我们在研究、教学过程中可以时时参考,而不必仅仅依赖于图书馆或深陷于“网洋大海”。全书末另附书名索引,可配合目录为读者查检、利用提供方便。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该书不仅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创作的初版本择其要而予以迻录,还将大量的翻译文学和不少理论、批评著作收纳进来,以图作平等之观照。收入该书的翻译文学的总体数量与其他创作文类不相上下,而理论、批评著作也占有相当的篇幅,足见编著者所理解的现代文学史,乃由翻译、创作、批评三脉互相作用、影响而成,无意制造创作“一枝独秀”“喜从天降”的假象。但对于全书这一特质的理解,也与我们如何理解其架构和叙述方式密切相关。
《图鉴》的整体架构和叙述,也构成其另一方面的贡献。该书的架构结合了编年和文类,叙述则包括了每一种书的图片、目录和简介。前者让我们联想到一般的文学史尤其编年文学史的架构,但与之相比,本书只负责提供文学作品为主(兼及理论、批评与翻译文学)的历史,且是其间“较为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初版本的历史,移用编著者的话来说,“选录的标准主要依据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同时兼顾版本某一方面的特殊价值”。换言之,本书既有版本学的视野、思路,更是别一种现代文学史,亦即论者所谓的“作品型”的文学史。尽管在介绍这些初版本时,编著者声称“一般不作内容上的阐释和评价”⑤,但在什么样的时间段,选录哪些人的哪些作品,自是其文学史观运作的结果,而看似客观、冷静的版本“简介”叙述背后,也同样表露出其对文学、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史的理解。
例如,在1925年的“诗歌”部分,即收入了蒋光赤(蒋光慈)著《新梦》一集。正文除收该书初版本封一、版权页、题辞页图片外,亦有此集总目及简介。其“简介”云:
诗集,上海书店1925年1月初版,32开。有高语罕《〈新梦〉诗集序》,作者《自序》。卷首诗人题词:“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全诗分五个总目,共收入四十一首诗歌。这些诗都是作者在苏联时创作的,充满了热情奔放的革命豪情,钱杏邨(阿英)称之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该诗集初、再版本很快销售一空,作者因这两个版本的格式太不美观,于1926年12月毁版重排,改成横式,48开小本,由新青年社出版了《新梦》第三版。三版不仅删去六首诗歌,各诗也略有修正,作者还增写了一篇《三版改版自序》。⑥
这里编著者并未因《新梦》令人可疑的文学性而将其排斥在外,相反,还在有限的字数之内,整理了其题辞内容,介绍了诗集所收诗作的数量,扼要地交代了此集的创作背景和主题,并诉诸权威,引用了蒋光赤(蒋光慈)的同道中人钱杏邨(阿英)的评论,作为对此诗的文学史意义、地位予以评断的根据——这些做法,在通行的文学史著中,我们也不难见到(至于做法本身如何评价,见仁见智);但从选录此书,并在简介中整理题辞、概括其创作背景和主题、引用评论突出其之为革命文学的开拓性作品之性质数语,显然可见编著者对革命文学遗产所持并非否定态度。凡此种种,也为我们说明,《图鉴》之名虽稍嫌通俗,但无碍其以文字、图像作为共同的叙事主轴,且以初版本及其图像为中心而建构的现代文学史之实。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简介”对此集当时的销售情况、版本与文本变迁情况,也有所涉及。而这恰是《图鉴》能够提供但一般文学史著不甚关心的内容,也是版本学、文献学及出版史研究夙所关注的内容。通过这样的描述和介绍,读者不仅可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有所注意,还能够大致形成关于此书的“知识”。须知强调“思想”“理论”“方法”有其道理,但向读者报告经过认真研究的、有效、准确的知识,乃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学术”对应的英文词Academia既指从事学术研究的群体,也指“知识的累积”)。
但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对这一“简介”中的“钱杏邨(阿英)称之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该诗集初、再版本很快销售一空”,“作者因这两个版本的格式太不美观,于1926年12月毁版重排”等叙述,还有必要提出疑问:上述说法的依据何在?其文献的来源何在?以限于篇幅、体例等原因,该书并未提供任何注释,而《参考书目》也只有十余种。但仅以这里所谓的《新梦》初版本和再版本畅销这一判断、叙述而言,窃以为,印刷不足百本,或两三百本(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许多新文学作品的初版印刷数)而引起的畅销,与巴金的《家》等小说的畅销不可同日而语,更进一步来看:1.作为文化产品的新文学作品的印刷、销售等情况(通常也被用作其在当时影响如何之大的证据),需要作实证的研究,不可作泛泛之语;2.作者、友好所言是否属实,也有待我们的“批判性思考”。
或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笔者发现,《桑干河上》《子夜》《种谷记》等书拥有不止一个初版本的现象,虽已引起编著者的注意,且被同时纳入本书并作了较为妥善的著录,但在学术界最早指出这一“同一家书局会有两个初版本”的特殊现象并予以辩证的一个原创性的研究成果⑦,无意间却被《图鉴》遗漏在外。
一般认为,一现代文学之书的版权页注明其为初版,即可证明其为初版本无疑,无须专事研究。其实问题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这些问题至少包括:1.同一家书局会有两个初版本;2.一本书也会有两张版权页;3.版权页上没有初版年月;4.初版时间印刷有误;5.初版时间与初版处无法对应,尤其是在重印、再版之时,有意将初版的出版处更换作新的出版处,版次却连续计算;6.同一种书,书名等未作修改,但在不同出版处,却仍作初版本;7.修改书名,又更换其出版处,导致同一书有一个以上的初版本。⑧据此检查该书,不少情况已有妥善处理,有些作了新的修正、补充,有些则取折中的办法,但似乎不够准确(如1947年6月上海寰星书店出版《呼兰河传》亦为一初版本,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更名为《饶了她》之后于1933年12月再出一删改本,亦为初版本,但此二书“简介”中并未言及),有些似乎还没有引起关注,恰恰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所有这些问题,虽然与该书贡献同在,我们在版本学、文献学乃至文学史研究中也经常遇到,不独《图鉴》为然,但作为其未竟之业,笔者仍希望,后续若有同类著作纂修出版,能广泛汲取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如编著者声称“现代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近一个甲子了,还没有一本专门的版本学著作”⑨恐不确,王宗芳、孙伟红合著《现代文学版本学》早在2002年1月已由珠海出版社出版,著者之一王宗芳的多篇论文此前也早已发表),并见示其详尽的参考文献、书目及进一步可以查考的线索、来源等等,以便同人复核、考校,从而持续推进相关研究。
三 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前瞻
关于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工作,如上所论,确已取得相当成绩,新世纪以来进展尤为迅速。但不同于举一机构、一团体之力者,《图鉴》的问世,则标志着单独、分散的学者个人担任这一工作,在现阶段所能达到的高度,其贡献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图鉴》已经为此一方面工作划上句号,相反,以笔者目前粗浅的观察,《图鉴》之后,仍有很大的发展、开拓空间。
质言之,包括《图鉴》及“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丛书所搜集、整理的“现代文学初版本”,只是其中一端。我们不仅需要扩展整理、研究的广度,也同样要尽力延展其深度。未来努力的方向,至少应在下述层面进行:1.重视文字资料,而较少关注图像资料的搜集、整理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这一观念、学风有待转变;2.与现代文学相比,晚清、当代作家作品更少整理,未来的研究应对此有所加强、补足;3.在现代文学内部,新文学资料整理已久,而学者们对晚清民国的旧体诗词、诗话词话、文章、八股文及其他游戏文章、章回小说等“旧文学”“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才刚刚开始;4.整理、汇集出版“资料汇编”性质的纸质图书之外,学者亦可尝试建立专题数据库。因这一超越目录和索引的新的知识生产工具,可以更大程度地服务、促进学术研究与知识生产的转型。
与整理工作所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严肃的学术研究无疑显得更为薄弱。但这里所说的“薄弱”,并非针对现代文学版本学而言(如所周知,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在发展,近年来学者们对“签名本”等的研究,更为此一领域开出新的分支),也不是说对近现代画报、画刊所作的专门研究付之阙如,而是指:利用包括现代文学版本的图像资料在内的视觉艺术资料,并以此为主要研究资料或研究对象,所展开的有关研究还十分鲜见,完全不成气候,以致我们忽视了我们这些研究者,以及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样都生活在“图像”与“文字”交错的语境之中,“文字”只是理解、重建这一语境的一种方式。
但要理解图像,殊非易事,这从不少西方学者倾心于撰述“怎样读懂一幅图”之类的论文即可看出。研究图像资料的取向,若要极其概括地叙述,可大致分作三种。一是以图证史(文学史、文化史,等等),二是视觉文化研究,三是艺术史研究。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以图证史”(这里的“证”并非“证明”,也包括重估、商榷、批评、补充等等)和视觉文化研究无疑是更为需要也可以学习、驾驭的取向。前一方面的典范性著作如布克哈特、赫伊津哈杰出的文化史著及彼特·伯克的《图像证史》、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后一领域的重要研究则有福柯对《宫娥图》的解读、罗兰·巴特对商业广告的批评及电影研究等等,皆可资借镜,这里也就不必赘言了。
最后,若可放宽我们治学的视野,不难见出:尽管包括“现代文学初版本”及其图像资料在内的一切版本、文献史料研究深具学术意义、价值,但其仍然并非是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的目标和目的。旨在探寻“客观”“科学”“真实”的版本、文献史料整理及研究,如何与文学(史)、社会、历史研究在承认彼此差异、保持张力的同时,避免自说自话或拘泥于其间的窘境,而走向互相沟通、对话,烛照我们理解文学,探索人性,直面新的时代向研究者提出的新课题,仍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许建辉:《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初版本图典·后记》,陈建功、吴义勤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6~1033页。
②大抵心安即是家:《有哪些古籍的影印本是经过修版后影印的?》,国学数典网2017年9月15日,网址见: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6453,2018年10月16日最后检索。
③⑨《新文学初版本寻访记(代后记)》,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02页。
④朱金顺:《讲究版本要靠实物,初版时间要凭初版本版权页——序〈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陈子善在研究及“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讲授中,一直践行并强调从实物出发这一作业原则。
⑤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例言》,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⑥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
⑦⑧金宏宇:《版权页论》,氏著《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4~346、341~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