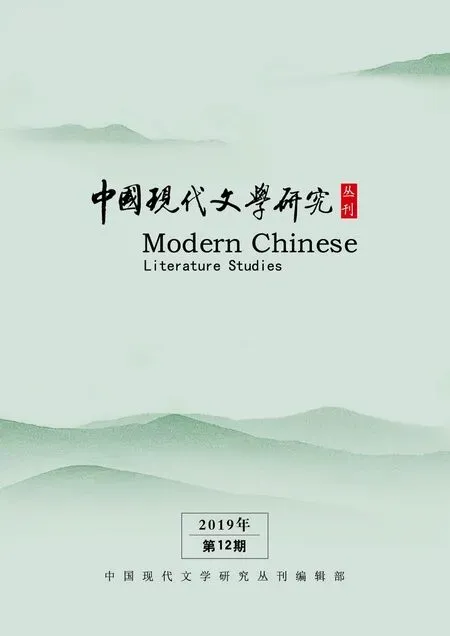韦素园与高晓岚的“两地书”
——《痕六篇》原型探微
内容提要:现代作家韦素园的女友高晓岚,是陈独秀夫人高大众、高贤萃的堂妹,1925年赴美留学。韦素园的散文诗《痕六篇》之二《“窄狭”》、之三《端午节的邀请》,分别书写了“我”与黎沙、少年与爱华的爱情。把《痕六篇》与高晓岚的一组诗歌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黎沙与爱华的原型均是高晓岚。黎沙的原型是以高晓岚为主,可以说是用化名写他们的爱情经历。但在《端午节的邀请》中,原型人物的本事材料进入散文诗后大致得到了保留,但同时经过了必要的删减、增添和重组。周作人关于韦素园作品的提醒,对于我们今天讨论文学虚构与非虚构问题,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鲁迅一生中,只给一位作家写过碑文,这位作家是比他小21岁的韦素园。韦素园是安徽霍邱县叶集人(今六安市叶集区),译著有俄国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散文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文学作品有散文诗《春雨》《痕六篇》等。韦素园与鲁迅关系甚密,他们在1925年一起发起成立未名社。韦素园逝世后,鲁迅手书碑文:“君以一九零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丛芜,友静农,霁野立表;鲁迅书。”从诊断出肺结核(当时是绝症),一直到去世,鲁迅一直十分关心韦素园的病情。在1927年1月10日致韦素园的信中,鲁迅劝慰他:“啊咯血,应速治,除服药打针之外,最好是吃鱼肝油。”在1929年3月22日的信中,鲁迅提醒他:“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的那样短文。”在给未名社其他成员写信时,鲁迅也常常记挂着韦素园的病情。
鲁迅与许广平(景宋)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的书信合集《两地书》,于1933年4月出版,而出版的一个直接原因便是因为韦素园。鲁迅在序言中交代编书的缘起:“这一本书,是这样地编起来的——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霁野、静农、丛芜三个人署名的信,说漱园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病殁于北平同仁医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为他出一本纪念册,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因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够痊愈的,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其次,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却有时竟没有想到,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我们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统名之曰《两地书》。”鲁迅在序言中,还介绍了出版《两地书》的一个目的,是纪念以韦素园为代表的“好意的朋友”:“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人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
1929年5月30日上午,鲁迅利用北上省母的间隙,在张目寒、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的陪同下,去西山病院看望了韦素园,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当天下午五时,鲁迅就写信给许广平,细谈会晤情形,“他也问些关于我们的事,我说了一个大略”。1929年3月22日,鲁迅在给韦素园的信中坦承了自己与许广平的恋爱,并描述二人从厦门到广东再到上海的经历,可见他与韦素园的私交关系非同一般。鲁迅探望韦素园时,韦素园还在关心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鲁迅对韦素园的恋爱也有所了解:“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霁野等四人同去。漱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画像,我有时瞥见这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脸,便仿佛记得有人说过,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痊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两地书》)鲁迅详细叙述了探望的情景和自己的感受,并提到了韦素园原有一个爱人。
1934年7月16日夜晚,鲁迅在写作散文《忆韦素园君》时,再次想到了韦素园的爱人:“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韦素园的爱人是谁呢?从语气上看,鲁迅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韦素园原有的爱人叫高晓岚(1899—1992),又名高筱兰、高晓兰,安徽霍邱县洪集人(今六安市叶集区洪集镇),陈独秀夫人高大众、高贤萃(高君曼)的堂妹(在陈独秀研究中,最大的乌龙是把他原配夫人高大众的姓名错成了高晓岚),1917—1922年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及其升格后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高晓岚之子为日本华侨作家林洲(笔名夏之炎)。沙琳在《洪门歌者——日本华侨作家夏之炎速写》(《中国作家》1994年第6期)中写道:“夏父林熙杰早年回国就读北京大学英文系,并参加五四运动。赴美就学芝加哥大学时与五四运动时的伙伴高晓兰重逢,并结婚。高晓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她曾投身新文化运动,是鲁迅的学生,与许广平交情甚厚,上海将解放时,许广平携周海婴躲在其家,解放后她任职上海市长秘书室。”
1925年至1929年间,在鲁迅与许广平鸿雁往来的时候,韦素园与高晓岚也一直在“万里飞书”,他们的“两地书”却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他们的爱情悲剧陷入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迷雾之中。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的实证材料,但韦素园的《痕六篇》(原载1930年4月30日《未名》2卷9、10、11、12期合刊)却留下了他与高晓岚的爱情痕迹。《痕六篇》之二《“窄狭”》、之三《端午节的邀请》分别书写了“我”与黎沙、少年与爱华的爱情。而实际上,只要把《“窄狭”》《端午节的邀请》与高晓岚的一组诗歌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黎沙与爱华的原型均是高晓岚,可以获取密码般的讯息。
一 地名:字母里的爱情密码
《“窄狭”》中的“异邦O地”和“K地”,《端午节的邀请》中的“A城”,是韦素园散文诗中非常重要的地名。这三个英文字母所指代的地方,留下了韦素园与高晓岚“万里飞书”的踪迹,皆有原型基础。
(一)异邦O地与美国欧城
1925年,在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长的高晓岚,考取官费生赴美留学。据现有资料综合分析,可以大致推算高晓岚留学美国的时间为1925年下半年至1929年上半年。1925年5月10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刊载了朱学静的《三月三日怀同学晓岚》。她的这首诗歌有一小注:“前奉吾师手谕,知同级高君将留学欧美中心,艳羡而自愧不如也。”从时间上看,高晓岚在1925年年初就在为留学美国而做准备。
1925年5月31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刊载高晓岚《赴美期近,离国在即,惧学识之肤浅,报国何从;怅师友之睽违,亲教无日。爰书所感,即向壬戍国文部诸师长学姊告别》,以及国文部老师顾震福的《次韵赠别》。从《次韵赠别》看,顾震福对高晓岚颇为欣赏。“五年三见送西征”句有小注:“辛酉送苏林二女士赴法,癸亥送刘女士赴美,今又送高君,计已三次。”1921年9月,国文部本科二年级学生林宝权、苏梅(苏雪林)由女高师肄业赴法留学。1925年5月,高晓岚赴美留学,顾震福又为她饯行,高晓岚应该又到了北京。“作客久如秋燕惯”有小注:“君连年客居京都皖宁”,指的是高晓岚一直居住在北京和安徽安庆怀宁。“皖水临歧有后生”句有注:“君任皖女师校教务长,兼教员,诸女生闻君远行,多送别者。”1922年从女高师毕业后,高晓岚回安庆担任安徽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务长。
1925年6月21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刊载了《本校毕业生高晓岚启事》:“晓岚南下匆匆,未获走辞。诸师友至谦。已定八月十七日放洋赴美,后此。”
1928年的《霍邱县志》载:“高晓岚,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现留学美国。”也就是说,高晓岚在1928年还在美国留学。
1929年7月16日,高晓岚被任命为安徽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该校由省立第二女师改组而成。高晓岚回国时间,应在1929年上半年。
1927年冬天出版的第十二卷第四号《留美学生季报》,刊载了高晓岚的诗歌《接素兰自纽约来信,感而写此(十月六日夕)》:
一
记得欧城课罢时,与君长话复论诗;
秋风零落经年梦,斗室孤灯更唤谁?
二
心血消磨志欲灰,为君振作几多回;
白头已让莺花笑,锦瑟华年暗里催。
三
霹雳未随残夏去,秋声已共雨声来;
明年何日知能见,海外黄花三度开。
这三首旧体诗后面,还附了两段白话新诗。三首旧体诗与两段白话诗中间,作者有一小注:
来爱城(Iowa.City)后人地生疏,交游所在,非异国诸女同学,即客气敷衍交初识者。一身如寄,百感萦怀。读忆旧思家之句,清泪为数行下也。友人宗瑶尝笑晓兰为“善感多愁者”,果阅及此,当又以他号相赠矣。风雨之夕,书成以下两节。九月二十四日
诗歌小注中的“宗瑶”是指王宗瑶,与高晓岚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同学,也是该校文艺研究会首批会员。1925年4月19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刊载《本校毕业生获得美国米西干大学奖学金》和《致王宗瑶女士信》。王宗瑶与女高师同学高晓岚、钱用和都是1925年赴美留学。后来做了宋美龄秘书的钱用和,于1929撰写《奥勃林大学(Oberlin College)之生活及附近参观游览》(《欧风美雨》,上海新纪元书店1930年初版),介绍了她造访米西根大学的情形,“奥校春假后乘兴至米西根安娜城游……沿途风雨交作,殊困人,幸到安时,即有女高师同学王君等接候,旧雨阔别,相叙畅谈,顿忘疲累矣。……中国同学之在米西根大学者不少,女高师友数人,均得于此相晤,海外叙首,亦非偶然也”。“女高师同学王君”,即指王宗瑶。钱用和在纽汉文参观时,也得到了“苏省同学王君之招待引导”,王宗瑶与钱用和均是江苏人。
诗歌小注中的“爱城(Iowa City)”,多译为爱荷华。从诗歌内容来看,高晓岚先在欧城读书,后来又到爱荷华攻读学位。
“记得欧城课罢时”句中的“欧城”,指的是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该校位于美国俄亥俄州(Ohio State),始建于1833年,以多元的人文思想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闻名。美国的第一位黑人女大学生在1850年毕业于此。1853年,美国第一位大学女教师执教于此。在20世纪以前,总共有128名黑人毕业于此,几乎占全国黑人学士总数的三分之一。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孔祥熙于1905年于欧柏林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耶鲁大学。钱用和在《奥勃林大学(Oberlin College)之生活及附近参观游览》中,称该校“对外国学生尤谦和优礼,体贴入微。作种种之联络,使不感客中之苦,故中国同学初次到美者入此等学校为最宜,尤以研究文学音乐艺术为佳胜”,“虽异邦学生,亦一视同仁”。高晓岚、钱用和留学美国的第一站,均是欧柏林。高晓岚诗题中的“素兰”,是指谭素兰,她1923年赴美学习钢琴,就读于欧柏林学院,是中国最早留洋的女钢琴家之一。
欧城与爱荷华都是韦素园魂牵梦萦之地,因为高贵的女郎高晓岚曾经在那里与他“万里飞书”。“爱城(Iowa City)”在韦素园散文诗《端午节的邀请》里变成了诗歌女青年的姓名“爱华”,“欧城”(Oberlin)在韦素园散文诗《“窄狭”》中变成了“异邦O地”:
日子向前过去。
忽然,忽然,有一天,来了一封奇异的信件,是从异邦o地寄给我的。哦,我想,这是谁呢?
拆开一看:——黎沙!
“从你兄弟那里,我才知道你到了K地,并且作着那样的工作,这是你的真心所愿么?我心中不胜惊奇和骇异!”
“听说你这是为着生活。并且为着朋友,也为着兄弟。但是我要请你,我要请你,为着人生的前途,你也要顾惜到你自己的。”
日子照例地向前过去。我又接到她第二封信。还是先前的那些话,不过末尾上似乎更多加添了一句:
“你太爱你的朋友和兄弟!”
《“窄狭”》中的“我”,收到了黎沙从异邦O地寄来的信件,这个“异邦O地”正是高晓岚旧体诗“记得欧城课罢时”中的“欧城”。这是一对曾经的恋人,留给我们的爱情密码。1929年5月,鲁迅去看望韦素园时,已经知道高晓岚与别人结了婚。韦素园的《“窄狭”》写于1929年11月24日,而此时的高晓岚已经从美归国,在安徽第二女子中学担任校长,并已嫁给林熙杰。卧在病床上的韦素园,默默地想着曾经爱过自己的女友高晓岚,回忆她从美国欧城(“异邦O地”)寄给他的信件,重温信里的内容,欧城便成了韦素园写作《“窄狭”》的情感按钮,勾起他的无限感怀。
(二)K地与开封
《“窄狭”》开头的第一句话,便写到了K地:
我那时是在K地,住在城的南门外慈关里。
我每日作着辛苦的工作,这事是我个人心中并不曾愿意做的。我感觉寂寞。
每天早晨,——我那时几乎失眠,——天一明时,我便从床上爬起。穿好了衣,携着手杖,冒着寒雪,我信步地走将出去。我那时是到一个离我住房处有四五里路的乡间火车站。我默默在想,今天我要会着了人呢。结果,我是孤单地又沿着原路,转到家去。
啊,啊,我原是要这样消磨我的生活。
散文诗里,“我”在“K地”收到黎沙从异邦O地寄来的信件。高晓岚从美国欧城写给韦素园的第一封信,收信地址在哪里呢?应该是河南开封。1925年,韦素园曾两次到河南开封国民军第二军,担任苏联军事顾问人员的翻译。曹靖华在《自叙经历》(《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中有过记载:
北伐,实际上是在1925年就开始了。当时大致有三个据点:一是广州的国民革命第一军;开封的国民革命第二军;三是包头的冯玉祥,是为第三军。第三国际向每个据点都派出了苏联顾问团。当时,我在北大旁听,与韦素园一道受李大钊同志的指派,于1925年春到开封担任顾问团的俄文翻译。……顾问团的办公地点,在行宫角临街的一所二层小楼里。1981年夏我重到开封,这所街角的小楼荡然无存了。
……
1926年春,吴佩孚攻占了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西撤,顾问团经蒙古草原回国去了。兵慌马乱中,我取道徐州、上海,由海路到天津,于“三一八”惨案的次日到北京。
曹靖华1981年写的散文《故乡行》也提到了“行宫角”:“行宫角附近苏联顾问团的那座办公楼,已荡然无存了。当年翻译《阿Q正传》的王希礼,就在那小楼里工作。我站在当年的小楼对面,迎着毛毛细雨,心里浮起当年共同打倒军阀,帮助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的情景。”苏联顾问团的办公地点,在行宫角临街的一所二层小楼里,此地与韦素园散文诗里的“K地”“城的南门外慈关里”完全吻合。行宫角在开封的南门外,距离开封火车站四五里路。清朝光绪年间,法国和比利时修建了汴洛铁路,1907年开封至郑州段竣工通车,当时的火车站还是开封的郊区,是“乡间火车站”。K地指代的就是开封,描写的场景完全符合当时开封的特征:“冒着寒雪,我信步地走将出去,我那时是到一个离我住处有四五里路的乡间火车站。”
慈关里这个地名,今不可考,可能与大相国寺有关。行宫角位于著名的佛教寺院大相国寺旁边,附近就有街道叫“慈善街”。“慈关里”应该就是指苏联顾问团的住地。俄罗斯汉学家王希礼也于1925年春天被分派到苏联军事顾问团,来到开封的国民二军中开展军事顾问工作,他不但会汉语,而且喜爱中国文学,后来用俄语翻译出版了《阿Q正传》。苏联军事顾问团住地有着浓厚的文学氛围,韦素园在此翻译过埃治的散文诗,落款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译于慈关里”,俄国都介涅夫(屠格涅夫)《玛莎》落款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译于慈关里”,俄国色尔格夫专司基《半神》落款为“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译者记于慈关里”(见《黄花集》)。这表明,至少在1925年12月14日至1926年1月4日期间,韦素园一直呆在慈关里。也就是说,1925年的冬天,韦素园又到开封工作、生活过。他“作着那样的工作”,让高晓岚“心中不胜惊奇和骇异”。
韦素园冬天去开封的路费,是向鲁迅借的。1925年12月8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夜素园来别,假以泉四十。”该年12月28日鲁迅日记记载:“访李霁野,收素园所还泉卌。”“卌”为“四十”之意。从语气上看,是李霁野替韦素园还款,鲁迅并未见到韦素园。1977年,李霁野在《厄于短年的韦素园》中记载有误:“一九二五年起,我们同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很多了。这一年春季,素园去开封国民军第二军担任俄语翻译,因为那时有苏俄军事人员在该军任职;鲁迅先生借给素园四十元作川资。《鲁迅日记》十二月二十八日记载:‘访李霁野,收素园所还泉册。’所还就是这四十元。”李霁野此处的回忆,出现了偏差。韦顺的《远志宏才厄短年——韦素园传略》(见《韦素园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也沿用了李霁野的错误记载。韦素园通过李霁野所还鲁迅的“川资”,是他冬天前往开封的路费,而不是春天去开封所借的。1925年12月8日话别后,一直到1926年3月21日,韦素园与鲁迅才重新会面。1926年3月21日鲁迅日记载:“曹靖华、韦丛芜、素园、台静农、李霁野来。”曹靖华是3月19日到达北京,韦素园极有可能与他同行。鲁迅日记与曹靖华《自叙经历》所记载的时间是吻合的。曹靖华、韦素园离开开封,与吴佩孚的进攻有关。吴佩孚于1926年1月兵分三路进攻河南,国民第二军于2月26日撤离开封 ,3月2日又放弃了郑州 ,苏联军事顾问团也随之撤离并解散。王冶秋的《鲁迅与韦素园》(见《狱中琐记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有着比较明确的记载:
记得素园在这以前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转托徐旭生先生的介绍,到了国民新报当副刊编辑,但似乎为时不久(约在一九二五年十一、十二月间)就到开封去了。
这期间,未名社逐渐成长起来,出了书,并把《莽原》改为半月刊在未名社编辑发行(第1期为1926年1月10日出版)。韦素园约在1926年的3月也回到北京,这时未名社似乎已搬到马神庙西老胡同一号。
韦素园1925年12月又去开封后,在那里所呆的时间,大约三个月。高晓岚1925年上半年准备出国留学的时间,与韦素园在开封工作的时间刚好重叠,她从美国给韦素园写的第一封信,应该就是寄到开封来的。高晓岚于“八月十七日放洋赴美”,韦素园在该年冬天收到她从欧城发出的第一封来信,也非常符合逻辑。
姜德明在《听曹老谈韦素园》(《散文世界》1988年第1期)一文里,记载了1972年8月5日他与曹靖华的一次谈话,曹靖华谈到了韦素园“痛苦的恋爱”:“素园的性格是沉默寡言的……他没有什么大作品留存下来,一生也没有结婚。当然,他恋爱过,是一次痛苦的恋爱……”韦素园在开封收到高晓岚从美国寄来的信件,曹靖华应该是知情的。从李霁野的回忆文章《流落安庆一年琐记》看,曹靖华与高晓岚可能也认识。1922年夏,曹靖华跟着韦素园到了安庆。李霁野回忆:“这年夏天,曹靖华到安庆,韦素园介绍我同他结识了,以后一同参加了未名社。”而那年夏天,韦素园、李霁野经常去访高晓岚。
(三)A城与安庆
《“窄狭”》中,“我”与黎沙初认识时,是在“扬子江边的一个城上”:
我当时很惊奇。黎沙,她是个高贵的女郎,当我和她初认识时,我们同住在扬子江边的一个城上。我每次到她家,都被她亲密地招待到她卧室里。这里面陈设的有碑体的字,有湘绣的画,有精雅的琴笛,有阔绰的几椅……啊,我那时想,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有这样的姑娘,这是何等的奇妙,这是何等的神秘!……
扬子江原本只是指长江较下游的部分,但由于这是西方传教士最先听到的名字,“扬子江”(the Yangtze River)在英语中也就代表了整个长江。“扬子江边的一个城”,实际上指的是安徽安庆。《端午节的邀请》中,韦素园用“A城”来暗示:“几年的光阴过去,少年却随着他哥哥漂流到A城里。”高晓岚与韦素园最早认识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安庆。黎沙屋里的陈设,都符合高晓岚的身份特征。李霁野1979年写的《流落安庆一年琐记》,是韦素园与高晓岚相识的最重要的佐证。李霁野的叙述,揭开了韦素园女友的身份之谜:
一位女的小同乡,在安庆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读完北京女子师范,1922年又回到母校服务。她同韦丛芜的大哥很熟,两个人常有旧体诗唱和,但我并没有看过这些诗,不知道内容和艺术性如何。韦素园从苏联回国后,夏冬都回安庆探亲,我们都觉得她是开风气之先的人,曾多次同访她谈天。
与高晓岚很熟的韦凤章,是韦素园的大哥。韦素园兄弟五个,依次为韦崇华(凤章)、韦崇义(少堂)、韦崇文(素园)、韦崇武(丛芜)、韦崇斌。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张目寒等人在叶集明强小学读书时,韦凤章曾担任过他们的历史老师。韦凤章还有一个名字叫韦启俊,民国《霍邱县志》记载,韦启俊毕业于“安徽优级师范学堂”。李霁野在他的散文里也多次提到韦凤章,如在《我的童年》里写道:“教我们历史的老师是韦凤章,素园的大哥。他在外乡大城市做过教育工作,经验较多,知识面较广,对学校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1918年3月至1920年6月,霍邱人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很多霍邱文化人在此期间到湖南任职。1918年韦素园的大哥韦凤章在长沙任湖南省第一区(兼第四区)省视学,又兼任省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所长。韦素园就到长沙,进了法政专门学校预科读书。1920年夏天,韦凤章转安庆任职,韦素园也就从长沙到安庆,考入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韦素园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等人一起赴苏学习,1922年回国,于当年秋天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夏,在江苏常州去官为僧的韦凤章病逝,这对正在北京读书的韦素园、韦丛芜兄弟是一个沉痛打击。《痕六篇》之六《焚化》,就是韦素园悼念他的。
韦素园与高晓岚的相爱相识,应该是大哥大嫂撮合的结果,而李霁野是见证人之一。1922年,韦凤章在安庆做教育工作,当时办一种报纸,李霁野便帮着选一些可以从外地报纸转载的材料。韦凤章后来又开办商品陈列所,商务印书馆拿来一部分书设了一个代售处,李霁野便在代售处当起了小伙计。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直到1923年春被韦素园带到北京读书。1977年,李霁野在《厄于短年的韦素园》中回忆道:“ 一九二二年夏季回国,素园到安庆去看望父母兄嫂”,“一九二二年秋他进了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这年寒假,素园又回安庆省亲,力劝我到北京读书,虽然我两手空空,友情的温暖却鼓励我次年春和他同行,开始写点文稿维持艰苦的生活,并换取入学的费用”。1922年夏天,高晓岚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回到安庆担任安徽第一女子师范教务长,与韦素园大哥韦凤章“常有旧体诗唱和”。李霁野对高晓岚的印象比较深刻:“韦素园从苏联回国后,夏冬都回安庆探亲,我们都觉得她是开风气之先的人,曾多次同访她谈天。”韦素园与高晓岚是不是1922年才认识,还是在留苏之前就认识了,从李霁野的叙述中,我们并不能明晰,但安庆的确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
二 人物原型:命名的意义
(一)黎沙的原型
《“窄狭”》里,“黎沙”在“我”的心中“是个高贵的女郎”。高晓岚在韦素园的心中,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在散文诗里用“黎沙”来指代高晓岚,对高晓岚的思念和回忆,是他创造黎沙这个形象的心理驱动力。
韦素园描绘了黎沙卧室里的内景:“这里面陈设的有碑体的字,有湘绣的画,有精雅的琴笛,有阔绰的几椅……”空间环境,尤其是卧室内景,可以看作是对人物的换喻性或隐喻性的表现。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一个男人的住所是他本人的延伸,描写了这个住所也就是描写了他。”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黎沙房间内景表明了她作为知识女性的身份,作为高贵女郎的身份。特别是“有碑体的字”,与苏雪林在《我的学生时代》(1942年4月《妇女新运》第5期)中对高晓岚的记叙高度吻合:“她在家塾读过几年的书,文理颇清顺,也能做几句旧诗,写得一笔远胜于我的很有腕力的字——我的书法到于今还是鬼画符,实为永不能补救的缺点”,“她的文字,也同她的书法一般,峭挺苍凝,不类出诸幼女之手”。
高晓岚比韦素园大三岁,他们的万里飞书是一种姐弟恋。在他们家乡霍邱,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窄狭”》中,黎沙与“我”似乎就有一种姐弟恋的色彩。黎沙在信中说:“听说你这是为着生活。并且为着朋友,也为着兄弟。但是我要请你,我要请你,为着人生的前途,你也要顾惜到你自己的。”“你太爱你的朋友和兄弟!”“我”当时想她的心,为什么这样“窄狭”?几年时光过去了,“我”终于明白她的“窄狭”,是对自己的一种关心,一种真挚的爱。
据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第一期记载,高晓岚有一个字:“曙岑”。黎沙的“黎”,与高晓岚名字中的“晓”“曙”都是一个意思,命名上是影射高晓岚。而黎沙的“沙”(莎)字,在韦素园翻译和阅读的俄罗期文学作品里经常出现。在写下“黎沙”这个名字时,韦素园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很多俄罗斯女子的形象。韦素园1925年12月18日译于慈关里的都介涅夫(屠格涅夫)散文诗《玛莎》,写一个车夫对亡妻玛莎的深切怀念。1926年4月,韦素园为李霁野翻译的俄国戏剧《往星中》(安特列夫著)作序,重点提到了变成白痴的尼古拉的未婚妻玛露莎。有人劝她不要再回到尼古拉那里去了,但是她说:“我要去。我要和保存圣物一样,保存尼古拉所留下的东西——他的思想,他的敏感的爱情,他的温存。”在剧末,玛露莎(两臂伸向大地):“祝福你,我的亲爱的受着苦痛的兄弟!”在写作《“窄狭”》时,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韦素园,与尼古拉的命运何其相似!高晓岚写作《接素兰自纽约来信,感而写此(十月六日夕)》的1927年,韦素园正遭受着病痛的折磨。1927年春季,韦素园被送到西山福寿岭疗养院,从此就很少起床,看书写字一般都伏在枕上。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写道:“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玛露莎最终没有回到尼古拉身边,黎沙最终没有回到“我”身边,高晓岚最终也没有回到韦素园身边,韦素园成了“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这个不幸的人,他与高晓岚的书信,他写给鲁迅的信,都无一幸存。与高晓岚万里飞书的两年里,也是韦素园与鲁迅交往最频繁的时期。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25年5月到1926年8月,两人自相识后的会面达到三十余次。在现有的鲁迅书信中,鲁迅给韦素园的信件共计28封,而1926年下半年最为集中,这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两人主要通过信件联系。1926年12月5日,鲁迅写给韦素园的信中提及:“留学自然很好,但既然对于出版事业有兴趣,何妨再办若干时。”鲁迅之所以这样说,说明韦素园之前写给他的信中提出了留学的设想。而韦素园萌发留学的念头,可能与高晓岚有很大关系。但到农历1926年底,阳历1927年初,韦素园的所有梦想戛然而止。李霁野在《忆素园》中回忆说:“有一晚他深夜不睡,想写完一篇绍介果戈理的文章,第二天就大吐血不能再起床。静农打电话让我进城,告诉了我素园的病已经医生诊断无治的时候,我们的周身颤抖,仿佛看见死亡的巨手就要擢去我们的最亲的朋友一样。”1928年10月28日,韦素园在《黄花集》的序言中写道:“我自去岁阳历一月卧病,到此刻已经是将近两年的时光了。在这期间,深觉以前过的生活是如何零乱,空虚,无聊,生命是如何毫无惋惜似地,无益地,静静地向前过去了。”
韦素园“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劝高晓岚另嫁他人的信件当在1927年发出。高晓岚收到信后,心里应该是十分难受的,同时又为韦素园的真诚所感动,肯定会回信表明一番心迹。韦素园不得不再次去信高晓岚,劝其死心。《“窄狭”》中,“我不久便也病了,而且很重。是一个阴黑的暮晚,是一个严冷的天气,我在十分垂危的病床上,接到了她最后的一个明片,上面写着仅仅四个字:——‘我很失望!’”黎沙寄出的这张明信片,符合高晓岚那时的心境。高晓岚写于1927年的《接素兰自纽约来信,感而写此(十月六日夕)》,无论是三首古体诗,还是几段新诗,都充满浓得化不开的悲伤情绪,“读忆旧思家之句,清泪为数行下也”。一直擅长古体诗的高晓岚,竟然为我们留下了几段白话新诗:“今朝又是阴天气,/惆怅天涯人,/憔悴凭谁寄?/心里辛酸/口头笑语!”新诗还有几个小注:“九月二十五星期日之夕,风雨甚骤,不能成寐,因写此节。”“不惯独去食堂自食,每每难下咽,感寂寞,因写此。九月二十五日。”她在食堂吃饭,“默,低头,/匆匆餐罢,/不敢勾留。/怕听他。/弦管歌讴,/引起离愁”。“弦管歌讴”后有注:“食室内有话匣故云。”1927年的高晓岚的确成了一个“多愁善感者”,她的诗歌记录了具体可感的忧伤场景,这与韦素园得了绝症有着直接关系。她与韦素园企图以诗歌的形式留驻生命的吉光片羽,但诗歌无论如何美好,也如黄花一样可能在岁月的流转中被遗忘、被摧毁。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9月,在高晓岚的要求下,从《莽原》杂志上的署名看,韦素园自己不再使用“韦漱园”,把名字又改了回去。在女师大学潮中,韦素园是鲁迅坚定的支持者,1926年9月,教育部下令撤并女师大,派林素园去武装接收,为表达自己对此人的厌恶,韦素园为此一度改名韦漱园。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写道:“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韦素园自己不用“韦素园”这个名字,要求鲁迅也不要用。韦素园曾因为自己已经改了名字,而鲁迅没有在通信中立即改过来,专门向鲁迅强调过。鲁迅 1926年10月15日给韦素园的回信,在第一段里就连忙赔不是:“九月卅日的信早收到了,看见《莽原》,早知道你改了号,而且推知是因为林素园。但写惯了,一写就又写了素园,下回改正罢。” 鲁迅还真照顾韦素园的好恶,在以后的书信往还中,便改“素园”为“漱园”。1929年5月3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讲述他去看望韦素园的情况,用的仍然是“韦漱园”。到1928年 9月,韦素园自己实际上已经将名字改回来了。李霁野在《厄于短年的韦素园》中回忆道:
在女师大学生驱逐杨荫榆的运动中,在鲁迅先生同胡适和陈西滢之流的斗争中,素园极力赞扬先生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说到,段派官僚林素园带兵接收了女师大之后,素园愤怒之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漱园”;后来因为一位相识多年的女友说不如旧名习惯,林某已经销声匿迹,素园才恢复了旧名。
韦素园这位相识多年的女友,就是高晓岚。从1927年6月25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开始,未名社在印书籍广告,连续几期列出“韦漱园译俄国短篇小说集《黄花集》”,1927年9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七期)改成了“韦素园译俄国短篇小说集《黄花集》”。这是韦素园最早恢复旧名之处。此前不久,高晓岚在写给韦素园的信中,应该提出了改回名字的建议。
在改回名字的前几个月,韦素园还决定将自己翻译的俄国短篇小说集命名为《黄花集》。高晓岚在《接素兰自纽约来信,感而写此(十月六日夕)》里写到了黄花:“明年何日知能见,海外黄花三度开。”高晓岚在北京女高师读书时还曾在《思亲》里写过:“荒径黄花曾冷落,禁城碧柳又缠绵。”黄花的意象,是彼此的巧合,还是互相的传染和触动?黄花,的确是他们爱情的最好隐喻。韦素园翻译的俄国短篇小说集,后来出版时定名为《最后的光芒》,而《黄花集》则成了韦素园翻译的散文诗歌小品集的书名。《黄花集》列为《未名丛刊》之十八,由未名社于1929年2月初版。司徒乔设计书面,封画构图寥廓而空疏,一枝藤蔓,几茎菊花,墨线勾勒的花瓣上,信笔缀以鹅黄的色泽,活绘出一派秋的气息,与书名“黄花”显得吻合无间。1928年10月28日,韦素园在只有几百字的短序中,重点谈到了命名:“现在承霁野的好意,将我病前几年中散在各处的译稿,差不多全搜集起来了。一本是短篇小说集,已在别处印行;另一本便是这些散文和诗,他所命名为《黄花集》的。实在,这些东西在新北俄,多半是过去的了。将这些与其说是献给读者,倒不如说是留作自己纪念的好。”韦素园的译作集命名为《黄花集》,不仅是对旧俄文学的欣赏,可能还暗含着另一层意思,纪念他与高晓岚的一段爱情。
高晓岚的三首古体诗,并不像写给女友素兰的,更像是写给韦素园的,只不过是借素兰的来信“有感而发”,会不会是高晓岚寄给韦素园情诗的一部分?韦素园的侄儿韦顺在《热血一腔入小诗》(见《韦素园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中,曾记载G君(高晓岚)与韦素园的“万里飞书”:“他的女友G君所给他的诗信,不复存在了。G君在国外留学时,曾有十首定情诗寄赠素园。素园病笃时,她又万里飞鸿,一倾衷曲。……现在只存有素园的胞弟丛芜在读G君的那封哀惋凄绝的长信时所写的一首诗,记下了当时的情景。”韦丛芜的那首诗,是《悼素园》中的第二首:
咯血盈盈气若丝,
昏灯昏室漏迟迟。
可怜万里飞书至,
字字痴情句句诗。
韦素园去世的1932年,高晓岚与林熙杰的儿子林洲(笔名夏之炎)出生。根据鲁迅的回忆文章,高晓岚与林熙杰应该在1929年5月之前就结婚或订婚了。1994年,林洲在华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怒海洪涛——现代洪门传奇》,附有其简介:“夏之炎,原名林洲,海南文昌人。祖居新加坡,一九三二年生,幼随母居上海,后至北京求学及工作,因父逝欲赴新而滞留香港,一九六六年迁居日本东京迄今。” 林洲出版了长篇小说《绝对零度下的钢》《飞向彩虹》《北京幻想曲》《北京又一个冬天》等十几部作品。林洲去世后,《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9年3月26日第3版)发布了消息,称其为“旅日爱国华侨、日本鹏达株式会社会长、知名作家林洲(笔名夏之炎)”。
林洲家族有着深厚的鲁迅情结,这与母亲高晓岚的影响有关。他与妻子在旅日初期,即创办了一所中国语言学校——“中国语之家”。林洲在学校中办了中国现代文学讲座,每周日下午,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学者从四面八方而来,听他讲授鲁迅研究,反响非常热烈。他们往往对鲁迅著作中的一个词讨论半天,结果经常研究出是日文的汉字。高晓岚的孙女林楠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也强调高是“鲁迅的学生”。晨光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当代爱国杰出人物故事100个》,曾收入对林楠的专访《一个中国女孩的东方梦》。这篇专访介绍林楠五岁时到上海和祖母相依,“林楠的祖母高晓兰是安徽一个书香门门第的才女。她是鲁迅的学生,田汉的文友”。“祖母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时结识了一位南洋华侨巨商的儿子林熙杰,他就是林南的祖父。祖母在美国学的是教育,学成后返回祖国从事教育和创作直到去世。”
高晓岚与鲁迅交往的实证材料,目前尚未发现。高晓岚与许广平,曾长期同时生活在上海。高晓岚“与许广平交情甚厚,上海将解放时,许广平携周海婴躲在其家”,高晓岚与许广平的友谊,也正是鲁迅与韦素园友谊的一种延续,而且这种延续持续了几代人。
(二)爱华的原型
1929年11月24日,卧在病榻上的韦素园,这个“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又写了叙事体散文诗《端午节的邀请》,只比《“窄狭”》晚一天。这篇散文诗中的少女爱华,与黎沙一样,也是对高晓岚的影射:“忽然有一天,日子是记不清楚了,他得到了一份期刊,上面有这样一首诗……少年读完了诗,看见下面署的是她的名——爱华。他默然良久,没有说一句话。”高晓岚在其诗中的注解中云:“来爱城(Iowa City)后人地生疏,交游所在,非异国诸女同学,即客气敷衍交初识者。一身如寄,百感萦怀。读忆旧思家之句,清泪为数行下也。”“爱城(Iowa City)”多译作爱荷华。名字藏密码。少女爱华的原型非高晓岚莫属。
在《端午节的邀请》中,少年“得到了一份期刊”,上面有爱华的一首诗,而实际上是韦素园得到了《留美学生季报》,上面有高晓岚的一组诗。《留美学生季报》是民国初年留美中国学生会在美国编辑、在上海印刷的一份中文刊物,从1914年到1928年持续了十四年的时间,是留美学生向国内介绍西方文化、科学和思想的重要平台,胡适、罗隆基、潘光旦、邱昌渭等先后担任该刊主编。从1917年开始,《留美学生季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每期印行1000册,其中500册由商务印书馆邮寄给在美订阅者,其余500册由商务印书馆各省分管承销,在国内代售。李霁野在《忆素园》里提到韦素园“在病中是怎样继续认真地读书”,“对于新的出版物他也并不忽略,在他去世后几天还有他购买的书从上海寄到”。韦素园得到《留美学生季报》,不仅看到了高晓岚的古体诗,还看到了她的两段白话诗。高晓岚白话诗的第二行写了天气,爱华的诗在第二行也写了天气。
高晓岚《接素兰自纽约来信,感而写此(十月六日夕)》里的新诗:
一
昨日初晴,
今朝又是阴天气;
惆怅天涯人
憔悴凭谁寄?
心里辛酸
口头笑语!
二
愁思无端,
客中滋味咀嚼烂,
是这般啊,
消失了甜蜜,
增长了苦涩辛酸,
堪怜:
一身飘泊,
客里客边;
风雨敲窗,
残灯黯淡,
谁与慰安?
只有多情衾锦,
给了我多少温暖!
默,低头,
匆匆餐罢,
不敢勾留。
怕听他,
弦管歌讴,
引起离愁。
再看《端午节的邀请》里,爱华刊载在一个刊物上的诗:
那青春底迷人的眼波,
是在江南的五月的天气,
这生命中唯一的一日,
我永远忘不了你。
啊,啊,不幸我已作了人家孩子的母亲!
我还能有什么希翼?
这不可抵抗的逼人的命运,
把我永远沉在黑暗里。
高晓岚的白话新诗开头:“昨日初晴,/今朝又是阴天气”。爱华的诗:“那青春底迷人的眼波/是在江南的五月的天气”。爱华的诗,从诗歌风格上看,正是韦素园自己所写。结尾那句“把我永远沉在黑暗里”,是韦素园那几年诗歌中最常见的句子,如“在这漆黑的夜晚里,/……便又向无极的太空里消灭了去”(《无题》)。“我恍惚地来到了一所阴暗的黑室里”(《忆“黑室”中友人》)。“一切日用的,亲密伴我的什物,/都沉默地浸沉在浓厚的暗黑里。”(《睡时》)在《痕六篇》的其他几篇散文诗里,这样的句子也频繁出现,如《影的辞行》中:“白墙上,静卧着,一个黑影,孤独冷清。”《小猫的拜访》中:“我感觉我的生命在这黑夜里是这样暗暗地消去。”爱华那首诗的开头,是韦素园对高晓岚“今朝又是阴天气”的仿写和反写,他在最痛苦中试图保存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除了借爱华的这首诗写到“天气”,《端午节的邀请》一开头就写到了天气:“是江南的五月的天气……”《“窄狭”》也写到了天气:“是一个阴黑的暮晚,是一个严冷的天气……”韦素园在两篇散文诗里,对天气都特别敏感,特别用心处理,是对高晓岚情感世界的一种呼应,是用文字的个性渲染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情感密码。
《端午节的邀请》在结尾还特别指出,发表爱华诗歌的“期刊原是她的Cecmpa编的,但少年终于没好去问详细情形”。俄语Cecmpa,即姐妹。为高晓岚发表诗歌的《留美学生季报》,她留美的姐妹可能参与编辑了,至少由她们推荐给了主编。主编邱昌渭,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硕士、博士,其夫人周淑清,字冰如,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刊载高晓岚诗歌的《留美学生季报》同时发表周淑清的《留美中国女子研究教育之我见》。高晓岚留美好友谭素兰,与河南信阳人李汉珍相识结婚。李汉珍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八年,1928年与邱昌渭同时毕业后回国。从时间和地点上看,与高晓岚诗歌题目中的“接素兰自纽约来信”相吻合。周淑清、谭素兰参与《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工作,也是有可能的。另外,高晓岚与她的姐妹们一起编辑过女高师《文艺会刊》,全部由女生担任编辑的文艺刊物,在民国并不多见。
1931年9月13日,韦素园创作散文诗《别》,他将女主人公命名为“琼华”,还写到了“琼岛也伸出了长长的暗影”。琼岛位于北海公园内,全园的中心是琼华岛,简称琼岛。韦素园曾与鲁迅、许广平等人一起到北海公园游玩。鲁迅1926年8月3日日记记载:“下午往公园。得丛芜函约在北海公园茶话,晚赴之,坐中有朱寿恒女士、许广平女士、常维钧、赵少侯及素园。”琼岛也是海南岛的别称,高晓岚嫁给了广东琼州人(海南)林熙杰,韦素园为《别》的女主人公命名为琼华,可能与此有关,用以寄托对高晓岚的眷恋。琼华的命名,无疑是爱华命名的一种延伸。
三 周作人的提醒:虚构与非虚构
(一)原型的增删和重组
鲁迅编订出版的《两地书》,并非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原貌和全貌,而是被他们删削、修改、增补过的,其中有的被整段整段地删去了,还有的将全信抽出不发,仅注明为“缺”某某日一封或数封而已。鲁迅对原信的删改,很多是顾虑到有可能“累及别人”,不得不有所舍弃。《两地书》的增删修改,比较多地集中在鲁迅与许广平的恋情上,这至少说明,即使是在他们的关系已经成为事实婚姻之后,仍不得不顾虑到社会舆论。与鲁迅相比,韦素园写作《“窄狭”》《端午节的邀请》时,高晓岚已经嫁给别人,韦素园怀着更多的顾虑。《“窄狭”》自传性质比较明显,所以用虚构的名字“黎沙”代替高晓岚,欧城在《“窄狭”》中变成了“异邦O地”,开封变成了“K地”,“爱城(Iowa City)”在《端午节的邀请》里变成了诗歌女青年的姓名“爱华”,安庆用字母“A”代替,高晓岚的诗被仿写成爱华的诗。从真实原型到文学形象,往往经过了叙事转换与虚构重组。在韦素园的散文诗里,原型人物的本事行迹,在进入作品的过程中,发生了凸显、隐匿和位移。比较而言,黎沙的原型应该是高晓岚为主,可以说是用化名写他们的爱情经历。在《端午节的邀请》中,原型人物的本事材料进入散文诗后大致得到了保留,但同时经过了必要的删减、增添和重组。
《端午节的邀请》的结尾,实际上是对高晓岚婚姻的反写和改写,借此抒发对人生或世情的感叹:
最后打听了一气,方知这少女是在极恶劣的命运中,遵着母亲的遗命,不曾在大学毕业,出嫁了一个心中所不愿意的乡下人。
这期刊原是她的Cecmpa编的,但少年终于没好去问详细情形。
这似乎也传达出韦素园对高晓岚的一种情感和态度。事实上,高晓岚嫁给了一位南洋华侨巨商的儿子林熙杰,高晓岚与林熙杰都是毕业了的大学生和留学生。1931年6月,韦素园为韦丛芜译作《罪与罚》写的《写在书后》中,特别赞赏“意志坚强且思想纯洁的美丽的都丽亚,拒绝了有钱的恶汉卢辛与色鬼司维特里喀罗夫,终于嫁给一个热心戆直且精明能干的穷大学生拉如密享”。穷困潦倒、重病缠身的韦素园,当得知高晓岚嫁给富商之子后,其心情一定是复杂的,其真实滋味如何,文字背后映射的正是他自己的命运。
刊发于《未名》2卷9、10、11、12期合刊的《端午节的邀请》,其结尾与原稿就有细微的差别,比较耐人寻味。原稿为:
最后打听了一气,方知这少女是在极恶劣的命运中,遵着母亲的遗命,不曾在大学毕业,出嫁了一个心中所不愿意的人。
这期刊是她的“Sister”主编的,但少年终于没好去询问详细情形。
《未名》刊发稿将“出嫁了一个心中所不愿意的人”,改成了“出嫁了一个心中所不愿意的乡下人”。对于整篇作品而言,这种修改没有多大意义。修改的目的,是韦素园不想让高晓岚与林熙杰对号入座,不想对他们有任何一点伤害,哪怕是很微小的伤害。高晓岚与林熙杰留学美国,说的都是英语,而结尾将英语“Sister”(姐妹),改成了俄语“Cecmpa”(姐妹),可能也是此意。这表明,一些本事材料被韦素园进行了有意识的改写,这也牵涉到写作者的伦理问题,显露出作家人格之光华。
《“窄狭”》《端午节的邀请》两篇散文诗里出现的地名,主要用英文字母暗示,出现的真实地名只有一个长沙城,而这个真实的长沙城,也是韦素园故意为之。《 端午节的邀请》写少年“三弟”与爱华相亲,由双方的嫂子介绍,发生地点是在长沙城:“是江南的五月的天气,一个青年,此时已经离了家,来到长沙城,住在一个公共的场所。”这些与韦素园的生活经历是吻合的,“三弟”也可以理解成就是韦素园自己。1918—1920年,韦素园在长沙进了法政专门学校预科读书。而这个时间段,高晓岚却在北京读书,寒暑假应该在安庆度过。韦素园所写的长沙相亲,有三种可能。一是从韦素园当时的创作心理分析,他描写的相亲场景是真实的,但有意把相亲地点写在长沙,是一种“障眼法”,而他与原型高晓岚的相亲地点事实上在安庆。二是韦素园确实在长沙相过亲,只是那少女不是高晓岚,爱华这个人物是高晓岚与那个少女两个原型“合成”的结果。三是前两种可能混合在一起,韦素园把“安庆相亲”与“长沙相亲”,都写在了一起,无论在哪里相亲,中国传统式的相亲场面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的。1936年,李霁野在《忆素园》中提到韦素园“热恋一个女子”,但却模糊不清:
这以后素园到长沙,到安庆,尝了许多生活的甘辛,增加了许多实际的经验,思想渐渐成熟了。我们的通信虽然继续着,可惜现在已经一字不存,无从引证了。也是在这时候,青春的悲哀潜进了素园的心。多年以后我们在北京相聚,他告诉我这时他怎样热恋一个女子。有一天在公园里遇见一个颇为相似的人,他回去整整睡了一天,怎样也恢复不了心里的宁静。虽然经过了约十年的时光,他的情热并没有稍减;就感情说素园实在是火山似的人。
然而更有力的思想支配了他的心,他的眼前呈现着他对人类的任务。决然和那女子相约再见,他就到那震撼世界的大革命的策源地去了。
《忆素园》中的那个被韦素园热恋的女子,是不是高晓岚,还是另有其人?他们在哪里相识的,是在长沙,还是在安庆?语焉不详,迷雾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韦素园去苏联之前就认识了这个女子。1920年夏,韦素园到安庆读书。1921年初,韦素园到上海一所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俄语。1921年夏至1922年夏,韦素园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0年和1921年,高晓岚虽然在北京读书,但假期在安庆,与韦素园也存在相亲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高晓岚是欣赏俄国革命的,如她在《女性与文化的关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三期,1921年4月1日出版)中指出:“俄国的劳农政府,也实行男女平等的条例。……俄国革命,女子立功甚伟,及劳农政府成立,自然有不能不与以平等权利之势。”韦素园去“大革命的策源地”前,可能已经热恋上高晓岚,也有可能热恋的是别的女子,但目前都未发现可靠的证据。爱华的原型,可以认定是高晓岚,但“长沙相亲”的情节可能综合了韦素园与别的女子的经历。
将高晓岚的诗与韦素园散文诗的人事、场景互相比附、印证,找出对应关系,可以看出《“窄狭”》里的黎沙、《端午节的邀请》里的爱华,其人物原型都是高晓岚,两篇散文的确与“非虚构”中的高晓岚与韦素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索隐出所写的“真内容”“真故事”。与时同时,我们必须得十分小心地区分文学的虚构与非虚构的问题,也就是写作的伦理问题。因为高晓岚当时已经跟别人结婚,韦素园采用了曲笔的办法,经过适度的虚构,不能使之完全对号入座。这是一种“不写之写”的技巧,因而不能简单地把黎沙、爱华与高晓岚画上等号,更不能认为描绘的全部就是事实。当然,这种强调并非否定文本和创作主体之间的血肉联系。
(二)读者的误读和重构
韦素园的侄儿韦顺是原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编辑出版了《韦素园选集》,撰写过一系列介绍文章,对韦素园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是韦素园文学作品最全面的读者。但如何弄清韦素园与高晓岚的爱情经历,却成了他久攻不下的难题,一直解不开的谜团。韦素园与高晓岚曾经谈过恋爱,有过诗书往来,是确凿无疑的。但由于双方的书信没有保存下来,加上当年的见证人也都讳莫如深,要弄清他们的爱情真相,并非易事。韦顺很早就注意到了散文诗《“窄狭”》《端午节的邀请》的自传色彩,试图在自己的文章里重构韦素园与高晓岚的爱情经历,但误读也随之产生。
1982年,韦顺在《远志宏才厄短年——韦素园传略》中写过韦素园的爱情,第一次爱情是“早年在长沙,一年端午节,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很漂亮的少女”。“一年后,素园在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国前由安庆去上海前夕,在公园里偶然碰到了她。当素园把即将出国的消息告诉她时,她感到很冒险,便依恋不舍,哭泣劝阻。”“韦素园却晓以大义,并握着她的手说:‘但愿生还再见吧!’他毫不动摇地踏上了征途。”“一九二九年,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了一份期刊,上面有这样的一首诗(韦素园以爱华名义写的那首诗)”,“诗的末尾现出了少女的名字”,“他偷偷写下了一篇怀念的短文,记下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爱情。”韦顺的叙述,显然是综合了韦素园的《端午节的邀请》和李霁野的回忆文字。韦顺没能发现爱华的原型是高晓岚,把虚构人物爱华当作非虚构人物处理。与此同时,韦顺对李霁野的文字进行了改写,作为传记文学可能是允许的,但作为“传略”需要谨慎对待。李霁野在《忆素园》中写韦素园“有一天在公园里遇见一个颇为相似的人”,韦顺将其改写成“在公园里偶然碰到了她”。韦顺生于1929年,其《韦素园传略》写于1982年8月。李霁野与韦素园一起求学和闯荡北京,《忆素园》写于1936年,自然比韦顺的“传略”更为可信。而吴腾凰则直接依据《端午节的邀请》,将爱华的诗写入《韦素园年表》。李霁野的《忆素园》、韦顺的《远志宏才厄短年——韦素园传略》、吴腾凰的《韦素园年表》都属于非虚构文体,对于真实性有着严格要求,但是韦素园的散文诗《端午节的邀请》虽有原型,却属于虚构文体,内含虚构的的成分,两种文体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学逻辑学和范围学的问题。
韦顺在《远志宏才厄短年——韦素园传略》中,写韦素园的“第二次爱情”,便是与高晓岚的爱情,用“高”的声母“G”来代指高晓岚:“那是去苏归国后的一九二二年冬。他寒假由北京回到安庆大哥处度假期间,结识了一位同乡女友G。她是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升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来的女师大),毕业后又回校任教务长的,家就在素园大哥家对面。本来他们经常见面谈心的,可后来一听家中人有提亲之议,就再也不去找她了。其后她公费赴美留学,从国外给素园写信。素园非常兴奋,但回书又很庄重。一九二六年底,G又写信来,并附情诗十首以示定情。这时素园吐血发病,他自料病将不起,深恐辜负了对方的爱情,影响了她的幸福……便毅然斩断这缕情丝。他命芜弟给她写信,一方面说明素哥重病无望,一方面婉劝她另选爱人。”韦顺对韦素园“第二次爱情”的记叙,也参考了李霁野《流落安庆一年琐记》和韦素园的散文诗,与真相较为接近。
2009年,韦顺在《江淮文史》第5期上发表《韦素园的星火之恋》,重新叙述了韦素园与高晓岚的爱情,直接用了“高晓兰”的真实姓名,而没有像以前那样用字母代替。高晓岚已经在1992年去世,用她的真实姓名,韦顺已经没有了顾忌。同时又因为这个原因,《韦素园的星火之恋》有明显的杜撰成分,所叙述的情形与《远志宏才厄短年——韦素园传略》《热血一腔入小诗》多有矛盾之处,《热血一腔入小诗》说高晓岚的诗信,“由于几十年的沧桑之变,未能保存下来”。但《韦素园的星火之恋》却附上了高晓岚的五首诗。2016年4月,笔者托叶集作家黄圣凤向韦顺求证,韦顺说:“诗歌原稿没有了,这五首是当年韦丛芜跟他聊天时背给他的。十首不全。”存疑。《韦素园的星火之恋》说“到了1931年,晓兰主动给他寄了封长信,并附来几首定情诗”,这与鲁迅的记叙不太符合,鲁迅1929年5月就知道高晓岚与别人结婚或订婚了,而《远志宏才厄短年——韦素园传略》则交代高晓岚寄情诗的时间是“一九二六年底”。韦顺在《韦素园的星火之恋》中, 再次写韦素园“两次星火似的爱恋”,“第一次爱情”写韦素园与爱华相恋,“第二次爱情”写韦素园与高晓岚相恋,“1921年,韦素园要去苏联学习。临行前夕,他约晓兰在江边亭子话别。……握着晓兰的手说:‘但愿生还再见吧。’”与《远志宏才厄短年——韦素园传略》相比,与韦素园话别的人,对韦素园说“但愿生还再见吧”的人,由爱华变成了高晓岚。《韦素园的星火之恋》中,说高晓岚母亲“只这么一个爱女”,实际上高晓岚有兄弟五个、姐妹六个,这说明韦顺对高晓岚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
《韦素园的星火之恋》还附上了韦素园的散文诗《别》,但里面的原型是谁,并不能确定。《别》中,虚构的成分与非虚构的成分各占多少,依据现有的材料,根本没有办法考证。我们如果没有掌握对应的材料去证实,仅凭名字,还不能够确认女主人公琼华的人物原型是高晓岚。也没有必要将写作的意义,一定要还原到作者的自传中去。韦顺对韦素园散文诗的主要误读——是把它当作散文来读。真实,是记人散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但是散文诗和散文是不一样的,诗歌是可以允许虚构的,诗歌可以借鉴小说的做法,给你讲个故事,并没有清晰的虚构与非虚构的辨识度。
(三)文体实验的越界问题
从文体上看,《“窄狭”》《端午节的邀请》与韦丛芜1925年发表在《雨丝》上的《春雨》,都是叙事体散文诗,与写真人真事的散文还是有所区别的。韦素园1925年翻译都介涅夫(屠格涅夫)的《门槛》《玫瑰》《玛莎》,色尔格夫专司基的《半神》,契里珂夫的《冢上一朵小花》等,都属于叙事体散文诗。它虽然来源于诗和散文,但在表现形式上已经超越了母体,吸取了戏剧小品、微型小说等艺术形式的特点。韦素园的写作,明显受到俄国散文诗的影响。韦素园的散文诗《春雨》在周作人主编的《雨丝》上发表后,有一位叫静贞的读者写信给周作人,认为“在《春雨》上所写的这位女学生”,和她的一位朋友差不多,她要为她的朋友辩护:
在《春雨》上所写的这位女学生,和我的一位朋友差不多,这并不是强往她身上拉,给她拾骂,实在是有几个相同之点——
一、她是一位女学生。
二、她在现在文学界是享盛名的。
三、他父亲在战舰上服务。
因此,我承认韦君所写的和我所认识的是一个人了。如果韦君是从自己脑里想出来的,不期然而然和我所知道的相同,那么,我这些话就算废话了。如果是韦君是听别人说的,当作实事来发表,我倒要说几句话……
从静贞的描述看,她应该是正在留学的谢冰心的朋友:“她现在已到远方求学去了,这件事她一时未必能知道,我是她底朋友,不能不就近替她辩护。”静贞指责韦素园“用不正当的态度来写”,“用讪笑讽刺的态度来写一个女学生的恋爱故事,这正可表现出来韦先生的头脑太不清楚!”周作人在回信中说:
《春雨》里所说的人,或者是您的友人,或者不是,但我以为这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文艺作品,本来作者并不当作实事写,读者也不当作实事看,即使知道里边的人是有模型的。譬如郁达夫先生的《鸟萝行》中声声口口自称是“我”,但是有人见他问道,“前回贵夫人投水……”,那一定要被人笑为痴人说梦了。韦先生的态度似乎也没有什么毛病,不曾含有讪笑讽刺的意思。或者内多虚构的分子,看去仿佛是在嘲弄,但这实在只证明他所记之不重在实事。……我对于韦先生也有一点不满,便是他不很能运用“玄化”(?Mystification)的方法,容易引起误会。——我和韦先生不熟识,不能替他说明那篇的本意,不过承来信见询,姑就个人所见略为答复而已。(《雨丝》1925年6月8日)
周作人的提醒,对于我们今天讨论文学虚构与非虚构问题,仍然有着重要意义。通过高晓岚的有关材料和诗文,虽然考证出《“窄狭”》中的黎沙、《端午节的邀请》中的爱华,是以高晓岚作为描绘人物的“模型”,但它们毕竟是文艺作品,不能完全当作事实看,“或者内多虚构的分子”。
在韦素园的叙事体散文诗,如《春雨》《别》《“窄狭”》《端午节的邀请》里,文体的界限的确不是十分清晰。散文诗作为一种现代文体是舶来品,其实在引进之初便碰到这样的问题,不很能运用“玄化”的方法,容易引起误会。在韦素园之前,刘半农译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最早汉译,是1918年《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3期)刊出的刘半农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二首》(《狗》《访员》)。这是“散文诗”一名最早见诸中国报端的实证。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意义的散文诗,是由刘半农译介屠格涅夫散文诗开始的。需要注意的是,1915年刘半农曾于《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期),初译屠格涅夫散文诗四篇(文言文,即《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哉愚夫》《嫠妇与菜汁》,韦素原1925年将《地胡吞我之妻》以散文诗形式译为《玛莎》),刘称“余所读小说,殆以此为观止,是恶可不译以饷我国之小说家”,误以小说视之。其实,屠格涅夫的一些叙事体散文诗,有一种特殊的小说味道,只不过如梦如幻的境界,又不是常态的虚构现实或者虚构故事的小说可比,所以更被看作散文诗。刘半农最早将其当作小说看,也是情有可原的。
鲁迅的《野草》中,也有一些叙事体散文诗,深得屠格涅夫散文诗之神髓,无论从情感指向到题材、构思、章法、技巧,甚至语言表达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染有屠氏的印记。鲁迅是一位有高度文体自觉的作家,在《野草》里,进行了多种文体实验。《风筝》《失掉的好地狱》《颓败线的颤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散文诗文本,富于小说特征。
与《“窄狭”》《端午节的邀请》这两篇散文诗相比,《痕六篇》中的其他四篇作品也都是抒情与叙事的诗性结合,从叙事中找到了自己言说的语感和表现的角度。《焚化》可以看作一篇记人的叙事体散文诗。《影的辞行》受鲁迅《影的告别》的影响比较明显,通过“我”与影的对话,影向自己辞别,写出了人被抛入世界的孤独冷清。《小猫的拜访》与“意外结局”的小小说结构十分相似,借与猫为伍,表达自己孤独寂寞的情绪。《蜘蛛的网》写的是房檐上的一个蜘蛛,终日缀网,即使“被风毁破”,却还“永是不息”地缀着。终于一只蜻蜓在网上被蜘蛛噙住吞食了。由此“一个男子”想到他“多年的生活”,觉得蜘蛛有如爱情,蜻蜓就是他,此刻正被缚在这丝网上。他多年想挣脱,却“愈被这丝网束缚”,他悲哀着这蜻蜓的不幸。《蜘蛛的网》通过描写客观对应物——蜘蛛吞食蜻蜓的场景,写出了一种确切、可以印证的,具体而感性的真实:“爱情的丝,也是精细不见的;它是一种透明的光体,永是飘荡在无限的空间和无尽的时间里。”
韦素园在对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译介和阅读中,对其散文诗的小说笔法耳濡目染、深有所悟,并在自己的散文诗写作中有着自觉不自觉的运用。韦素园的《“窄狭”》是一种传记式表达,但《端午节的邀请》确实存在着小说的虚构成分。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的界限在哪里?我们阅读韦素园的散文诗,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不仅散文诗,关于散文能不能虚构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讨论的话题,而周作人的提醒仍然是有效的。一个虚构写作文本,永远大于原型。把一个虚构写作文本还原为对原型的证明,是要小心辨析的。把一个文本的虚构性,还原到它的真实性,更是要格外谨慎。有学者没有经过考证,附会韦素园散文诗的情节和人事,直接将其作为“实事”“史料”写入韦素园的年表或传略里,好像不是太妥当。历史人物的年表与传略,是一种“非虚构写作”,必须坚持对“真实”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