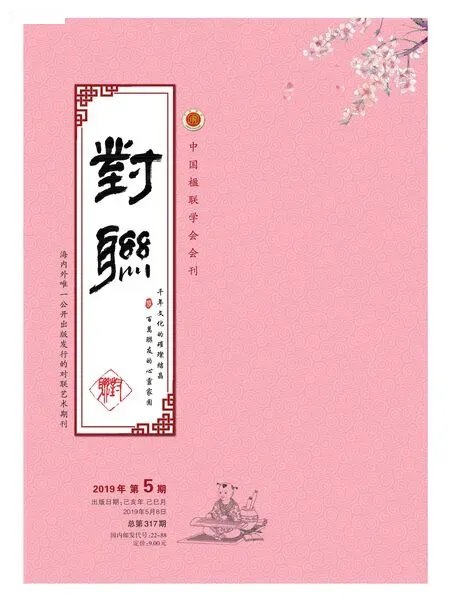对联案头化趋势探究
□陈修歌

一、什么是对联案头化
对联脱胎于民俗活动,长期以来以民俗活动为载体,承担一定的社会功用,目前学界还是笼统地把对联文化归结于民俗文化之中。然而透过对联漫长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对联有雅俗之分,俗的那一部分属于俗文学,即通俗化、大众化,与严肃文学、雅文学相对。而雅的那一部分对联更趋向于案头化、雅文学化。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的基本特性是集成性和模式性、传承性和扩展性、相对稳定性和变革性、规范性和服务性。可以发现,我们在新春纳福、店铺开业、婚寿庆贺等民俗活动上的对联,它们被我们广泛使用并有自己固定的使用形式和场合,其影响远达日韩、东南亚等地区,这很好地印证了这部分对联具有的集体性、模式性、传承性、扩展性等功能,属于民俗化的对联。然而还有一部分对联并不具备民俗化特征,它们被束之高阁,具有极高的文学性,难以向底层群众传播,这部分对联属于案头化的对联。案头化这个词本来是针对戏剧说的,案头化是戏剧创作发展到清朝的一个变化,简言之,就是戏剧剧本更加经典化和书卷气息,就像放在案头专供文人研读的文本,而不是像之前那么下里巴人,也不再适合搬演,更适合放在案头阅读。对联和戏剧一样,都经历了案头化的过程,对联在肇始之初以及后来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形式简单,内容通俗易懂,像刚开始的戏剧一样,文学性不强,更注重表达效果或其他的一些功能。对联作为一种与诗词等韵文学关系紧密、相似度高的文体,必然会受到文人阶层的注意。在对联文化达到兴盛时期的清代,士大夫阶层的文人创作了数量颇多的极具文学价值的对联作品,这类对联中的大部分被置之案头,去实用化,成了供文人雅士玩味、欣赏的纯正文学,不具备民俗的集成性和群众性两个基本特征,属于案头化的对联。
在别集数量猛增的清代中期对联作品当中,有一大部分的对联都应该归属到案头化对联当中。
从对联家的著述中,也可以发现对联案头化分野的趋势,这是对联案头化的一个重要佐证:在谷向阳的《对联入门》一书中,将对联分为三大编,分别是文学编、实用编、谐趣编,在前两类中,虽然文学编和实用编不能完全割离,但是可以看到对联案头化的一个分野演化,它更偏于文学性而区别于对联长久以来自身烙刻的实用性。常江的《中国对联谭概》、刘振威的《楹联学概论》、余德泉的《对联通》等著作,都是自开先河,从不同的角度对对联进行分类。而之所以今人著述中对联分类角度各异,纷繁复杂,笔者认为是因为清代中期大量对联别集的出现,冲击了一直以民俗活动或民俗事务为载体的民俗化对联,这些别集内容丰富,种类繁茂,功能各异,互有交叉,不再单一化,才使后人在分类上难以厘清,各表其家。可以说在文人对对联文化的润色加工下,对联案头化趋势渐渐明朗。
对联案头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大的趋势,一方面是对联创作的案头化,创作目的和创作意图并不为民俗活动服务;另一方面是民俗化对联的案头化转变,一部分民俗化对联失去民俗功用:被更新替换或随民俗活动退出,因为具有一定的价值被人们收编成册,这部分对联可能会被永远置之案头,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重新被张贴悬挂出来,那它就从案头化走向了民俗化。比如一些景观联,人们的创作目的可能只是自我欣赏,被收编在文集里,后来读者觉得这副对联悬挂在某处正合适,于是将其单独摘出来,这副对联就与名胜景观融合成一体,走向了民俗化。因此,我们判断一副对联到底属于民俗化对联、还是属于案头化对联,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准确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非甲即乙,甚至难以找出清晰的界限,只能说案头化是对联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对联在千百年间自身的分野,而不是对联固定的某种分类。
二、对联案头化出现的原因
1.脱离载体—— 民俗活动
对联在肇始之初,就是作为民俗活动或民俗事项的附带品出现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性:新春兆福、婚寿庆贺、哀丧吊挽、记录事件、宣传教化等,依赖于民俗活动为载体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进入清代以后,文人们创作的大量对联不再需要依附于民俗活动,它们被集结成集子,放置案头,如同韵文学一般,这些对联文学性很高,分类繁复。比如文人创作的激励自己或他人的格言联:
学问多自虚心得;
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类对联很少会应用在民俗活动当中去实用。再比如被悬挂在亭台楼阁的风景名胜联,当它因为更新景区设施等原因被撤换的时候,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载体,走上了案头。比如在抗日时期,日本侵略军飞机几度轰炸苏州,享有『江南名园精华』的拙政园远香堂受震破损,南轩被焚毁,园内亭阁倾圮,随之一炬。部分名联没有再悬挂出来,而是收录进了对联集子里,走向了案头化。
从古至今有很多民俗活动都已经销声匿迹或者被简化,比如『七夕斗巧』『画九九消寒图』等等。油坊、梳篦店、砚店等在古代寻常巷陌里经营的商铺如今已经在大街上难寻踪迹,而与它们共生的对联也再难见到,比如油坊的:
欲把名声充宇内;
先将膏泽布人间。
梳篦店的:
兰陵妙制工镂月;菱镜新装助掠云。
这些对联失去了载体,随着收编整理进入了历史,也就走向了案头的方向。
2.文人的创作参与
对联文化从『俗』到『雅』离不开文人的创作参与,这也是对联自身发展的需要。一般认为,五言、七言对联来源于律诗,而杂言对联来源于魏晋骈文体,程千帆认为字数不等的长联由骈文中分化而来,白化文则认为早期的对联是骈文和律诗共同影响的结果。骈文在清代一度蔚为大观,清初毛奇龄、陈维崧的推崇使骈文创作兴起,为对联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从对联的发展历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统治者的重视,比如写出第一副春联的后蜀国王孟昶,第一次提出春联并要求百姓张贴悬挂的明太祖朱元璋,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也都亲自写过不少对联。统治阶层的重视,就会引起民间尤其是文人阶层的上行下效。清代涌现出了一大批联家,有对联集子传世的清代对联家就有三百多位,比如文焕的《对联》、俞樾的《对联录存》、何绍基的《对联集帖》等等。文人阶层的创作参与,极大地丰富了对联的内涵,对联从『俗』变『雅』,内容和形式上焕然一新,衍生出了对联创作的诸般规则,抬高了对联创作群体的要求,也提高了对联文化的艺术水准,文学性大幅提升,但也导致曲高和寡,失去大量底层群众的支持和传播。
对联的案头化进程类似于戏曲、竹枝词,比如竹枝词的原型是各地民歌,尤其是表达爱情的民歌,后来被文人阶层加工改造成竹枝词,一开始形式上只是七言四句的体式,韵律上无须那么严格,语词上带着些民歌情韵的色彩,比如唐代刘禹锡的『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山桃红花』属于典型的四平头,不合格律要求,在其后逐渐发展完善的竹枝词体式中,竹枝词逐渐演变为固定的七言首句入韵式格律创作规范。或许民歌已经不再传唱了,但是负载着民歌自身情感的极具文学价值的竹枝词却收编在册流传了下来。
3.对联自身内蕴提升的需要
早期的民俗化对联都是俚俗的,通俗易懂而且没有严格的平仄韵律,比如祭灶仪式上出现的:
上天言好事;
回宫降吉祥。
『上天』与『回宫』作为上下联相对的节奏点,『宫』处应为仄声字。随着对联体系的发展,这副对联衍生出了:
上天言好事;
下界降吉祥。
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
等版本,这不得不说是对联规范的逐步完善。这副对联经过改造,实现了民俗性与文学性的兼美,千百年来,绵延传承,一直活跃在大众的视线当中。
对联文化要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必须进行内蕴(语言、修辞、格律等)的提升。对联的案头化趋势也使民俗性的对联文学价值剧增,更好地在民俗活动或民俗事项中发挥价值。对联创作逐渐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创作规则、艺术手法的限制带动了民俗化对联创作的程式化,对联文化的内蕴在文人的助推下实现了升华。不同场景的民俗对联,内容、意义、功能也会各不相同,比如晋商大院里的对联能够体现晋商精神,往往是经世致用之联;寺院悬挂的对联,往往体现佛教经义,悯恤众生疾苦,劝人向善;风景名胜对联则是播扬此地名胜之美誉。这些比较著名的民俗化对联,往往是由文人创作的,甚至是从案头化对联演变过来的,艺术价值都很高,与普通的民俗仪式上的对联有区分之处。
结语
对联案头化的趋势大致从清代初期开始,清中期形成,一方面是对联创作案头化,大批文人参与创作,创作目的并不为民俗活动或民俗仪式服务,更多的是像创作诗词一样,放置案头陶冶性情;另一方面是民俗化对联的案头化转变:对联从民俗文化中诞生而来,在发展的过程中走上案头化的分野,与此同时,一部分案头化对联走出书本,走下神坛,被大众所熟知并承担起一定的社会功用职责,这部分案头化对联便转化为民俗化对联,在带有民俗化特征的同时,其自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始于民间,又回到民间,生生不息,持续传承。之所以会出现案头化的分野,前提是对联脱离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载体—— 民俗活动,开始去实用化,走向案头;最重要的是上层文人的创作参与,使对联化俗为雅,增加了文学性和经典化;结合其他文体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也是对联文化自身内蕴提升的需要,对联的案头化趋向为对联文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民俗化对联与案头化对联之间有着一定界限,但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案头化对联如果开始实用于民俗事务、节日、场合、景点等,就可以认为是复归民俗化;民俗化对联失去载体的支撑,要么消亡,要么趋向案头化。二者之间又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对联的民俗化有利于对联文化的传播,而它的案头化则促进了对联自身作为一种文体的内蕴提升,因此对联的民俗化与案头化有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关系,二者共同促进对联文化的发展。
【注】
[1]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一版。
[2]刘太品、谷向阳《对联入门》[]M,北京:中华书局,二〇〇七年版。
[3]数据来源于张小华博士论文《中国楹联史》。
[4]刘禹锡《刘禹锡集竹·枝词》其[四]M江苏凤凰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

陕西省宝鸡市宏文路2-8号报社美摄部 上官守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