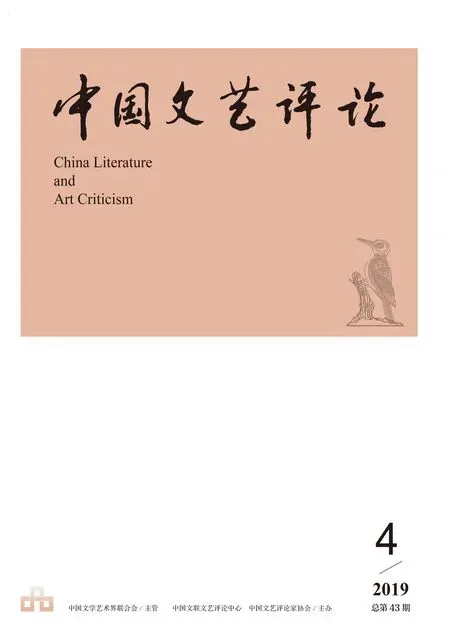叶锦添的东方美学思想探析
张郑波
凭借电影《卧虎藏龙》获得2001年奥斯卡“最佳美术设计”和英国影艺学院“最佳服装设计”奖的华人艺术家叶锦添,提出了“新东方主义”设计理念,并用三十余年的跨界设计实践,包括电影《夜宴》《赤壁》《风声》《一九四二》和电视剧《大明宫词》《 橘子红了》《红楼梦》等服装及造型设计指导,向全世界展示了现代东方主义视觉景象的独特神韵。无论是舞台剧的服装道具设计,还是影视剧的服装造型美学指导,抑或《繁华》《留白》《神思陌路》《〈赤壁〉美工笔记》等文学创作,均从不同角度进入东方意蕴深处,为观众捧出颇具现代感的古中国风审美意象(简称“古意”)。围绕他的几乎所有汉语题材视觉艺术创作,“他都试图向着这个靶心射击”,直至打磨出柔美生动的东方气韵。
一、“东方主义”等概念辨析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是指研究东方各国的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总称。在“东方主义”范畴中,“东方”包括中国、印度、近东、非洲和拉美等被称为“第三世界”、被烙印着“殖民地”文化印记的总称。“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演说:“他们(东方)在现代世界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仅仅因为那些强大的、现代化的帝国有效地使他们摆脱了衰落的悲惨境地并且将他们转变为重新焕发出生机的、具有创造力的殖民地。”“东方人”被称为“臣属民族”,帝国行政官员克罗默更是认为“东方人永远是并且仅仅是他在英国殖民地所统治的肉体物质”。可以说,“东方主义”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知识体系中,被构建为一种异质的、愚昧的和“他者化”的思维形象。
对此,第三世界的后裔萨义德予以强力反驳。他认为“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习俗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为悠久”,有着自身的历史、文化、思维和意象等体系。西方“不怀好意”地构建“东方主义”,旨在人为划定“西方”和“东方”,并于两者之间设置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进而“扬西、抑东”地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同时“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这种处理东方的机制和君临东方的方式,明显带有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并且,其构建方式是认定式、驯化式的,“东方是被‘东方化’了的”,具有较强的主观臆断性。他甚至借用基尔南之辞称之为“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认为由此构建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必然带有偏见性,尤其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可见,萨义德在据理力争地为“东方主义”进行解构。因此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学界众多讨论,促发了此解构主义的广泛化和纵深式推进,但仅停留于“解构”和“辩驳”,并未有实质性内容和形式的规范性建构。
叶锦添开始构建东方风格的国际视觉形象。他认为“殖民国以好奇与猎奇的态度认识东方,又以占领与掠夺引发了战争与征服,使东方的文化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产生断层、扭曲与变形”,落入西式文化范畴和价值逻辑框架,成为其文化奴役和界定的附庸。他不满东方国家“仍然被框定在‘东方主义’的学说里,被当作世界文化印象的边陲地带,被认知、辨析与重组”。为了让西方乃至全世界认识到“东方”在现代时间坐标中的位移和新的变化,就必须实现从西方化到东方特色的有力反转,寻找、把握住自身的文化根脉与精髓,重塑“东方”在世界文化中的新印象。这并非是古典的复制、再现,而“是一种经过系统的整理与创新,逐步形成的一种有机的重生,而且自然而然地融会在今天与未来的讯息之中”。
二、回归“原初信念”和“心灵本真”,寻找东方文化之根
叶锦添说:“在欧洲,我感受到某种发自个人内在的不安。我们已经失去西方一直信守的深厚文化信念,对于固有美好的一切和经过累积而流淌着浑厚的永恒感,产生了断线的苦涩。我们的文化零落断裂,贴满了毫不相干的标签。回头之路,仍不可见。”对于这种文化失根的不安,他不断朝古代东方智慧源头探思,尝试从宗教中汲取“原初信念”和“心灵本真”,激活东方智慧创生机制,对抗精神的飘零和迷失。
东方宗教思想底蕴深厚,并对西方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东方印度教与佛教,禅宗与寒山子,重新影响了西方这一代年轻人,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智慧里寻找心灵的慰藉。禅学以简约主义介入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化……东方对于精神、心灵与身体的原始观念,通过瑜伽、东方武术,发展出与某种精神记忆融合一起、诠释古代智慧的另一个模式。”这股宗教思潮潜流到西方,不仅影响了某种西方的超感思维,而且坚定了我们对东方宗教哲思智慧的自信。
叶锦添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返回到佛教、禅学和道家思想中寻找智慧的根源。他在佛教中参悟虚实并存的关系:“佛教的宇宙是虚空,而不是西方所描述的那个神谕实证的世界。虚与实并存成为佛学的重要领悟。它所呈现的东方精神,是人类相对于自然,虚相对于实相所产生的空净与空无”。他在禅学中感受到了“空”的万有动力,“从六祖慧能悟道以来,在禅学中我们可以碰触到一个统一的世界,生死的界限模糊,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有此时此刻,那是宇宙概念的唯一说法。它包藏万有却空无一物,把一切有情世界纳入梦中。奇妙的是,禅的‘空’却产生了万有的动力”,并认为这是泛亚洲文化的一个动人特色;在道家思想中,他领悟到了“有无相生”(《道德经》第二章)和“虚无”的无穷作用:“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第四章),“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五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第十一章)。他感受到中国空间筑居内涵着“一种叫无用,就是无形”的虚置设计思想。
由此可见,虽然这些宗教、哲学的主要思想不同,但它们具有共同指向性和内在一致性。有无相生、虚实并存和虚空的无限衍生性,便是叶锦添从中淬炼出的核心要义。从他的众多创作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核心要义的无限孕育力,可以感受到虚空的恒定和派生意象的变幻莫测。“当我更清楚这些内在形式的意义后,我发现,不论你做什么,都有一个东西是跑不掉的,它可以有多种形态,但终究它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变的。”这种“本质”他称之为“本源”:“很多东西都是来自本源,却往往发展出不一样的结果,产生出很多独立的存在物,我觉得艺术就有这种多样性变化并存的性格。”之于艺术,他认为“留白从空虚中成为母体,虽然是空,但却十分真实”,“留白象征着空的力量,画面里的空象征了隐藏,甚至是无限的可能”,因此,无论从哲学思想层面还是艺术表现层面,都要抓住促生“无限延伸、无限可能”的本源与空无力量,它将“与现实意外的多维世界交流,产出生生不息的精神素质”。
叶锦添以此作为美学设计思想指引,在他者文化中得到了自我解脱,塑造出了一种东方文化印象,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与欧美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感性归属,使无根之心得以重新安放和滋长。
三、解蔽“古意象”,构建东方文化之体
叶锦添童年时期非常迷恋梅兰芳妩媚妖娆的侧面剧照,他说:“那种神秘感、魅惑感,使我不断回溯源头、寻找养分,好像只有发现的喜悦,才能满足我少年的心,去对抗他者文化的占据。”正是这股“对抗他者文化占据”的执着和使命感,使他不断深入东方千年文化的腹地,“深入古典的世界,去寻找那种丰富而独特的养分,重新建造自己的语言体系,传达一种深邃、丰富、变幻闪烁的民族精神”,只有打开这道“东方”的意象法门,才能在世界文明中保持东方文化的个性,这是超越手法、材质和符号等之上的一条文脉。并且,他未停留在经验认知层面的追问和抽象的观念思辨,而是将东方古意融入到了自己的设计实践之中,同时,主张将这种形而上的思想推进到形而下的物美设计诸领域,转换成现代化可视媒介物象,从建筑园林、服装造型、家居器物、影视舞美到雕塑装置等方面全方位地呈现东方视觉景观。
叶锦添“热衷古典范围”,“对古典美有独特的情感”,那么,“古典是什么?是音乐、韵律、和谐的节奏,还是赋予情感和温度、流畅的线条?不同生活的脉络,使我看到很多超越想象的细节”。可见,他并未为“古典”设立一套既定的范式或标准,也不赞成将其具化为节奏、线条抑或色调,甚至不单纯拘囿于东方。他认为,应是蕴藏在历史脉络中的一种文化印象。东方古典内聚东方气韵,外显古审美意象。我们要恰如其分地“探内”和“采外”,为“东方”注入古典灵气,令观者心神为之震动,进入神思、冥想状态。叶锦添将此灵气称之为“神”,且看他是如何在古典范围内游走打造东方神韵的。

图1 《赤壁》剧照
他追求复古主义,首先必然是向着复古的方向挺进。拍摄《赤壁》时,为了构建一种近乎史实的三国世界,“筹备初期,我们利用大量时间搜集数据。每天与不同层面的专家交流,希望能呈现最接近真实的历史,内容包括史实、建筑、军事、政法、兵器、服装、民生等各个方面。”不仅如此,“在他们军事的分组与服装的考究上,皆以出土文物、有实物见证者为先,其他兵器、旗阵与战船等道具也都经过严格的考证”,并且,为了更好地重现三国的历史质感,他还认真、严谨地深入研究了诸如铠甲缝制、古兵器制造和徽号分野等细节内容,让观众无论从宏观的大山大水,还是细致入微的针线缝制,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三国争雄之气势。

图2 《长生殿》剧照
再有,叶锦添认为,正统的传统表演应保持传统,比如京剧、昆曲等,有其独特的韵味和程式化表演,他会小心翼翼地守护属于它们的传统印象。以《长生殿》为例,除了适度调整色彩、造型以更好地融入昆曲连绵、迂回和含蓄的韵味之中外,“其他如翎子、水袖、髯口、甩发的突出技术,则全依古法,保留了原本的风貌”,在舞台空间设计方面,“以一桌二椅及‘出将’‘入相’构成整个舞台的传统空间关系……全力寻回一种古老的表演模式,抗拒切入一切现代舞台的观念”。但这种“抗拒”不是“晒古董”,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唯古是崇”,而是某种传统艺术形式的特性使然。
还有,叶锦添并不主张“全然传统”,他表示,“全然传统的做法徒具形式的模拟是不合时代的”,需要在坚守传统意志内核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这种突破不是改变,而是一种创新。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把东方古典之美与现代性品质有机融合,扫除具有年代感的“古典”“传统”在现当代社会传播的疏离性障碍,令观者在饱览视觉美感盛宴的同时,更愿意、更容易拥抱传统之美。比如《卧虎藏龙》,故事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这一历史时期的北京城是繁杂的、艳俗的,但叶锦添有意“去掉最抢眼的清朝青花瓷、王府大门的彩绘与红柱子,洗去整个京师的色彩浓度,隐藏颜色,使它空间化”,为演员出场提供一个简约场域,为整部电影提供一个意象空间,强调他们在其间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语。
服装造型设计也是如此,“先做出唐朝衣服的‘形’……再抽掉整个细节如刺绣、颜色等,以素面呈现整个形态”,从视觉效果上,能够更加清晰地捕捉人物的肢体语言和内心声音而不被干扰,尤其是李慕白和玉娇龙在竹林中穿梭打斗时,衣服均被洗褪为米白色,轻盈、飘逸,侠者之风、不安之心在无垠翠绿中“被逼”得无处可藏。另外,为让演员摇曳出南管戏的婉约、清雅之美,他同样“把所有服饰细节处理为简约的线条”,再配以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古董发饰与配件进行诠释。笔者认为,抽掉这些繁复、累赘之物,更能传递出一种兼具古典与简约的美感。吴兴明先生将其称为“现代感”,“所谓 ‘现代感’,不过是在价值三维(功能、物感、意义)中最大程度地删除了意义的维度,物感由于意义的删除而凸显”。

图3 《夜宴》剧照
在《夜宴》中,叶锦添则用中、西古典主义“叠加”的方法,“探索将西方戏剧元素诠释在东方电影中的可能性,我尝试把两者放置在一个陌生的地带——古典。……在这种氛围里,我们寻找两者在古典上的定位。”他调配出了一种含有莎士比亚味道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偌大的黑色空间、黑红高贵华服、兽形图腾和神秘的面具等,这种“叠加”的古典必然是极为厚重的。这时,他运用中国山水画“疏密相间、虚实相生”的技法,打造了一座隐于竹海中的艺馆:那是另外一种充满禅意的古典风味,“竹、水、风、人,围绕在一个场域内,形成了一个磁场”,风中有竹,竹中有音,山、水聚集着灵气,王子等人着白衣、着白面,唱舞着凄切的《越人歌》,意欲远离尘嚣,使得一股清冽之气穿过“厚重”飘浮其间。这种冒险式的三重“古典”叠加令观众耳目一新。此外,《昭君出塞》《红楼梦》等,叶锦添同样秉持“发觉传统与创新并不矛盾,未来的发展亦必以双头并进为重,两者互为表里,各司其职”的理念,推进着他的东方文化形象塑造实践之路。
另外,除了挖掘古意、创新古意,他还总“迫不及待”地将古意融入到影视、舞台剧等艺术形式之中。以京剧元素为例,在电影《诱僧》中他特意选用京剧脸谱(从“金脸”到“素脸”的转变)这一媒介物来隐喻主角石彦生的人生起伏跌宕,权倾一时——失去身份——遁入空门,因为他认为,由于戏曲艺术的需求而产生的色彩与线条、图案与肌肉表情的有机联结,京剧脸谱会有“一种对东方艺术的神秘领会”;创作舞台剧《楼兰女》时,也是以传统京剧作为主要形象的母体,在此基础上进行延展;舞台剧《十面埋伏》“底子是现代舞的底,却在引发京剧传统艺术的介入”。
总之,叶锦添在重新凝视传统美时说,“找到一种可以连接古今的心境,而不断将其翻新,建立新的神思时代,追溯它的模型,达到那种共同的骄傲感与归属感。”这大概也是他重塑“东方”时坚守的一种心境。因此,我们要始终保持一颗寂静空灵的心,自在地回到古意象世界,而不受任何既定观念的干扰,完全自我舒展地去感受每一个美的瞬间,从空无的角度去重新发现古意的玄妙趣味。如此一来,纵然东方文化在西方现代性历程中被冲刷解构,或说被西方哲学社科体系支配过很长时间,但只要把握住这股原动力,定会驱动“古意”重新绵延开来,绽放成“东方”视界形象。
四、后现代拼贴措置,重塑东方文化之形
叶锦添重塑的东方文化没有政治意义上“东方主义”那么霸道,它是开放性的,可兼容他者的。这与他开放的美学思想、人文情怀不无关系。“我努力去寻找世界上所有文化的根源,脱离狭隘的民族情结,开放地面对这个世界,而不是甘于定义下的反派。一旦脱离强烈的自我意识,大量吸纳种种资源,再重新潜入自身的文化底蕴中,反而可能在各种系统下带来新意。”可见,他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东方文化根源的同时并不排斥他者文化,而是主张万物皆为我所用。
在追溯过程中,他发现“在传统的古代世界中,真正能遗留下来的也只有碎片,它意味着不完全,以及需要不断推敲和无法定论的结果。因此,碎片成了追溯远古的论据”。对于叶锦添,这些碎片犹如上古时期的龟甲、兽骨,带着各种神秘的文化符号进入他的脑海,在这个晦暗、虚无的空间里不断蓄积、发生联系,然后,他“开始把碎片转化成整体,又从一个整体的印象中,开始寻找它分裂后产生的各个片段所蕴藏的可能性。……都会产生意想不到又肌理分明的意象。”如此一来,不仅碎片复活了,而且还将呈现出无限可能和带来意外的惊喜。
这种“无限”和“意外”,不易产生西学惯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伊始,欧美艺人大多采用立体透视法对“意象”的某一面向实施对象化清晰研究。虽然,自摄影技术诞生、印象派和包豪斯功能主义以来,对立体透视法有了颠覆性的反思批判和艺术创新实践,但传统惯例机制的顽固性仍然左右着西人习惯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对象化思维,固然能让局部变得越来越清晰,但也越容易陷入单一向度、单一层面物的视角自负,或者说停留在主体单向度视野的自我封闭中。时间久了,就难以觉察到这种单一视角的局限和清晰化造成的认识偏见、视野区隔,而忽视错综复杂的整体关联性。叶锦添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他走的是一条“去特征”“去对象化”的路,打破既有格局,扫除带有规定性、确定性的和形式性的障碍,将僵化的逻辑形式、知识语汇及感知模式撕裂开来,让意象的内在肌理结构敞亮开来,通过拼贴措置重新组合成新的形象。
叶锦添甚为推崇后现代主义舞蹈家皮娜•鲍什和编舞大师彼得•布鲁克,就是因为他们都善于应用重复、疏离、蒙太奇拼贴措置来创造个性化艺术风格。皮娜•鲍什能拼贴各类舞蹈动作,她能将芭蕾、欧式现代舞、美国街舞、亚洲民间舞乃至日常姿态语言有机勾连起来,在摒弃传统单向度的唯美技巧中,表达现代人的都市情感经验。彼得•布鲁克在拆解分化与空间错置中,将神圣与粗俗、僵化与灵活、残酷与温馨剧场错置勾连起来,让观众瞬间体验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贝克特、肯宁汉乃至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剧场意象。

图4 《楼兰女》舞台剧照
叶锦添也用后现代拼贴措置手法进行了大量实验与实践。他为舞台剧《楼兰女》设计服装造型时,采用东西合璧剪裁的新方式,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带骨架的大裙子上,又加入了中国式的大袖子”,“以传统京剧为主要形象的母体,延伸到西方宫廷华美的巴罗克风格、前卫的歌德、意大利的威尼斯面具舞者和日本古典传统的文乐剧人偶,并渗入了现代前卫舞蹈形象,而这些元素在瞬间中和,成为体积庞大的文化复合体,富含指涉性的象征意味。”他在错综复杂的文化中大胆尝试与冒险,将多种文化个体进行转换与拼贴,却意外地突破了各种界限,创造了一个多元、开放的新母体,并包含着衍生出无限创意的可能性。
舞台剧《罗生门》也是一次东西方文化元素融合的实践,叶锦添说:“在衣服的裁剪上,我保留了京剧里的水袖,但在外袍与裙摆间却运用西方的剪裁,起到了大开大阖的移情作用”。在与德国舞台设计师安得瑞克斯合作创意设计瓦格纳歌剧《崔斯坦与伊索德》时,又带入了东方神秘主义色彩。此外,在设计《艳歌行》《俪人行》《荔镜奇缘》《梨园幽梦》等舞美作品时,也秉持“碎片化-拼贴措置”的理念,先让碎片化的服饰、动作和道具等游离起来,再将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乃至非洲、拉美印象带入当下舞美设计的神思空间,由此连成内含新素材、新角度的“东方”写意画面。于是,诸如印度史诗剧《摩诃婆罗多》的深邃悠远与形幻绵密,《后山海经》的诡异妖艳与绚丽巫风,《十面埋伏》的幽道梦魅与沙场离魂,《红楼梦》《牡丹亭》的鬼魅幽影与孱弱柔美等东方美感品质的出场,均可领会到古今中外“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与极浦书》)意象感拼贴措置后的奇妙效果。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的拼贴措置,不是简单的媒介拼凑或符号混搭,而是像中国古人那样于“形神兼备”中完美营构当下东方式错置印象。中国古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注重先验性认知、客观本质和精神超越性探索,而倾向于沉浸在“有无相生”“虚实互补”“神思妙悟”等精神状态中。因此,“东方”意象创构应为庖丁解牛式“不以目视而以神遇”的“以神接物”法,用心神领会意象之物,沉思于“物”的整体结构和脉络肌理,沉浸于“物”之周遭气韵,聆听“物”之关联性的静谧声音,深入“物”所从属的历史生活场景,在传神领会中让“物”灵动鲜活起来,充盈在心窍灵府之间。
五、借用数字媒介,传播东方文化之象
随着“世界图像时代”与“比特信息时代”的到来,数以万计的讯息、图像和视频等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不间断地冲击着人们的感官神经系统,让每一个关联者都进入了一场场“自始至终全然匿名或使用假名的游戏虚拟空间”,不仅令每一个参与者深陷其中无以逃离,而且深刻地左右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理解与判断。
在这种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叶锦添认为,东方人借助电脑、影视、媒体等硬件设备和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等,在较短时间内获取了大量知识,获得了精神娱乐满足,但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出,“这易于引入另一个由西方建立的虚拟世界,渐渐又大面积取代了各地原来的空间文化”,而“第三世界的年轻公民已被教育成先进城市国家的外围文化道场,只提供吸收与传播的功能,成为延续市场,没有自主性的发言权”。如此一来,必将导致东方世界出现一种“文化失根、形象失源”的危机现象。失根,将失去东方文化的话语权;失源,将无法抵抗西方文化的移植。对此,叶锦添也曾有过漂泊感、空洞感体悟。但他上下求索,执着、坚定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归属。他的落脚点“落”在“旧物”。
他认为,新产品没有旧物的时间深度,“在旧物中吸收时间质感的味道,那黄金岁月留下更精致的手工艺,在先进文化中重新使用旧物令这种回忆的温暖重生”。于是,他重返“旧物”历史场域,萃取东方古典神韵与意象,成功打造了诸多东方文化形象作品。他知道,如果仅止步于闷头打造而不去传播,一切努力将成徒劳。如何将“精美的木偶”变成“皮影戏”,令观者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表演的快感之中,进而感受其中的艺术魅力和东方文化底蕴,才是其创作努力的真实用意所在。叶锦添一直在探索通过电影、电视、戏剧和歌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借助先进的数字媒介技术,逐步将东方文化形象传递到国际舞台上,敲打东方人逐渐被西化的神经,以唤醒其民族意识与精神,重塑东方文化魅力和艺术感召力。
作为“新东方主义”的提出者和践行者,叶锦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目前,其探索范围虽主要为古典中国风审美意象,但所构建的“东方”美学设计思想体系将成为日韩、印度、泰国等东方国家进行本地古典文化挖掘与创新传承的重要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