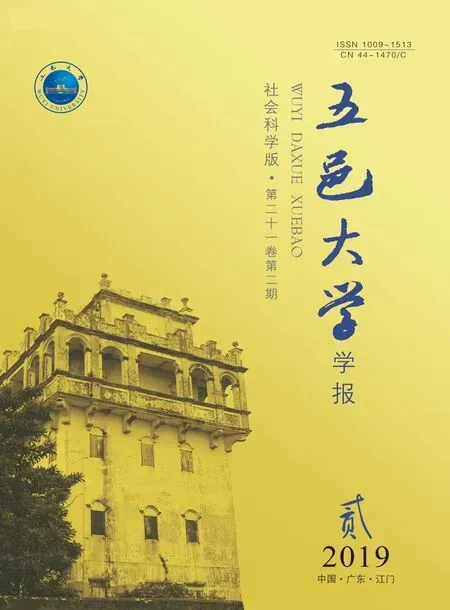论谭宗浚早逝之成因
徐世中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303)
谭宗浚(1846-1888),字叔裕,广东南海(今广州)人,为近代岭南著名学者谭莹第三子。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授编修。光绪二年(1876)八月督学四川,八年(1882)六月又担任江南乡试副考官。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功臣馆纂修等职,因伉直为掌院所恶,出为云南粮储道,再权按察使。后引疾归,卒于途中,终年四十三岁。著有《希古堂文甲集》《希古堂文乙集》《荔村草堂诗钞》《荔村草堂诗续钞》《芸洁斋赋草》《辽史纪事本末诸论》《皇朝艺文志》等。
谭莹是近代岭南著名文学家,其所作骈文深得时任两广总督阮元赏识。而谭宗浚“少承家学”,加之“聪敏强记”,故创作骈文时往往能 “下笔千言”[1]。其十七岁赴京应试途中所作的《览海赋》一文,因其“俯仰时事,凭眺山川”,“凡数万言,都人士交口称颂”。“迨通籍后,声誉益大著,硕德名臣,争以文字相结纳”①。他的骈文前期呈现出“绚烂”风格,后期则转为“平淡”。其诗也能做到“醇而肆,不名一体”[1]。由此可知,谭宗浚不仅以骈文著名,而且其诗也自成一家。
相较于其父谭莹七十二岁寿命而言,谭宗浚可以说是早逝,而学术界对其早逝的原因却甚少关注。笔者总结,谭宗浚的早逝,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 理想失落之苦闷
对于谭宗浚自光绪八年六月充江南乡试副考官后的任职情况,唐文治在《诰授中议大夫云南粮储道谭先生墓表》①有如下记载:
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功臣馆纂修、本衙门撰文、起居注协修、文渊阁校理。庚辰癸未两科会试磨勘官、教习庶吉人。乙酉,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初,尚书吴县潘文勤公祖荫总裁国史馆,嘱先生纂修《儒林》《文苑》两传。先生博稽掌故,阐扬幽隐,方脱稿而简放云南。
在京城翰林院任职期间,谭宗浚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获得坊局,以便整理自己的著作。如在《于滇日记》②,他有如下表述:
先是余在翰林,资俸已深,计今年可得坊局。曾向掌院力辞京察,而掌院徐桐必列余名。或云徐公有意倾陷,故京朝官多代余惋惜者。其实京官、外官皆朝廷雨露之恩,余亦何敢稍为歧视。惟是京官已为熟手,外官诸多未谙,且近年著述粗有端绪,今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将来拾遗补坠又不知何时,此则余所耿耿不忘者耳。
徐桐为当时朝中守旧派代表人物,向以反对西学而著称。谭宗浚认为自己出任云南粮储道,就是因为徐桐嫉妒他的才华与不满他刚直的性格。在《旋粤日记》③中,谭宗浚对此有进一步说明:
余在词垣,素不欲外任,为东海徐尚书中伤忌嫉,强以京察一等保送。乙酉五日,遂拜督储滇南之命。
由于理想的落空,谭宗浚心中极度苦闷。这种抑郁的心情,可从他的部分诗歌和日记中得到印证。如在《出都口述》②中,他抒发了如下情感:

在诗中,谭宗浚揭示了自己当时身陷迫害而朋友想帮他却无计可施的情况,诗心一片苍凉。类似的诗歌,在谭宗浚的《于滇集》中还有很多。故谭祖任在《荔村草堂诗续钞跋》④中总结说:“维先君以不乐外任致损天年,其郁伊牢落之慨,一于诗寓之”。
除了诗中表达这种抑郁心情外,谭宗浚在《于滇日记》中也一再流露出这种情绪,如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云:
三更后,北风如虎,颠簸异常,念眷属今日方过福州洋,猝遇此飓风,必遭惊怖,为之辗转不寐。吁余以薄祐被遘谗人,远宦边陲,妻孥阔别。每见船中长年三老辈,犹得篝灯促膝与孩童稚子戏谑为欢,胜余辈多矣。
再如同年十一月初三日的日记记载:
嗟呼!鸣钟落叶, 逐臣所以伤心。黑塞青枫,骚人于焉殒涕。仆也见谗彼妇,远涉蛮荒,悽闻巫峡之猿,愁对长沙之鵩,得不衰同楚些,怆甚越吟也耶?
长期的抑郁苦闷心情,会导致他饮食、睡眠等方面问题,自然会给他的身体带来伤害。
二、 旅途往返之艰辛
我国西南边疆的滇黔桂地区,自古重山盘郁,交通闭塞。这种状况在清代同光时期仍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变。谭宗浚到云南任职,在由湖南至贵州这段路程中走的是水路,到了贵州后改为陆路。至于入滇途中的具体情况,谭宗浚在他日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如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日记:
晴暖。行廿五里许,至团山外一沙滩宿。晚二更前,飓风大作,黑云如 盤。遥闻波涛汹涌,翻簸之声,令人震駴,我舟为风所撼,搁浅在沙滩下,幸得无恙。至五更,刁调犹未息也。……每诵东坡诗,我生类如此,无适不艰难,为之流涕,意造物以余性乖戆,宦海风波或未深悉,故以此尼其行耶?
日记中谭宗浚不仅形象描述了这次旅途中台风肆虐的场景,而且还据此联想到人生的风浪,徒增几多感慨。再如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日记云:
阴寒,无雨。晨过大恶滩,惊湍骇浪,已足怖人。午过柑子坳、乌龟滩、王八滩、打卦滩、白猫洞滩、老猎洞滩,滩均峻驶。……最后为满天星滩, 黄石滩,滩喷起数尺,如云际梯,中含长风,内盪高壁,鼓櫂前进。殆疑溟波飞扬簸摇,震駴颠眩,生平所未睹也。土人复筑鱼汕其上,累柴石为之,致使水益怒猛,行旅至此,多断篙折缆之虞,此亦斯土者所宜属禁也。
以上几则日记表明,由湘入贵再到云南,沿途滩险风急,谭宗浚可谓是历经重重磨难。
旅途之中,谭宗浚不仅经历有恶风险滩,而且还遇到饮食与住宿问题。《于滇日记》中,他也作了详细说明。如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记云:
是日,路荦确而泥潦又多。晚宿贵定县,县有行台,为一新任豪令所踞,余寓破店中,溲溺纵横,如入鲍鱼之肆。
再如同月廿九日日记记载:
清晨,大雨如注。……沿路层峰叠岭,屡转不穷,泥滑途敧,舆夫屡踣下山视所行处,几在霄际矣。……晚抵贯子窑宿。居人墙壁颇峻整。惟街衢及房室均溲溺纵横,如入秽人之国。晚所居店,尤垢浊不堪。虽焚迷迭之香,浥蔷薇之露,而秽气未尝少减也。村中竟无白粲,仍煮面食之,已数日矣。
可见,整个旅程既让谭宗浚惊心动魄,又让他寝食难安。
光绪十四年二月,谭宗浚因病情加重而辞官。返粤途中,他遇到的困难与他赴滇途中情况差不多。在《旋粤日记》中,谭宗浚对此也作了许多描述。如光绪十四年二月廿三日日记记载:
晴寒,大风。晓行里许,即登大坡,盘折而上,至阴凉箐,其地本尖站, 而地方官无设站者,然计只得一茅屋,亦万不能供张也。余馁甚,食蒸饼数枚以充饥。
再如同年三月初四日日记云:
晴热。甫出门,即行坡岭数十重,沿路皆荒田,无垦辟者,与前数日所见绝异。舆夫又不识路,屡屡迷途。 家人从小水井办尖站,而舆夫从山上过,遂至相左。余馁甚急,催赶至三道沟,始得脱粟饭之计。是日,路程应住小水井,而驮夫欲住三道沟,计行约九十里,已车殆马烦矣。晚酷热。
从以上日记可知,除了天气异常和路途坎坷不平之外,谭宗浚返粤途中同样遇到饮食和住宿等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种酷热天气所造成的后果,谭宗浚在日记中也有提及:
毒热非人境,至新店宿。……热至不可刻忍。余左臂感暑无力,然尚无大礙。迨三鼓后,左腿筋络猛跳异常,急服补药镇之,然不可止。侵晨起来,则左足跛矣。嗟呼!东海尚书忌才陷善,一至于此。设余非外任,又何至奉父母之躯,而行此播州非人居之地耶?为之泣下。
总之,在出入滇境的旅途中,谭宗浚的身心均受到极大伤害。最终在返粤途中,因病情加重,不幸病逝。
三、 云南理政之劳累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谭宗浚到云南接篆视事。在此之前,云南粮道署基本处于一种无人管理的境地。针对这种情况,谭宗浚日记有如下感叹:
是日,路益平豁,已近南中景象矣。 嵩明州牧叶君(如桐)暨委员周太守(廷瑞)来谒。而粮道署书差尚未见来迓,公事废驰如是,可叹也。
后来在《止庵笔语》⑤中,谭宗浚对云南粮道署公事如此废弛的原因作了如下分析:
余在滇见前任贪赃婪劣所不忍言,以为滇去京师太远,且经大乱,故不及闻。唐鄂生中丞言蜀事,则亦犹夫滇也。过黔,闻同乡言黔事,则亦犹夫滇也。至闻诸友言楚事、豫事,则亦犹夫滇也。
对于谭宗浚在云南的工作情况,唐文治在《诰授中议大夫云南粮储道谭先生墓表》有较为详尽的描述,他说:
之任后,详询地方利弊。治水道,亲诣覆勘,次第修浚白龙潭等十余河,灌田六千余亩,废工费时。躬至诸村传谕乡民,给领不假书吏,一切火耗等弊胥革除,民大悦。丙戌冬,兼权按察使。于历年积案多所平反,然精力过耗,气血日虚,得脮肿症。于是引疾乞退,而上游方资倚畀,绅民攀辕固留。不获,已复回本任,设古学以课士,开堰塘以灌田,办积谷以备荒,增置普济堂以惠故寡。百废举兴,勤劳更甚,而体不支矣。戊子二月,再请开缺回籍调理,始获请。顾贫甚不能具资斧。大吏拨志书局费千金以赠。始得脂车以行。盖先生固兼任志书局总纂,平日不受薪费者也。呜呼!其廉洁如此,足以风世矣。
谭宗浚也在《旋粤日记》中对自己工作情况作如下评价:
又余在滇南,无善可称。惟究心水利,倡修官渡河,又增普济堂孤贫二百名,添建房屋七十所,及设古学以课士,办积谷以备荒,是三年来所稍称意者。
谭宗浚之所以如此勤政,这与他所受家庭教育以及光绪帝对他的期望有很大关系。据廖廷相《希古堂集序》⑥云:“君家世儒学,自髫龄受训,日浸淫于四部之中。性又聪敏强记,故下笔千言,不假思索。”受家庭氛围影响,谭宗浚自幼就形成了这种忧国忧民情怀。出京之前,光绪皇帝特在养心殿召见他,并予以温语慰勉。谭宗浚心情异常激动,当即就向皇帝发下了“誓捐肝脑报,遑恤顶踵私”的誓言。后来在《赴任滇南留别诸同人得诗六首》其一中,谭宗浚再一次流露“上报君恩、下安黎民”的想法:
丹诏朝来下九阍,矞云辉映到衡门。誓盟止水微臣志,眷念长途圣主恩。
辛苦惯同驴踏磨。氋氃真愧鹤乘轩。由来报称无中外,只要心肝奉至尊。
正因这两年多的辛勤劳作,谭宗浚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旋粤日记》中,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如下说明:
是年十二月,接篆视事,然眷眷恋阕之意,未尝忘也。先是在京时,友人或云粮署风水不利者,余弗深信。及抵任,见公事不能大有作为,而郁郁独居,遂婴痼疾,上书移病者屡矣,而为绅民所留,上游亦弗允。迨丁亥八月,得疟疾,未几渐愈,而元气大亏,变为两骽酸輭。至戊子正月,脚气益甚,行步蹒跚,尝衙参须两人扶持,上游始有怜悯之意,滇省医生又无能辨病源者。
出于健康原因的考虑,谭宗浚“于是决然作归计矣”。
四、 亲友离世之伤痛
赴滇途中和任职云南期间,谭宗浚接连接到众多亲朋好友相继辞世的消息。为此,他心情十分沉痛。光绪十一年八月初四日,谭宗浚接到弟弟来信,得知堂兄于该年四月四日病死,心里悲伤不已,当即撰写了《季弟来书,知伯兄以四月四日病死,今已三阅月矣,人事牵迫无暇追輓。舟次潞河,乃和泪哭述四章以志哀感,悲恸痛切,情见乎词》组诗。下面试以其中一首为例作一分析:
我生甫龆龄,失恃嗟茕茕。幼年苦荒旱,弱冠遭夷兵。提携赖君共,跋涉恒兼程。当时性跳荡,岂免君怒攖。倘非守严诲,濩落将何成?微名幸一第,蹩躠惭簪缨。君今已长诀,胡不燕台行?想应魂魄弱,未惯风涛惊。哭君涕血迸,思君愁绪萦。酹君君未觉,空有壶觞倾。愿为松与柏,常得依君茔。
谭宗浚四岁时母亲去世,在“失恃”之后,谭宗浚的这位堂兄不仅周到照顾他,而且严格要求他。也正是因为有这位兄长的关心,谭宗浚后来才能一举中第。故接到这位兄长去世的消息后,谭宗浚满怀悲痛写下以上诗篇。诗中悲情,溢于言表。
这段时间,除了亲人离世外,谭宗浚的众多朋友也相继辞世。如在《伤逝铭序》⑥一文中,谭宗浚对此作了详细说明:
余在滇中,端居多暇,岁云秋矣,风雨凄然。追忆朋侪,本多殂谢,乃 慨然叹曰:呜呼!夫萍之泛水,随逐浪而遂飘;蔦之附枝,值凌飙而便陨。草木无情,固其宜已。若吾人者,生同里闬,长仕京朝,陶陶永夕,欢乐侪于伊班;济济同僚,结契隣于王贡。谓宜金石同寿,丹青弗渝,而乃直弦见摧,甘井先竭。乞筮爻于管辂,莫永其年;求丸药于韩终,难延其算。去岁已伤刘子,今兹复悼王生。巫茢叹于屡招,童书忙于赴告。湛湛江水,甫送归魂;累累古邙,又增新冢。老氏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不可为大慼乎之!数子者,并已发藻儒林,振华朝列。绾半通之绶,恒思追辙龚黄;著一卷之书,亦欲附名游夏。迹其辫志贞亮,讬怀冲邈,兰芬蕙洁,玉润金铿,皆一时之俊也。
畴昔之年,曾陪欢笑;傲睨风月,攀临台榭。习池杨柳,度度停鞭;庾幕芙蓉,时时命嚥。行沽已罄,犹呼湔上之童;垂钓相邀,或遇坛边之叟。何图睽隔,忽已陈人。木卒草亡,风流顿尽。嗟蛇之兆,竟厄善人;嫁鹜之言,翻成谶语。
呜呼哀哉!尤可痛者,编修崔君夔典。陆机壮岁,盛宪中年。昨者都门,殷勤祖饯,离亭孤笛,握别徘徊。使车甫抵于洱海之阳,噩耗已传于燕台之馆。才高命促,已矣忽焉。仆与君生未效刘尹秤水之劳,死亦愧范卿素车之送。眷怀良友,惭负幽冥。
呜呼!娲土抟人,不能使俦侣无分张之候;轩皇画地,不能使山川无睽隔之殊。并尘世者,孰是心交;在泉台者,偏多故友。听雍门之曲,容易成悲;呼公孙圣之名,何能复应。以此思哀,哀可思矣。况复参辰迹阻,舟楫路穷。绝徼长羁,等张衡之远宦;瘴乡苦湿,同顾协之衰年。丰钟鸣而万籁凄,邻笛起而百忧集,漫漫长夜,空静听于汝南之鸡;蔼蔼停云,难寄声于塞北之雁。郁愁肠于转轂,激清泪于闻笳。绿发渐凋,朱颜非故。既伤逝者,行复自痛。
呜呼!于是列叙其人,各为之赞。凡廿一人,皆同官京师及曾计偕入都者。庶陵谷已迁,而芳馨无绝。所望华表之鹤,或返精灵;延津之龙,时腾光焰。
从这篇序文可以看出,谭宗浚是一个极重情义之人。众多好友的辞世,让他痛心不已。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获悉如此多亲朋辞世的消息,谭宗浚心中的悲痛应该是难以想像的。这同样也给他的身体带来严重伤害。
五、 饮酒过度之危害
众所周知,过度饮酒则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谭宗浚在诗文中一再提及自己有嗜酒的爱好。如《舟中与诸子剧饮》一诗,从诗题“剧饮”二字中即可看出谭宗浚的这种爱好。再如《旅寓京邸杂忆粤中旧游得诗二十首》其十九首云:
育贤坊路酒家楼,幕地帷天此快游。
但有作碑钱可索,不妨连日醉糟邱。
此诗注曰:“余自廿岁后,每卖文有余赀,辄与陈孝直、张端谷、王峻之、邓啸筼、廖泽群、梁庾生、郑玉山诸君,醵饮于育贤坊之酒楼。”⑦此时谭宗浚的日子,过得如唐代李白般潇洒。
饮酒一方面可以加深朋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还可以触发诗兴。在《止庵笔语》中,谭宗浚就谈到了饮酒这方面的作用:“余少年诗文成于酒后者皆多,有天趣,较之于醒时殊胜”。
除了能从酒中能获得创作快感外,谭宗浚有时也借酒浇愁。如在《对酒怀孝直》中,他说:
我昔年少真酒狂,意气突兀凌溟沧。城南城西酒家坊,十十五五纷成行。 鲂鱼鲜白鹅臛黄,芼以越笋兼吴姜。濡头叫呼没杯底,下视俗物皆茫茫。君时角逐同千场,往往把臂齐颉颃。直疑天地苦窄狭,未觉日月随奔忙。宁知离合本难定,驹影倏忽徒悲伤。奔蹏屡蹶已嗟恸,麻衣三载弥凄凉。今年又逐计车去,青枫叶赤天雨霜。爱君忆君不得见,岭云江月遥相望。北风吹人不可当,白草飒飒尘沙黄。前飞鹳鹤后鶖鸧,大小百鸟皆双翔。而我远在天一方,恨不与君共徜徉。人生得丧果何常?富贵岂及铜台倡。北邙道上吹白杨,故人又已归茅冈。百年鼎鼎但刍狗,身外物累真豪芒。暂时得过且须过,莫待发缟须眉苍。愿我常作元漫郎,愿君同作王醉乡。买田种秫珠湄傍,酣乐欢宴久未央。一石一斗何足量,余事洒笔飞词章。雕刻造物无遁藏,不然著书满箧箱。上掩董墨追荀扬,留之石室久愈昌。纵令饿死作寒隶,犹胜奔逐驰车航。君能相就赴要约,便拟拂袖还耕桑。作诗相寄慎勿忘。
有感于“人生得丧果何常?富贵岂及铜台倡”的社会现象,以及面对“人生若朝露,聚散良不恒”的自然规律,谭宗浚心中自然有许多不平。为了宣泄牢骚,此时的他便借酒浇愁。
对于过度饮酒的危害,谭宗浚也有明确认识,如《止酒》云:
兼旬病酒困难支,百罚深杯且暂辞。旧议食单门下供,新丸药裹箧中随。
清闲不扰安禅梦,戒律真同禁体诗。最是旅怀禁不得,被稜如铁倦醒时。
尽管知道过度饮酒的危害,但谭宗浚依然控制不了自己。如在赴云南任前,他还写了《别酒》一诗,表达了对酒的恋恋不舍:
美酒乃天禄,于官却非宜。爱官不爱酒,俗病从何医。忆从使吴蜀,供传罗珍奇。兼年累病肺,杯勺安敢窥。及乎返里后,辄复思朵颐。乃知赋命薄,官脔难充饥。酒兮我与汝,遭际吁可嗤。昔为相见数,今为长别离。衙斋风日美,当复时相思。愿言解龟去,一石浮鸱夷。有酒不能醉,嗟嗟远官为。
从以上内容看出,过度饮酒确实给谭宗浚的身体造成了极大伤害。
综上所述,理想的落空、旅途的艰辛、理政的辛苦、亲友的辞世以及嗜酒的爱好,都是造成谭宗浚过早离世的重要原因。谭宗浚的早逝,不仅是他家人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近代文学与岭南文化的重大损失。
注释:
① 参见谭宗浚《辽史纪事本末诸论》,民国二十年刻本。
② 谭宗浚《于滇日记》,清光绪年间抄本。
③ 谭宗浚《旋粤日记》,清光绪年间抄本。
④ 谭宗浚《荔村草堂诗续钞》,光绪十八年羊城刻本。
⑤ 谭宗浚《止庵笔语》,民国十一年刻本。
⑥ 谭宗浚《希古堂文集》,光绪十六年羊城刻本。
⑦ 参见谭宗浚《荔村草堂诗钞》,光绪十八年羊城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