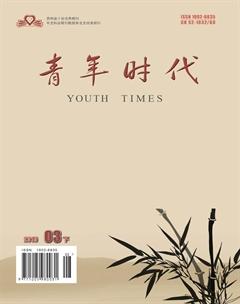艾吕雅《自由》:超现实的梦幻意象中的本我言说
刘婧妤
摘 要:艾吕雅的《自由》是二战期间流传在德寇占领区法国人民手里的一份诗传单。本文力图从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梦幻的意象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三方面解析诗歌形式和内容上的特色,指出矛盾而杂乱无章的意象群背后的同一性和“梦幻记录法”具有的本我言说意义,揭示梦幻不是逃避现实的方法、而是重新获得力量去支配环境的方式,从而阐明诗中超现实与现实的矛盾统一。
关键词:超现实主义;保尔·艾吕雅;《自由》;意象;精神分析
艾吕雅亲历两次世界大战,他对战争的厌恶和对自由的追求在其诗作中多有体现,《自由》就是其中灯塔般存在的一首。国内对本诗的研究主要以对意象的解读为重点,分析超现实意象中体现的呼吁自由的主题。本文力图从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梦幻的意象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三方面解析诗歌形式和内容上的特色,指出矛盾而杂乱无章的意象群背后的同一性和“梦幻记录法”具有的本我言说意义,揭示梦幻不是逃避现实的方法、而是重新获得力量去支配环境的方式,从而阐明诗中超现实与现实的矛盾统一。
“自由”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大文学主题。不同于此前的拜伦等诗人对“自由”的直抒胸臆式的、口号式的歌颂,艾吕雅在这首诗中使用了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一串串意象仿佛在梦境和无意识中流动到诗句中一样,矛盾且无逻辑,给“自由”添上了神秘梦幻的色彩。但在这看似非理性和无逻辑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艾吕雅对民族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浓烈的情感和热切的向往,甚至感受到的这种情感和向往比那些直抒胸臆的诗作更加浓烈、更加热切。根据精神分析学说,这是因为在无意识和梦幻中流动到纸上的物象正表现了诗人最原始的本我。
一、《自由》中的超现实主义手法
“超现实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法国流行到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其基本特征是强调表现“超现实、超理性的无意识世界和梦幻世界;主张用纯精神的自动反应进行文学创作,广泛使用‘自动写作法和‘梦幻记录法进行创作,具有晦涩神秘的特征。”
杜布莱西斯在《超现实主义》中说:“在梦幻和疯狂的状态下,由于所有控制活动都松弛下来了,所以无意识就自发地表现出来,而自动写作就可以使人记录下无意识的信息。”
《自由》全诗结构严谨整齐,每一小节都包含四句且都采用了“在……上/我写上你的名字”的形式,这是古典主义的特征。但被写上“自由”的名字的种种物象的自动地、无意识地罗列,却很好地了现代主义的特征。
诗歌第一小节:“在我的练习本上/在我课桌和树上/在沙上在白雪上/我写上你的名字”。学生时代在练习本上写字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诗人又从练习本联想到在课桌上写,这是很自然易懂的联想。然后突然转到在树上、沙上、白雪上写,显现出了思维和意识的自发流动。这自发流动体现出了诗人童年记忆中烙印深刻的物象,以童年练习拼写“自由”一词的练习本为意识自发流动的起点,一发不可收拾。第一小节的物象在现实中真的都可以在上面写字,而后面的物象则越来越奇怪、晦涩甚至虚无缥缈,从“金色的画像”到“童年的回音”、从“黑夜的奇迹”到“阳光发霉池塘”,从“飞鸟的翅膀”到“大海和舟楫”,从“拥挤的广场”到“燃亮的灯泡”,从“一切为二的水果”到“我温顺的馋狗”,从“我房门的跳板”到“我朋友的额”,从“惊讶的玻璃”到“我烦恼的墙”,从“死亡的台阶”到“无记忆的希望”……艾吕雅的意识逐渐进入自发的梦幻和疯狂,无论是从记忆中唤醒的物象,还是神游天外想象出来的物象;无论是身边真实存在的人、事、物,还是头脑中闪现的虚无的意念,都被忠诚于无意识的诗人记录了下来。读者在阅读诗歌时,便跟着艾吕雅的无意识和自发的漫无边际的联想,仿佛乘着诗人意识的洪流飘荡,走进诗人灵感迸发时的梦幻世界。这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二、意象的无逻辑与其精神的同一
杜布莱西斯在《超现实主义》中说:“在超现实的领域里,人远离开了观念清晰、材料确凿的世界。形象变得混乱芜杂,的确如此,但是,这些形象的不连贯性和无条件性,只是和我们实用的分类习惯相比较才存在。相反地,诗人用他那敏锐的感觉,却能捕捉住这些形象深藏着的相似性,捕捉住他们所由产生出来的源泉,而这个源泉正是诗人所向往重返回去的地方。”
现在我们试图摆脱固有的分类习惯、弱化清晰确凿的世界,跟着诗人的意识,从《自由》中的具有不连贯性和无条件性的梦幻意象群中捕捉这深藏着的相似性,即意象在精神上的同一性。
诗歌前四节表现了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从第一节“练习本”、“沙”、“雪”等纯粹美好的意象,到第二节突兀地出现“血”和“灰烬”,随着年龄增长,被迫遭遇伤害和毁灭。但第三节告诉我们,有神圣的领袖和崇高的精神在抵抗:“在金色的画像上/在战士的武器上/在国王的冠冕上/我写上你的名字”。第四节又突然转向“丛林”、“沙漠”这两个宏大的自然景观和“鸟巢”、“染料木”這两个温馨有生活气息的意象。在纯真与已经现形的伤痛之间曲折前进,突然这一切都成了童年的虚无缥缈的回声。诗人“在我童年的回声/写上你的名字”,在人最本真的岁月上写”自由”的名字,正照应了诗歌结尾的”我生来就认识你”一句,说明”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本真的渴望。
第五节的意象都是关于时间的,逝去的童年第一次在诗人的生命中标记了时间。“在黑夜的奇迹上/在白天的白面包/和问候的四季上/我写上你的名字”,夜里梦境的奇幻,白天生活的实在,一个个昼夜积累成四季的一次次轮回。把“自由”写在这永恒轮转的时间上,便能让“自由”随着时间永远流淌下去。
第六节到第九节,意象再次转向了自然:天地、山海、云雨。“蓝天”、“阳光”、“月光”,与人类相比它们是宇宙中的永恒;“地平线”、“飞鸟”、“暗影的磨坊”,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机勃勃的大地;“大海”、“火山”、“云彩的泡沫”、“雷雨的汗水”象征着强大的自然,人类敬畏却无法控制。这无意识地联想体现了诗人的感恩和恐惧。人类曾在自然中幸福地生活,但人实在太渺小,想要被强大的力量毁灭太容易了。但即便这样,诗人也要勇敢地在强大的自然身上标记“自由”之名。
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意象又转回人工世界,诗人将“自由”写在了“自然”和“真理”上,申明自由本为天性和真理。诗人不仅要申明,还要在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标记上“自由”之名——“小径”、“大道”、“广场”,以及诗人自己的住所乃至爱犬。接下来诗人想到了他身边的人们,那些为了自由牺牲了的人们、他的对自由有着虔诚追求的朋友们、那些同样向往自由的民众,在他们身上写下自由,标记他们为“自由”的信徒,蕴含着诗人由衷的赞美。
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在梦幻中,诗人的意识摆脱了实物,流动到了自己的内心之中。“被毁的藏身之处”和“我倒塌的灯塔”都是指精神上的追求民族和个人自由的理想的“毁灭”和“倒塌”;“不掩饰的孤独”和“死亡的台阶”透露出了诗人的无助和绝望,但即便如此,诗人仍要坚持不懈地写上“自由”之名,绝望中的反抗更加震撼人心。忽而,一丝希望又将诗人从绝望中救出:“恢复的健康”、“消除的危险”、“无记忆的希望”。不应固执于绝望和痛苦的记忆,应该怀有重获自由的希望。
最后一节,诗人在全诗结尾进行了一次直抒胸臆的表白,第一次在诗中直呼“自由”,在结尾达到了情感的高潮。在全篇无意识的梦幻之后进行了古典主义式的有鼓动性和感染力的收束,符合诗歌的诗传单的身份。
分析了全诗的意象,我们发现,这些看似无逻辑无条理的意象实际有着深刻的联系:广阔的空间、永恒的时间、外界的人、兽、物……这些共同构成了无意识世界中与“我”相对的“物。诗人在无意识中几乎将世界上所有外物都“标记”了一遍,哪怕是自己的绝望和孤独。他巴不得全世界都被我写上“自由”之名,这体现了他对于“自由”的热烈向往和追求自由的决心,在他看来,在时空上,“自由”这个永恒普世价值应该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贯穿整个人类文明。
因此,现实和超现实的同一性在于,二者共同构成了诗人的身体和意识所存在的完整世界。
三、精神分析:《自由》中的本我言说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其中“本我”是人格中最早、最原始的部分,由各种生物本能所构成,完全处于无意识水平中。超现实主义诗人运用“无意识”进行创作时力求表现最原始的“本我”。
在《超现实主义革命》中有一篇文章“非医生的分析问题”中说道:“在本我之中,不存在任何冲突。各种矛盾和各种相反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不互相干扰。各种折衷的方法也经常来调解各事物之间的关系。……‘本我是不连贯的、无条理的,它的每一种渴望都是在这无条理中追求自己所特有的目的,从不考虑其他方面。”
在惯常思维里,“对自由的赞美和向往”可能属于“超我”范畴,但是在《自由》一诗中,艾吕雅运用“自动写作法”和“梦幻记录法”,将各种矛盾的意象紧密结合在一起,就是想要表明自己对自由的向往不是后天教育之后获得的情感和道德认知,而就是最原始的本能,属于“本我”范畴。这样更突显了“自由”的合理性,更增加了这份诗传单的震撼人心的力量。通过《自由》,艾吕雅完成了一次铿锵有力的“本我”言说,更是完成了一次人类对于“自由”的“本我”言說。
这首诗运用新奇的手法表达了人类永恒主题之一——自由,在形式上让人耳目一新、欲罢不能,在内容上能引发共鸣、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对各个层面的“自由”的本能的渴望——个人自由、民族自由,甚至精神自由。
参考文献: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郑克鲁,董衡巽.新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3]杜布莱西斯著,老高放译.超现实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8.
[4]张传开,章忠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述评[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