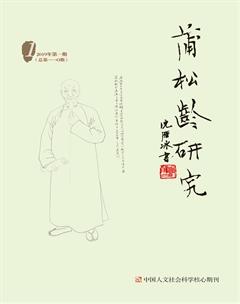蒲松龄诗歌里的暮夜书写
张姣婧
摘要:蒲松龄以“诗人”的身份在暮夜诗歌中展现着最真实的生活与情感状态。他的日常之夜在经历上是贫乏的,情感上是苦痛的,而难得的行旅之夜则使其突破了既有的局限,在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方面皆开拓了新的局面。此外,暮夜不仅是蒲松龄诗笔的重点关注对象,更是《聊斋志异》的惯常书写背景,将诗文二体对观,可知小说笔法于诗歌中的渗透使蒲诗具有了个性鲜明的“聊斋味道”,而两者的内容差异则体现了蒲松龄通过虚幻之笔对现实情感需求所进行的有效补偿。
关键词:蒲松龄;暮夜诗;聊斋志异;笔法渗透;情感补偿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以其小说《聊斋志异》闻名于世,这部被誉为“清代文言小说高峰”的作品受到了研究者广泛且持续的关注,然而,这座“高峰”的缔造者在诗歌领域的毕生投入却是问津者寥寥,着实令人感到遗憾。诚然,一位作家在文学创作时诸体兼善的可能性并不高,蒲松龄的小说艺术成就也的确大于诗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诗歌作品不具有研究的价值。一方面,在诗之体裁的限制下,蒲松龄有其个性化的,无法为小说所取代的艺术与情感表达,当我们以评价“诗人”的眼光看待蒲松龄时,也许会突破对其为“小说家”的有限认知;而另一方面,鉴于诗歌多反映现实生活,小说多建构虚拟世界的一般文学书写规律,探究蒲松龄的诗作,并将之与其小说对观,即可通过不同文体间的关联对蒲松龄的思想情感与创作理念形成更为深透的了解。
暮夜是人一天中相对最寂寞,最能够回归自我的时间,光明的褪去,漫漫长夜所造成的空虚都是激发文学家创作灵感的催化剂。对于蒲松龄而言,暮夜不仅是《聊斋》故事的惯常背景,更是其诗歌书写的重要内容,研究蒲松龄的暮夜诗,对了解其人及其艺术思想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在蒲松龄现存的一千余首诗作中,题目中包含暮夜字样者就有四十六首,而题中无“夜”却写“夜”者亦有二十四首,同时,全诗非作于暮夜,但于诗句中提及暮夜的更有数十首,由此可见,暮夜在蒲松龄的诗歌创作中诚占据着一定的分量。本文将目光聚焦于蒲松龄写于暮夜,描摹暮夜的诗作,于其中探视蒲松龄暮夜时的生活状态与情感流露,并在把握其诗歌艺术的同时,对其小说创作进行关照,在二者的联结中感受蒲松龄独具个人魅力的暮夜情思与文学表达。
一、日常之夜:独处的孤苦与交游的畅怀
蒲松龄因《聊斋志异》享誉后世,成为了人们口中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但当我们回归到历史的现实,可知作为一名终身落魄的乡村知识分子,蒲松龄的一生其实是那样的平凡,甚至可以说有些许的惨淡,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当了一辈子默默无闻的乡村塾师,做了一辈子始终未能实现的科举梦。那么,在如此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蒲松龄是怎样度过漫漫长夜的,他那饱含真情与灵性的诗笔又在暮夜之作中展现了怎样的思想情感与艺术才华呢?
首先,独处是蒲松龄暮夜里最惯常的状态,在孤单寂寞的时刻里,一首首自我慨叹与抒怀的诗作接续而生,形成了蒲松龄暮夜诗的基本色调,如《夜坐》一诗反映的就是频现于蒲松龄暮夜生活中的情境:
短榻凝寒客思清,时闻里落短长更。松阴破碎秋光漏,髭影婆娑短烛明。文字逢时悲老大,晓床欹枕笑平生。年年落拓成何事?揽镜忽看白发盈。[1]811
诗人于榻上独坐,在凄清寒冷中感受着时间在打更之音中的流逝。松阴的破碎与髭影的婆娑,秋光的滴漏与短烛的微明,构成了人与自然的交织融合,在自然光影的变幻间,人生的光阴也随之散去,投射在了离散垂老的髭须之上。如此由声音到物象,从体感到视觉,诗人巧妙地调动多重感官描摹出了一幅深夜独坐图,静谧中带着淡淡的感伤。而到了诗的后半部,诗人则直抒胸臆,悲叹、苦笑、反思自己的落拓不得志,忽然看到鏡中的自己,盈盈白发又给诗人的心中平添了一份无奈与辛酸。诗人将身与心皆完全融合在了诗歌所营造的意境中,充分展现出了其内心对自我人生的最真实感受。
除了如此孤身独坐外,蒲松龄之所以会在夜间频频抒怀,离不开外在环境的有效刺激,而刺激的主要来源便是雨雪天气,尤以雨之为最。雨夜中,蒲松龄既会在微雨时分如《夜雨》中的“夜寒烛影深,残红生壁上。飘风搴空帏,独坐如梦想。但闻疏雨声,入竹敲清响” [1]786般,于安静凄凉的氛围中静静怀想,也会因“窗风忽碎击,树露时急坠” [1]787的急雨而触发“幽怀逢物伤,往事皆可泪。有情解悲秋,此夕何能寐” [1]787的愁肠,又或是在暴雨中感受“隔院松涛终夜闻,万绪纷来伤胸臆”的持久苦痛 [1]800,更或在“青石裂破碧天漏,郁郁浓烟蒸宇宙。玉女无声迸线条,一夜乾坤亦应瘦” [1]164的电闪雷鸣之际表现出“胸中垒块如云屯,万盏灯光和酒吞。醉中披发作虎叫,天颜辄开为我笑” [1]164的狂放姿态,可以说,通常情况下,蒲松龄的情绪与诗笔的收放程度是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加以变化的,然而无论是微雨里的静静感伤,急雨时的忽现悲怀,暴雨夜的万箭穿心,还是雷电中久郁后的爆发,所有的一切皆因诗人终年不得志的心结而有所生发,情感的起伏并不意味着诗人心态从根本上有了变化,一切都不过是环境刺激的结果而已。
而最能体现蒲松龄心声的则是其超越了环境限制的呐喊,他在《夜微雨旋晴,河汉如画,慨然有作》一诗中曾言:
夜搔短发哭歧途,狂歌击剑声呜呜。歌阕粉绿扫重云,天开星眼泣露珠。[1]155
微雨后又是晴空万里,若非心有千千结,诗人当不至于有搔发、悲哭、狂歌与击剑这般激动的表现,在诗人眼中,晴天里的露水也不过是苍天的眼泪,如此看来,当心头的落寞苦痛达到一定境界时,外在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去承载诗人呼之欲出的情感,而该诗标题中“旋晴”、“如画”与“慨然”的字样都给人以积极明媚的感觉,与诗之正文所形成的反差更加深了诗情的悲凉,既体现了诗人的心境,又不失为其诗歌创作的一次小小突破。
以上深夜里的寂寞感怀皆是蒲松龄向内进行自我关照的结果,然而,在孤单夜里的某些特定时机,蒲松龄还会表现出超越小我的,对民生疾苦的挂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旱灾的忧心。在天气干旱时,蒲松龄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六月无苗热似焚,老农无望复耕耘” [1]468,他殷殷企盼雨雪,状态如《夜小雨》所叙,可谓是“愁绪纷来思不穷,五更梦醒听归鸿。惊心浑似敲窗雨,落叶萧萧趁晓风” [1]479,只要雨雪一刻不来,他就会一直愁绪不断、心神不安。而当足以缓解灾情的雨雪在夜晚之际到来时,蒲松龄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在“枕上忽闻雪乱飞,眼中已见麦掀舞” [1]460与“梦醒初闻零雨声,恍疑殊死得更生。床头爽气清余睡,坐听高檐滴到明” [1]467之诗句中展露无遗,旱情得到解决可以说是独处之夜里唯一能够令蒲松龄感到喜悦的事。如此说来,在寂寥无人属于自己的夜晚,蒲松龄并没有将自我全部局限于个体的得失中,而是能够在忧心民生中实现对小我的超越,由此得见这位乡村知识分子对外界的关怀。然而,所谓的关怀也仅停留于此,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这既可以说是蒲松龄的局限,但又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其对自我的敏锐察觉与细腻表达,只能说这就是蒲松龄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而在独处之外,交游是蒲松龄度过漫漫长夜的另一重要方式。然而,理论上与人相处时可以存在的各种生活与情感体验在蒲松龄这里却被单一化了,又或者说,蒲松龄也许有着丰富的暮夜交游生活,但他于诗作中留下的,即他认为最值得被铭记的却都是在觥筹交错与吟诗唱和间的情感宣泄。然而,交游并不能因此消除他独处时的那份压抑伤感与孤苦难耐,最多也不过是通过分享一畅忧怀,在知己的共情下获得短暂的情感慰藉。比如友人王玉斧的偶然到来,就为蒲松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抒怀机会,其诗《王玉斧忽至,夜出壶酒,对酌倾谈》道:
故人落丹霄,握手破忧悯。入夜出壶酒,促膝话中悃。为我开聋聩,惊怪胡可忍!世途尽陷阱,闻之涕既陨。对酒发狂歌,停杯时一哂。夜阑灯烛辉,放谈酒行紧。含吐快纵横,不觉香醪尽。罢酌成瑶章,衰翁谢不敏。[1]453-454
王玉斧与诗人许久未见,二人促膝夜话间,王玉斧给蒲松龄带来了些许反映社会黑暗的见闻,从诗文中我们无法知道王玉斧具体说了什么,但能够使蒲松龄感到惊怪、难忍甚至落泪的所谓“陷阱”,想必多少都能让蒲松龄联想到自己的坎坷经历,以至于对酒狂歌,慨叹不停,心头的无限郁结唯有通过不停的倾诉与饮酒才能加以排遣。如此以酒遣怀的场景可以说是蒲松龄暮夜交游诗中必然出现的画面,亦如《中秋微雨,宿希梅斋》其二所述:“三径苍茫满绿苔,高斋把酒共徘徊。几家烟火芳邻隔,四塞凉云薄暮来。义气相逢清夜悔,艰难深历壮心灰。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 [1]81在这首诗中,诗人由前诗中的独自洒泪变成了与友人的共同悲凄,一句“世上何人解怜才”的共同呐喊既令蒲松龄感受到了知音的陪伴,又在宣泄之中使郁结的情绪得到了暂时的释放。然而,可以想见,这种释放是不彻底的,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集体化的自怜自哀中加重内心的伤怀。相比较而言,在交游中互相鼓励,以此激活对未来的信心更能够给其心灵带来慰藉。最能反映这般境况的诗作便是《如水新酿熟,清夜见招》一诗:
秋思无聊见雁行,黯然搔首白云乡。故人酒熟仍相忆,中夜开樽待我尝。
词赋人登百尺楼,狂搔头发看吴钩。醉眠钟漏声交夜,痛苦溪山路尽头。诗酒难将痴作戒,文章真与命为仇。欲从緱岭寻歌吹,瑶水苍茫不可求。破帽垂垂影自羞,玉壶敲断恨悠悠。林泉久臥成疏放,阅历十年积悔尤。病鹤不忘湖海志,飞鸿宁为稻梁谋。相逢且尽杯中物,犹喜同人尽黑头。[1]794
蒲松龄的友人王如水请其饮酒,二人在饮酒之际经历了狂、醉、痛、苦、羞与恨的丰富情感变化,在充分发泄了因科场蹉跎而导致的悲愤后一饮释怀,归于“喜”之状态,一展“不戒痴”、“不忘志”的豪情壮志。可以说此情此景下的蒲松龄是真正得以畅怀的,如此积郁后的淋漓爆发在蒲松龄的暮夜交游中实属罕见,从其以超越平常暮夜交游诗的笔墨来对此加以记录,可见这番经历给蒲松龄心灵带来的影响。
总而言之,无论是展现独处还是交游时的暮夜诗,蒲松龄诗笔于此最鲜明的特点是“我”始终存在于诗作中,高度的主体性使其诗作的情感浓度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无论情感的具体表征如何,这些贯穿了蒲松龄一生各个时期的暮夜诗最终指向的都是其内心无处安放的孤苦寂寥与愤懑失落,可见这位终身落拓的乡村知识分子,穷其一生都未能彻底走出科举的藩篱。
二、行旅之夜:蒲松龄暮夜诗的别样笔墨
行旅因与日常生活,家乡故友的疏离,易使人在陌生的地域产生有别于寻常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对于内心敏感的诗人而言,暮夜的到来则更会使这份别样的心情在四下无人时被放大突显,由此展现出的则是诗人心底最真挚的思想与情怀。在蒲松龄的一生中,他仅有一年时间离开家乡山东,应孙蕙之邀到宝应做幕僚,且他在山东境内游走的经历亦十分有限,对于这样一位诗人来说,行旅中的暮夜就显得尤为珍贵了。“暮”、“夜”是蒲松龄行旅诗中出现频次相当高的词汇,而“行旅”同时也是其暮夜诗中重点着墨的内容,可以说,漂泊之夜的个中滋味在蒲松龄的内心留下了颇为深刻的烙印,而行旅迥异于日常生活的体验实为蒲松龄在此情境所作的暮夜诗赋予了有别于日常之夜的别样韵味。
蒲松龄在日常生活中所作暮夜诗的情感大多都是较为痛苦的,然而在旅途中,却不乏表现出平和恬淡甚至是欢愉畅快的情感状态的作品。如《扬州夜下》一诗,描写了诗人从高邮至扬州的行舟途中所见到的景象,“梦醒帆樯一百里,月明江树密如排。舟中对月拥窗坐,烟舍村楼尽入怀” [1]41,彼时月色已现,周围的风景仍清晰可见,说明正是黄昏日暮时分,诗人的眼光随着船只的行驶缓缓移动,树木、明月与村舍人家从眼前一一略过,同时进入到诗人的心怀,在简单的意象与舒缓的节奏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蒲松龄气定神闲地安坐船头,悠闲地欣赏着窗外的一切。如此心绪平和的情境在《十月初七日途中日暮》中亦可见一斑:
驱马上西山,驽钝策不前。悬车日欲落,山脚没深烟。霞照暮山紫,白衣忽变迁。敛光淡将夕,黑云界遥天。星密雁声隐,路侧马蹄偏。尚余二三里,新月照吟鞭。[1]436
诗人策马归家,马钝步缓,但诗人却并不着急,而是观察到了摇摇欲坠的夕阳与烟云笼罩的山脚,在一片和缓朦胧的氛围之中,诗人怀着闲适的心情发现:晚霞将夕阳下的山体映成了紫色,白衣也随着霞光改变了颜色,紧接着阳光点点淡去,黑云在遥远的天边画出一道道界限,星星大片地于天空中显现。日暮之时,人与自然在颜色的更迭与光影的变幻中融为一体,诗人细腻的观察与生动的笔触充分展露出其美好的心境,可以说他已然将全身心投入到了这番美景中,是那样的舒适与放松。结尾处,在接近目的地的地方,诗人于新月的映照下挥动马鞭,口中随兴作诗,悠然前行,仿佛是一张意境恬然的月下吟哦图,极具画面感,既可见诗人心情之美,又足见其笔墨之精。
此外,旅途中还有令蒲松龄情绪更为欢愉高涨的暮夜,如《二十七日旋里,至夜大雪》一诗所写:“行旅休装日,马蹄带晓晖。途遥苦倦惫,雪甚幸旋归。炉火帏房暖,儿孙笑语围。始知在家乐,禽犬俱忘机。” [1]603诗人在日暮时奔波至家,虽然辛苦,但却幸运地避开了大雪,还能够在回家后与家人在火炉旁团圆说笑,在旅途的苦倦与围炉的笑语,以及雪夜的寒冷与房内的温暖的对比间,诗人溢于言表的快乐跃然纸上。而最能够体现蒲松龄欢愉情绪的暮夜诗当属《泛邵伯湖》:
湖水清碧如春水,渔舟棹过沧溟开。夕阳光翻玛瑙瓮,片帆影射琉璃堆。游人对此心眼豁,拍案叫绝倾金垒。湖风习习入窗牖,开襟鼓楫歌落梅。遥堤欸乃声陆续,镗鞳近接湖东隈。烟色苍苍日色暮,欲行且止犹徘徊。俄顷星出湖墨黑,城门久闭驺人催。扶醉下船事鞍马,炬火光天归去来。[1]38
诗人与友人泛舟于扬州邵伯湖上,在夕阳的光影与绚烂的晚霞之下,邵伯湖水浩渺无垠,清透碧绿,渔舟在其上缓缓驶向远方,面对这样一幅色彩纯净,视野辽阔的画卷,诗人感到心胸豁达,甚至拍案叫绝,举杯相庆,可见其情绪的高涨。拍案、叫绝、饮酒、歌唱、徘徊、迷醉等一系列的行为描写将诗人的沉醉与留恋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诗尾处的“炬火光天归去来”看似只是写其举着火把踏上归途,但因“光天”一词与“归去来”三字的使用,却别有了一番畅快之意。前者意为火炬将整片天空照亮,而一把小小的火炬实际上只能起到微弱的照明作用,如此夸张之笔可谓是诗人喜悦心情的放大,而“归去来”是于“归去”后加上了“来”之语气词,使“归去”的表达在语音上有了绵长舒展的效果,展现出诗人豁达畅快的心情,而此三字亦化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的典故,又暗示了诗人洒脱超然的心境,可以说诗之尾句将全诗的情感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皆推向了最高潮。
由此可见,行旅带给蒲松龄的非日常化体验使其在暮夜时得以感受到少有的平静与愉悦,蒲松龄在让我们看到其面对暮夜的另一面的同时,亦展现了其将小我融于自然,融于生活的生动艺术笔触,可谓是既有心情,又显才情。而有意思的是,这些情绪较为平稳乃至积极的诗歌,表现的全部都是夕阳将坠欲坠,日光尚明,深夜未至时的情景,也就是说,严格讲属于“暮诗”而非“夜诗”。不难理解,相较于黑漆的夜,余温与光明仍在的日暮能够给人以更加积极的心理感觉,天时与人情如此高度的契合,再度反映出蒲松龄与自然的合二为一,心灵相惜。
而当黑夜完全来临,孤单寂寞的感怀已然构成了蒲松龄日常之夜的习惯性状态,虽然同样的心情在旅途中亦有存在,但不同的是,在日常情况下,诗人的暮夜所感侧重于向内的忧思,对个体志向难酬的愤懑,而在行旅之夜,旅途的漂泊感则使诗人对离别与陪伴格外地敏感,由此生成的大多都是由内及外的挂怀与聚散离别的悲叹。
中秋佳节之际,蒲松龄孤身一人游历在外,在寂寞的夜晚,他于《中秋早眠》中写道:“旅况萧条最可怜,良宵辜负月明天。星河一片清如水,空使寒光照客眠。” [1]424这里虽然并无“亲人”、“聚散”等字样出现,但“萧条”、“可怜”、“辜负”、“空”与“寒”等饱含苦涩与寂寥之感的词语已然道出了诗人在中秋之夜不得与家人团圆的孤独与伤感,可以说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一种含蓄但亦动人的表达。而在远离亲朋,只能独酌的夜里,蒲松龄于《舟中独酌》中道:“偶邀江月成三客,又踏烟云第几程。我欲扣舷歌水调,残荷风起落红英。” [1]70天地间只有一轮江月与他的身影,他想唱一曲思亲怀友的《水调歌头》,可见到的却是那风卷残荷,红花零落,如此萧条的画面破坏了诗人的心情,离愁之感也随之油然而生。
而在两首《客斋》诗中,行旅中乡思的感怀表现得更加明显:
其一,高斋灯火客思清,旅况萧条华发生。自有酒人来击筑,欲招小妇坐鸣筝。频年忧患凭天地,中夜悲歌忆弟兄。岭上寒梅零落尽,徒教春梦满江城。[1]57
其二,烟波万里一身遥,湖上春残燕子娇。乡思多因闻雁发,离魂只为看花消。云迷芳草愁中路,月满春城柳外桥。搔首天涯仍涕泪,五更风雨自潇潇。[1]58
这两首诗皆以“客思”、“旅况萧条”、“万里”、“一身遥”、“雁发”、“离魂”与“天涯”渲染旅途的遥远与诗人身处异乡的陌生感,可以说诗歌处处都是引发乡思与惆怅的契机,叫诗人怎能不叹息。而在诗之其一中,击筑与鸣筝的欢愉反衬了忆兄弟时的悲凄,其二中,“燕子娇”的明媚与“花消”的黯然,“雁发”的心有所向、满怀希望与游子“离魂”的飘零不定、无处安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愈发突显出了诗人浓郁的怀乡思友之情。此外,两诗的尾声也都十分耐人寻味,诗之一中零落的寒梅就仿佛无依无靠的诗人,如同寒梅无法真正走进春天,诗人春归的想法也不过是一场虚空的梦,在这番情与景的巧妙交融间,游子渺茫无定的心伤便被诗人饱含深情的笔触定格了下来。而诗之二的尾句妙在“仍”与“自”二字,“仍”写出了诗人虽翘首天涯,但涕淚始终绵延不绝,道尽其情之深痛,然风雨之“自潇潇”则意味着自然始终不动声色地保持着同一状态,不为人之情感所转移,如此的“冷漠”景象与诗人情感的决堤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使得深夜之愁绪显得更加痛彻心怀。
最后,在表达有别于日常之夜的情感之余,蒲松龄暮夜行旅诗还有一番日常书写所无法涉及的内容,即描写旅途中惊心动魄的体验。可以说蒲松龄全部的“惊魂”皆由风雨而来。如《瓮口道夜行遇雨》与《榻上》二诗,叙述了蒲松龄偶遇暴雨,投宿无门的惊魂一刻,这件事给蒲松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甚至是心理阴影与创伤,此番详情将于后文中予以剖析。然而,“惊魂”所带来的不只有恐惧与心慌,豪情与释然亦是如此经历后诗人的另一种表现。前者如《雨中夜归》一诗,诗人面对“天涯咫尺见迷途,村树楼台半有无。大野回风虎啸鬼,深林篝火夜鸣狐” [1]766的不寻常情境,却激发起了“壮心恨不能千里”的壮志雄心 [1]766,可谓是风雨之中愈见坚毅之心。而后者则如《湖津夜泊》所写:
朔风蓬蓬动江渚,断篷惊折阻归橹。大舟摆簸小舟摇,惊起鱼龙跳波舞。两人中夜揽衣坐,静听楼船逗风雨。浪花斜卷半天来,窗入波星沾白纻。俄倾风定夜迢迢,月桂凄冷霜天高。[1]39
诗人与友人在行船上遇到大风,在一番令人惊颤的摇摆颠簸后,两人静坐听雨,而不因风浪影响心绪,直至一切归于平静。如此船摇篷断、鱼龙皆起的风雨之行想来必是一场动魄惊心,然而诗人却以云淡风轻之笔将其缓缓道来,最终将诗歌引向一片平和意境,足见诗人内心的从容与淡定。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情此景在蒲松龄的诗作中已然是二度出现,另一次为《舟中夜坐》一诗:
胡风萧飒浩无主,断篷惊折雄心苦。大舟哑哑小舟啸,惊起睡龙跳波舞。两人中夜起长叹,卧听楼船逗风雨。[1]165-166
此诗与《湖津夜泊》的前半部高度相似,赵蔚芝在对该诗进行笺注时由“萧飒”是秋风声,不至使“断篷惊折”,“起长叹”与“卧听”矛盾,认为“《夜坐》恐是未定稿,《夜泊》始是定稿。未定稿恐系误入。” [1]166若此论断成立,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到蒲松龄作诗与修订的創作过程,并从中感受其对诗艺的追求。譬如蒲松龄将“萧飒”改为“蓬蓬”,确如赵蔚芝所言,更具有“断篷惊折”之力。而将“雄心苦”改为“阻归橹”,“起长叹”改为“揽衣坐”则是一种淡化情感的表达,如此不言“我”之惊心与无奈,反倒能够于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蕴藏更为丰富的情绪,换言之,含蓄比直白更能引人联想、耐人寻味。同时,“起长叹”后接“卧听”从逻辑上讲,无论于人物动作,还是情感承接方面都不甚合理,但修改后的“揽衣坐”与“静听”却是恰切顺畅的。此外,“大舟摆簸小舟摇”相较于“大舟哑哑小舟啸”而言更富有动感,因而更有助于营造出惊险刺激的场面,而以“鱼龙”替换“睡龙”,即是在传说之物“龙”外,增加了现实存在的“鱼”之意象,如此便使画面具有了真实感。综合而言,蒲松龄对诗句的修改是成功的,而这并非一蹴而就的成功,充分体现了其对文学创作的不懈努力与执着追求。
三、诗与文的联结:《聊斋》创作的笔法渗透与情感补偿
如果将蒲松龄的《聊斋》创作与其暮夜诗对观,可以发现,小说笔法在其诗歌中的渗透使其暮夜诗不自觉地具有了“聊斋味道”,而小说较暮夜诗在内容上质的差异则形成了虚幻世界对现实情感需求的有效补偿,在诗与文的互应书写中,蒲松龄彰显了其独具特色的艺术笔力,实现了文学抚慰心灵的艺术追求。
首先,极力摹写环境,营造氛围,并在寥寥数字间创设出极具冲击性与画面感的情境,可以说是蒲松龄将《聊斋》笔法渗入暮夜诗歌创作的一大表征。如《荒斋不寐》一诗:
荒庭无人树纵横,青草长合空阶平。雨余向晚昏黑生,残雷隐隐电飞明。北风灭烛扉閛閛,抱膝独宿心惶惊。巨鼠叫窜声嘤狞,鸱鸟啁啾又夜鸣。徘徊百感愁思萦,素髭白发添数茎。[1]225
诗歌描写了蒲松龄独居荒斋,愁思百转,内心惊惶的景象。“荒庭”、“无人”与“空阶”三重意象叠合着肆意生长的青草树木,写出了荒斋的寂静空旷。在雷电风雨中,烛火熄灭,门吱呀作响,声音的顿起与光影的变幻不经意打破了荒寂,却使诗人内心愈发的不寒而栗。忽然,巨鼠嘤狞的叫声与鸱鸟啁啾的夜鸣划破夜空,促使诗人的不安与愁绪达到了极点。然而诗人到这里却笔锋一转,将画面定格在了自己新添的几根髭须白发之上,岁月的无情,愁思的环萦都于一瞬间凝聚于此,使全诗的情感走向了最高潮。
如此精心营造环境,渲染氛围,频频调动感官,并借人之心理使其完全融于周围的情境,直至最终生成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的写作手法是《聊斋》中的常见笔法,如《连琐》开篇描写男主人公杨于畏所处环境为“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夜阑秉烛,方复凄断” [2]331,蒲松龄在这里由旷野与古墓的意象展开环境描写,融入了萧萧白杨之音以及烛火之光,为故事渲染出一种阴森凄清的氛围。继而“忽墙外有人吟曰:‘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反复吟诵,其声哀楚” [2]331,女主人公连琐未见其人,先现其声,哀吟之音打破了固有的沉寂,在表现出连琐悲苦心境的同时,将小说的情节推向了高潮。此番情境的营造、人与景的交融、人物心理的体现以及声光意象的使用都与《荒斋不寐》一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蒲松龄是将写小说的惯用笔法融入了诗歌创作,使其暮夜诗染上了些许“聊斋味道”。
与此相似之作又如《夜电》之诗的第二首:
夜深有鼠大如驴,咤咤霹雳啮破书。疾风窗户自开掩,若有人兮来荏苒。鬼母啾啾狐狸啸,摄魄摄魂梦惊魇。城头隐隐鸣鸱枭,闯然一声闪红绡。[1]164
这首诗写夜半闪电惊扰了蒲松龄的美梦,除了风使窗户自开,鸱枭鸣叫的环境描写,外加闯然一声闪电突现的声音效果及视觉冲击与《荒斋不寐》所用的《聊斋》笔法相近外,极度夸张的如驴般硕大的老鼠,啾啾的鬼母,吟啸的狐狸,以及被摄的魂魄皆频见于蒲松龄的小说叙事,更有如《公孙九娘》中“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 [2]482的描写与此诗中的情境如出一辙,再度体现了《聊斋》笔法向蒲松龄诗作中的渗透。
不仅如此,蒲松龄的暮夜诗还表现出高度的叙事性,可以说是《聊斋》笔法融于诗歌的更为鲜明的体现。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蒲松龄将夜行时遇到暴雨山洪,但却投宿无门,颠簸辗转才得以落脚的经历写成的诗作《瓮口道夜行遇雨》:
日暮驰投青石关,山尘横卷云漫天。望门投鞭纵马入,庭户冷落绝炊烟。主人禾黍堆满屋,人无汤饼马无粟。拍肩挽臂求作谋,苦辞不能留客宿。下关暝黑闻风雷,倒峡翻盆山雨来。潦水崩腾没马膝,激石擂炮鸣相催。水猛石乱马蹄破,动骨骇心欲倾堕。人马不惜同时饥,颠蹶还愁丧身祸。来时当道僵尸横,我行至此马腾惊。云是虎噬远行客,髑髅啮绝断股肱。念此毛寒肌粟起,心急行难步不咫。电青乍见水磷磷,径昏惟觉石齿齿。三漏始入土门庄,挝门下骥登人堂。渭城已唱灯火张,唤起老妪炊青粱。篾席破败黄茅卷,如醉醇醪卧香软。[1]68
在这首诗中,诗人先交代了日暮天变的背景,而后写人马向人家投宿,主人家里堆积满屋的粮草与人马的饥饿形成了鲜明地对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庶之家,却无论诗人怎样拍肩挽臂地求助,都拒绝为人马提供一个歇脚之处。拍、挽、求的动作描写将诗人的落魄、焦急与诚意展现得淋漓尽致,使一个走投无路者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苦辞”与“不能”二词彻底将诗人拒在了门外,这里虽没有详细的语言或动作描写,但读者已可如阅读小说般看到主人冷漠的嘴脸,两相比照与摹写之间,可谓深得《聊斋》笔法塑造人物形象的精髓。
由此,遇雨事件进入了情节高潮,倾盆的暴雨,翻卷的山洪使人马惊慌失措,被虎噬过的僵尸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寸步难行,这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险象环生的描写如同在叙写一个惊心动魄,却足以引人入胜的故事。其间的场面、视觉、音效与心理等小说叙事元素皆被运用得恰到好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诗人对于人物心理的捕捉,面对“水猛石乱”的险象,诗人表现出的是惊骇,而在不那么激烈的颠蹶时,诗人的内心则是愁苦,继而,听说老虎食人后,诗人心中的恐怖转化成体感上的“毛寒肌粟”,心中越是急迫,脚下却越迈不开步伐。诗作将不同情境下人物最真实恰切的心理状态通过精准的词汇呈现出来,并将心理的体验转化为了外在的表征,可以说是小说创作时所用的刻画人物心理的笔法的高度渗透。
在历经坎坷后,诗人又以“水磷磷”与“石齿齿”这样相对平稳的景物描写将事情的发展引入最后的阶段:终于来到土门庄,敲门下马,远望灯火,唤妪备食,卧榻歇息,一系列的动作描写与空间转移使叙事得以有序推进,对事件有惊无险的结局的交代也使整首诗具备了叙事意义上的完整性,如此即与要使故事情节有始有终的小说叙写思路一致,而与一般诗人所采取的只突出展现事件或情感片段的写诗方式有所不同,体现了蒲松龄对《聊斋》创作经验的灵活调用。
而继《瓮口道夜行遇雨》一诗后,蒲松龄紧接着又创作了一首《榻上》来对事件的后续进展,或者说是最终结局进行描写:
解衣榻上息惊魂,枕石久眠被始温。瘦骨着床初放胆,搔来犹觉此身存。[1]69-70
诗人脱下外套,在床上平复惊魂,因为身体寒冷,被子很久才变暖,“瘦骨”只有在床上才能放开胆量,发现自己还平安地活着,竟是件多么幸运的事。诗人感官的体验写出了天之寒,身之寒,也不乏透露出投宿被拒的心寒,而“惊魂”、“放胆”与“犹觉”,即从惊恐到释然,再到后怕的心理变化过程,细腻生动地揭示出了诗人真实的内心状态,如此不仅形成了高度鲜活的细节刻画,更从身与心的双重角度与前作《瓮口道夜行遇雨》形成了紧密的关联,如同小说写作的续篇一般,可以说是蒲松龄暮夜诗叙事特色的又一体现。
蒲松龄的暮夜诗除了在笔法方面与《聊斋》存在渗透关系外,在情感层面,《聊斋》的相关小说的叙写也可以说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蒲松龄在暮夜诗中所流露出的情感缺失。
诚如前文所述,在反映蒲松龄现实生活与情感的暮夜诗中,无论是日常还是行旅之夜,无论是孤身一人还是与他人同在,蒲松龄的夜间生活无外乎是观景、饮酒、听雨、怀人与感伤悲叹,偶尔激起的波澜也不过是旅途中的小小意外,总体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与此同时,孤愤始终蕴藏于平淡的生活中,由此更加重了暮夜给蒲松龄心灵所带来的苦闷。面对如此现实,唯有找到一份情感的寄托才可以缓解这样的苦痛,而创作可以任凭作家想象与虚构的小说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正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自序中所言:“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 [2]3《聊斋》故事成文的主要动力源自于蒲松龄无处安放的满腔孤寂与愤懑,特别是到了夜里,孤愤之感在被激活放大时,往往就催生出了用以弥补现实缺憾的天马星空的小说,催生出了《聊斋》故事里丰富多姿的暮夜书写。
譬如,在现实世界里,蒲松龄于旅途的舟中只能孤寂地独自饮酒(《舟中独酌》)或经历些许风雨(《湖津夜泊》),总体来说较为乏味,但在《聊斋》中,他却可以想象出一场发生于夜间的别开生面的水上蹴鞠表演来作为生活的调味剂(《汪士秀》)。再比如,我们由《瓮口道夜行遇雨》和《榻上》二诗知道,蒲松龄有过暴雨中投宿无门的不愉快经历,此番特殊的体验原可以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来加以使用,但也许蒲松龄不愿再回忆往日的痛苦,甚至不自觉地要通过创作小说的方式来弥补曾经的心理创伤,于是在《聊斋志异》所有主人公遇雨并想要躲避的情节中,他们都得以在第一时间顺利地找到避雨的场所,甚至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发生,如《窦氏》中的南三复,不仅成功投宿,还得到了主人的热情接待;《宦娘》中的温如春因遇暴雨进入一户人家,与美丽的鬼女宦娘相遇,还在其帮助下与良工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阿纤》中的奚山遇雨被阻,老叟主动开门邀请他,帮助他与阿纤成就了良缘。如此惊喜连连的避雨体验可以出现在一天中的任意时段,虽不完全从属于暮夜,但他们积极的,没有拒绝与伤害的共同指向,却有意无意地弥补了蒲松龄于现实暮夜中的情感缺憾,相信蒲松龄在进行如此创作时内心多少都会产生些许的满足感。
而完全聚焦于《聊斋》的暮夜书写时,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尸变》《喷水》这样纯粹的恐怖故事外,蒲松龄写的最多的都是书生与丽人,尤其是狐女、鬼女与仙女这样的异类丽人的相遇相知,甚至是女方主动来投怀送抱的故事,如《连琐》中鬼女连琐深夜主动前来陪伴书生;《红玉》中狐女红玉与书生月下相见,之后主动助他娶得佳人,振兴家业;《小谢》中小谢与秋容两位佳丽共拜书生为师,全心依附于书生,并伴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林四娘》中的林四娘不请自来,夜夜与书生吟诗奏乐,好不快活,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这些虚幻世界里“和易可亲”、“多具人情” [3]187的佳人成就了蒲松龄寂寥深夜里的快乐,他用一个个美好虚幻的故事填补着现实生活的贫乏与情感的缺失,既将文学抚慰心灵的功能开掘到了极致,又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篇足以传世的经典作品。
四、结 语
透过蒲松龄的暮夜诗作,我们发现了他平凡人生中无数个漫漫长夜里的真实心态,了解了他于难得的行旅之夜中的别样体验与人生感怀,由此既还原出了一个立体鲜活的诗人形象,同时又多少开掘出了其诗歌创作中的精到之笔。不仅如此,《聊斋》创作笔法向诗歌中的渗透展现了蒲松龄自由驾驭并融通不同文体的艺术才华,由此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而将蒲松龄的暮夜诗与小说对观,又可知《聊斋》创作是为蒲松龄对现实生活经历与情感缺失的有效补偿。可见,仅就暮夜诗这一类诗歌题材而言,蒲松龄的诗作就有如此丰富的研讨空间,如若未来能够发现蒲诗中更多值得探析的内容,并对其进行与《聊斋》的关联式研究,或可对进一步认知蒲松龄的思想情感与艺术创作产生有益的助力。
参考文献:
[1]赵蔚芝.聊斋诗集箋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2]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蒲松龄.聊斋志异[M].于天池,注.孙通海,于天池,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