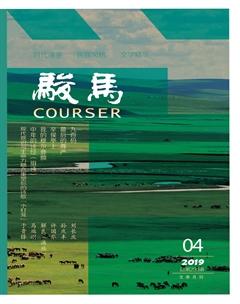现代意识与生命力融合重塑后的诗歌“小灯笼”
于贵锋
现代诗的自我教育,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看网络上对现代诗的大面积抨击,以及理由的驴唇不对马嘴时,有此想法。在重读到《探索诗集》中,那些三十多年前的诗文本,和袭小龙先生那篇《诗人探索着的世界》时,再转头看现状,甚至都有些“杞人忧天”般的绝望。而张凡修的诗歌,却提供了一个体现足夠难度的、典型的,而结果令人欣喜的案例。
在诗歌现场的人都知道,截止目前,张凡修出版了《丘陵书》《土为止》《地气》《隔着绿篱》《月光干草》等五本诗集。即便单从诗集名也可以看出,他的诗离不开泥土,有一股“地气”。事实也是这样,张凡修曾被评为“中国十大农民诗人”,这多少反映出他的题材视野和精神源头。但当翻开这些诗集,一首首读过去,突然又会发现,这些诗出乎预料,和大量的乡土诗,无论在写法上和意识上,都是那么不同。一句话,现代性的浸淫,让张凡修特立独出,在摆脱现实主义固有意识形态理念对诗歌限定的同时,又从泥土深处汲取着养分,借助强烈的生命力完成了意识和语言在诗歌上的深度融合,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整体观照和探察时代景观的艺术能力。
这其中的不易及其难度,更让人钦佩,尤其当下,还有那么多写作者满足于浅表的乡村抒情的时候。是的,乡村、农村、泥土不是不可以写,对那些出生农村的诗人来讲,这是他们几乎无法割裂的。但问题就在这儿,必须不等于必然:写作,写的是生命的经历,是在自己的生命上打下烙印、甚至生根的事物。无论喜悦与高兴,谴责或赞美,都必须被生命意识浓烈地渗透。这是最基本的前提。
写作,我认为不是跟着变迁的美学潮流走,而是跟着生命走。在跟着生命走的同时,若能与随时代应用而生的美学相融合,那才叫“写作面对了时代”。可以说,张凡修做到了。
若要做到不浮泛地抒情,就必须依托于事件和细节。张凡修写有大量与母亲有关的诗,像《稀释》《冻土》《余烬》《尽头》《藏在火焰里》《啃春》等,每一首都有一个“事件”,比如《尽头》,就是写母亲栽秧、自己打井水供水这样一件事,中间强化了“把脸埋进叶蔓”“接续绳子”等细节。在整体的事件框架中,内在情绪起伏跌宕,但不滥情。可以体会到,如同水流一样,漫过并渗入秧苗的根部,那些秧苗挺了起来,存活了下来。这些诗几乎首首精彩,情感饱满。
当然,这里面还是面临着选择。如果我们习惯于假大空一类的高腔高调,就不会作出改变;同样,如果我们不把叙事/叙述作为促进诗歌成长的重要元素,同样也不会作出改变。显然,张凡修接受了来自艺术本身的吁请,改变是明显的。
还是那首《尽头》吧,它体现着张凡修如下基本叙事观念:事件不仅有事件本身呈现的意义,而且必然有一种“支撑”与构筑:一种对生命情感的“跌陷、提升,循环有序的支撑”;即便如《尽头》等诗中在写母亲,但母亲的爱不是单纯的“自然之爱”,而是包含着辛劳和付出,是在生命成长过程中体现在行动和具体劳作中的呵护,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可以说,叙事是为了建立并形成事件中人、事、物等相互之间的生命和情感关系。也就是说,诗人的抒情是有依存的:依存事件,也依存事件中的关系。
这种基本的叙事观,为张凡修打开自己的叙事通道奠定了坚实的结构基础。就艺术实践来看,总体上可概括为重塑和融合。各有生命感受和艺术上的偏重,但几乎是互相作用,互相生成。叙事带给诗歌结构的优势也是明显的:相比纯抒情,它让结构更为稳定;特别是诗歌本身和事件本身结构咬合紧密的时候,诗歌的结构甚至具有了厚重的形式意味。
像是作为叙事的例外,张凡修在《诺言》一诗中“直接抒情”。细辨,他还是把抒情建立在一种稳定而又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关系和结构上。其中的消逝带来的不安和担忧,并不代表这种关系会存在情感强度不足的问题,只不过,爱以另外的一种心理状态体现了出来。而这一切,来源于“关系中的时间意识”。任何一种关系的建立或持续,都会与时间有关;或者说,都发生在时间中。已经发生的事,既有事实的过去性,也有记忆带来的现在性、当下性。在张凡修的时间意识中,“写下那时”,显然是在时间中“推远”,而不是靠近或拉近;而一旦“握住瓢把子开始舀水”,把记忆中的事件坐实,“字就消失了”。改变这种“失真感”,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情感、事件和时间共存!换句话,这种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幻觉或“错觉”,是一个“瞬间”。在诗歌推进中,诗人借助细节和情感的延宕变化,将这个“瞬间”拉长了。诗人的取舍,让已经发生的在瞬间“继续发生”,把抒情关系牢牢地建立在了生命的时间关系。
不可否认,这个瞬间具有历史性也具有当下性。由此拓展,横在诗歌和生命中的裂痕,被开始弥合——当然,这种弥合行为,也可以来自生命和艺术直觉。
题材上的转变,或者说意识上的转变,我并没有细察张凡修是何时开始的。不过,这转变确实发生了。就题材而言,前期的作品,更多取材于农村经历,那是一种记忆中的经历;而到近几年来,农村题材成为一种背景,并且这背景在不断淡化;或者说,农村素材和其他正在经历着的大小事一样,都被时间和生命,作为当下日常生活和生存的一部分,开始加以观照。虽然,他最拿手和感受最深,写得最好的,还是得自于农村那段深厚的生活积累和生命经验的诗,但可以明显看出,他已经能够剔除题材本身带来的固有诗意对诗歌目的和方向的“固有”影响。我确信,他把一种生命的经验和体悟,已经转换成了一种写作技艺和诗学追求。
需要辩驳的是,长久以来,或者我认为,现代诗中的一个较大的误区就是:关于农村题材的写作,都是非现代的,都会因题材本身携带的固有意识,减弱现代性的强度。不可否认,农耕意识对现代性的偏离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但是否具备现代性,就农村题材而言,我认为就看是否体现出了对农耕意识的现代性观照,以及更为重要的,就是把那些“农事”是否确实融入了生命感受和生存境遇中。现代诗的根基,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就是基于生命感受和生存境遇的当下的存在意识。而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典范,比如弗罗斯特;甚至法国诗人雅姆,也具有很强的现代性。
张凡修完成这样的转换,当然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并在其作品中被语言、技艺和意识等所呈示。《被看见》中,有“他们只盯着红松林与玉米林/不可捉摸地,发呆”这样的句子,其中“红松林和玉米林”,明显地指向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借代直接、稚拙。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它们构成了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部分,但没有达成内心的“一致”,有你是你我是我、各自強调存在的味道。
这种语言上的疏离感,至少从两个不同的向度,体现出融合的努力。
一方面是对“引用”的发展。张凡修有相当数量而质量也非常好的诗,像《我有黑暗》等,引用了其他诗人的诗句。这种“引用”,或顺接延展,或丰富内容,或反转其意;有的属于借用,有的属于化用。可以说,妙用“引用”,在张凡修做得比较充分。而基本的效果就是通过语感的变化,以陌生感提升诗意,以疏离形成诗中事物与内心相对应的现实结构。
另一方面是两种或多种事物(事件)间的呼应。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几乎成为张凡修的“基本技法”。比如《水流》,在做火烧和面,与“河流暴涨时夹滩被吞进吞出”,有一种大的对应框架,而后水和河流、夹滩和驴之间有小的对应,如此等等。这类诗,明显可以看出,他往往从自己最熟悉的事情(比如做火烧)入手,找到依凭的意义或经验结构,再与触动自己的情景或事件对接,在呼应中找到相同或相异,并在结尾或合一(像树干)、或分述(像开花)。
语言和技艺层面,终究反映的是内在的意识。前述疏离,不仅是“分析”出来的,而且张凡修通过诗歌也在“自我陈述”。《框定》起句就是:“碱泥里泡大的我无论从哪个方向走出家门/都要踩一脚碱”,就像是自我辨析。碱泥,这种根性的事物是浸透进生命的,它不仅是某一阶段经历的“意象”代表,更是人生的质地,艰难而坚韧。这不仅是事实,也有表达的诚实。而且这种“框定”带来的是“走出”、是“另一种可能”,是“钻进不透风的雨中,大限度发挥这样的框定”,就像“在替庞大的风/框定/旗的边棱”,展示的是一种生命的不同形态和巨大的张力。另外,张凡修的诗中,“夹滩”“楔形物”等物象反复出现,经过语言和时间的打磨,变成了对应于作者生命体的“意象”,它们不断被观看、描写、扩展、浓缩,而有两个基本内涵未变:一是在固定的位置;二是这位置在其他事物的缝隙。这必然形成不同位置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依存之外,是对立,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在对立中依存,在试图消解中牢固,在平静中紧紧抱在一起。这样的形象,像“负伤的红薯”(《出口》),在撒上泥土后可以继续生长;是尖锐的,疼痛的,但也有如楔子一样把其他事物“团结”在一起的本体意识和生命的满足感。
按《夕歌》中的说法,张凡修的诗是“磨道里的混音”。而一个“捻”字,不止是一种指法和技法,更是一种来自身体(指肚)和生命的细微辩认。他不喜花哨的泛音,也不喜表面(平面)化的假声。他很好地运用“断音”完成节奏与呼吸的转换,给诗行带来不同的变化。
在呼应中疏离的方式,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内或之外的结果,那就是诗歌结构的完整性。起承转合,张凡修作诗,确实很是讲究。除了呼应所要求的事物之间必然的咬合带来的紧凑之外,“过渡句”的使用,尤显良好结体、结构和融合意识。像《水流》中,“一直低着头走”带来的外在和内在视角的转换;像《我有黑暗》中,“我可以转身/阴影转不了身”,在反转中的衔接和融合等等,都值得细细体味。
语言中的变化也显露出来。《虚幻之物》只有两行:
“以另外的方式”,你认出那光芒
饼干桶塞入一只矿灯
而其中蕴含的力量,令人震撼。依然是将意义附着于物象和形象,但更加凝练、简洁,有很强的冲击力和爆破力。从题目到两行诗,似乎都是虚幻的,无着落的,但感觉又是如此的结实;矿灯与饼干桶之间的虚实互生,也令人叫绝。这样浓缩了生命的诗句,正如矿灯,瞬间便照亮了人的内心,也照亮了诗句本身,照亮了诗行间的空隙和饼干桶内部的黑暗,具形光芒,写出了“光芒”的形状,把“虚幻之物”移到了生命中。凭《虚幻之物》,张凡修就是一个优秀诗人。而《月光干草》那样的杰作,也正是从语言中“剔除”了杂质以后出现的。
行文到此,我想该说说那个“揉”字了。写到栗子时,诗人有一句“褪尽硬壳脱落后的内膜/需一生的雨水”(《未及》),雨水起的是浸泡和剥蚀的作用;而内膜作为栗子的一部分,作为栗子的附着物,要“褪去”并露出纯粹的栗子并不容易。诗歌其实也一样。只不过在张凡修的诗歌中,“雨水”会被其他的事物或行为所代替。无论是在语言上、技艺上还是作品样貌上,张凡修的诗都体现了一个“揉”字,就是把不同的事物揉在一起变成一种新的事物。前面已经提到,语言本身(像“饼干桶塞入一只矿灯”)就是在“揉”,而“呼应”也是揉(寻找黏合面与水的度),而坚硬的外壳和柔软的内核这一作品样貌,也是“揉”。石头与流水共生,这当然是好的作品;刚柔相谐,当然也是。但就诗歌创作而言,却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因为还没有达到内外无碍、浑圆融通的境界。就像和面时,把面里面的疙瘩揉没了,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力道和功夫。张凡修的诗歌经历了把不同的事物打碎了揉在一起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必然的技巧和结构痕迹明显的阶段,也经历了题材本身带了的诗意间隔的不协调,到《月光干草》《所幸》等作品,达到了刚柔相济,形成了诗歌的合金;而对应着,也在经历生命的诸多“伤”之后,把悲喜、把不同经历都揉合在了内心的感受中,打通了生命中时间带来的阻隔,重塑了生命。把生命感受与诗歌本身,在一种现代意识观照下实现融合,并非每个诗人都能做到,而张凡修,他开始达到这样的境界。
生命融通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能够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以内视之眼,穿透“夹滩”的上游和下游。也惟其如此,才真正有能力把“外物”纳入内心,并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再看《汉阳造》,就知道一个学历不高、出身农村、经历平凡的诗人,如何把素材打碎重塑,写出自己的近代史观了;甚至可以在《凝视》中,体会到与生存现状对应的一种结构,有一种潜在的、深刻的社会视野;而《剥蚀》等诗,也可理解为,稻草人抑或生命被纳入了一个时代背景中观照,在疼痛中显露出光芒。
“她接受了被限制的战栗”,但“随之撑起一切”。这不是简单地归结为命运,而是对命运的深刻理解。张凡修,以自己的优秀诗篇,表露了对生命力、语言和艺术本身的高度信任。他对诗歌的热爱,并没有被琐屑和充满挫折的生活所消磨,而是将这些生命感受,变为丰富的营养,化入了诗行,“揉圆了太阳”(《我有黑暗》)。他实现了生命和诗歌的“转身”:“无数的小灯笼/必然,亮起来”。他以自己的生命和诗歌经历,成为时代和诗学变迁中一个可能弱小但醒目的个体。他成为了他自己。
结语:
以上文字写完放了一个多月,我一再审视,这些文字。在我又不断翻阅他的诗集,和我读过的一些诗歌比较,甚至放到一个较大的时代背景中去估量后,我还是坚持我的判断:张凡修是一个真诚生活,将写作融入生命,试图与这个时代的语言形式靠近并试图有所变化的优秀诗人。诗歌的现代性改变,起初于他或许不是自觉的,但在长期的停顿之后,他并没有去拒绝,去躲在“现实主义”和古典的传统房间里不停埋怨,而是积极汲纳和拣选与自己的生命有关(不管是相融还是冲突)的部分,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景。这不仅于一个“扎根”农村,受过被意识形态支配的“现实主义”根深蒂固影響的诗人,对于当代许多借助对现代性危险的警醒而实际在反对现代诗的年轻诗人,都是绝对困难的。张凡修完成了这样的改变,并写下了许多值得反复品味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优秀作品,再一次体现了真与美如何在一个诗人的写作中借助生命力完成了裂变与再次凝聚。从他新近出版的两本诗集看,无可置疑,他仍然会提供新的阅读期待,并且诗歌中那种看似“过渡性”的谨慎意识,正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在生命中的真实投影,有一种看似笨拙但坚实的生命和艺术结构互相支撑与生成,克服了抒情过程容易出现的不稳定感和情感或情绪的无根性。他是新诗百年历程中,一部分诗人如何沉浮、如何拯救自身写作的缩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如写作的根性、自觉性、探索性、生命独立性上,他虽然“名头”不响,但仍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个案”,因为他立足于对诗歌本身的执著与热爱,将语言和生命紧紧地揉进了每一首诗中。他的生命以及诗歌,一直在这个时代的生存现场、诗学现场,这对一个诗人而言,并非可有可无。即便是一个个体、“个案”,力量不够强大,但那个紧密的时代结构所露出的一点缝隙中,我还是听见了诗人的呼吸。那些诗歌的“小灯笼”,正是一个诗人转身的引领者,也是一个诗人转身的结果。我喜欢这些诗歌的“小灯笼”,因为它们来自于生存的艰辛与生命的坚韧中,来自于对一切美好事物的不懈追寻与持续的热爱中。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中的艰辛,在成就他的写作的同时,就我所了解,并没有损毁他的心性,而是不断地丰富他的内心,让他的生命质地更为坚实,诗歌之光从内部增加了他生命的亮度,生命和写作之间,完成了另一个层面的重塑和融合。
责任编辑 五十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