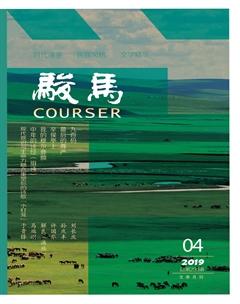我的穆尔登额
解良
夜央时分,我从森林中的一幢小木屋里走出来,攀上一座山峰,去看“穆尔登额”。这是一句满语,即天边晨星。在山峰的周围,正在接受时光漂白的墨云冥雾像一场天然森林大火过后野地上落下的厚厚一层灰烬,一颗颗晨星似埋在灰烬里还没熄灭的火星,晓风轻轻吹拂,它们在灰烬中一闪一闪地发光,幽如豆火,在黎明的鼠皮色里若隐若现。这时候,我看见一颗大而亮的行星尾衔东方地平线,临高启明。于是,这一幕景象便印在我心中。许多年之后再度回忆森林木屋村的这次同学会,最令我难忘的就是照片之外的这幅“穆尔登额”。
满语,用满文书写。有人将满文比作穿越历史时空的流星体,留下一条璀璨三百年岁月的光迹,隐身而去。时下,说满语、识满文、能书写满文的人仍晨星可见。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满文的窘涩。
我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当兵,还乡后见县民委办公室写着双语门牌,左为汉字,右侧书写着我在草原上目染了三年的蒙古文字,当时我对家乡新宾的历史知之甚少,盲翁扪钥,找人去问蒙古文字与家乡有何渊源,结果被打脸,知情人告诉我,这是满文,满文是参照蒙古文字的字头创制的。我家乡新宾的佛阿拉城就是老满文的诞生地。知情人并没有羞辱我,我却有点抬不起头,内心的尴尬一直伴随着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就感到脸上发烫。这种内心的纠结就像隐私,我没有公开,却在暗中悄然探询满文的前世今生,以此来弥补自己的无知。
还记得我第一次倾听满语朗读的心动。
家乡还有一座赫图阿拉城,这座古城因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这里创建后金政权而青史垂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赫图阿拉城南门下,台地上有一所启功先生捐助的满族小学,校舍被一道柴栅墙圈起来,栅栏上爬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几幢教室是用砖和石头加黄泥垒起来的,屋檐下露出一个个椽子头,麻雀从椽边的小窝里飞出来,落到房脊上叽叽喳喳叫。这年春天,大雁从南方归来,小学校里有一位中年男老师在课堂上教孩子们朗读“曼珠,乌克素啦”,我仿佛听到大雁在长空中吟唱鸣啭。孩子们双唇抖动练习发大舌音,让我想起儿时与小伙伴在苏子河里洗澡的往事。孩子们每人嘴里含一口水,仰起头,对着太阳眯起双眼,舌头翻卷着嘴里的水,发出“嘞嘞嘞嘞”的声音,看谁持续的时间长。满语大舌音就是通过舌头在发音部位颤动发音,教学中还真的有嘴含一口水练习大舌音的“呛水法”。一位音乐老师说,完美、纯正、连续的舌尖震颤,发出的声音清脆悦耳,美妙超出你的想象。
还记得我拿着手书的满文字体比对家乡山水的那份兴致。
家乡的佛阿拉城现今只剩下遗址硕里岗,这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山城在公元1599年圆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民族文字梦,老满文在这里几经阵痛,像一个婴儿在盘有火炕的“口袋房”里落草,像一支歌,先在硕里岗上唱,随后走下山岗,唱遍了整个民族。清史馆校勘奎善在为《国语志》撰写的卷首《满文源流》一文中这样形容满文:“满洲故里多山林,故文字矗立高耸,如古树,如孤峰。”他说的满洲故里即我的家乡新宾,这片土地一如奎善所描述,群峰峻拔、大树参天,又与满族先贤有翰墨缘,老满文的两位研制者——额尔德尼与噶盖一缘一会,撑起老满文的骨胳;这时,一个土生土长的语言神童已经悄然来到二人身邊,只是尚未引起人们注意。被后世誉为满族圣人的达海出生在佛阿拉城西北不远的烟囱山下觉尔察地方,年仅四岁就跟着父亲艾密禅来到佛阿拉城追随努尔哈赤,成为额尔德尼的弟子,九岁即精通满、汉文义。三十三年后,达海遵照皇太极的旨意,凭借新宾人文地理赋予他的聪颖和灵性,在沈阳完成了对老满文的充实与改造,让新满文借天籁之音,潜山岳之形,圈点字头,箭标句逗,建构了满族语言的新体系,成为有清一代的国书。
我为自己能够出生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而骄傲,家乡山水秀,犹怀翰墨林。我找来直立书写的满文字体,像鉴宝一样行走在家乡的山水间,在满文字体里寻觅家乡景致,用峰峦树木比对相似的满文字体,兴致勃勃。烟囱山,满语呼兰哈达,立在峰间的那根高高的像烟囱的石柱形似满族先人的图腾柱,犹如满文的一个字头。苏子河满语为苏克素护别拉,我在她的九曲十八弯的形体里找到了满文的字牙、字圈、字点和字尾。我踏察辽宁屋脊岗山“足音空谷”的脚印峰,“微距”木奇古榆树雄浑苍劲的身影,往返于历史与现实、文字与风光之间,感受着形似与神似,仿佛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我与满文的美结构在一起。
人都有遗憾,有些可以弥补,有些只能叹悔。我一直生活在新宾这座历史文化浓郁的古城,一出溜便人过中年,看上去已经很像一个文化人了,对于满语满文仅仅是知道个大概而已,既不会说,也不会写。有一年我写传记文学《代善》,想知道主人公名字的含义,只好求人给翻译。县内有三两个这方面的专家,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送包烟,请人喝一顿小酒,人家都给面子,只是我心急,恨不能马上知晓“代善”的意思,但有些满语词汇专家也非张口就来,还要回去查辞典才能翻译出意义。代善满语意为“哭闹,捣蛋”,求人等人的滋味险些酿出我同样的孩子气。这之后,我每用一个满语词汇便求人一次,等得心焦,久而久之脸皮越变越薄,嘴也张不开了,几曾下决心要自学满语满文,只是当时满哪儿也找不到教材,就近也没有学习班,互联网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便泄了气。
那时,我觉得自己与满文有缘无分,便转头忙碌生活去了。进入互联网时代,我隔三岔五就能从网上以及少数纸媒和书箱里读到一些用汉字标音注义的满语词汇,这些词直观、形象、生动、鲜活,与大自然关系亲密,如蟫叶黏霜、蛛网黏絮,能让我产生许多联想,缘情体物,于是我在电脑里自建一个文档,不经意地收藏这些词汇。网上时常有热心满族文化的人挂上各种汉译满语帖子,我四处拼取,探骊得珠,这里采摭几句谚语,那里收获一段俏皮嗑,一条一条地攒,像儿时积攒一分二分硬币放进储钱罐一样,我的文档里渐渐有了一点库存,虽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但为文需要时打开文档挑选,“贤能”为之用,乐在其中。春山如笑的季节,有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进城市周边的一处草莓采摘园,在园中随心所欲地采摘,满载而归。梦醒后,我突发奇想,给我的收藏文档取名“穆尔登额”,变收藏为搜集,搜集汉注满语词汇,丰富自己的语言。我用“穆尔登额”这个名字提醒自己,你要搜集的文辞寥若天边晨星,持而宝之,贵在坚持,一片如草莓采摘园一样供自己随意撷取的汉译满语词汇小园子才会金桂飘香,如你所愿。
当然,我没有把这种搜集当成一个专业,只做业余的“淘宝”者。
人间有书海。我将一只小舢板划到茫茫的大海上,像搜索先人百年前投放的漂流瓶一样寻找,得知世上曾有过一种活泼有趣的教材,民国之前流行于满族私塾的话条子——右侧书写一个满语单词或例句,左边用汉字标音注义。我没有找到整本的话条子,只找到一句满族土语“趟子直”,仿佛看见一匹彪悍的骏马“一马三箭”地奔跑成一条直线,一溜烟,不拐弯儿;世上有遗宝,我又去做“拾荒者”,在家乡的一条河边拾到一本掉页飞边的《满语地名考》,身边这条河的流水声似满洲先人射出的哨箭发出的啸声,哨箭满语“占贝”,这条取名“占贝”的河流让我看到了满语描绘的各种水姿,有流水湍急不结冰的地方,秋水消减露出的潲脸儿,鱼游在水下造成的水纹,还看到一条船那么大的狗鱼。传说中满族先祖乘着船那么大的狗鱼沿着松花江来到长白山地区。满语“苟仁尼玛哥”意为像船那么大的狗鱼,这只“祖先之舟”带我心游万仞,悬想示现;乡间有野趣,我又像一个山村里的孩子,去剜野菜,拾稻穗儿,在田野里看见一个唱曲的少女。茶茶咳勒,满语即少女唱曲;远方有梦想,我追寻着一阵悠扬的琴声来到北京的一个满语沙龙,在这里碰到一位寻找“雅图翰”的东北姑娘。雅图翰,传说中的满族古筝。琴声引出我歌唱的欲望,于是,我为家乡唱了一曲《遥远的赫图阿拉》:
日出长白依格啦
月落呼兰哈達
苏子河边围柴栅
马蹄行歌山对答
汗王的城在山岗上
启运的鼓响天下
啊,遥远的赫图阿拉
天眷满洲力亚
我梦寐的故乡
给我姓氏哈苏里哈拉
在我的唱词里,储存在“穆尔登额”里的词汇你方唱罢我登场。伊格啦,是满族民歌的衬词。满洲力亚,满语意为吉祥幸福平安的土地。我唱第二段的时候,又用了亮红朵子和嬷嬷人,亮红朵子是人参花,嬷嬷人是满族民俗剪纸的俗称。
亮红朵子开红花
嬷嬷人做年画
传说中的雅图翰
茶茶咳勒弹着它
古井的水一掬乡心
绿树村边话桑麻
啊,神鹰飞过赫图阿拉
我穿旗袍回家
享受吉语忂谣
带回祝福呼突里波也阿
我的“穆尔登额”在我的生活里寥若晨星,又灿若晨星。每当我感到自己想象乏力的时候,就会打开它,挑选一个黏着乡土气息的既陌生又新奇的满语词汇,让它统领着鲜活的语素进入我的心灵工作室。这时,我就像坐在一面山坡上,山野里吹来的阵阵清风会拂去我的审美疲劳,激发起我对美感的新一轮追求,诱发出我新的想象。
责任编辑 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