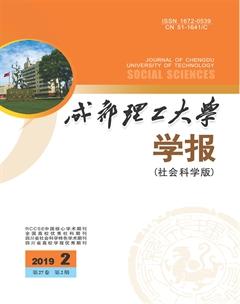心灵阅读视域中的嵌入叙事
管海佳
摘 要:认知科学中的心灵阅读与叙事学中的嵌入叙事的结合为研究《洛丽塔》中两位主人公——亨伯特和洛丽塔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心灵阅读的映照下,拆解嵌入式意向性,通过微观嵌入叙事构建的亨伯特的精神困境将更加直观地展现,体现了作者的精妙操控。宏观嵌入叙事包含了亨伯特、夏洛特和圭尔蒂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展现了洛丽塔从顺从到反叛的心理历程、乱伦的家庭诱因以及绝望困苦的心理状态。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的结合使得两人鲜为人知的心理状态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展现,构建出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唤起读者不同的阅读情绪。
关键词:洛丽塔;纳博科夫;心灵阅读;嵌入叙事
中图分类号: I712.07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2-0068-07
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从1955年出版至今,热度不减。阿尔弗雷德·卡津称纳博科夫为20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伊哈布·哈桑认为他是对战后小说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人物。其独特的主题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更刺激了读者隐秘的好奇心。但其文学价值绝没有因为其富有争议的主题而减损,学界对作品本身的关注从未削减。其精妙的叙事技巧、独特的语言风格等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洛丽塔》的两位主人公——亨伯特和洛丽塔的形象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读者通常认为两人的形象构建依赖于叙述者以及背后的作者,但聚焦于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理论,可以发现,亨伯特的心理状态在微观嵌入叙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洛丽塔的情感变化也在多个人物的宏观嵌入叙事中完整地展现。微观角度的分析使亨伯特细致入微的心理变化一览无遗。宏观角度来说,多个人物通过心灵阅读构建的洛丽塔形象更加丰满与复杂,实现了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
一、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
心灵阅读(mindreading),亦称为心靈理论(theory of mind),是认知心理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与所谓的“心灵感应”并无关系,其核心含义为“人们通过解读他人的行为来推测其思想、感觉、信念和欲望”[1]6。心灵阅读能力显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这一能力受损的典型病症便是自闭症。除却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心灵阅读也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者通过心灵阅读构建人物及故事,读者借由心灵阅读来推测人物情感、欲望以及作者的意图。一方面来说,小说能够“欺骗”我们的认知机制,赋予读者在场感,使读者进入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另一方面来说,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心灵阅读机制“时刻待命,观察叙事中的环境变化,以期寻找输入的条件”[1]10。心灵阅读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机制,是构建虚构作品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在小说研究中有过度泛化的趋势——优秀的小说从不同层面彰显作者的心灵阅读能力,也拷问读者的心灵阅读能力,甚至将这一能力推到极限。
嵌入叙事(embedded narratives)意为叙事中的叙事,也被称为元叙事。巴思(John Barth)称这种叙事策略为“故事中套着故事”[2]218。内尔斯(Williams Nelles)在《故事中的故事:叙事层次和嵌入叙事》一文中指出:“‘故事中的故事又被称为‘框架叙事‘中国套盒‘俄罗斯套娃‘嵌入叙事。它被广泛地运用于任何文化背景、任何时期的叙事作品当中,几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叙事技巧。”[3]79嵌入叙事是一个基础的概念,在不同理论的关照下,可以对文本形成不同的解读。尽管学界不乏对嵌入叙事的研究,但极少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解读其中蕴含的认知机制及其对文本和读者产生的作用。
帕尔马在《虚构的心灵》(Fictional Minds)中首次将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结合,探究嵌入叙事的产生机制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认知机制。这个机制便是连续意识框架(the continuing-consciousness frame),是作者构建虚构的心灵所依赖的机制,也是阅读他人心灵必不可少的机制。其运作过程中,大量现实世界的、结构化的知识会被引入,达到理解的目的。首先,作者能够通过连续意识框架构建叙事与人物形象,甚至可以将人物的意向、欲望和情感嵌入叙述者或其他人物的情感中。其次,读者可以通过连续意识框架阅读人物的心灵——在《洛丽塔》中,尽管某个特定人物的信息并非集中呈现,而是分散在不同的章节和不同人物的叙述里,也不妨碍读者对人物的理解,因为读者可以调动连续意识框架来将所有的信息点串联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叙述者对人物的心灵阅读,人物对人物的心灵阅读,人物对群体的心灵阅读,群体对人物的心灵阅读,共同编织嵌入叙事的网络。这个网络不仅仅是单层嵌入的,还可能多层嵌入,挑战读者的认知能力。
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的结合给文学评论带来了丰富的启示:读者的心灵作为原域(source domain)投入故事世界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使得读者直观感受虚构心灵的精巧运作;将连续的虚构意识(有些人物意识可能信息量极少)构建成完整的人物形象,使得阅读的过程不再是“读者静态的接受过程,而是更加动态的创造过程”[4]178;读者总是趋向于通过阅读获得最大的认知体验和信息量,这本质上挑战了读者心灵阅读能力的极限,赋予读者更大的阅读快感。与以往的嵌入叙事研究不同,心灵理论视角下的嵌入叙事不仅包含了宏观视角下“叙事中嵌套着叙事”,更有微观视角下的“意向中嵌套着意向”“心灵阅读中嵌套着心灵阅读”,为理解作者的叙事手法、人物的情感变化以及读者阅读中的认知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微观嵌入叙事
嵌入叙事从宏观角度看,可将关于一个人物完整的叙事嵌入到另一个人物的叙事中。从微观角度看,可以将意图和情感嵌入到意图和情感当中。相比之下,微观角度可以构建多层的嵌入式意向性(Embedded Intentionality)。嵌入式意向性是心灵阅读中独特的一部分,詹塞恩在《我们为什么阅读虚构作品:心灵理论及小说》(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中详细讨论了这个概念,其概念便是“人们追踪叙事中多层意向的能力”[1]28。心灵阅读本身便是二层意向,例如:“我认为A想要B”。同时,意向具有多层递归性(recursiveness),例如:“我认为A知道B想要C知道……”便是典型的四层意向。意向的层数原则上可以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认知结构限制了这一趋势。大部分人能够有效处理三层或四层意向,虽然认知上已经过载。但面对五层和六层意向时,大脑很难准确追踪意向中的对应信息,甚至可能出现误读。文学中,有些文本晦涩难懂,往往就是因为多层嵌入意向的出现。嵌入意向不仅挑战读者心灵阅读的极限,“同时也会将读者的情绪推向边界,使读者情不自禁发笑或深受震撼”[1]31。不少现代和后现代作品正是利用了多层嵌入意向,立足于人物意向的军备竞赛式累加,给读者增加了阅读难度。
(一) 回溯往事:亨伯特的精神困境
于晓丹曾指出亨伯特形象的特殊性:“他虽然与现实社会发生着某种关系,但他似乎对事业、职分、等级、权力等字眼所代表的现实性均不感兴趣,他似乎更从不关心政治、宗教、社会问题或日常生活中的新闻事件。”[5]75在纳博科夫的笔下,亨伯特似乎只为追逐洛丽塔而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亨伯特的形象将趋向于扁平,他是作者构建的“极端个人化的、化了妆的艺术家,是一个从社会人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意识形象,这个形象敏于思而慎于行”[5]75,也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具有极强“自我意识”的人物。亨伯特的生活游离于“整体现实”和“个人现实”之中,两个现实中形成的巨大张力,使亨伯特陷入困苦的泥淖,难以自拔。亨伯特关于自己精神困境的叙述往往累加了多层意向,仔细挖掘,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的痛苦与挣扎:
“在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我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这种幻想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并且促使想象中的每一条线在我过去那片复杂得令人发疯的境界中漫无止境地一再往外分岔。可是,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6]19
在上述自白中,亨伯特试图厘清自己恋童的根源。回溯童年时,大量的意向性嵌入其中,若将其中的意向层层分解,可得到以下五层意向:作者想让读者明白,亨伯特认为“在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我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可是,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
通过将意向层层分解,暗藏在文字间的信息跃然纸上。首先,在这段内心独白中,叙述者经历了三次情感转向:第一次是“苦恼”。在“努力分析自己的欲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作者为“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而感到苦恼,以为追忆往事会“促使想象中的每一条线在我过去那片复杂得令人发疯的境界中漫无止境地一再往外分岔”;第二次是作者感到苦恼的同时,觉得“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认为回忆对自身的分析官能有益;第三次是叙述者坚定地得出的结论,即“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认为自己恋童的根源是童年时代失去安娜贝尔所致。
这三次情感转变,展现了亨伯特对“时间”的焦虑与误解。安娜贝尔是亨伯特回不去的“过去的时间”,于是洛丽塔作为“现在的时间”便成了亨伯特回到过去、重温旧梦的方式。过去与现在的时间注定无法弥合,所以当亨伯特强行将洛丽塔作为安娜贝尔的影子扯入他的个人记忆中时,“时间被残忍地扭曲了,甚至被残酷地扯裂了”[5]76。因为记忆无法召唤过去的时间,纵使亨伯特找到安娜贝尔的替身,她也只能在记忆中鲜活,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现实。时间与现实的不和谐已然为两人的未来染上了悲剧的底色。值得注意的是,亨伯特不仅失去了过去的时间,也失去了未来的时间。亨伯特的叙述在狱中完成,作为囚徒,他的未来便是监狱的高墙和死亡。对亨伯特来说,他回不到过去也没有将来,唯一拥有的便是记忆。在悲剧性的归宿中,他找到了对抗时间的方法——叙述,将洛丽塔永远地留在文字中,使她拥有超越时间的永恒力量。正如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中写道:“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7]68
同时,这三次情感转变也将亨伯特的形象打造得更具体。虽然亨伯特罪行确凿,但他并非一个心安理得的恋童癖罪犯。面对自己与洛丽塔的恋情,他的情绪百转千回,焦灼与无奈隐现在文字中。同时,他的追问与反省引领读者暂时超脱于他的罪行本身,而去思考罪恶的诱因和根源。亨伯特拷问了自身罪恶的本源——“宿命”,看似借口,却解释地恰如其分。亨伯特的罪行无需辩驳,但其原因可以有多种解读。若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看,亨伯特的“本我”过于强大,没有得到良好的规训,追求欲望的即刻满足,导致了犯罪行为。这或许是原因,但不是根源。“本我”过于强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如此追问下去,是否只剩下“宿命”?“每一种悲剧都在编织该悲剧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圈着人和社会的发展,人会陷入不同的生存困境,即从一种生存困境走进另一种生存困境,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8]315两人反道德的“畸恋”与道德高墙的碰撞如同以卵击石,其本质展现的是诗性生存在现实生活中的残酷处境,这便是亨伯特所说的“宿命”的黑白底色。亨伯特的自省实质上呼唤的是读者关于诗性和宿命的反省。
通过将嵌入的意向分解,亨伯特的形象不再只是一个罪恶的符号,反而愈加饱满地矗立在眼前。同时,读者也在层层深入亨伯特的内心,暂时抛却他罪犯的身份,追问小说的深层意蕴。若只是粗略地阅读这段文字,读者也能将其中意思把握个大概,但是亨伯特坎坷的自省路程、作者极力呈现的逻辑递进关系便被忽略了。
(二)形象的颠覆:货真价实的恋童犯
嵌入式意向性在构建多面形象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在前文的例子中,读者层层深入亨伯特的内心,暂时抛却他罪犯的身份,呼唤心底的悲悯,但在这个例子中,亨伯特的形象被彻底颠覆。在这段文本中,嵌入意向不止于上述例子中的五层,达到了六层,将读者的心灵阅读能力推向极限。亨伯特带着洛丽塔周游美国时,在入住旅馆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不知怎么,由于我在那个安静的、富有诗意的下午十分挑剔地四处采购,我竟然想起了具有“着魔的猎人”这个吸引人的字号的旅馆或客店,夏洛特在我获得自由前不久偶然對我提过这家旅馆或客店。凭借一本旅行指南的帮助,我在布莱斯兰那个僻静的小镇上找到了它,从布莱斯兰到洛的营地开车要四个小时。我本来可以打个电话,但又怕自己的嗓音可能会失去控制,讲出一些吞吞吐吐、低沉嘶哑、很不流利的英语,就决定发一份电报,订一间明天晚上的双人房。我是一个多么滑稽、笨拙、犹豫不决的白马王子啊!要是我告诉我读者我在拟定那份电报的措辞时感到十分为难,他们有些人准会对我大肆嘲笑!”[6]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