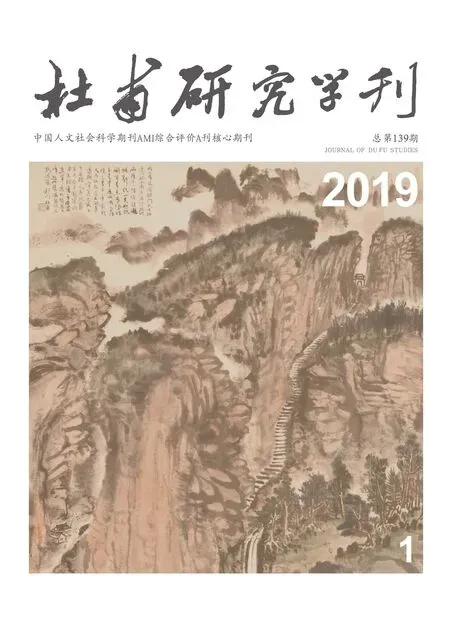乾隆的杜诗观
陈圣争
作者:陈圣争,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675000。
据现存乾隆御制诗文集统计,其存诗约为44028首,文1370多篇。内容包罗广泛,“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不过,庞大的御制诗文集中亦有不少谈论诗文之道的文字,虽然较为零散而缺乏系统,但大致可见乾隆一贯的诗学思想及旨归意趣。
曾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控制的”,这在乾隆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不仅通过扶植诗坛代理人(如沈德潜、翁方纲等)的方式,宣传其诗学主张,更是躬亲上阵,制作了庞大数目的御制诗文,以树立其文化权威形象。在诗歌领域,他在充分吸收儒家传统的诗学观念后,建立起了颇具帝王特色的核心诗学观念,即将诗教观转化为世俗的“忠孝论”——以“忠孝”论诗、论人。为了更好地宣传和让世人理解“忠孝论”,他在考察古今诗人之后,将杜甫树立为“忠孝论”的典型,而杜诗则相应地成为“忠孝论”的标杆。
一、传统诗学观念向“忠孝论”的转化
在传统儒家诗学观念中,“诗言志”被后人称之为中国传统诗歌理论中“开山的纲领”,“温柔敦厚”则自先秦以来视之为“诗教”,二者是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两大基本理论。虽然二者的具体指向层面不一,但基本上涵盖了诗歌的内容、表达方式及艺术审美等层面,故历来谈诗者大都或多或少地用以评论古今诗人、诗歌。乾隆亦概莫能外,其论诗力主“诗言志”、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在御制诗集中有数十处一再强调“诗以言志”。他所谓的“志”,有时是指对事情和心情的记录,如《陕西秋禾被旱歉收诗以言志》《平定准噶尔功成恭上皇太后徽号御殿受贺诗以言志》等诗;有时是指表明心迹,如《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序》中说:“予之所以早作夜思、弊精劳神者,庶可少逭穷黩之讥耳。观斯图也,不啻共将卒之辛苦,实并切心膂之恫瘝。诗以言志,其志亦不外乎此尔。”又《鉴始斋题句》(《余集》卷19)“后记”中亦表明自己临御六十余年诗文多为关心民事、国事而作,并且说“即寻常题咏,亦必因文见道,非率尔操觚者比,乃质言非虚语”的心曲等等。在这些诗文中,乾隆犹如在向他人表明心迹,希冀天下人理解其苦心。


在他看来,作诗就是为了表达个人的心志和情思,不是为了夸耀词藻与别裁。这并非是因为他怕雕章琢句之苦累,而是认为那样容易使心志混乱。诗歌,是用来表达志向的,只是这志向又归于圣贤之道。
且不论乾隆对“诗言志”的认识是否有偏颇,又是否在为他作诗不讲辞藻、不尚雕琢辩解,仅从他一再反复强调这一观念的态度来看,“诗言志”是乾隆一贯的主张。他甚至还希望通过他的身体力行——御制庞大数目的诗歌并以固定年份刊刻颁布天下——并借助官方的权威话语姿态,支持和引导天下文士皆以诗“言志”,以促使整个诗坛树立起“诗言志”的统一认识,而不是陷入各自的吟咏之中,在文辞上“夸别裁”。



随着乾隆政治地位日益稳固,他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也日益加强,并经常体现出他的绝对权威存在。在他看来,传统的“诗言志”之说众说纷纭,容易引起歧义;而诗教观已显得空虚化,对于文化程度高的文官来说或许尚可理解,但对于层次稍低的下层文士或民众则一时间难以普行,而且这一观念也不太容易用俗世的标准衡量。不过,诗教观在伦理道德领域的终极目标就是谐和人心,安定社会,创造一个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下的理想社会,这一导向发展到极致就容易变成世俗化的“忠孝”。

二、“忠孝论”的典型与标杆:杜甫、杜诗
在确立“以忠孝论诗”之后,深谙儒家文化的乾隆深知要在士林或当时社会推行这一观念,强硬的政治手腕或政策性宣传未必有切实收效,而是需要更为文雅、隐性的手段,是以他多管齐下,如扶植诗坛代理人、御制诗文集、组织儒臣编选诗文选本等等。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一方面树立诗文领域体现“忠孝论”的正面典型,让众人知其所归,并以之为标杆衡量古今、反躬己身;另一方面打压“不忠不孝”的反面另类,口诛笔伐甚至刀俎斧钺而绝不留情,让世人有所惕栗,不可随意逾越“忠孝”的红线。





在题画诗中,他从画面上看到的仍是杜甫的忠君爱国的思想:





乾隆为了更好地宣传其“忠孝论”,在正面树立杜甫、杜诗的同时,对在他看来的“不忠不孝”之反面人物的打压亦绝不留情。对于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屈大均等人,当以“忠孝”来衡量时,乾隆毫不客气地詈骂:



三、对杜诗“诗史”精神的重新阐释
乾隆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崇杜甫、杜诗,除了杜甫为人“忠孝”、杜诗总体上“原本忠孝”这一首要因素之外,还在于杜诗体现出强烈的“诗史”精神,通过杜诗可以观察当时的政教人伦。在艺术原则上,乾隆将杜甫雕塑成“忠孝”论的最高典范;而在诗歌的内容上,他又祭出了杜诗“诗史”观的大纛。

工拙非所论,岁月差可征。诗史让少陵,我作方农经。(《捡近稿偶志》,《御制诗初集》卷27)
况乎治乱兴衰具诗史,岂可与批风弄月以为诗者同日而与同时观。(《读杜诗率题》,《初集》卷39)
天地间自有元声,于诗得者惟杜陵。一生出处可概见,千古诗史真定评。(《读杜诗》,《二集》卷10)
治乱当时况,了凭诗史看。(《夕烽用杜甫诗韵》,《二集》卷78)
例视杜诗堪号史(《重刻淳化阁帖颁赐群臣联句》,《御制诗四集》卷9)



由此可见,在乾隆的观念中,凡是他所统治下的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可以入诗。不过这还是在内容上的要求,在价值取向或风格要求上,亦须讲究“温柔敦厚”或“忠孝”。如在描写战争类诗中,就不能表达征伐之苦及战栗之惧等情感,他曾借乾隆四十年(1775)朝考题《赋得“大车槛槛”得“还”字》一诗大发议论地说:


这一观念,甚至在他授意选评的《御选唐宋诗醇》中也有明显表现。如评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其四“谁道君王行路难”(卷5)、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卷9)、苏轼《鱼蛮子》(卷37)等诗,评语皆言可称“诗史”。
这种要求虽然非常过分,但作为那个时代的枷锁,一般人还是难以与之抗争,有的甚至还积极响应这一观念。如纪昀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涉亲家卢见曾盐务案被发配乌鲁木齐,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召还,在三十六年(1771)的归途中,他一路观风俗,忆旧游,作有《乌鲁木齐杂诗》一卷。在序中,他如是说:

由此可见,纪昀《乌鲁木齐杂诗》之作,亦是为了报效国恩,歌咏休明,颂扬乾隆这位圣天子的威德,且在序言之末还特别强调这套组诗的根本目的是用来昭示圣明,而不是作为友朋茶余酒后关于异域风情的谈资。在全诗之后,友人钱大昕所题“后记”亦曰:
同年纪学士晓岚,自塞上还,予往候。握手叙契阔外,即岀所作《乌鲁木齐杂诗》见示。读之,声调流美,出入三唐,而叙次风土人物,历历可见。无郁轖愁苦之音,而有舂容浑脱之趣。……今天子神圣威武,自西域底平以来,筑城置吏,引渠屯田,十余年间,生聚丰衍,而乌鲁木齐又天山以北一都会也。读是诗,仰见大朝威德所被,俾逖疏沙砾之场尽为耕凿弦诵之地,而又得之目击,异乎传闻影响之谈。它日采风谣、志舆地者,将于斯乎征信,夫岂与寻常牵缀土风者同日而道哉!

乾隆对“诗史”如此情有独钟,其心态可能有三:一、粉饰盛世伟业之功,二、表现忧患民生之心;三、炫示个人才学博赡之意。不过,乾隆对诗歌内容上要体现世俗化的“诗史”精神,客观上迫使当时文士从书斋走向社会,用诗歌去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事实上,当时确实有不少人积极响应乾隆的“诗史”观念,主动向“纪实”靠拢(至少面上文章要如此说),如纪昀、钱大昕等人。
四、对杜诗艺术价值的探索



他对杜诗的钟爱,除了一再推崇杜诗之外,对偶像最好的膜拜方式或许莫过于模仿其行为。乾隆自少年时就开始窥得杜诗藩篱,对杜诗就一直在模仿之中。乾隆对杜诗的模仿主要表现有四种方式:一、直接用杜诗原句或将原句稍微改写,二、化用杜诗句式,三、模仿杜诗的特殊结构或表达方式,四、用杜诗之意自成诗或“和杜诗”或叠杜甫诗韵。



第四种方式,在御制诗中数量虽相对较少,但因全诗或用杜诗之意,或用杜诗之韵,实际上更体现了对杜诗的膜拜和亦步亦趋之情。如乾隆十年(1745)年所写的《落花诗》一诗:

在诗注中明确注明曰:“用杜甫诗意”,其所用之杜诗当是《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一诗。杜甫这首写于晚年漂泊状态的“落花诗”,实际上从落花的境遇感慨个人漂泊、人情冷漠之状,但在诗中亦流露出杜甫的自傲之情。乾隆此诗虽是用杜诗之意,但在诗体上与杜诗却不同制,杜诗为一七言古诗,此诗乃用七律出之。其中“踪迹飘飘杜甫蓬”句,乃寓杜诗“飘飘何所似”与“老病有孤舟”二句的无所依靠而漂泊孤舟之意,这也与杜甫“落花诗”中“吹花困癫傍舟楫”一句的境况类似。尾联二句更是化用杜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句式而来,亦与杜诗原诗一样表达了落花孤傲而自信的内在品质。
又如《和杜甫〈遣兴五首〉》组诗曰:
天用莫如龙,用吉见无首。变化故莫测,神功在不受。凭云乃自为,撄鳞亦何有。豫且得制之,是宜慎所守。
地用莫如马,水行不如舟。物各有所长,乖宜失良谋。而况鲜伯乐,盐车老死休。举肥肉胀群,常装金络头。
陶潜避俗翁,避俗亦避世。柴桑乐无闷,自著桃源记。肩舆命二子,偶顾亦何害。杜陵忠厚人,个翁乃深刺。
贺公雅吴语,老大故乡回。儿童不相识,问客何处来。可以喻宦况,浮云何系哉。山阴泉石佳,浊醪常满杯。

诗题小注曰:“首句皆仍其旧,而意自别”,每诗首句确是用杜诗《遣兴五首》原句,不过各诗的用韵、用意与杜诗则异。杜诗第一首所表达的是天意难测之意,御制诗乃是表达慎守的观念;第二首是突出千里马不同群种间的怀才之意,御制诗则是突出在于遇与不遇的问题;第三首是认为陶渊明虽自命隐士,却并未真正地达观而通透,御制诗则陶渊明可作避世之人,但对其子又有所期待并不影响陶渊明对自己行为的选择;第四首是感慨贺知章的清狂自傲少有同道者,御制诗则是认为宦海沉浮不如泉林之乐;第五首是抒发对孟浩然怀才不遇的同情,御制诗则认为孟浩然风雅之意自有人知。御制诗与杜诗立意的不同,乃在于乾隆与杜甫二人所处之位与境不同,杜甫在诗中将个人身世境遇之况糅合在所咏之物与人中,作为君主的乾隆则从俗世的至高点来俯察世间人与物。
五、余论
综上所论,乾隆的诗学主张,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并由他的特殊身份所决定,但反过来又对整个乾隆时期的诗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其核心诗学观念“忠孝论”,是他意识到传统的诗学概念颇有分歧且日渐虚化后,对之进行了他独特的改造而成,其实质是以更简洁、更直接的方式指出诗歌需要干预生活、干预现实的特征和方式,当然这种干预是以“忠孝”为限制,强化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而为了宣传和推行他的“忠孝论”,采取了各种手段,尤其是正面树立杜甫、杜诗为“忠孝论”典型、标杆的行为,对当时诗坛、士林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乾隆对杜甫、杜诗的推崇,除了这一深层次的原因之外,还在于充分挖掘杜诗的“诗史”价值,并进行重新阐释为诗歌的纪实性,以便更广泛地去书写和纪录当时的社会情形。此外,还在于从文士的角度和立场,借鉴、欣赏杜诗的艺术价值。
纵观乾隆对于杜诗的认识,不乏出于功利因素而存在有失偏颇甚至扭曲之处,但他以帝王之尊,如此大力提倡和推崇杜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客观上对于清代中期(至少是乾嘉时期)的趋杜之风和杜诗学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释
:①按:乾隆的诗文数目,乃笔者据现存乾隆《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余集》、《御制文初集》、《二集》、《三集》、《余集》、《乐善堂全集》(即位前所作,内含诗文)统计而来。
②弘暦:《初集诗小序》,《御制文初集》卷11,《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第107页。
③按:可能有人疑问其中是否有代笔之作,若为代笔捉刀之作,又如何确定为乾隆的诗学观念?事实上,关于乾隆御制诗的代笔问题,在稗史中有些捕风捉影地零星记载,一些学者也有不少,但谁也没法一一考证,只能悬疑。不过,对于御制诗文的“制作流程”,拙文《也谈乾隆的诗》(《书屋》2017年第7期)中曾略有论述,若将御制诗看作是“制作”而非“创作”,至少可以暂时抛开“代笔”的问题,而将之视为是经过乾隆钦定,至少是代表了他的观念和主张。且乾隆关于杜诗的观点,在他作皇子时所作的《乐善堂全集》中即有类似看法,说明这些观点是他一贯的主张,只是在后来更进一步强化。
④严迪昌:《清诗史》“绪论之二”,《清诗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⑤按:拙文《沈德潜的生前名与身后事》(《粤海风》2017年第4期)、《翁方纲“忠孝观”诗学思想探论》(《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等文对于沈德潜、翁方纲等人因乾隆的扶植而大力宣传乾隆诗学主张等问题曾有相关论述。
⑥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4页。
⑦《礼记·经解》,《礼记正义》卷50,《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影印本,第1609页。
⑧弘暦:《御制文三集》卷9,《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0册,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