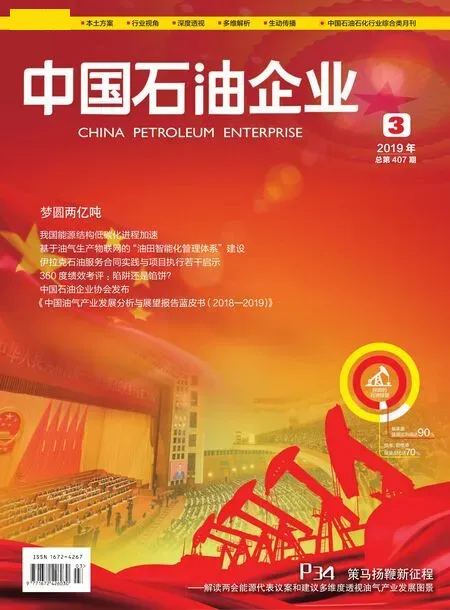【延伸解读】大炼油时代的困惑与迷惘
根据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数据,随着地方民营大型炼化项目相继投产,2019年全国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将净增3200万吨/年,全国炼油总能力将达到8.63亿吨/年;过剩产能将升至1.2亿吨/年,同比增长1/3。
众所周知,国内炼油产能过剩的格局已延续多年。2014年以后,国内经济增速减缓,但在刚性需求惯性增长带动下,炼油产能仍保持4%以上扩张速度。目前全国炼油产能利用率仅为65%,相比之下,钢铁虽过剩,但其产能利用率仍有72%-75%。可见,炼油行业的产能过剩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站在大炼油时代的开端,蝴蝶已扇动了翅膀,但风暴尚未到来。可以预见的是,大的洗牌随即开始,起因是炼油产能过剩已由以前潜在的、阶段性的过剩转变为目前实际的、中长期的产能过剩,而其中最尴尬的是,由于部分落后产能未能及时淘汰,导致整个产业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炼油加工企业众多、利润率低,布局相对分散、低效落后产能明显偏大、产品附加值不高、装置效率较低、转型升级阻力大、市场竞争无序等。
炼油产能与市场“馒头”大过“蒸笼”,但去产能却又陷入“囚徒困境”。让低效无效产能退出,让僵尸企业淘汰,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做起来却是乏善可陈。尽管所有石油化工企业都明白只有淘汰落后产能才能为先进产能腾出空间,但凭什么要我先减产?想想过剩产能出清后行业会回暖,减产的动力又从何而来?与1998年产能过剩不同,那时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国企,融资来源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产能过剩具有较大的内生性特征,适度收缩信贷既可以使落后产能逐渐出清。本轮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有关,而且大量产能过剩主要来自于经济外生性,去产能复杂度较高。内生性特性产能过剩只要适度收缩银行信贷,过剩产能进恶化势头既可得到有效遏制。但外生性特征产能过剩处置起来更加复杂,周期也将更长。这就需要政府统筹规划,不能无限制地搞炼油大跃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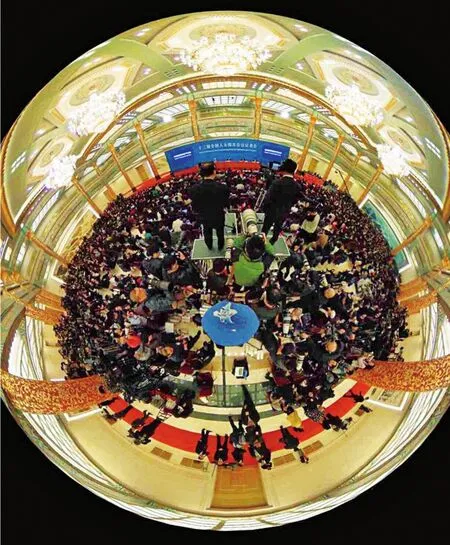
在炼油装置规划方面,美国经验可以借鉴。美国是世界上炼油能力最大的国家,2016年炼油能力达9.08亿吨/年,占全球原油一次加工能力18.9%。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的大多数时间,美国炼厂的开工率都在85%以上,保持着全球先进水平。从1982年到2016年,美国炼油企业从320家降至139家,降幅达到57%。期间经过活跃的兼并与重组,保留优秀资产,淘汰落后产能。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炼油产能自1982年后几乎没有大的扩建,1982至2010年近30年里产能仅增长3000万吨/年,增幅仅4%,直到页岩油气革命成功之后,这一局面才又发生变化。美国炼油产业的集约化发展特点明显,前10大炼油企业加工能力占全美总炼油能力的67%,平均规模在1000万吨/年以上;炼油产能主要集聚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炼油能力占全国总能力的52%。其他炼油发达国家也呈现这一特点,韩国80%的炼油产能集中在蔚山、丽水、仁川地区。日本近90%产能集中在东京湾地区,23家炼厂产能合计1.96亿吨/年,平均规模800万吨/年。
美国炼油产业带给我们的启示有三点,一是规模化和炼化一体化成为炼油行业重要发展趋势,代表着更低的成本优势、更高的整体利润率和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二是物流条件是影响炼厂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其次才是市场。在市场尚未饱和时,炼油厂布局主要考虑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因此炼油厂布局因素会把靠近市场优先考虑在内。而进入产业的调整阶段时,各个区域市场都基本处于饱和状态,炼油企业的目标市场无法再局限于当地,尤其对于大型炼化基地,其产品除了满足当地需求外,更多需要销往区外甚至大量出口到海外。三是虽然规模经济有其巨大优势,但决定炼厂市场竞争力的还是其盈利能力。美国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进行落后产能的淘汰和过剩产能的分解,因此,获利能力是决定炼厂竞争地位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