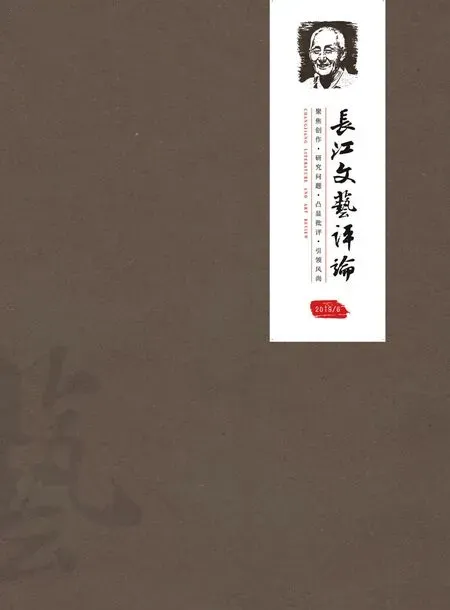中国科幻:自我、世界与未来的想象
◆青 屏

□ 科幻电影的内核是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深层次的叙事维度当中,怎样解决国家民族叙事的基本诉求,是国产科幻电影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 “硬核”这个词,代表了我们对中国科幻片长久以来的期许,“硬核”一定是建立在大量的视觉特效基础之上,它需要创作者架构整个科幻的空间。
□ 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应该怎样讲述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落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表达方式。
□ 中国科幻电影必须得回应“后发国家”的现实:一是如何吸引被好莱坞电影调教了口味的观众;二是如何在对标好莱坞模式的同时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
本期主持人:
朴婕(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特邀嘉宾:
高晓晖(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韩永明(湖北省作协理论室主任)
蔡家园(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长江文艺评论》执行副主编)
胡瑛(湖北省电影家协会秘书长)
对话嘉宾:叶琼琼、瞿文妍、李汉桥、陈荣、杨晓帆、朱旭、秦琼、吕兴、林东林、刘天琪、陈婉清、韩明明、李海音、刘萍娉、刘丽娟、周聪、黄馨瑶
被誉为“中国科幻电影里程碑”的《流浪地球》,何以成为现象级话题?从小说到电影,经过了怎样的改写?它所指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构成了怎样的对话?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应该怎样讲述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乃至构想世界的未来?在高科技建构的未来图景中,中国被放置在怎样的位置?中国科幻文学与科幻电影的发展,面临着哪些挑战?
朴婕(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中国科幻”包含两个关键词:“中国”和“科幻”。这两个关键词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一是“中国的科幻”,它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的发展状况;另一种是关于“中国”和“科幻”,“科幻”凸显出了“中国”的哪些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中国的科幻”,“中国的科幻”这几年有很可喜的发展迹象,是时下很“热”的话题,这可以分解成两方面的“热”:一是“科幻”之热,可以追溯到刘慈欣获奖,让科幻题材一跃进入主流视野,关于中国科幻的研究层出不穷,并渐成完整的体系。二是“科幻电影”之热,《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的出现,尤其是《流浪地球》的成功,刺激起大家对于中国科幻电影的关注,所以今年被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第二个层面是“中国”和“科幻”,我们关注科幻是因为中国科幻有所发展,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关注点,常常围绕在中国科幻是否有能力进入世界科幻殿堂,中国科幻电影如何与世界电影相抗衡,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在关注“中国”这个问题。
科幻在中国的创生本就与反思“中国”相关。“科幻”和“中国”之间是存在张力的,科幻刺激中国人意识到自己落后于世界,因而开始寻找一个自己的探索空间,刺激了民族意识觉醒。我们的关注点始终没有离开中国,科幻在中国的发展也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也在反思中国问题,既有对科技发展的想象,也有对中国在科技发展中的位置的思辨。同时,其作品还以现代化的历史观来阐释中国当代史的特点(比如《三体》第一部)。
电影本身会把科幻所提示出的问题进一步放大。首先,电影本身它就是一个科学幻想,没有科技就没有电影,而且从电影的诞生之初就有科幻电影。第二,电影技术更容易凸显出中外科技实力的差距,当科技的想象力也不在一个层级时,就很容易显出中国技不如人之处。第三,因为电影是一种工业生产的艺术,极大地依托于资本与技术,一部成熟的科幻电影,要求制造足够的视觉奇观,它需要大量资本投入,需要大量技术投入,它也容易体现出中国产业结构还不够完善的软肋。
科幻常常在假想现代文明的界限,假想外在的威胁。在这一方面科幻片和恐怖片的界限其实有些模糊,前者是假想高于我们的威胁,后者假想更低的文明带来的威胁,科幻叙述就是制造一种紧迫感,去思考当现代文明遭遇危机时,我们的解决方案在哪里,我们的合法性在哪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科幻之所以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和科幻本身它就有这样的危机感也是相关的。因此也可以反思,中国科幻的发展是不是应走出这种对立的模式。
陈婉清(芳草杂志社新媒体主管):
刘慈欣的科幻作品恢弘大气、想象瑰丽,有现实的厚重,有宇宙的辽远,有科学的内蕴,并最终落脚于对人类现实问题的终极思考和深切关怀。
作为硬科幻的代表,刘慈欣书中提出了很多概念,比如“降维打击”,出现在他的科幻小说《三体·死神永生》。“降维打击”顾名思义就是将攻击目标本身所处的空间维度降低,致使目标在低维度中生存,从而毁灭目标。
《流浪地球》从架构到故事到细节到对白都有很多毛病,如批评者所言很多地方可谓不及格,但我以为,这是中国导演拍出的最像大片的电影。它有点像当年文学中的《伤痕》,过后几十年不忍卒读,但它却是划时代的,成为了一批作品的代名词,叫做“伤痕文学”。《流浪地球》的出现,会不会带出一批“流浪电影”?我甚至认为,所有质疑刘慈欣的意见都是悄然来临的“流浪电影”浪潮的一部分,我相信从电影《流浪地球》开始,中国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会逐渐走出困境,走入新天地。
秦琼(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
在科幻电影当中是否存在民族国家叙事,在我国无论是科幻文学,还是科幻电影,都是小众的文化类型,科幻片一直都被认为是儿童片的亚片种,80年代、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的很多科幻片,实际上都是用成人的眼光去设想少年儿童的世界,认为科幻电影都是以教化为主,意识形态的制约比较少。
但是在这些科幻片当中,同样有一些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这种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要怎么解读?可以关注三个方面:第一,科学家的形象。在西方科幻片中,通常情况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疯狂的科学家,他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给世界造成重大影响。但在国产科幻电影中,科学家的形象是暧昧的,他们既不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力量,也不具备主观作恶的动机,而总是缺席,反而是少年儿童成了科幻电影的主角。第二,科幻电影关注社会现实。1997年有一部给我留下了童年阴影的科幻片《疯狂的兔子》,它用大量隐喻和象征折射现实,表达了对集体无意识癫狂的忧虑。2008年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科幻片《长江7号》,用一种象征的方式反映了国家在高速发展当中的不平衡状况。第三,国家民族的现实诉求。《流浪地球》的原著有着非常强烈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国家没有了,种族没有了,婚姻解体了,家庭根本不存在。如果把它直接平移到电影当中,就会遭遇文本转换后的水土不服,因为电影的接受和文学的接受不太一样,它强调观众的共情能力,所以电影创作团队在改编的时候进行了非常聪明的处理。
《流浪地球》的成功,极有可能会引发系列跟风之作,在一段时间内,国产科幻电影可能是对《流浪地球》叙事模式的重复,但是这样的叙事模式是不能无限复制的,因为它存在问题。首先,科幻电影的内核是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深层次的叙事维度当中,怎样解决国家民族叙事的基本诉求,是国产科幻电影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二,国产科幻电影的制作水准,虽然《流浪地球》是一部“硬核科幻”,但对标好莱坞,它的特效水准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段距离。
瞿文妍(武汉传媒学院副教授):
“硬核”这个词,代表了我们对中国科幻片的一种长久以来的期许,“硬核”一定是建立在大量的视觉特效基础之上,它需要创作者架构一个整体的科幻空间,不只是单一的场景单一的人物,而是需要有一个世界,比如《阿凡达》,它构建了一个连语言连文字连生存方式和沟通方式都是全新的一套星球系统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它会让中国人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就在于它打上了一种真正的国产的标签,中国人的民族情结近些年在很多电影的营销中被很有针对性地调动了起来。
中国的价值观体系是非常健全且有着深厚历史根基,文化门槛是比较高的,如何尽可能多地与观众做链接,就存在着一个价值观的嫁接。嫁接不是改变价值观,而是尝试将价值观翻译成门槛外的观众能够读懂的语言,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表达,往小了说叫争取最大范围的观众,往大了说就是文化交流和文化输出。《流浪地球》在一个科幻的商业的故事基础上,没有放弃“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为国捐躯”等中国传统价值观,同时又注意到了表达的“语言”和方式,应该说做了一个极有意义的尝试。
中国电影需要在内容上牢牢站稳在中国的这块热土之上,中国现实和庞大的电影产业提供了大量的选题和投资,与此同时,在技术层面上,大胆地与好莱坞商业电影进行嫁接,用娴熟的能够为最广泛观众所接受的叙事模式和视听手段讲述中国的故事。
吕兴(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不管是中国的研究者,还是读者,都习惯于刘慈欣对未来的那种想象,可能认为中国科幻对于世界和未来只有这一种想象,只有这一种关于自我、世界与未来的建构。我想提一下中国别的科幻作家对于自我、世界和未来的另一种想象,如科幻作家韩松的作品。
比起大刘的作品,韩松的作品被称为软科幻,很多人甚至对他的作品属性产生怀疑,因为其中有对玄幻、悬疑等多种元素的杂糅,他的作品很少谈及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很少涉及科学前沿议题,主要醉心于对未来社会形态的一种想象,对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一种比较诡秘的描述,所以鬼魅、晦涩、阴暗就常常被当作他作品的主要特色。与大刘对科学词汇的严谨使用相比,韩松对科技词汇的使用达到一种滥用的程度,这种对科学词汇的滥用并没有让他的作品产生一种科技感,而是有一种滑稽的效果。他并不像大刘一样希望重新建构出一种新的社会体制理论,譬如《三体》中所提到的“黑森林体系”,他更多地是把已经存在的伦理体系和社会形态随意地放置在各个不同的时间段。
朱旭(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鲁迅曾说科幻小说其实就是“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科幻小说或科幻电影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情”。无论是西方的价值观,还是中国输出给世界的价值观,最终都是通过“人情”呈现出来,无论怎么科幻或者如何理性,“人情”的表达与呈现都是无法回避的一环。美国大片不也有一个英雄救美或个人主义英雄的表达吗?《流浪地球》架构起家园、家国这些典型的中国式叙事伦理,也会有牺牲个人拯救世界,牺牲小家成就大家的叙事模式的表达,而这些叙事伦理和表达都是通过一个一个、一段一段具体的人情叙事连缀而成的。科幻小说或科幻电影表达“人情”的时候,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呈现,使其不同于歌舞片、武打片和爱情片,怎么通过科幻元素呈现出独特的“人情”,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科幻中的“人情”表达是独特的中国伦理价值观的一种输出,更是创作者们路漫漫但必须上下而求索的重中之重。
韩明明(湖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关于《流浪地球》和《独立日》两大主题精神上的共通与不同之处:首先,两者在主题叙事上,都将情景设置于人类在面临一个共同的宇宙性灾难时,能够抛开歧义和偏见,用love和peace拥抱并团结在一起,最后赢得人类大圆满的结局。其次,两者都展现出人类在命运面前微不足道的渺小和无力扭转现实的真实状态。最后,两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又展现了各自不同的信仰与立场。《流浪地球》体现的是通过牺牲小我保全家园的集体主义精神内核,《独立日》则充溢着浓浓的美式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所有的人都带着国民性情怀冲锋陷阵拯救世界,为了人类的生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美国式中心主义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感,与中国式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集体主义似乎在相近之中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
李海音(《长江文艺评论》特约编辑、博士生):
《流浪地球》的意识形态功能非常强大,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但是,我认为电影并没有把价值观念很好地植入它的科幻肌体中,或者说,正是对价值观念——特别是对所谓的“家国情怀”或“家园意识”过分的强调,导致电影出现了不少硬伤,以致于削弱了它的“科学幻想”的性质。例如,对于为何要实施“流浪地球”计划,电影反复传达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思维决定了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家园,以至于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当moss自动启用“火种”计划时,刘培强直接把它烧坏了,以一种英雄主义的姿态牺牲了整个空间站,哪怕要失去保存整个人类文明的可能。这种情感化的处理方式,固然体现了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也是真正区别于西方科幻片的地方,但却违背了科幻电影应当具有的理性和科学导向。
揭露电影的问题,并不是为了否定它。“科幻”固然是一种“幻想”,不是为了传授枯燥的科学知识,但也不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不是某种个人意志的产物,而要讲究理性,以科学为起点,促使人们对未知领域和人类文明的大胆想象和理性探索,激发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慈欣的小说的确值得我们重视。
刘萍娉(《长江文艺评论》编辑):
对于中国科幻电影未来的发展之路,我谈两点:一是科学技术与科幻电影的关系。科学技术的进步直接推动着科幻电影的发展,《流浪地球》中75%的特效镜头是由中国公司制作,由此说明发展中国科幻电影是可能的。二是文学小说与影视剧本的关系。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短篇小说,但是我们对照两种文本发现,电影与原著小说的人物设置、情节发展有着诸多的不同,电影更注重叙事细节、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关系、叙事的冲突设计,甚至会安排代表中国元素的场景,迎合当前观众的审美需要,这都说明了影视剧本并不能直接沿用原著文学小说,它需要有一套自己独立的产业发展。
胡瑛(湖北省电影家协会秘书长):
电影具备多重属性——产品性、艺术性、工业性、意识形态性,因此对一部电影的判断应该是多维度的。诚然,《流浪地球》在艺术性和电影的完成度上有一定缺陷,与文学文本对照来看,无论是在故事性还是在思想性上都有所削弱。但是电影的产品性决定了它的受众群体比文学作品更为广泛,因此在情节和细节的设计上会更容易迎合当下的娱乐趣味,在价值观的传达上会更加简单和直接。从意识形态上看,《流浪地球》在价值观的表达上,比《红海行动》《战狼》等有了很大的提升,影片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阐述中国民族精神和国家力量,容易引起更广泛的共鸣。
刘丽娟(5号车间艺术策划、博士):
“科幻”应该如何定义呢?它是一个鉴于科学的幻想,还是在幻想的层面上加入科技使之显得更加可信?或者说在科技出现之前,想象、幻想早已经存在。然而“科幻”的出现,也从某种程度上源于我们理解的世界,科幻的源头是否来自于我们之前所认为的基于梦境的“超现实主义”,或者是来自于那些癫狂的、不合逻辑的,或者是那些不受我们自身束缚和限制的幻想所诞生出的一些没有一定规范的形式。只是现在把这种来自于幻想的东西以一种逻辑性的、科技的或科学的方式阐述的时候,它就变成另外一个系统。但我们发现,在视觉层面上,“陌生”总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真正“陌生”的东西,所以不论是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绘画、电影,或是科幻小说或电影,角色、物件、器具都与其所身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幻想”都源自于现实的生活。
林东林(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
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应该怎样讲述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落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表达方式,当然选择内容也是一种表达方式。面对全球观众,我们是用中国的表达方式还是西方的表达方式,是用中国化了的西方表达方式?还是用西方化了的中国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一个无分国界、无分民族、无分文化、无分宗教、无分性别的普世的表达方式?这牵涉到如何理解现代性语境的问题,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现代性可以说就是一种个体性,注重个体感受和个体表达,在最小的个体中也包含着最大的集体,一个人就是人类,个体可能决定了集体所能达到的深度。
科幻电影和科幻文学是两个重心被前移的词组,重心的落点是科幻,而不是电影和文学,我们谈论和关注的更多是科幻。作为一个定语,科幻给文学和电影限定了一个类型,但是反过来,作为一个主语,文学和电影又给科幻提供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才是科幻最应该琢磨的地方,也就是回归到一种艺术本体的层面。怎么定义文学和电影决定着我们能做出来什么样的文学和电影。
杨晓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类似《流浪地球》等科幻电影,必须得回应“后发国家”的现实:一是如何吸引被好莱坞电影调教了口味的观众;二是如何在对标好莱坞模式的同时又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正是在这第二点上,我觉得《流浪地球》其实不得不回应此前《战狼》《红海行动》等引发的难题:就是在征用民族主义情绪达成国内市场的关注度之后,如何在“大国崛起”越来越被渲染成“中国威胁论”的复杂国际形势中,正面、积极地去完成中国价值的输出。由此来看,简单从民族主义(比如占据营救计划C位的中国英雄、中俄合作的国家政治想象投射)、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刘培强的个人牺牲)等角度去批评《流浪地球》,恰恰没有看到电影在我所说的难题方面做出的努力。比如,带着地球家园去流浪、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调,就是既有中国人家国情怀,又尝试以“小家”联系“大家”超越国家这一政治单位的调试。无论是中国科幻电影还是科幻文学,“后发”、“舶来”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对与世界同步的时代命题做出自己的思考。
周聪(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
结合阅读《流浪地球》的小说文本和观看这部同名电影,我有两点感受:第一,《流浪地球》的小说文本从叙事上来看,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展开叙述的。但在电影里,“我”的视角被弱化了,电影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全景式的镜头。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这种呈现方式会不会对作者的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产生一定的压迫性?第二,小说中家庭情感书写占据了不少的篇幅,而在电影中,个人和家庭叙事让位和从属于英雄主义叙事,叙事的落脚点是凸显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宏大主题。这种从个体话语到集体话语的转变,透露出作者和电影创作者在主题选择上的某些倾向性和差异性。
黄馨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
当下中国科幻研究的视角有很多,有科幻伦理、科幻审美、科幻文体等,但是一直不太关注性别视角。其实就性别本身来说,科幻是一个最具探索性的文类。性别问题总是和种族、阶级、国家等问题密切相关。正如詹姆逊所说,第三世界中的文本,任何个人的故事也是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所受冲击的寓言。如果我们去阅读当下这些科幻作品,就会发现在他们的写作之中,不仅个人是有性别的,国家也是有性别的,宇宙也是有性别的,性别的隐喻充斥在他们的文本中。那么如何从性别来进入科幻呢?男性研究或许可以提供一种研究视角。男性研究是70年代在社会学中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它在承认男性总体上对女性造成性别压迫的基础上,认为男性内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除了少部分特权男性外,大部分男性也受到这种父权制性别秩序的压迫和边缘化。男性研究对男性同盟、男性神话、男作家的创作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非常有趣的见解。
李汉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
科幻电影最核心的命题是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博弈。科幻文学的出现是伴随着近代科技发展而来的,以前人们以为上帝拯救世界,后来人们相信科技拯救世界,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无论是《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还是《从地球到月球》,科技作为工具,是达到人类理想的阶梯和手段,那时候人们对于科技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上帝死了没关系,还有科技文明。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当科技文明铺展开来,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叫“技术大地化”,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人类用科技创造生活,科技也可能毁掉世界,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品倾向于科技给人带来的威胁,像机器人、异形、外星人、生化危机等,在科技的力量面前,人类的火种很快就要毁于一旦。
《流浪地球》里面,太阳要熄火了,地球要灭亡,这个时候,人类拿出来的最后拯救手段就是科技。造一万台发动机举家搬迁,但是造成了极度严寒和资源的匮乏,首先科技手段就让人类死了一半,而行星发动机所用的燃料,也是要将地球挖干殆尽。宇宙飞船里,面对最后的抉择,人工智能首先抛弃的就是地球上的人类,所以科技的拯救之道往往是冰冷的。
在危机面前,能够力挽狂澜的是人文精神的高扬,这是所有科幻小说最后的幻想,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乔治·斯拉瑟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说:“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推理逐渐改变着想象的文学世界,同时也侵蚀着人类特权中心说,把人类置于麻木的物质世界之中,而文学则以其不断发展的技巧力图恢复人类自身的精神价值。”这也是一场博弈,是人类与科技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谁掌握主动权。《流浪地球》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核心价值观:第一是牺牲,为了人类生存,一半地球人要牺牲;为了儿子,父亲要做出牺牲;为了集体,个人要做出牺牲。这种牺牲是壮丽的美,悲剧美。第二是亲情,里面的父子情、爷孙情、兄妹情,让冰冷的地球变得温情脉脉。第三是团结,这是中国电影的核心价值观,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在最后危机时刻,所有国家的队员,放下偏见、放下自我,都投入到拯救地球的最后举措之中。这种人文精神是科技文明无法达到的边界。
刘天琪(湖北省作协理论室编辑):
我认为影片选得非常好,《流浪地球》和《独立日》这两部影片提供了一个东西方科幻影片的比较,也提供了新旧科幻片的一种比较。现在的《星际穿越》《美国队长》这些系列的科幻电影,有很多一脉相承的地方,比如说意识形态,背后文化话语权的植入,英雄主义的情怀。但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发展进步的地方,科幻片中科技细节和元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展示。《独立日》当中,并没有多少科技元素的展现,现在的科幻片加了很多的现代科技细节。科幻影片中这些科技元素的细节性展现,体现了科技自信。科幻影片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人类心理的成长、成熟过程:由一种“全能自恋”的状态,转换到现在我们与环境与他人与未来的一种依恋的关系。
叶琼琼(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
电影文本源于小说文本,但是小说的故事用电影这种艺术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必定会屏蔽小说文本的某些特质,突出另外某些特质。比如说刘慈欣的《三体》有比较强烈的精英话语的味道,它从历史性、人文性、终极关怀、人性善恶、文明优劣等角度出发去创作,引发长久的深刻思考,思维空间无限拓宽加深。但是电影更多的是强调娱乐化、大众化、狂欢化,它面对的是市场,强调的是票房,不同于可以反复阅读的小说,它使用的是快速多变的电影语言,强调视觉冲击,它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用连续多变的紧凑的情节把一个故事讲得跌宕起伏,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并用光影声色等多媒体手段和特技手法带给观众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从传播的角度看,网络的发达让电影能够轻而易举拥有尽可能多的观众,比小说文本多得多,受众的层次也复杂得多,对浅层的娱乐性和大众狂欢性的需求更加强烈和迫切一些。同时,因为电影具有滞后性,往往是小说创作出来以后,经过了广大读者的检验,拥有比较稳定的市场之后,导演才会选择这部小说作为电影的蓝本。当然两者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比如小说同样也关心读者市场,也会注意故事是否好看,可读性强不强,电影也会在关注票房的同时,尽可能拍得有深度。但从目前的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看,小说显然更加深刻一些,容量更大一些,电影娱乐成分更多一些,视觉冲击力更大一点,这源于二者的传播媒介和受众的心理期待的差异。
陈荣(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
把《流浪地球》和《独立日》的音乐放在一起,如果不特别对比很难分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科幻类型电影音乐,一种类型电影音乐。科幻电影音乐从1951年开始,从电影《地球停转之日》之后,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用电子音乐、实验音乐,使人听到一种不太相同的东西,这种电子音乐形成了科幻电影印象,形成了十几年的科幻电影音乐潮流。大家认为这样的音乐才是科幻电影的音乐,它很虚空,很电子,很诡异。
未来我们希望的科幻电影音乐是什么样的?虽然科幻音乐有固定的类型,但是一定要创新,要出现1951年的那种突破。为什么?因为只有用未来音乐结构,后现代音乐结构才能承载未来想象。如果科幻电影一直沉浸在现代音乐体系中,音乐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向前发展了。
(朴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