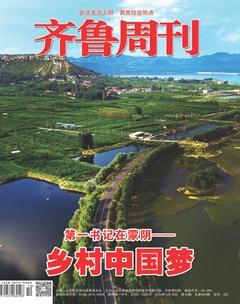东紫:“通往生命最隐秘处”
董忱 陆洋


东紫,本名戚慧贞,山东莒县浮来山人。2004年始在《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创作长篇《好日子就要来了》及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若干。出版中篇小说集《天涯近》《被复习的爱情》《白猫》。曾荣获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泰山文艺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等奖项。
东紫的本职是药剂师,正因为从医的职业经历,使她能够窥见生命深处的隐秘。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小人物”往往辐射“大事件”。她记录触动她的生命个体,并与他们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抵抗宿命的残忍与不公。
执着于“发声”的潜在根源
很多年以后,在和文友闲聊童年时,如春忆起哑巴东,总会不由得坐直了身子,回望着遥远的生命历程,在心底里惊问——难道是它垫起了自己自信和悲悯的第一块基石?这是她执着于写作,执着于“发声”的潜在根源吗?——《迎风帐》
东紫出生在鲁东南的一个山村里,贫穷是她童年的记忆。
“冰冷的煮地瓜”“锅底的肥肉渣”“被一切三瓣的苹果”都曾是她成长过程中奢侈的味觉记忆。极度封闭的环境和匮乏的物质却滋养了东紫细腻的情感,而被她所观察、记录的一切也成为她日后创作的养料。《迎风帐》中,如春就是东紫的影子。她用细腻而克制的笔触完成了对童年的回望以及对自我的注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讀初中的东紫第一次受到了诗歌的启蒙。彼时,诗社在中国颇为流行,东紫的语文老师王世联是农民诗社《山地》的主编,同桌就是社长张荣山。在他们的引领下,东紫荣幸地成为诗社的帮工——帮着刻板、油印、装订,目睹了诗歌带给他们的快乐、分享、友谊、爱情……那一切,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既新奇又魔力无穷。
直到现在,东紫还常常想起那些日子。“我刻着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闻着文字散发出的神秘气息,就这样爱上了文学。”偶尔,东紫也学着老师的样子写点什么。但那时她还不很清楚文学对于她的意义。
直到十几年前,家中接连遭遇变故,东紫坠入人生谷底。在绝望中,东紫收到了《人民文学》,那一期的杂志上,有她的一部中篇小说,“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的脊柱仿佛被打上了钢筋,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垃圾筐式的人生,你遭遇的一切挫折和屈辱,都是你独特的生命体验,只要你真诚地对待文学,文学最终都会回报你,文学可以支撑生命,可以兜住你人生的底,文学不会让你的生命脆弱地倒下。所以如今有人问为什么写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为你的生命写作。”
写作也是“孤独地抗争”
白猫一动不动。我突然想起五年前母亲临终的时刻。那也是个深夜,我孤独地守在她的病床前,眼睁睁地看着她一点一点地衰亡。远离。我被无能为力的悲哀控制了,看着自己的双手痛哭不已。年富力强的它们竟然成为了一种摆设,丝毫没有用处。幼年的时候,弱小的它们都能牢牢地拽住妈妈的衣角呀。我抚摸着白猫,生怕在抬手的霎那间丢失了它的呼吸。这一刻,我重新记起了守在亲人病床前的强烈感觉——渴望着那呼吸是有形的,是能够用手牵拽住的。渴望人和死神之间是有绳索的,是能够由亲人组成队伍力拔的。但是,生命在危机的时刻总是孤独的。孤独地抗争。——《白猫》
东紫的写作过程往往从容而漫长。她喜欢把好的素材和故事焐在心里,焐人物的性格,焐写作的语言,等到一切都成熟了,提起笔来,早已被“焐热”的故事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了。《北京来人了》《白猫》《春茶》《乐乐》等多部获奖作品都是这样被焐出来的。
但这样的过程也是个“煎熬”的过程,每个漫长的创造,都是一场“孤独地抗争”。人物、情节不断在东紫的脑海中浮现、发酵,故事一天没写完,他们就一天在东紫的心里装着。
除了作家,东紫还要兼顾其他同等重要的角色,她是妻子、女儿、母亲,还是一名药剂师。白天,她穿梭于医院中,与药品、病人打交道;回到家中,她是贤惠的妻子和母亲,沉浸在日常的生活琐碎中。工作日以外,她把儿子的课外班全都安排在周六,周日这天,才是她奢侈的、自由的写作时间。
与其他作家比起来,东紫的写作时间少得可怜,她也常常用“自我宽解自我原谅的借口”来宽慰自己。但事实上,多种角色的切换反而为作家东紫提供了更多观察生活的视角。当她午休时走过医院大院时,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放风”的病人使她心生悲悯;陪伴儿子成长的片段是她的创作缪斯;与爱人、朋友间的交流让她得以接触更多值得被记录的个体生命。
作为药剂师,东紫精通药理。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就是东紫的一剂精神良药。她眼见生老病死、人生百态,以文字诠释生命,以一颗作家的“仁心”叙述一个医者、母亲的内心世界。
消散自身的颜色博取一声喝彩
她看着那个无法伸展成叶片的芽苞,那树林一样拥挤着拼命消散自身的颜色博取别人一声喝彩的短暂,想到那其实就是一个个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没有两只水袖的女人。或许水袖是有两只的,但舞动的只能是一只。另一只必须是紧握着的,是永远不能顺应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抛撒舞动的。——《春茶》
东紫人很温和,外表单薄、柔软,但她的小说“笔力锐利,常刺入人性中薄弱的间隙”。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称她的作品锐利之外,笔调又是间离和幽默的,不断以喜剧的色泽冲淡悲剧的压抑,从中获得一种奇特的修辞效果。东紫对人性的观察是全面的、健康的,而不是褊狭和极端的,这种观察也造成了她的创作的敦厚气质。
在东紫长篇新作《好日子就要来了》中,以做假文凭为核心的小说情节,将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讽刺性做了文学的表达。文学评论家李掖平评价说:“东紫的小说擅长在人性的善恶复杂纠结下,在生活的尴尬无奈中,在感情的微妙边缘处,描写个体生命悲欢离合的遭遇,拿捏其灵魂深处的伤痛,文字时而犀利冷峭时而缠绵悱恻,摇曳出一种迷人的风情。”
天才女作家奥康纳认为写作应该“沾染一身尘霾”,奥康纳长期在很简陋的环境中写作:她的房间里窗上没有窗帘,屋顶正中垂下一根长长的电线,系着光秃秃的灯泡。她总是独自一人,拉下百叶窗,坐在打字机前,面前一叠黄色的纸,或是写作或是修改。对此,东紫深以为然,写作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现实生活中,不沾染世俗,又怎么看见个体命运在社会中的脆弱呢?
写作就是要写“和你生命相契合的东西”,写“让你疼痛的东西”。“文学是最公正的,只要我们真诚地去对待它,它就会真诚回报我们。这种回报,不仅仅是作品得到了发表、赞扬,它最大的回报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撑——因为它,我们生命中所遭遇所承受的一切不公、不幸、屈辱、挫折等等,都能成为可利用的材料,成为写作时深入描写人物生命体验的一种直接经验。由此,写作成为我们日常的保健理疗师,把那些容易导致人气滞血瘀的东西,进行了排解转化。”东紫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