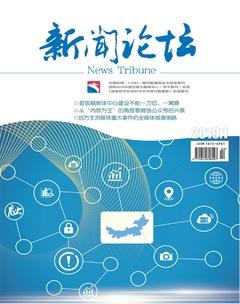弹幕视频的大众狂欢及其文化溯源
宋豆豆
【內容提要】弹幕视频产生于社交网络蓬勃发展的传播环境,在青年群体中是一种新兴的互动形式。与传统视频不同,弹幕视频具有碎片化、颠覆性、“一对多”传播模式等特点。弹幕视频在快节奏文化消费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并且衍生出其他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当下新媒体急速发展的时期,弹幕视频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溯源。
【关键词】弹幕视频 解构 狂欢 亚文化 仪式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传播媒介的变化不断塑造着社会文化的演进,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随之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弹幕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首先出现在小众范围的传播环境中,主要在受二次元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少年之间进行传播,并未形成大的规模。如今弹幕发展势头迅猛,其群体狂欢的特点具备非常大的发展潜力,逐渐被大众文化收编。2014年,弹幕在短时间内占领了各大主流视频网站,优酷、土豆、爱奇艺等都不失时机地上线了弹幕功能。虽然弹幕仍不符合某些群体的观看习惯,但是其逐渐进军主流文化领域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现实。弹幕通过集体围观的方式,在集聚志同道合的用户进行互动交流、传递感官愉悦的同时,也构建起独特的亚文化传播扩散的社群。
一、何为弹幕
(一)弹幕的发展概况
弹幕一词原为军事术语,指的是集中火力对某一地区进行射击轰炸,凭借发射大量弹药,最终将目标摧毁。1993年,日本的游戏公司开发出一款游戏,该游戏在屏幕上充斥大量低速飞行的弹丸,让玩家操作飞机在弹丸空隙中不断躲避射击。日本游戏玩家将这种类型的射击游戏称为“弹幕系射击游戏”。
“弹幕”一词后来被引入ACG(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是动画、漫画、电子游戏的总称),后来流行于动漫网站中,最早可追溯到日本公司的NICONICO动画,即在视频播放时增加了即时评论的功能。观众在观看视频时,观众的评论会直接“飞过”屏幕。同时观众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发表评论,而之后观看视频的人也能在屏幕上看到该评论。在剧情进入到高潮时,无数的弹幕会在屏幕上飞过,如同子弹一般,这种视频被称作“弹幕视频”。
弹幕视频最早出现在日本,2008年,国内的AcFun视频网站将其正式引进。随着A站和B站两大弹幕视频网站的发展壮大,“弹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即时评论的视频被部分青年群体接受和认可。在新媒体急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弹幕视频冲破原有的“二次元”文化,逐渐被各大主流视频网站所接受,还与电影、电视等形式结合起来。土豆、爱奇艺等视频网站纷纷推出弹幕功能供用户选择。2014年,国产3D电影《秦时明月》在院线上映时,首次尝试弹幕功能;《小时代》也紧跟潮流举行弹幕专场等。主流媒体的尝试,使得弹幕文化突破自身原有的文化圈,进入大众的视野,引领着新型的网络文化互动潮流。
(二)弹幕的特点
在发达的网络环境下,观看视频的用户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其依据自身日常经验所发表的即时评论拥有各种各样的特点。在原有的视频文本上线后,随着后来者评论的不断添加,原始文本的意义不断得到新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广泛的信息传播。弹幕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在互联网积极的传播环境下,具有极其复杂的特点。
内容上,弹幕可分为基于视频文本的弹幕、闲聊式弹幕、无文字弹幕。基于视频文本的弹幕较为常见,包括对文本的分析与解读、对当时视频情节的调侃吐槽等,例如“这女主的眼睫毛简直了,能再夸张一点么”“您的好友胡歌已上线”;闲聊式弹幕既包括网友的互动,例如“前面考六级的别走,等等我”,也包括无意义的弹幕,例如“空降成功,感谢指挥部”;无文字弹幕则大多以表情符号形式出现。
弹幕具有高度娱乐性。人们在视频网站上打开弹幕,有时候不是想从弹幕中获得实质性的信息,而是单纯享受匿名性互动带来的快感。弹幕的流行与网络环境中的恶搞和吐槽文化息息相关,满足了网民在生活压力下的娱乐心理。
弹幕具有实时互动性。传统评论被置于视频的下方,观看评论与观看视频这两种行为难以同时进行。弹幕视频则互动程度高,能够与已有评论进行及时互动,后来者也可用同样方法与前人互动。弹幕中经常会出现“前面绿字你是来捣乱的么”“和我一样明天要考六级还看视频的举个手”。弹幕的实时性、动态性与在场性,对于网民来说是新的体验,这也是互联网不断普及的成果。
弹幕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蕴含着对原有意义的解构。弹幕视频是典型的“生产性文本”,即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用户在发表弹幕的同时,基于原有的文本进行初始解码与二次编码。视频本身是封闭的、固定的空间,而用户可以在空间内不断发表基于自身经验的见解,对文本进行源源不断的新的意义阐释。用户发表弹幕,在对视频文本进行初始解码的同时,也可以无门槛地进行二度编码,对视频原本想要传达的意义进行解构。弹幕与文本之间的交锋,也会对后来者的文本信息解码造成影响。
二、弹幕视频衍生的文化现象
弹幕视频是群体传播中的一种形态,其自身具有去中心化、非制度化的特征。弹幕视频的流行迎合了当下年轻人标新立异,意图打破传统生活方式中的刻板与保守理念,强调多样性与创造性。用户面对转瞬即逝、大面积覆盖性的文字评论时,在这种充满仪式感的行为中获得视觉冲击和心理腧悦。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弹幕视频中催生并发展了一系列衍生品,空耳文化和鬼畜文化就是其中的典型。
(一)空耳文化
B站对“空耳”作出注解:“空耳来源于日语,原来在日语中是幻听的意思,现在专指一种将原歌曲中的歌词,故意用另一种语言,取其与原语言相似的语音,写出与原本歌词不同,甚至毫无相关的新的歌词,以达到恶搞或双关的目的的文字游戏”。空耳并非单纯的空洞和无意义,而是以文字传播的方式,对作品内容进行二次加工。网民在对文本的解构中,通过恶搞获得感官和心理的娱乐,在纷繁的弹幕刷屏中寻求视觉狂欢。
(二)鬼畜文化
新媒体时代,网民自制视频成为流行,催生出以高度同步、快速重复的素材配合背景音乐,以达到洗脑效果的恶搞视频。随着社交媒体的兴盛,人们利用网上的视频素材进行解构与重构,进行夸张化的处理来彰显个性。弹幕的兴起将这一另类文化推向了高潮,人们通过实时弹幕表达自己的情绪快感。应接不暇的画面、快节奏的音乐、铺满整个屏幕的弹幕,在这个时候,观众的所见所听的实质内容已经不重要。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视听盛宴中,人们集体达到了感官的高潮。
三、弹幕视频背后的文化溯源
(一)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解构与重建
亚文化的前缀是“sub”,意为从属的、次要的文化地位以及具有叛逆和反抗意识的文化精神。伯明翰学派将其概念界定为“一种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青年亚文化在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表现形式也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在初期阶段,青年亚文化表现为以标新立异的手段与主流文化争夺话语权,标示自己的亚文化身份,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文化更加多元化,青年群体可以通过媒介建立自己完整的、独立的精神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亚文化不再处于边缘地位,亚文化群体成为了统治者,可以通过独特的娱乐方式在彼此之间获得认同感。青年群体可以自由使用媒介工具,随时对主流文化进行调侃和颠覆。对于青年群体的精神空间来说,它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开放性在于其载体属于网络空间,是对所有人敞开的。封闭性在于它的参与者大都是青年群体,别的群体即使有意参与,也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障碍。
新媒介的出现本身就带有亚文化的基因,迎合了当下青年群体叛逆性和抵抗性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新媒介文化属于青年亚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互联网时代下,弹幕成为继微博和微信之后一种新兴的网络交往方式。视频文本属于主流文化的范畴,而用户以弹幕的形式随意发表评论,表达对主流文化的调侃与背离,对主流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神话和价值观进行颠覆。主流文化在转瞬即逝、纷繁多样的弹幕中,被肢解为碎片化的符号。在这些符号的基础之上,弹幕视频的参与者不断对其进行解构与组合,表现出自身所处群体的精神面貌与集体心理。
众多飞驰而过的弹幕、戏虐性的话语、不拘形迹的吐槽,用户地位的重要性被体现地空前直观。在亚文化群体的精神空间中,等级秩序被颠覆,严肃统一被破坏,视频原本的叙事和内涵不断被消解,人们毫不吝啬地将情绪发泄到弹幕中。
(二)“N级传播”模式下的大众狂欢
任何文化形式都具有仪式性的存在,作为仪式性存在的文化大都会出现集体狂欢的现象。“狂欢化”概念由前苏联思想家、文论家巴赫金提出,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狂欢节是一场全民的娱乐,人们冲破各种规范和束缚,随心所欲,可以不受限制地开玩笑和戏谑。相比较常规性、教条性、规范性的生活来说,巴赫金认为狂欢就像人们在广场上的欢声笑语的“第二种生活”,人与人之间可以不受拘束进行自由自在地进行交往。在这种程度上,狂欢文化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相对的文化状态,日常生活按部就班,狂欢文化则倡导标新立异,追求精神的解放与张扬,其精神的真正原则是平等与自由。
约翰·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认为:狂欢节的功能是解放并承认一种创造性的、游戏性的自由。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再是受体制欺骗的“文化笨蛋”,而是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不再不加判定地接受文化产品,而是参与到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中,并在其中起到积极的能动作用。大众在对文化产品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创造力,是自下而上的,以自身的创造性和抵抗性,创造着自己的意义和快感,并且消解着现代性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新的历史语境下,大众消费的时代已经来临。“利用他们的商品,达到我们的目的”。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并习惯在公共空间内表达自身意愿,参与到议题讨论之中,彰显自身个性,暂时脱离现实生活中各种规范和秩序的制约。这使得近年来的民间狂欢文化潮流愈演愈烈,在网络空间里表现尤为明显。
2017年央视综艺《国家宝藏》以官方姿态入驻B站,引发了二次元群体的狂欢,在B站预先发布《国家宝藏》的MV《一眼千年》、前期的节目预告、高清正片、后期的独家花絮、人物的专属剪辑等充分满足受众年轻化、多样化的需求。数据显示节目播出前两期,B站评论累计超过600万,播放量超过200万。针对节目的弹幕文化也在豆瓣、微博、微信等社交群体引起二次传播,进行娱乐化、戏剧化的内容解读,如“败家儿子乾隆的农家乐审美”“别人打call你盖章题字”“小贱贱(越王勾践剑)”等在各社群传播中引发激烈讨论。
弹幕建构起作品与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使得视频空间内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传播模式成为过去,“多对多”或“N级传播”模式成為潮流,这使得引发群体的狂欢成为可能。传统网站视频下的评论区侧重个人意见的表达和用户问的交流,而新形势下,弹幕视频的用户在已知自己的评论必然会被他人观测到的情况下,更加热衷创造性地解读文本和生产意义,以引发他人的关注。每个人在网络所造就的精神空间中地位是平等的,能够针对视频阐释出各种各样的内容,视频原本蕴含的意义被不断曲解和重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身份参与到这场众声喧哗中去,正是狂欢化的表现。
(三)传播仪式的再现
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凯瑞认为,与“传递观”中强调信息的位移本质相比较,传播的“仪式观”意义更为广泛。在仪式观中,传播的原型是指一种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是一种共同信仰的表征。@在凯瑞看来,仪式是文化的最佳体现,而文化序化了人类生活,因此仪式是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序化。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体现为会话,而会话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形式化和仪式化的特征。人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动物,人类社会生活就是符号互动的过程。人类的行为是文化的产物,因而也伴随着仪式化。人们之间的符号互动有着仪式般的社会功能,继而起到社会凝聚的作用。
弹幕视频所具有的交互性正是传播仪式的再现。在用户观看弹幕视频时,一方面接受视频文本传达的信息,另一方面在“虚拟在场”中,与其他用户共享符号被解构和再创造后的意义。在同质化群体充斥的网络精神空间中,视频文本中情感的表达能够在瞬间引发人们的共鸣,促使人们表达自身情绪,产生弹幕刷屏行为,继而人们会在这样仪式化的行为中获得极大的认同感。在密密麻麻的弹幕布满屏幕时,与其说人们在视频与弹幕文本中寻找意义,不如说是发泄情感、寻找共鸣,以此享受给自身带来的高度的仪式化快感。
四、总结
对于人类的传播史来说,每次新的传播形式的出现,都意味着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改变,并伴随着集体性的精神狂欢。媒介技术的进步为亚文化的发展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空间,对亚文化传播群体的心理状态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成为其寻找志同道合者的文化场域。
在网络时代,弹幕所具有的极强的互动性适应了当前传播环境注重互动的现状和趋势,迎合了当下人们对主流文化叙事的解构与戏虐。弹幕本身不仅仅是内容,更是当下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集结同好,用娱乐的态度构建属于自身的社群文化,从而满足社交需求。弹幕视频的低门槛使得参与者更加积极热情,渴望在网络的各个社区中寻找相近特质的伙伴,传播自己的想法。任何流行文化的出现都反映着某一群体的生存样态。在互联网环境下,弹幕视频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流行文化现象,其旺盛的生命力体现了大众的社交需求,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