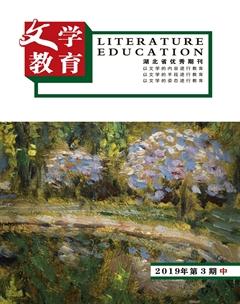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小说中“家”的空间隐喻
内容摘要:柳得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是当代俄罗斯炙手可热的作家、戏剧家。作家赤裸裸地还原了家庭生活的粗糙阴暗面,展现了家庭空间对于体现女性自我存在意识具有的独特意义。在作家笔下温暖的庇护所变为禁锢女性独立个体的枷锁,成为其难以摆脱的梦魇。
关键词:彼特鲁舍夫斯卡娅 女性 家庭空间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1938年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期时逢二戰,过着颠沛流离甚至食不果腹的生活。战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先后当过编辑、记者和编剧。七十年代因处女作《穿过田野》而一举成名,随后几十年的一系列力作异彩纷呈,备受欧美评论界的青睐和读者的普遍欢迎。多次成为各类文学奖项得主,与乌利茨卡娅、托尔斯泰娅一起并称为“俄罗斯女性文学的三剑客”。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创作题材多样、风格不同,惯用“冷静叙述”生活及其细节的超写实主义,再现改革时期苏联和俄罗斯民众的生活状况。始终贯穿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创作的核心是女性,而家庭则成为其笔下女性生活悲剧的演绎场。
“家”是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创作的轴心之一,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或寻找或逃离家庭,或创建或毁灭这一精神的栖息之地。家作为固化的物质存在的意义减弱,其意象已不局限为一个供人居住的场所,首先,诚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家是“避难所、后方基地、洞穴和子宫,为躲避外来危险提供藏身之处,混乱的外部世界由此变得不真实”。“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彼得鲁舍夫斯卡娅鲜有对女性所栖居的作为空间意义的家——房屋进行直接描绘,它往往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出现,但却极具象征意义。它们是狭小的出租屋、公共住宅里的两居室、黑暗潮湿的地下室或是腌臜的厨房。这是女主人公试图完全统治的领地、充分享有话语权的场所,是女性价值存在的体现:女人们采买食物、洗衣做饭、收拾打扫,在其间日复一日地操持家务琐事。俄罗斯男人们却曾一度因为频频的战争和革命而被排除在外,或者由于婚姻变故等离开家庭,女人们替代男性成为了家的庇护者和捍卫人,变得比男人更加具有阳刚之气。她们建造着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常常是只有外婆、母亲、女儿和孙子存在的私密而封闭的женские дома——女性部落。
作家刻画的女性居住的空间影射的是封闭残酷的生存环境,既象征着女性生活的边缘性,也暗示了社会对女性生活环境的隔离和漠视,这成为了造就主人公们扭曲的心灵和复杂的性格的外部因素。一方面,住房是女性生存必备的最紧迫的物质资料之一,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他们要么居住条件恶劣,要么压根儿没有栖身之地,终身为了得到房子而斗争。女人的感情因此让位于生存,为了丈夫单位分配的住房甚至可以忽视他的种种风流韵事(《有这样一位姑娘》)。另一方面,即便身处这一赖以生存的空间,女人们也未必能实现精神的自由。她们实践着根深蒂固的东正教传统思想以及国家对女性“母性”与“生育”的诉求,独自担负着抚养孩子的任务。从这种意义上说,家成为了禁锢其身体和心灵的枷锁,束缚自我实现和发展的屏障。
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注定了女性在本能地渴求实现自我理想时必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理想囚禁于现实生活的牢笼中。在《幸福的晚年》中我们看到,女主人公选择了逃离。丈夫的冷漠使退休的波林娜“早已视他为仇敌”,婚姻只剩形式上的外壳,与儿孙也形同陌路。家庭空间成为了由婚姻、孩子、琐事引发的无形的精神压力场,使她厌倦了履行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责任,波林娜“就像一头困兽,夜夜被各种思绪折磨得辗转不眠,想找出路,却又寻而不得”。长期以来波林娜一直处于迎合男权社会塑造的理想的“安琪儿”的状态,波伏娃形容这一时期的女人“注定要不断重复,她看不到未来的任何事情,只有过去的不断复制”,重复无趣的忙碌却不能给她们带来任何收获。恰好此时,去世的姨妈留下的住房成为她远离家庭压力的避难所,她“为自己要这套房子的,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完全在为自己做事”。在这个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她养花种菜,过得清苦却幸福。但她终究无法摆脱家庭如监狱一般的规约,享受了绝对独处的轻松时光和暂时的安宁后,波林娜又走回了自己的家。波林娜在受局限的家庭空间,试图争取属于女性的尊严和权利,寻求妻子的身份和生存的意义,但这并非女性单个的个体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像波林娜一样的“套中人”们想要安排自己的命运无从谈起,家庭这艘诺亚方舟也总是游离于现实的彼岸,并不能带她们躲避生活的磨难。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冷峻地审视女性爱情、家庭日常生活、人际关系中的善恶美丑,将其中最阴暗恐怖、肮脏丑陋的一面赤裸裸地还原和放大。让家庭日常进入到文学视野,从这一层面来说,作家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中以果戈里为代表的自然派客观真实的描写方式。评论界将她归入“残酷”作家的行列,认为她的作品“真实得令人战栗”,细加研究的是“庸俗”、“晦暗”甚至是“粗野”的现实生活,“每个故事都在讲述周围世界对人的摧折”。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坦承自己的小说是“从市民群众的喧闹声中、从街头的闲聊中,从医院的病床边,楼边的长椅上”汲取情节创作的灵感,并且认为“艺术中的不幸越是回归真实的生活,完整地还原人的痛苦和恐惧,越能彻底地涤荡和净化灵魂。”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对改革前后俄罗斯这个瞬息万变、命运多舛的国家城市普通民众的生活进行了超写实主义的描摹,她沿袭了谢德林和高尔基,到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特里丰诺夫等人的传统。这些作家绘制了与社会变革、革命进程格格不入的、或维护私利、或贪图安乐、或沉沦人生的小市民形象。其中,被称为“当代苏联文学的显著现象”的特里丰诺夫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一样,都特别善于描写日常生活。他认为,“日常生活是伟大的考验…是各种各样的联系、观点、友谊、结识、厌恶、心理、意识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生活。”细致地了解人的内心世界,从多方面多层次地表现人,要深入研究现代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容,发掘生活里层,就要注意日常生活,从揭开日常生活的帷幕来洞察人的灵魂,触感到社会生活的脉搏。
两位作家在执着于真实地反映生活上达到了共识。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固守或者争夺住宅这一苏联特有的边缘场景,以及夫妻关系、男女关系、父子关系等生活琐事的细微描写,“把被文学虚伪地蔑视的庸俗日常生活复归到文学”。所不同的是,特里丰诺夫在60年代末及70年代,即“解冻文学”之后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新道德准则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表现和检验。”他的着眼点首先在于揭示这种日常生活的道德内容,从精神道德层面鞭笞“现代市侩”普遍存在的问题。指出市侩庸人的本质是在社会道德和追逐膨胀的一己私欲之间作出抉择,利用极端的利己主义的道德同他人的社会道德作交易、用自私庸俗的道德感情同高尚纯真的道德感情作交换。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看来,对社会的诟病、对官方思想意识和权威的挑战让位于撕开生活的真相,她没有特里丰诺夫等作家的理想主义式的体悟,也没有索尔仁尼琴等对苦难的悲壮的激情,而是还原生活本质的悲剧性的审视。这种悲剧性有别于其他作家描写的社会的不完善,从根本上说是发生在人性内部的个人选择的结果,它融合了文化观念、生活经历,当然,还有时代烙印。
对家庭空间中女性命运后现代式的解构意识与作家内心深处深刻的使命感化学反应后生成了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复杂而独具匠心的创作风格。描写琐碎的生活日常中交织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悲剧情节时,她打破了一般的语法规则,突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段,采用克制性的黑色幽默叙述和反讽、夸张、悖论的手法来表达对女性生存问题的独特思考。从这种意义上说,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正是契诃夫所形容的站在幸福的人们家门口那个拿小锤的人,提醒人们别忘了生活中粗鄙悲哀的另一面。尽管鲁舍夫卡娅本身反对被归入女性作家的行列,但作品中对女性家庭、爱情、女性意识和老年问题等主题的高度关注使她被公认为俄罗斯女性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作家聚焦女性个体身份的诉求、女性的生存和自由的同时,并不限于对性别问题的探讨,她从新的角度对整个人类的生存进行深邃的思考,传承了俄罗斯文学人文关怀的传统。
参考文献
[1]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谈古论今[M].莫斯科:阿斯特列尔出版社,2012:45.
[2]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33.
[3]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谈古论今[M].莫斯科:阿斯特列尔出版社,2012:45.
[4]巴恩.《沿着爱神的道路》作品集中的诗学问题[J].星,1994,(5).
[5]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6]特里丰诺夫.特里丰诺夫两卷集(上集)[M].莫斯科:苏联文艺出版社,1978.
[7]纳塔利娅·伊万诺娃.烧不掉的鸽子[J].旗,1991,(8).
[8]阿巴舍娃.不記仇恨的纯净生活[J].文学评论,1992,(3).
(作者介绍:曾佳,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