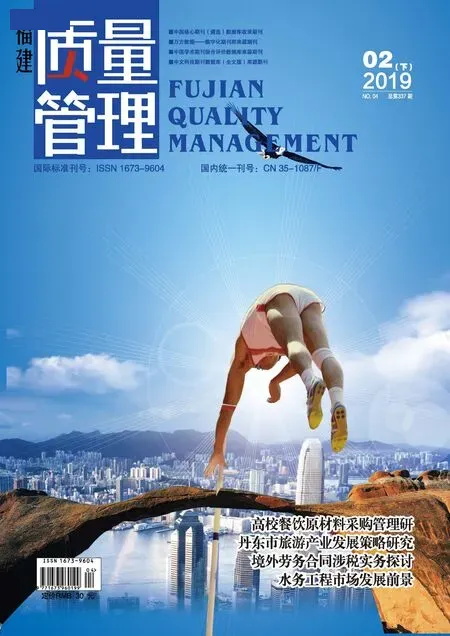关于“风险刑法”的风险控制
——以危险驾驶罪为视角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提出
(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之后增加了第133条第1款,将“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规定为犯罪,其法定最高刑仅为拘役,从而使我国刑法中出现了唯一一个没有有期徒刑的法定刑。近年来,危险驾驶行为的危害性越来越严重,成都孙伟铭案、佛山黎景全案、南京张明宝案、杭州胡斌案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这类行为多为富二代或官员实施,民间对该类行为深恶痛绝,网络上群情激愤,媒体上口诛笔伐,行政执法部门手忙脚乱,法律界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地企图用刑法遏制该种行为,一时间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一些人大代表因而提出应当将其入罪。刑法学界之外的人士多认为该罪的设立有其必要,全国人大在浙江、南京等地调查时,民间对危险驾驶的行为反应强烈,呼吁用刑法手段严厉打击该种行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时,委员们多支持设立该罪名。相反,除个别学者支持该罪名外,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做法却受到刑法学界的普遍质疑。在2010年8月《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公布之后,学术界就多有反对之声。《刑法修正案(八)》已经获得立法机关通过并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成为国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但围绕刑法是否应当设立危险驾驶罪的争论并未尘埃落定,相反,对该条文进行评估,仍然是法律学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二)判决情况
“醉酒驾驶”的危险驾驶罪是仅次于盗窃罪的“高发”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对自己以及他人生命健康予以尊重的体现,然而我们通过统计2014年-2017年判决发现,在判决总数最多的5个罪名里,危险驾驶罪判决数量位居第二,达464645件,其中“醉酒驾驶”案件有320817件,也超过位居第三名的故意伤害罪的案件数量。可见“醉酒驾驶”情况还是极为普遍的存在,应当引起我们每个人的注意。
二、问题的症结: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必要性探讨
(一)理论牵引:风险刑法的立法目的
支持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学者多以风险社会理论作为论述前提,认为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刑法应该对危险驾驶这样的高风险行为提前介入,以利于保护法益,更好地控制交通运输领域中的风险,从而体现出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的立法特征。传统刑法的中心议题是犯罪后行为人的公正处置和社会回归。但在预防刑法的框架中,犯罪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危险,既然是危险,国家就会倾向于诉诸预防性措施。刑法演变成一套控制法益侵害危险的手段与机制,刑法制度的中心问题转变为国家如何通过刑法实现对法益侵害危险的有效预防和控制。
虽然以启蒙运动为思想起点的传统刑法奉行自由意志与风险自担,不主张刑法对社会秩序过分干预。“然而,相较于启蒙哲学时代的政治经济氛围,现实风险社会的规范议题不再是强调国家统治权力的过度集中,或是自由应如何分配等,而是聚焦在社会持续处于一种高度依赖社会控制机制的氛围,亦即要求国家积极采取行动排除危险,实现安全保证的需求。”①法律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力保障实施的公共政策,其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国家透过风险管控完成维护安全的任务。现实社会因风险而特别呈现出一种不安全的社会结构及情绪氛围,针对人们日益不安的情绪,控制风险以安抚民众成为现代社会压倒性的政治需要。②因此,社会需要国家提供一套担保仪式,此一担保仪式便成为刑罚的正当性所在。较之以保守和谦抑性为特征的传统刑法,预防刑法可以向国民更有力地展示刑法的担保仪式,满足国民对安全的渴望,亦可以向国民展示国家对民众负责的姿态,从而赢得国民对国家的支持。而一旦国民对安全的现实需求汇聚成刑事政策压力,并最终通过目的的管道传递至刑法体系内部,则难免驱使刑法体系向预防目的的方向一路狂奔。③
(二)特殊个案的处罚必要性探析
1.关于隔夜醉酒的问题
在青田人民法院判决的陈肖灵危险驾驶案件中④,其是在凌晨5点醉驾被查获处刑。案件查明,嫌疑人认为自己已经经过长时间的醒酒,主观认为自己已经恢复清醒,随后开车被查获,不想依然处于醉酒状态,经过检测是105mg/100ml,因此而获刑。行为人已经认识到了醉酒的社会危害,并进行了休息,在依然还存在醉驾情况下开车,导致刑罚的后果,这就是典型的隔夜醉酒的问题。尽管依法进行了处罚,我们在考量凌晨、醒酒、酒精量接近临界点、耐酒性、行为人处于清醒状态等各种因素,是否可以适用情节显著轻微进行处罚?⑤在司法实务中,对“隔夜醉驾”性质的判定涉及对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的具体理解在“隔夜醉驾”的场合,行为人在前一天醉酒但并未驾驶机动车,在时隔一个夜晚后的第二天才驾驶机动,但是仍被查明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对此,有观点认为,一般而言,在“隔夜醉驾”的情况下,机动车驾驶人认识不到自己是在醉酒驾车的,不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将有客观归罪之嫌。但是,如果驾驶人明知自己仍处于醉酒状态而执意驾驶车辆的,则应按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观点在考察“隔夜醉驾”行为的定性问题时,合理地区分了行为人主观方面的不同情况,是较为妥当的。在我国,很多食品或饮料的生产者为了使其产品更加可口、独特,而在产品中添加了一定量的酒精或含有酒精的制品。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明确的标识等告知消费者,其在食用或饮用后又去驾驶机动车辆,则由于行为人在完全不知的情况下食用或饮用了含有酒精的食品或饮料,所以不能认定其在明知自己处于醉酒状态的情况下而仍执意实施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不能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指出,驾驶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呼气中的酒精含量超过标准值,属于过失酗酒驾车,不成立犯罪。例如:漱口水的酒精含量很高,据说是啤酒的几倍有余。假设驾驶人开车前使用大量的漱口水,呼气中的酒精含量就可能超过标准,但由于主观上出于过失,刑法不干涉。饱足姜母鸭之后,血液中也可能含有浓厚的酒精。如果开车遇上路检,也许通不过检测。驾驶人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是酒后驾车,主观上出于过失,理论上不能处罚。
2.认识错误能否作为抗辩事由
笔者在一篇化学论文中看到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20mg/100ml且<80为饮酒驾车,血液中的酒精含量>=80mg/100ml为醉酒驾车。大李在中午12点喝一瓶啤酒,下午六点检查时符合标准,紧接着晚饭时又喝了一瓶,凌晨2点检查时被定为饮酒驾车,两次喝同样多的酒,检查结果却不一样。作者建立饮酒后血液中酒精含量的数学模型后,得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喝啤酒时虽然未达到检测的醉酒的酒精浓度,但是其体内仍有酒精含量,因此虽然是同样的时间间隔,加上后面的酒精浓度,就达到了醉酒。笔者认为这种情况,行为人有意识地避免醉酒驾车,在实践认定中应当谨慎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更多的采用行政处罚,而非肆意入罪。
三、问题的思考:风险刑法的风险控制
(一)风险刑法的风险
前文提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不自觉地进入了全球化的高风险时代。又由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风险意识和权利观念日益增强,对社会和生活安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法律理所当然地成为对付风险和管理不安全因素的重要工具。刑法自然也要以控制风险为己任,因此,“风险刑法”的诞生有其必然性。但是,由于“风险刑法”偏重预防和管理,本身就蕴含着摧毁自由的巨大危险,因此,德国刑法学家黑尔扎克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危险(或风险)刑法”对刑法形成的危险(或风险)。除此之外,“风险刑法”还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1.由于应对风险的刑事立法受政治与政策因素的影响很大,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对由不被容许的风险行为激发的公众怒气,常见的政治反应便是应急性或报复性的刑事立法,即大多表现为通过创设新罪名给国民一个认真对待且已适当处理的印象。但是,这种刑事立法往往只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通常只是舒缓公众怒气、安抚公众和恢复刑事司法体系的可信度,并不能真正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因而使“风险刑法”的相关规定仅具有象征性,这或许正是外国部分学者将“风险刑法”称为“象征刑法”的原因。
2.“风险刑法”在刑事立法上的突出表现是将刑法的防卫线向前推移,实行所谓法益保护的提前化或刑罚的前置化。在德、日等国,这种处罚的早期化主要是通过在各种行政刑法中增设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来实现的。这样立法的风险是导致刑法适用的泛滥,使刑法保护社会的机能无限扩张,从而导致其人权保障的机能大大减弱。
3.由于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不被容许的风险行为就可能成立风险犯,因此就有可能产生扩大刑事处罚范围的风险。又由于被容许的风险行为与不被容许的风险行为在有些场合只有一线之差,因此很容易出现两者之界限难以划清的问题。此外,扩大风险犯的处罚范围还会使人们丧失挑战风险的信心,从而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对风险刑法的风险控制
我国的立法者在立法时自然也得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不能把外国将某种不被容许的风险行为规定为犯罪作为我国刑法中也要将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根据。例如,对酒后驾车行为,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为犯罪,并将其纳入“风险刑法”风险犯的范畴。但是,我国的立法者显然忽视了我国的道路交通法将酒后驾驶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对其给予行政拘留、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行政处罚的规定,这些处罚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规定的刑罚并无实质的不同,惩罚的轻重程度也无太大的差异。⑥笔者认为,将仅实施了酒后驾车但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不仅与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以及设罪的标准不协调,而且也与民众心目中的犯罪观念不相符。况且,治理酒后驾车的关键并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司法。因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效果并不是由惩罚的严厉性所决定的,而是由惩罚的必然性和及时性决定的。如果说外国法律规定为犯罪的不被容许风险行为在我国刑法中也应该规定为犯罪,那么,日本道路交通法除了将酒后驾驶规定为犯罪之外,还将疲劳驾驶、超速行驶、无执照驾驶、在禁止超车处超车等行为也规定为犯罪,这是否意味着我国也应当将这些交通违章行为规定为犯罪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刑法中没有必要规定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是“后现代的背景,前现代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在后现代背景下为反思现代性而提出的“风险社会”的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不能以风险社会作为论证危险驾驶罪合理性的根据。并非以科学的方法获得的“民意”不能成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民意基础。行政权重效率,司法权重公正,以刑罚方式惩治多发但危害不大的危险驾驶行为反而不利于遏制该种行为。
【注释】
①古承宗.风险社会与现代刑法的象征性.科技法学评论(第10卷),2013年第1期,第130页.
②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③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④丽青刑初字第225号判决书,2011.
⑤周宏伟.危险驾驶罪中醉驾认定的疑难问题实证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⑥刘明祥.风险刑法的风险控制.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