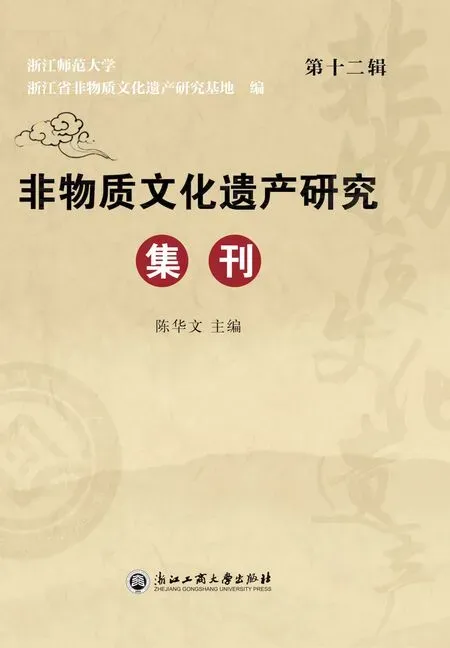越裔导演电影中的民族形象及其文化表征
陈爱国 章 雄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1)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电影逐渐成为亚洲电影的有生力量,这得力于越南革新开放政策的实行与越南对电影事业的扶持,更得力于一批欧美越裔导演的积极参与。他们将法国“艺术电影”、美国“新好莱坞电影”的先进观念以及拍摄技术带入越南,通过获得各种国际电影节的重要奖项,改写了越南题材电影和越南电影的历史,也建构了多重的越南民族形象。
这些让全球刮目相看的影片,主要有法籍越裔导演陈英雄的“越南三部曲”《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美籍越裔导演包东尼的《恋恋三季》、阮武严明的《牧童》、刘皇的《穿白丝绸的女人》等。他们明白“电影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是诗的语言”(1)[意]皮·保·帕索里尼:《诗电影》,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77页。,运用充满诗意的镜头来构建越南电影新形态,往往通过象征和隐喻来传情达意,将越南文化的韵味呈现得淋漓尽致,创造了越南式的“诗意电影”“文化电影”。这种艺术观念也逐渐影响了越南本土导演,拍出了一些风格近似的影片,如邓一明的《番石榴季节》、阮青云的《流沙岁月》、吴光海的《飘的故事》等。
更进一步,这些越裔导演由于身份认同、文化观念、生产目标等多种原因,他们将欧美的电影语言和价值观念带入越南题材和越南文化,将此岸现实与彼岸理想杂糅起来,将越南文化和地域空间装点成时髦而独特的影像产品,以便将越南电影推向世界,重构越南在国际文化视野中的多重形象,同时寄寓海外游子复杂的文化关怀。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意义不在客体或人或事物中,也不在词语中。……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建构出来的”,而所谓表征,就是“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2)[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29页。由此可见,他们将传统与现代、故国与西方的文化观照糅合其中,建构出“故国越南”“田园越南”和“丛林越南”的不同民族形象,而且这些形象在他们的影片中都是并存交织的,表征着他们复杂的文化关怀。对于他们而言,这既是一种文化怀旧,也是一种文化反思。
一、“故国越南”:民族本土文化的归依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越南题材电影基本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越南本土导演拍摄的政治电影、抗战电影,遵循着胡志明的“极左”文艺思想,对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鲜有真实反映,比较优秀的有《浮村》《琛姑娘的森林》《回故乡之路》等,因为切入角度较小,具有一定娱乐性。一种是欧美导演拍摄的殖民电影、越战电影,基本都是西方“他者化”的文化想象。如法国人拍摄的《情人》《印度支那》等,无非是慰藉自己的殖民情结,追忆昔日浪漫荣光;美国人拍摄的《现代启示录》《猎鹿人》《野战排》《天与地》等,作为美国人的一种战争反思与人性关怀,依然带有美化侵略的大国倾向。
不同于越南本国规约化的政治图解,不同于纯粹西方他者化的文化想象,一些欧美越裔导演对故国民族文化的回望与凝视,勾勒出基本真实的历史面貌,倾注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抒发着浓厚的怀旧情绪,为世人塑造了不带明显政治偏见、接近历史真实的“故国”越南形象。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和谐的人伦关系并非凝固不变,而会与现代文明产生某种冲突,处于动态的纠偏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是越裔导演建构故国越南形象的场域与主题之一,也是文化反思、价值融合之后的民族文化的自新。如果说《青木瓜之味》中小梅从女仆到主妇的身份转换还体现着越南的传统本色,并非人心不古的现代性后果,那么《夏天的滋味》中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映射着越裔导演对越南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复杂心情。该片对都市婚恋情感进行深层开掘,在温暖而朴素、诗意而怀旧、安静而祥和的传统家庭生活之外,现代人的精神困惑与非常情欲接踵而至,困扰着河内的富裕家庭,喻示着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传统伦理道德,可能有点偏离了真实的人性。但是纠结纷乱的最后,整个家庭又回到新的平衡状态。陈英雄的“越南三部曲”都有女人洗头洗澡的镜头,洗浴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身体清洗、精神洗礼的象征。
其次,努力塑造具有民族文化底蕴的符号化人物形象,如文人、女人等,他们是“故国越南”的灵魂人物,是民族文化精神与伦理道德的体现。文人、艺人或文艺爱好者是民族文化的直接载体,是审视社会文化的窗口。在越裔导演的电影中,尤其是陈英雄的“越南三部曲”中,文人的形象始终是一个重要角色,寄寓着他们内心深沉冷峻的怀乡情怀,给影片增加了鲜明的文化质感,在不知不觉间唤起民族的文化记忆和诗意联想。《青木瓜之味》中,布店男主人是古典音乐的代表者,低缓而悠长的月琴声是他的全部心声与情感寄托。这种古典“艺痴”与“怨夫”的形象,似乎暗喻越南民族文化遭受过外界严重的隔离与打击。阿权是现代音乐的代表者,即便如此,他也极力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其节奏缓慢的钢琴乐曲具有自然音乐的韵味。《夏天的滋味》中,大姐的丈夫昆是个摄影师,二姐的丈夫金是个作家,他们热爱植物与山水,对传统伦理和自我欲求都有过一些想法,但他们跟《青木瓜之味》中的男主人一样,最后都带着创伤回归传统家庭。
《三轮车夫》中的现代诗人是个很复杂的人物形象,可能更接近现代文明中的越南文化人,其文化回归也运用了死亡情节,却不是死而复生,而是向死而生。本性善良的他在都市中沉沦,杀人越货,逢场作戏,为传统父亲所不容。他还替三轮车夫的姐姐拉皮条,将伤害她的嫖客杀死。但是他内心空虚而痛苦,有流鼻血的毛病,唯有从纯真善良的车夫姐姐那里得到慰藉,迸发写诗的灵感,渴望一片光明。一直在痛苦中挣扎的他,最后纵火烧毁自己经营的地下妓院,在大火中自杀,以求灵魂的新生。最后车夫带着姐姐离开都市时的画外音,是死去的诗人吟诵渴望光明与超脱的诗歌。
《恋恋三季》在民族文化认同上的意义表达,更为鲜明而强烈。该片中的老诗人杜先生,是个喜欢用古体诗歌表达民族心声的诗人,年轻时因参加民族独立运动而被逮捕、迫害,也是个罹患麻风病而幽居几十年的老者,行将就木之际,采莲女的儿时歌谣打动了他,唤起他生命中创作诗歌的热情。用美丽词句尽情歌颂荷花的诗人,代表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而其长期身患绝症的痛苦,则象征越南民族的外来戕害。病入膏肓的诗人去世,是饱经战争苦难时代的离去,而留下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诗篇,在采莲女那里得到延续。这种由诗人形象所构建的文化图景,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寓言的性质。
越裔导演电影对越南女人形象的持续关注,不仅是对故乡老家的依恋,还是审视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祖国与母亲之间具有文化原型意义的亲密联系,而儒家文化背景下女人的家庭重负也成为国家命运、民族精神的表征。美籍越裔导演郑明河的《姓越名南》,对饱受战争苦难的越南女人的采访,具有家国同构的意义。对越南女性形象的关注,也是陈英雄“越南三部曲”的重点。《青木瓜之味》中的布店女主人,几乎独立支撑整个家庭,还要忍受丈夫的一再偷钱、离家、出轨,因为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女仆小梅从小到大操持主人的家务,不断生火、做菜、洗衣、擦地,最后成为心仪男人的仆人,成功变身为女主人,两情相悦,还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本色。《穿白丝绸的女人》中的丹,忍受着来自总督、富人、战争、洪水的无尽折磨,依然心志坚定,忍辱负重,直到被洪水吞没。为了支撑家庭,不得不将本该给小女儿的母乳,卖给富人家的白发老头,而当她将白发老头抱在怀中喂奶时,那种伟大的母性被升华起来,犹如地母、圣母一般。这虽然有讨好西方的“东方奇观展示”的嫌疑,但民族文化意义的升华不容否认,这里既有佛教的舍身精神,又有儒教的舍身精神。
最后,重视运用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符号,如植物、服饰、器物、音乐等,构建越南传统的民族形象。这些属于传统越南的东西,与民族文化内涵息息相关。这里“已经触及了某种形式化……它多少代表着一种进步,这种形式化可以在合理的期限内加以考虑:其任务是通过言语之间的相互转换,建立能指物质的确切特征”(4)[法]克里斯丁·麦茨:《电影语言的符号学研究:我们离真正格式化的可能性有多远?》,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54页。。这些具有意境美和文化美的东西,既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荷花是越南的国花,也是佛教文化的符号,寄寓力量、吉祥、平安、光明之意,表征着传统越南的文化形象。越裔导演的电影经常出现荷花的意象,很多女孩的名字叫莲,包东尼最早完成的影片《黄莲》,即展示以莲花为依托的越南民族风情。《恋恋三季》中,老诗人住在荷塘中间的屋子里,多次出现荷塘轻舟、荷花浮动的画面,荷花成了人们热爱生活、传递善意的道具,也是荷花将三个毫无关联的故事巧妙串联在一起。尤其是美国退伍老兵将一束荷花送到女儿手上,荷花便成为谅解、重生和希望的代名词。最后,女佣们齐唱着歌谣,将许多荷花撒入湄公河,祭奠诗人杜先生的亡灵,愿他的灵魂化为荷花,洁白无瑕;愿他的灵魂像湄公河的河水,奔腾不息。
丝绸长衫是越南的民族服装,甚至是越南女性的国服,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奥黛”,改装自中国清代的旗袍。越南的街巷与村落,随处可见身穿奥黛、裙角飞扬的女性。《穿白丝绸的女人》中,驼背男人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件白丝绸,送给丹作为结婚礼物,被她视为爱情的象征,后来没钱给女儿买白纱绸做校服,不得不将白丝绸嫁衣改小,让两个女儿轮流穿着上学,最后女儿在纷飞战火中高举白丝绸,作为寻找离散家人的信物。影片结尾,出现很多身穿白丝绸的女人背影,揭示了影片的主题:“妈妈说,白丝绸象征的是,越南女人无尽的苦难,还有宽容,经过无尽战火和艰困环境的摧残,越南的白丝衫依然美丽。越南女人的美,无法用白皙的皮肤、丰腴的脸颊和红润的嘴唇来衡量,而是由优雅的白丝绸衣衫来彰显,它代表的是真诚、纯洁与优雅……”《青木瓜之味》中的女仆小梅、《恋恋三季》中的妓女莲,在人生最美丽动人的时刻,都穿上了丝绸长衫。
除此之外,姜祈还报名参加了两个月后举办的全国高中生数学竞赛,似乎表明抽签入学的学生也非等闲之辈,一时成为高一年级颇有话题的风云人物。
越裔导演的影片中,被作为民族精神、东方情调、影像景观的文化符号,还有传统音乐、传统器物等。几乎每部影片都喜欢将越南民族音乐作为背景音乐予以贯穿,渲染出浓厚的东方韵味,这既与主人公的文人、艺人身份有关,又寄寓着一种浓郁的文化乡愁。还有水中的高脚房屋、幽静的庭院长廊、安静的雕花家具、泛光的瓷器古董、优雅的商品包装,等等,都在诉说本土文化与故国越南的点点滴滴。这些空间影像的美学符号构成了贯穿全片的线索,服务于或清新或淡雅、或哀痛或坚韧的民族形象的塑造,从而成为影片人物情感外化、主题彰显和文化审美的重要部分。
越裔导演通过“文化电影”基本还原了越南的历史文化形象,实现了民族文化认同。他们的文化凝视不同于西方人,但在西方人眼中,又是具有东方面孔的越南人,因此他们需要从自己的故国文化中寻找自己的身份源泉,“回望故乡,是每一个人自我辨认的需要,也是远行的证明”(5)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页。。
二、“田园越南”:生命栖息家园的想象
对越南本土来说,欧美越裔导演因为有移居海外、接受欧美教育的经历,多少是以“他者”的身份出现的,其作品的拍摄得力于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注定会以“他者”的眼光来凝视越南,多少带有西方文化的痕迹。这种他者化的东西不是政治偏见、文化隔膜,而是西方人眼中预期的异域文化,是越裔导演和现代西方都希望看到的田园牧歌,这是越裔导演追求艺术成功与商业价值的重要保证。更准确地说,越裔导演在展现“故国越南”、纠正越南国际文化形象的基础上,还企图将越南提升为温馨而浪漫的人类栖息家园,想象成具有诗意与生态特征的“田园越南”。这可能是他们创作越南式“诗意电影”的真正目的,也是对“故国越南”进行文化反思的一种结果,即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现代性价值的联系。
首先,田园想象与越南人的诗歌崇拜情结紧密相关,唯美的画面与缓慢的节奏指向一种诗性的“慢生活”。越南新电影的诗性特征,既借用了欧洲艺术电影常用的散文诗形式,又与越南作为汉文化圈的诗性传统有关。“在越南近1000年的文学发展中,民间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民间文学历史发展体现了越南民族意识的复兴和提高”,也深深影响了成文文学,因为“越南文学的发展里程,不难发现越南文学史上的一些大诗人如阮廌、胡春香和阮攸等都受到了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歌谣的巨大影响”(6)于在照:《越南文学史》,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7页。,可见诗歌在越南民众文化生活中的普及性与重要性。陈英雄也曾说,“对越南人来说,诗是非常重要的”“越南似乎总能唤起影片制作者诗意的想像。”(7)高远:《越南影片〈盛夏时节〉——评价与导演访谈》,《世界电影》2002年第2期。越裔导演身在海外,对故乡的怀念无时不在,与故国的精神联系更是无法割断,随之将这种诗性崇拜情结糅合进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在越裔导演的镜头下,越南的各种空间影像大多意境深远、韵味恬淡,以此凸现越南的东方文化形象。无论是古香古色的封闭庭院,碧波荡漾的辽阔水域,还是历经战乱的故国山河,都呈现为一个宁静、悠远、内敛的古老世界,苦难中包含着希望,动荡中孕育着幸福。这些归自海外的导演就像抒情诗人一样,尽情渲染一种气氛,造就一种心绪,“帮助我们自己在心中发现一种静观的快乐,这种快乐是那样容易扩张,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个切近的对象面前体验到内心空间的扩大”(8)[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在诗意镜头的抒写下,银幕上的“田园越南”形象裹挟着一股永恒的唯美诗意,成为一种奇特的神秘诱惑,令人欲罢不能。陈英雄镜头下那种缓慢得令人窒息的画面节奏,可能会被指责是阿伦·雷乃或塔尔科夫斯基的,可包东尼、阮武严明、刘皇的镜头也不全是科波拉或斯皮尔伯格的,他们和中国的费穆、侯孝贤、王家卫、霍建起一样,都将东方题材指向一种现代文明之外的、传统的、诗性的“慢生活”。
在越裔导演的镜头下,精致唯美的景物造型和空间影像被强化,既具有“诗意电影”主体结构的作用,又表征着“文化电影”的东方情调。电影是依靠镜头语言来组织结构框架的,而诗意电影渲染气氛最重要的手段,是强调视觉画面感官的冲击,淡化故事情节的作用。陈英雄说过:“我心目中真正理想的、完美的电影,是一部经由影像的结构化过程产生意义与感动的电影。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因电影语言受到感动,而不是因为故事内容受到感动。”(9)陈明华:《浅析越南影像的文化表达策略——以陈英雄的作品为例》,《电影文学》,2008年第16期。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意电影”注重画面的情调营造,有别于阿伦·雷乃或塔尔科夫斯基的,后二者的“诗意电影”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包东尼的《恋恋三季》在注重线性结构的同时,尽情渲染莲花、荷叶、轻舟、歌谣、采花女等诗意画面,令人仿佛触摸得到古典诗歌里的柔软与清香,而漫天飞舞的凤凰花、越南少女的典型白衫、车夫和妓女的真诚笑容,更是令人动容。越裔导演们都非常重视选择或搭建景色优美且与影片格调搭配的地点进行拍摄,追求影像空间的诗情画意,淡化情节的作用,力求镜头语言的精雕细琢。其电影中,幽幽道来的故事情节是第二位的,而东方情调的空间影像是第一位的。
其次,越裔导演所凝视的镜像世界,流淌着浪漫温馨而诗意盎然的乡土家园气息。这不单单是越裔导演对故国山河的拔高,更与越南本身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有关。越南是山林与平原并举的热带国家,被称为“美丽的绿色国家”,因为“越南全国山林面积16万平方千米,占土地面积的50%左右,其中森林面积10.4万平方千米,覆盖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在此绿色生态环境之中,“西原地区肥沃的红土泥层及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水和丰富的水源,十分有利于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农业可以实现一年种植三到四季,可谓物产丰富。越南是咖啡、大米、橡胶、椰子的重要出口国,还盛产“香蕉、菠萝、柠檬、柑橘、杧果、龙眼、荔枝、木瓜等热带水果,味美可口;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四季不断”(10)张加祥、俞培玲:《越南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自然、农业的条件,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而且民间文化和士子文化的乡土气息、自然色彩都极为浓厚。
在越裔导演的镜头下,无论是悠闲生活的个人化回顾,还是苦难民生的深度化阐释,都是以“乡土家园”为中介或者线索展开的。“乡土家园”或者“家”的形象,在越裔导演这里是一个具有诗性和延伸意义的具象符号,是萦绕在越南人心间的永恒命题。 一般说来,“现代人徒有快活却不感到幸福,不仅情感无处依托、灵魂毫无遮蔽,而且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把握连续的历史和完整的生命状态,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浮在活的表层,在当下的时间体验中感受这种文化的‘断裂感’”(11)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页。。身为海外游子的越裔导演们,这种“断裂感”既来自普遍的现代文明,也来自他国的异域文明,于是努力寻求那种“被环绕和被拥抱感,一种亲切的联系和信赖”(12)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页。。具有自然色彩、永恒意义的“乡土家园”,因此成为越裔导演们诗意凝视的最佳载体。
阮武严明的《牧童》以充满诗意的格调,描写湄公河三角洲的日常生活:古朴的茅屋、平静的水流、河中的扁舟、悠闲的牛群、远处的森林,再现了导演对于乡土家园的无限留恋与深深忧伤。《穿白丝绸的女人》中,温润的汗珠水滴、丰盈的绿色植物、潺潺不息的雨声,衬以纷乱的革命暴动与战争炮火,表现了导演对田园牧歌的向往,而丹一家人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始终相聚相守,相濡以沫,也勾起人们对人类乡土家园的渴望。越裔导演在心灵深处构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乡土家园,为解读越南形象提供了一种想象方式。《青木瓜之味》利用缓慢的移动镜头,通过小梅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静谧的越南大宅院中诗意唯美、温婉安详的生活画卷,同时多次利用战机划过天空的声音和宵禁的警报声,提示人们这是殖民战争、南北战争中的越南社会。具有古朴情韵的“乡土家园”,是被残酷历史背景衬托出来的,这似乎是“乡土家园”现实处境的一种隐喻,即需要人们自己在艰苦环境中去追寻、建构。
越裔导演电影也存在着明显的植物叙事的倾向,无论都市题材还是乡土题材,都注意用一种或几种植物作为文化符号,寄寓着“乡土家园”或者“家”的信息。《青木瓜之味》中,庭院中挺拔一棵茂盛的木瓜树,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而将木瓜做成菜肴,绿色木瓜的形象就容易让人联想到操持家务的女性,一种来自“家”的母性。《三轮车夫》中,车夫姐姐发现了堕落诗人的纯真一面,特意买来一盆绿植送给他,绿植与诗人自焚后的废墟形成对比,绿植无法拯救他,却变成他灵魂得以升华的象征。《穿白丝绸的女人》中,驼背男人一直守候在一棵榕树边,那是母亲指定的,后来他有了安定的家,就在自家门前栽下一棵槟榔树,其意义都指向了普遍意义的“家园”。《恋恋三季》中,荷花将三个毫无关联的故事串联在一起,还起到沟通人际情感的作用,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女人和“家园”。而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可食性植物在影片中的反复呈现,不仅是越裔导演们对故乡食物的留恋,也成为他们电影的一道文化消费景观,颇有点美食片的味道,于是获得了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最后,作为独具特色的镜头语言,绚丽色彩也帮助“诗意电影”呈现出富有梦幻色彩的异域情调。越裔导演对光影色彩的娴熟运用,是他们对生活的思考、感悟的结果,赋予其作品“一股内在的力量,这股力量凝聚于影像中,以感性的形式向观众呈现,引发出张力,直接回应了作者的叙事逻辑”(13)[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夏天的滋味》中,妩媚柔和的色彩展现了水彩画般的画面:姐妹三人水蓝色的衬衫和乌黑的长发,热带水果橙黄的皮和红色的瓤,“山抱水围别有天”的碧水,神秘女子在飞机上用口红涂写的数字,在镜头的注视下缓缓推动情节的发展。《穿白丝绸的女人》中,全片色彩清新且干净,是人物身上着装的朴素淡雅,是高大槟榔树的葱翠欲滴,是废弃建筑外闪现的绿意,是苦难生活时的黑白影调,在展现故国人民苦难的同时,又为劳苦大众顽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所倾倒。绚丽色彩给观众带来不同凡响的视觉享受,同时能够参与情节的进展和情绪的酝酿,既符合“诗意电影”的审美情趣,又增添诗意的异域情调。
在越裔导演的镜像式想象中,越南民众传统的诗歌崇拜情结、浪漫温馨的乡土家园气息及对绚丽色彩的运用,被整合在一起,抒写着“田园越南”形象的唯美诗意画面,打破了西方导演镜头下越南被描绘成蛮族形象的局面,进而成为异域文化与精神家园的一种现代性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越裔导演的“诗意电影”成了越南扩大文化旅游、吸引外国游客的隐性广告。
三、“丛林越南”:平民社会生活的关怀
在缅怀故国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之时,越裔导演们并没有忘记故国现实生活的问题与战争历史的症结。“1986年实施革新开放政策以来,越南城乡居民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困率日益下降。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乱,底子很薄。总体而言,越南民众还是非常贫苦。”(14)孙兆东、张志前、涂俊:《越南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72页。越南盾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遇上持续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众多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就显现出来,人心浮动,民怨沸腾。“越南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已经节省到只能以鸡蛋、腐乳、蔬菜为主,偶尔才能吃上顿肉,也算是打打牙祭。”(15)孙兆东、张志前、涂俊:《越南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72页。在残酷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丛林越南”的形象被凸显出来。
越裔导演在注视越南的残酷社会现实时,运用的叙事视角是平民化的,表现出的艺术精神不是丛林法则与强人哲学,而是平民意识与人道主义。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问题,是越裔导演文化关怀的一个层面,必须在文化关怀的框架内,进行一定的文化反思,予以话语意义的解决。他们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比越南本土导演有着更深入的了解,也比他们更懂得民主人道的含义。他们的电影展示了有关“丛林越南”形象的平民生活景观,触及越南社会各种复杂的现实纷争和观念冲突。
首先,对越南现实社会进行文化审视的最佳切入点是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客观呈现底层人物的境遇与命运。这其实是一个“丛林求生记”的过程。关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命运历史,摒弃政治标准和非人标准,这是亚洲新电影普遍采用的叙事视角和价值取向。1987年,即越南实行革新开放政策的第二年,本土导演邓一明推出爱情片《江上姑娘》,在越南电影史上第一次关注人物的普通生活和真实人性,运用平民视角而非政治视角,颠覆了人们以往对于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认识。但是在至今强调主旋律的越南,这只是一缕清风。从平民的视角讲述小人物在当下社会的命运,实现文化内涵的延伸与富足,这是越裔导演“诗意电影”喜爱的叙事模式,也是其诗意关照历史与现实的一般方式。这里不是故事情节的高潮式推进,而是对小人物生活的片段表达,“讲述的故事因此被看作生活与痛苦的基本观点之上的想象力的变化”(16)[加]马里奥·J.瓦尔德斯:《诗意的诠释学——文学、电影与文化史研究》,史惠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充满着点到即止的深意。
《三轮车夫》是年轻车夫的“城市历险记”,真实地表现出越南社会底层的残酷生活现状。神情麻木的三轮车夫、突如其来的暴力、混乱不堪的街道等等,该片从个体的命运纠葛中,深刻触及越南当下社会的真实现状。该片被官方指责为“阴暗面表现太多”,一度在越南禁映。但是,在平民化视角的观照下,困难与幸福、暴力与和平、泪水与笑颜、期待与失望、愉悦与沮丧,小人物人生的两极被混合在一起,没有传统的喜剧与悲剧,唯有混沌复杂的现实人生,电影文化内涵的包容性被大大拓展。该片一举夺得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至今仍是越裔导演和越南导演获得的最高奖项。
《牧童》是牧童金姆的“水上历险记”。他将两头水牛带到附近山坡吃草,开始踏入令人晕眩的成人世界,霸凌、斗殴、吸毒、强奸、酗酒等社会罪恶,纷纷进入他的眼中,他逐渐变得凶狠无情,为父母所不容。再次踏入征途后,他俨然成为强者,收获了友情、亲情和爱情,实现了自己作为当代越南乡村男人的“野蛮生长”与“生命轮回”。该片作为一部乡村成长电影,对应着当代越南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而牧童在成长过程所遇到的各种困惑,更是越裔导演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观照与反思。
其次,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是越南社会现代化绕不开的主题,其共同点是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怀。越裔导演对热带故乡的怀恋与想象,使得他们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对还未受到现代工业文明侵袭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美化和眷念。当他们从西方重新踏上故土时,或从西方媒体感受到故国时,按理应该产生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即“那些初到那个地区的人只要留在那儿,其行为方式便会被当地同化”(17)[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但是在现代经济力量的驱动下,越南社会传统的纯真受到侵蚀,正在变化的生活景观让他们觉得熟悉而又陌生。诗意想象之余,越裔导演依然保持着清醒,没有忽视对社会问题及其历史背景的关注,注重表现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尊重与追求,辩证地看待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诗是一种对世界的了解,一种叙述现实的特殊方式,所以诗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指南。”(18)[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借助于“诗意电影”的诗意凝视,越裔导演们可以包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寻求人类共同的情感与价值,也即一种普适价值:关爱生命。《恋恋三季》的三个主角都是社会底层人物,身处各种困境,依然坚持自我,没有对现实生活丧失信心与追求。采莲女对莲花和诗歌的爱恋,三轮车夫对沉沦妓女的守望,流浪儿对影视和游戏的投入,都显示出生命的本真和朴实的快乐。该片着重表现的是越南进入革新开放时代后的民众生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比十分明显,是迷失自我的“丛林越南”的生动隐喻,寻找本该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成为该片的最高主题。现代文明在推动社会发展时,也在摧毁传统生活方式,致使越南社会变得畸形化,人性扭曲冷酷,丧失本真自我。该片三条线索的贯穿动作都是寻找,老诗人杜先生寻找逝去的青春与激情,车夫海寻找美丽的爱情,流浪儿胡迪寻找丢失的售货箱。他们的各种寻找可能是卑微的、可笑的,却是他们个体生命意识的显现,也即对本真自我的寻找。
《三轮车夫》中的现代都市充斥着各种暴力场面,正如车夫所遇见的屠宰场杀猪的血腥场面,而历经苦难、生不如死的年轻车夫一家,最终得到人性化的谅解与解脱,又回到那种虽劳累穷苦却安稳祥和的传统乡村生活中。无论是对社会暴力的风格化展示,还是对畸形社会的符号化解读,都没有简单地批判现代文明的侵蚀、传统文明的固守,更没有自然主义地展示弱肉强食、黑白颠倒的荒诞哲学,而是处处体现对生命意识的还原、尊重与追求。这是“丛林越南”形象建构中一个讨巧的价值标准,既具有永恒意义,又能缝合越南国内外观众的价值裂痕。
最后,对“丛林越南”进行文化关怀,必须遵守伦理自律意识。这是尊重个体生命意识的另一面,也是对“故国越南”的某种回归,越南民族文化中的和谐人伦关系,其核心之一是伦理自律与自省,而且上下每人都必须遵循。在越裔导演的诗意镜头下,平民化叙述视角决定了主人公身份的卑微,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意味着人物命运的多舛,在此人文关怀的基础上,强调一种普遍的伦理自律意识,可能会有助于现代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越裔导演在审视越南社会现实、塑造“丛林越南”形象的过程中,那种源自西方法制社会的清醒,使他们敢于面对真实人性场景,最终回归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换。
《夏天的滋味》中,大户人家的三姐妹过着富足和谐的家庭生活,但潜藏的情欲将家里的三女三男都投入“偷妻”的情感旋涡,尤其是大姐夫妇双双出轨,三妹莲与哥哥差点乱伦,物质的理性拯救不了精神的非理性。他们最后都纷纷回归家庭,体现出一定的伦理自律意识,但是这种意识是依靠各自的感情伤痛换取的,似乎说明他们都不是“圣人”,都是“凡人”。自我追求与自我批判,是人类生命意识的基本内在动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内在动力。《恋恋三季》中,妓女莲唯利是图,纸醉金迷,一心想通过勾引豪华酒店的客人来摆脱生活困境,不肯下嫁给车夫海。海在她被客人侮辱、抱病在家时悉心照顾她,实现了她“在有冷气的大床上安睡一夜”的愿望,她最终被车夫海的真诚所打动。这种意外的突转,让精神的渴求最终战胜物质的诱惑,而这种精神不仅是真诚的爱情,还是伦理自律意识。这种意识也不仅是“妓女天生配车夫”,还是因车夫海诸多关照、无私奉献而激发的良心与良知。
总之,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有助于越裔导演最直观、最残酷地切入越南现实社会,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可以审视人们如何迷失自我、寻找自我,对伦理自律意识的提倡则可以看作是“丛林越南”的出路与良药。在真实人性的关照与递进下,越裔导演打破了越南本土电影以意识形态宣传为重的局面,打破了越南底层题材“健康向上”“励志奋斗”的褊狭观念,为世界塑造出真实生动的“丛林越南”形象,并给予了一定的文化反思。
四、结 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越裔导演陈英雄、包东尼、刘皇等人,出于身份认同、艺术目标等原因,先后拍摄了一批越南题材的著名电影,创造了越南式的“诗意电影”“文化电影”,并将传统与现代、故国与他国的文化观照糅合其中,建构出“故国越南”“田园越南”和“丛林越南”的不同民族形象。而且,这三重民族形象在他们的影片中都是并存、交织的,寄寓着他们复杂的文化评判态度。
可以说,缅怀传统、想象田园、反思现实,这三者构成了越裔导演文化关怀与反思的三个支点。缅怀传统是其民族身份的文化归依与文化记忆,想象田园是对民族文化与地域空间的现代性价值提升,而反思现实是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的文化融合。
由于特殊的双重身份,他们在面对故国题材时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情感,总体上流露为文化价值的怀旧与反思。他们带着“中间人”的眼光审视越南的历史与现实,注定逃脱不了满足西方人猎奇心理和奇观展示的窠臼。但是,“欧洲国际电影节上欧洲中心主义的呈现,并非始终索求着某种‘滞后’、贫穷、愚昧的第三世界图景,在更多的情况下,它相反渴求着差异性的第三世界文化所可能携带的生命力”(19)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241 页。。欧美越裔导演们对故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凝视,极大地提升了越南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地位,改善了越南在国际社会的文化形象,为越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这批欧美越裔导演对越南题材的关注与弘扬,基本集中于1993年至2006年,此后大多转向国际题材,刘皇虽然至今坚持拍摄越南题材,但都是商业电影,不再有艺术佳作问世。这批导演都步入中年,对于故国历史与文化不再有昔日的艺术激情与文化想象,这使得越裔导演的越南电影成为一段辉煌的历史记忆。不过这是一个极有意味的电影现象与话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