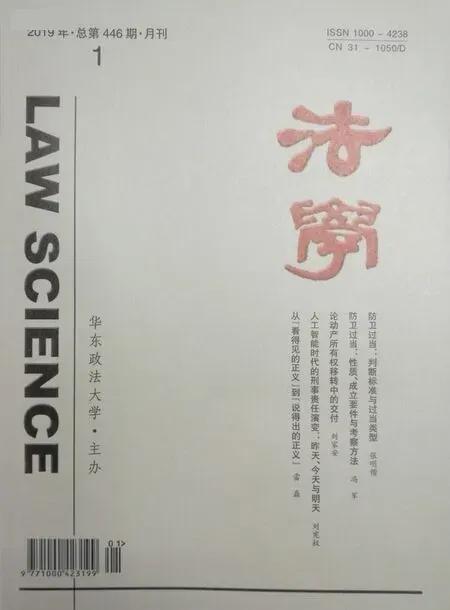物权公示原则的理论构成
——以制度正当性为重心
●张双根
物权需要公示,物权法贯行公示原则,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原理。但是,物权法为何需要实行公示原则、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模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系、通常所说的物权公示的三重效力(即物权转让效力、善意取得效力与物权推定效力)之间又处于何种关联等疑问在学理上却未必均已得到回答或澄清。目前的民法典编纂工作似乎已近尾声,但稍稍浏览2018年9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布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即可发现涉及物权公示原则的相关条文,除些许无关实质的措辞外,基本上是复制现行《物权法》的规定。这也表明民法典编纂工作并未给立法者提供深入思考物权公示原则法理的契机。鉴于物权公示原则乃物权法上一项基本的结构性原则,直接决定相关条文的设计,而这些疑问又关乎这些条文能否得到正确的理解与适用,本文特着眼于该原则的理论构成,贡献一隅之见。
一、物权公示原则的正当性基础考察
(一)物权公示的法政策基础
学理上的通行观点认为物权公示的正当性源于物权的对世效力或绝对排他效力。〔1〕如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版,第89页(但须注意的是,该书自第5版起采刘家安教授的主张,详见下述);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版,第50页;郭明瑞:《关于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诸问题的思考》,《清华法学》2017年第2期。但是,只要对比一下物权与人格权,这一说法之不可靠也就不揭自明,即同样具有绝对排他效力的人格权为何并不遵循公示逻辑。这也意味着仅凭物权的绝对排他效力显然尚不足以推导出支撑物权法体系建构的物权公示原则。为把握物权公示的逻辑,不妨自权利的一般理论出发逐步予以观察。
首先,暂不考虑各种权利效力构成的差异,自权利概念的一般理论来看,包括物权在内的一切私法权利,均是法律概念的构造产物。具言之,权利概念是法律思维工具,属于无形的精神世界范畴,须借助语言或文字予以表达,并经由表达而在法律共同体内部获得沟通、认知与理解,并导向实现(也就是权利的享有与行使,进而包括权利的效力属性与射程范围)。因此,除表达工具(即语言或文字)外,是否须借助外部性手段使权利为外界(公示意义上的第三人或社会公众)所感知,并非权利概念(包括成立与行使)的内在构成要素。〔2〕Vgl. Hedinger, Über Publizitätsdenken im Sachenrecht, Abhandlungen zum schweizerischen Recht, Bern 1987, S. 8 f.; 类似看法,亦参见聂卫锋:《动产所有权的交付变动规则》,《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这是基于权利概念的一般理论所获得的认识。而这一认识也进一步表明物权之异于其他私法权利,尤其是异于仅具有相对性效力的债权,要求须为外部感知或认识,须满足公示要素,并不能从权利概念构成的内在逻辑进行推导。反面言之,在公示原则之下所要求的公示要素,只能从物权概念的外部找寻,亦即公示要素只能构成物权概念的外置性要素。
其次,着眼于物权的客体。虽同为绝对性支配权,但物权区别于人格权等支配权的最本质特点在于物权的客体为物,且为有体物。〔3〕须先行交代的是,本文在论说上先围绕有体物展开,至于权利上物权的公示问题,则在下述相关环节作特别处理。物权以物为其权利客体,而物又经由物权概念的作用得以归属于特定的主体,从而在主体(人)与客体(物)之间形成特定的法律归属关系,物的归属秩序也就得以形成与维系。〔4〕就物权性质本文采“物的归属说”,其相关理论争议,可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这种物的归属关系尽管只能借助物权概念得以表达,不能显现于感知世界,但作为客体的物因其有体性,其存在却可以为人所感知。〔5〕相关论述参见张双根:《物的概念若干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物权成立于有体物之上,有体物又可为人所感知,这一点恰恰暗合了上述物权公示为外置性要素的思路。这种暗合也似乎意味着相较于其他的绝对性支配权,外在于权利概念且可感知的有体物自身至少可以在物权公示手段上多出一种设计选项。
最后,再落脚于对物权公示之意义的追问,即在整个物权法领域中,公示制度是对所有各项制度均具有实质性意义,还是说其功能主要体现在某一或某部分制度中?物权法规范在内容上可大别为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静态方面的规范主要包括物权的享有、除行使处分权以外的物权行使以及物权保护等。这些静态方面的规范均以物权人如何实现其物权利益为核心,而物权人以外的人一般只负有尊重与不侵犯的义务,且主要体现于物权保护规范;就该尊重义务的构成,倘若在侵害人的主观认知方面有所要求的话,那么这一认知的界限仅在于使侵害人认识到所侵害之物属于他人,且仅此即为已足,至于该物到底归属于哪一特定的他人,则已无关该尊重义务的成立;倘若为了满足这一认知目的而设置物权公示规范,那么这样的规范与其说是“对外的公示”规范,不如说是“向内的私示”规范,这显然已不是公示原则的本义了。〔6〕Vgl. Shuanggen Zhang, Das Publizitätsprinzip und der rechtsgeschäftliche Mobiliarerwerb, Berlin 2004, S. 23 ff.而动态方面的规范也就是物权变动规范。其中就法定方式(即非依法律行为方式)的物权变动而言,〔7〕在现行法上主要体现于《物权法》第二章第三节,共4个条文。顺便指出,这4个条文(实为3个,第31条在性质上仍属于法律行为方式之物权变动)虽为例示性规定,但就非依法律行为方式的物权变动来说,此种立法方式的问题在于:其一,其方式与种类本就繁多,难以穷尽;其二,各情形的要件不一,且在适用上还须结合或援引其他相关规范(如第29条关于继承之取得);其三,若干情形是否有必要体现于立法尚存疑问(如第30条关于房屋的建造与拆除,本可让诸关于物的学理予以解决)。其最突出的共同特征恰在于使物权变动的效果不必受制于外部性公示要件的相应变动,因此在这一制度领域找寻物权公示的意义无异于缘木求鱼。
如此一来,最后只剩下基于法律行为方式的物权变动制度。在这一领域也确实可能存在实行物权公示的法政策理由。〔8〕尽管已有不少论著指出物权公示原则对物权变动的意义,但多未有进一步的论证。参见刘家安:《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56页(从其表述者,如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5版,第85页);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3版,第301页以下;叶金强:《公信力的法律构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以下。(1)法律行为是私法制度所提供的交易工具,故此处的物权变动就是物权的交易。〔9〕前引学者著述主要以保护交易安全阐释物权公示的成因,本文在此亦沿用“交易”一词。但须指出的是,以“物权交易”代称“物权变动”并不确切,因为单纯的物权变动,尤其是采物权行为理论下的物权变动行为,并不具有对价要素的构成,无从构成“交易”。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本文所称“物权交易”仅是指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法律行为,且偏重于行为的结果,也就是物权取得的结果,从而所谓“保护交易安全”,也就在于保护取得人的物权取得预期。正因为交易安全的要旨在于物权取得的安全,故是否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对本文的立论原则上不产生本质性的影响。交易是各交易主体的计划与安排,寓有交易主体的目的;物权交易的目的就在于使物在不同主体之间流通。物是财富或财货,是人类支配外界进而满足自身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物只有通过流通才能找到发挥其最大效用的处所;在此意义上,物的流通性或者说可转让性是其天然属性。〔10〕关于物权可转让性原则及其限制,可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8页。而这样的流通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非依法律行为方式的物权变动虽然也能导致物的流通,但终非主体的主动且积极的安排,其意义在物的市场流通中几可忽略。正因为物权交易辐射之广且深,如何保障物权交易的安全性与效率性自然也就成为立法者法政策考量的首务。(2)物权交易以转让人的物权为起点,以取得人获得物权为终点。〔11〕需说明的是,物权交易或物权行为的种类有物权让与、物权设立等,其主体也就对应地称为“让与人/转让人”与“受让人”、“设立人”与“取得人”等。为简化行文,本文将其统称为“转让人”与“取得人”,仅在他物权设立情形称其为“设立人”与“取得人”。所谓的交易安全指的就是取得人能够有法律保障地获得按照交易安排所希望取得的物权,即取得人的物权取得计划不会落空或受挫。(3)取得人主观性交易计划的设计,端赖对具体交易情境的认知以及对交易信息的掌握。而在物权交易中最核心的交易信息无疑是转让人拟让与的物权是否真实、可靠,因为一旦不真实,那么取得人拟受让的物必然会触犯真正物权人所享有的具有对世性效力的物权。与此同时,转让人的物权信息,尤其是转让人的处分权信息、物上是否已存在其他物权性负担的信息,是否全面而无遗漏也至关重要,因为一旦不全面,取得人所获得的物权就有可能陷入与他人在先顺位物权的冲突之中,自己的交易计划就会受挫。(4)取得人如何获取关于转让人物权的真实且全面的信息,就成为取得人设计物权交易计划、判断并避免其隐存风险的关键。由转让人以言辞方式告知,虽然是取得人获取信息的首要渠道,但言辞之不可靠,对稍加谨慎的取得人来说是无待论证的经验法则;取得人在作出交易决策之前围绕转让人物权状况所展开的一切调查,往往就在于证明转让人言辞的虚实。因此,倘若在转让人的言辞告知之外能有某种可感知的甚或能直接“表达”出物权相关信息的“媒介”,且这种“表达”又是可靠的,那么这种“媒介”的存在对取得人来说无疑就是一颗“定心丸”。
推论至此,物权的公示需求似乎也就呼之欲出。立法者此时只需顺势而为,在物权的外部创设出一种公示手段,即可自制度层面确保取得人的物权取得预期,进而保障社会整体的交易安全。
此外,一旦确立起物权公示制度,其意义又可逸出物权交易领域,惠及物权法的其他制度,尤其是物权保护制度,因为物权公示手段在一般情形下至少可以为物权的存在提供较便捷的证明作用。
(二)法政策思路的缺陷——物权公示原则得以制度化实现的前提条件
上述以物权交易论证物权公示的必要性,无疑是一种抽象的法政策考量的论证思路。法政策以利益衡量为其思考特征,且多是抽象的利益分析。利益关系尤其是利益冲突虽可抽出其共性,但在各个具体情形,又不免存其个性。因此,私法制度凡以法政策为其立基的,多半会遭遇例外,不得不在规范效力的射程范围上或收紧或扩张,以兹应对。具体到物权公示制度,正是其法政策考量的制度立基,不免为具体贯彻该原则时会遭遇例外情形埋下了伏笔。〔12〕详见下述对动产物权领域物权公示原则的分析。
更为重要的是,法政策考量下所推导出的法律制度的成效如何,能否贯彻到底,又取决于立法者为付诸实施所能或所应采取的法技术措施。物权公示制度能贯彻到哪一步,按诸上述论证所揭示的思路,必然会取决于下述两方面的设计。第一,选择或设计合适的公示手段。倘若不存在合适的公示手段,或者所设计公示手段的制度成本过高,则物权公示也就止于思想层面,难以付诸实施。第二,既然物权公示最直接的效用存在于物权交易领域,那么在物权变动的制度构成上如何嵌入公示要素,同样成为公示思想能否实现的关键。
二、物权公示手段的选择与设计
(一)物权公示手段所应具有的品质
公示手段担负着公示要素的功能。充当物权概念外置性公示要素的工具,在理论上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具有外部可认知性,即不能如同被公示的物权仅存在于概念思维世界,而应能为外界所感知,否则就丧失其作为公示工具的价值。第二,最好能具有较精确的表达能力,亦即通过其对外的表达,能清晰且准确地使其他主体掌握该物上全部的物权关系信息;因为一物之上所能成立的物权常不限于一个或一种,倘若所选取的公示手段不能精确地表达出各个物权的全部信息,那么建基于其上的公示体系将必定是残缺不全的。〔13〕Vgl. Hromadka, Sicherungsübereignung und Publizität, JuS 1980, S. 89, 91.
如果要求同时具备这两个品质,那么理想化的公示工具应是带有文字载体属性的有形介质,因为文字本身就是表达,且其表达之精确性、通用性与有效性也是其他任何表达手段所不能比拟,而有形载体又能满足外部认知的要求。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票据,因为票据权利因记载于票据得以表彰,且二者合而为一,票据权利的发生、移转和行使须臾离不开对票据的占有。〔14〕相关论述,可参见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以下。
但是,票据式设计的思路显然无法移用于以有体物为客体的物权公示。这是因为票据所表彰的权利只是债权性请求权,指向的是一特定主体向另一特定主体的金钱给付请求,故其权利之构成与行使可完全内化于借以表彰的票据之中。反之,作为物权客体的有体物,是永远独立于物权概念及物权主体之外的客观实在,因此即使能够设计出类似票据那样的表彰手段,作为客观实在的有体物也无法为该表彰手段所内化,不可能达至合二为一的境地。有体物只能为表彰手段所指称,而且该表彰手段也必须指称作为所表彰物权之客体的有体物。
准此而言,作为物权的公示手段,还必须满足一项要求,即该公示手段须指向或指称作为所公示物权之客体的特定有体物。唯有如此,公示手段才能既可表彰特定的物权,又可指称特定的客体物,使二者间一一对应,进而也契合物权客体特定性原则。揭示出物权公示手段的这一要求,其意义在于对公示手段设计思路及其要求的启示。(1)鉴于物权区别于其他绝对性支配权的特点恰在于以有体物为其客体,从而也就存在利用有体物自身所具有的外部可认知性特征设计其公示手段的可能性。这也揭示出对物之占有可以充当公示手段的机理所在。(2)在不以占有为公示手段的场合,也就是在登记公示情形,此时的登记设置虽然已脱离物的本体,但必须指称所公示的物;同时又因便利于登记程序操作以及公众查阅等要求,故在设计该登记设置时,须能够比较便利地指称所公示的物。
(二)占有作为公示手段及其缺陷
在我国物权法体系之下,占有在性质上只是一项事实,所展现的是主体(占有人)对于特定占有物的事实控制关系。占有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外部可认知性,故可满足充当公示手段的第一项品质要求。但在另一方面,占有又仅是一项不会说话的事实,通过某人对某物的占有,只能得出该人对该物有事实上控制的结论,并不能进一步告诉人们,该人对该物的占有是有权占有还是无权占有,其占有是基于所有权抑或基于质权甚至基于借用、租赁等关系。
尽管不具备作为公示手段的第二项品质要求,但物权公示制度的演变历史〔15〕就物权公示制度的历史发展,参见前注〔2〕,Hedinger书,第13页以下、第45页以下。也显示出物权法即使已发展至现代社会,凡是在采物权公示制度的立法例中,〔16〕此尤以德国法系最为典型,其中的德国民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自不必论,奥地利民法亦大体如此;就奥地利物权法上的公示原则,可参见 Iro, Bürgerliches Recht, Bd. IV: Sachenrecht, 5. Au fl., 2013, S. 3, 19.占有仍担负作为动产物权公示手段的重要使命。各立法例在选择占有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时并非没有认识到占有之表达能力不足的缺陷,实属出于无奈的选择:〔17〕当然,立法者选择占有作为公示手段亦非毫无依据:有体物之进入法律世界,成为法律所规范的客体,其第一个环节就是与主体之间所发生的这种事实控制关系,因此占有是物权关系得以建构的基础,在此意义上,称占有是人类财产关系的起源亦不为过;而从经验世界看,对物的占有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对应着占有人对占有物的权利尤其是所有权。Vgl. Heck, Grundriß des Sachenrechts, 1930, neuer Abdruck Scientia Aalen, 1960, § 4, 4, S.15.动产的天然属性在于“动”,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动产的价值又千差万别,既有价值连城者,亦不乏轻若鸿毛者;与不动产的寿命不同,动产既有经久耐用者,又有如消费物一经使用而瞬间消灭者。为种类如此丰富繁杂的动产世界设计出一种统一的公示手段,尤其是仿行不动产公示的思路,设计一种系于某一固定地点的登记公示,其客观上的不可行实无待论证也。退一步说,即使是采取登记公示的方法,也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的动产类别(详见下述),余下的动产世界仍无从采用这种人为的登记技术予以公示。
选择占有这种“极不完备的工具”〔18〕语出 Wolff/Raiser,参见 Wolff/Raiser, Sachenrecht, 10. Au fl., 1957, § 4 II 4, S.23.作为公示手段,也就意味着在动产物权领域,基于法政策考量而实行的公示制度自始就背负难以贯彻到底的命运。这仅是基于将占有定义为对物之事实控制即可得出的结论。
更麻烦的是,占有概念自《德国民法典》之后已不能简单地等同为对物之事实控制:一方面是限缩,即占有辅助人尽管掌握对物之事实控制,但在法律上并不享有占有人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扩展,也就是间接占有人尽管对物不存在事实控制关系,但在法律上仍被赋予占有人之地位。〔19〕我国《物权法》并未使用“占有辅助”“间接占有”概念,而学理就占有辅助制度几无异议,但对是否采纳间接占有制度则略有争议。相关论述参见张双根:《论间接占有制度的功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这一限一扩使得表达能力本就“极不完备”的占有在公示能力上就更趋恶化。这尤其体现在一扩之后所形成的间接占有概念上。间接占有的成立须借助某一特定的法律关系,而法律关系恰又如同权利概念,存在于无形的思维世界,不具有感官上的可认知性,从而一旦将间接占有与直接占有并列,使其承担起同样的物权公示功能,则在采行物权公示的体系内无异于为自己培植掘墓人。〔20〕详见下文论述;同前注〔6〕,Shuanggen Zhang书,第64页以下。
(三)登记作为公示手段
如果说占有是一种“天然的”公示手段,那么登记无疑就是“人为的”公示手段。登记形诸文字,表达力之精确不成问题;登记须有载体(纸质版或电子版),又可满足外部可认知性的要求;在不动产领域,登记机关的设置与登记管辖基本采属地原则,更是有助于登记程序的操作与登记公示功能的发挥。因此,以登记作为物权尤其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可以说是完美的技术设计。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发明,其意义几可媲美有限责任之发明之于公司法的意义。
更具探讨价值的是,登记技术在何种范围与程度上可移用于动产物权领域。由于存在天生的缺陷,所以在有更适格的公示手段出现时,占有就应该让出其公示手段的地位。但问题是,作为具有更强公示能力的登记,在动产物权领域,是否可以随意地人为加以设计。按照前文所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本文看来,动产物权领域采行登记公示方法至少需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哪些动产可以实行登记制,在立法上自始须有明确的规定,甚至是限定。与不动产概念相较,动产概念所涵盖的更为宽泛与复杂,因此倘若不加限定,则动产取得人自始无法预测并判断哪些动产交易需要查阅相关登记,哪些动产交易又可省去对登记的调查。不能为动产取得人提供明确的交易信息,这样的登记制度也就不能达其登记公示的制度目的。
准诸这一原则,则现行《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7项关于可抵押财产范围的“兜底条款”(即“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之规定)就极为可疑。这不仅是因为现行法就这些“其他财产”的抵押未指明相应的登记机关,更因为倘若这些“其他财产”真的办理了抵押登记,则对于按一般规则(即《物权法》第23条、第25~27条)进行物权交易的取得人来说,无异于安放了一枚不定时炸弹,随时摧毁其物权交易。〔21〕关于动产抵押与质权之间的冲突详见下文。
而关于立法上如何规定可登记动产的范围又有以下两种思路。其一,直接列明可登记动产的种类,也就是列出可登记动产的清单,其例可如《物权法》第24条之列举式,〔22〕关于《物权法》第24条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详见下文。此思路近于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的“物的编成主义”。其二,借鉴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的“人的编成主义”,以权利人作为编制登记簿的主线,再辅以该权利人名下可登记的动产清单,《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4项并第181条与第189条所规定的动产浮动抵押体现的就是这一思路。前者以特定种类动产的特殊性提示取得人查阅登记;后者以特定主体的特点预警取得人有查阅相关登记簿的必要。
第二,须选择适宜的动产登记机关。就特殊动产大多存在相应的管理机构,故以该机构承担登记任务较为可行;对于“人的编成主义”下的动产,以主体登记机构兼任登记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务实的做法。之所以称其“可行”与“务实”,是因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与制度成本考量下,这样的登记机关设置尚能满足较便利地指称所公示动产的要求。
(四)以权利为客体之物权的公示手段问题
以上所论均为以有体物为客体的物权情形。在有体物之外,现行法亦认可权利得为物权客体(《物权法》第2条第2款第2句),形成以物上物权为原则、以权利物权为例外的格局。细考现行物权法体系,严格意义上的权利物权种类基本上为担保物权。这是因为担保物权在属性上为价值权,重在充当担保客体的变价性,从而凡是具有可让与性的财产性权利,自无被排除充当担保客体的道理。
依权利是否源于有体物,权利物权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如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虽然作为客体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为一项权利,但该项权利仍源于作为有体物的土地(实为土地所有权)。此类权利物权的公示问题,尤其是公示手段的选择,仍基本遵从有体物的规则,亦即遵循不动产的登记规则,故不生特别疑问。第二类是作为其客体的权利并不源于有体物或不与有体物直接相关的权利物权。其典型者则是权利质权,即《物权法》第223条所列各种情形。因为与有体物无关或不直接相关,因此其公示手段自始就不宜遵从有体物的思路。不过,因为担保物权的实现,也就是担保客体的变价,最终以让与担保客体体现,故在学理上,权利质权的设定方法,一方面遵从作为客体之该项权利的让与规则,另一方面为避免质权设定后对相关利害关系人的不利影响,特别强调须完成其公示要件。〔23〕其原理可参见本文下述关于公示要素嵌入物权变动的分析。至于其公示方法,可为权利凭证上的记载操作,如票据或证券质押;亦可为权利登记,如股权质权之登记;甚至可为单纯的通知,如普通债权上设定质权时对债务人的通知。〔24〕现行法未规定普通债权质权,实务上甚至以此为由,认为普通债权质权之设立有违物权法定原则。参见方建国、蒋海英:《商业银行保证金账户担保的性质辨析》,《金陵法律评论》2013年秋季卷。此论显然是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误解。
(五)一物之上可否并行两种公示手段
多多益善,虽为事理之常,但似乎并不能适用于物权公示手段的设计。一物之上若并行两种公示手段,则更真实的情况往往是,这两种公示手段之间所产生的并非互补效应,而可能彼此龃龉,使公示呈递减效应。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现行法上至少有两处规定所引发的争议与此有关,且各具代表性:一为《物权法》第24条,涉及一个物权能否并存两种公示手段;一为动产抵押与质押间的纠葛,涉及一物之上能否并存两个以不同手段予以公示的物权。〔25〕另外,2015年中国民法学学会所提出的“物权法司法解释(讨论稿)”就一房多卖问题曾规定以占有作为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一个判断标准。这不仅是对现行法的背离,也违反了“同一物权之公示手段唯一性原则”。分述如下。
第一,对《物权法》第24条关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学理争议极大。〔26〕代表性文献,可参见杨代雄:《准不动产的物权变动要件》,《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汪志刚:《准不动产物权变动与对抗》,《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龙俊:《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王利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冉克平:《论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物权的变动》,《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其中一项核心争议在于,在特殊动产所有权转让等物权变动中,其物权变动在转让双方当事人之间何时产生效力。不少学者认为,此时仍应适用《物权法》第23条,以交付作为其所有权取得的生效要件。
这一理解思路不仅有违《物权法》第24条作为第23条例外规则之下的体系解释结论,即使在该第24条内部也难以证成。申言之,《物权法》第24条已明确将登记作为对抗要件,这也意味着登记在该条中的功能在于对外宣示已发生的物权变动,进而发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倘若以交付作为物权在转让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变动的生效要件,那么在当事人未交付而径行申请登记时,就会使登记机关面临登记还是不登记的两难困境,并引发难以化解的矛盾结果:若办理登记,则该登记在当事人间是否会覆盖掉本应由交付所承担生效要件的功能呢?若发生覆盖的结果,则该登记就与本应发挥的宣示功能相去甚远;若不能发生覆盖的结果,则会出现该物权变动在外部已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在当事人内部却尚未产生效力的怪异现象。若不办理登记,则现行法并未规定登记机关调查在当事人内部是否已交付的审查义务,登记机关又该以何种理由拒绝办理登记呢?〔27〕对照不动产物权领域采取登记对抗的相关规定,即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地役权的设立,其物权变动在当事人间均实行意思主义,从而也就不会给登记程序的办理制造理论麻烦。
准此而言,对《物权法》第24条所规定的当事人间的物权变动采取意思主义的理解,是最合体系从而也不会产生体系内矛盾的解释。换句话说,一旦立法者就特殊动产选取登记作为其物权的一般性公示手段,则占有就不应继续占据公示要素的地位,在其物权变动中也就不应承担任何性质的要件功能。以交付作为当事人间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究其错误根本,则是无端地为特殊动产设置两个不同属性的公示手段。因此,就同一个物权,采公示手段唯一性原则应最契合物权公示的法理。
第二,我国法上动产抵押与质押之所以会形成冲突,乃现行法就动产抵押客体未加限制而过于泛化的结果。具体来说,一方面,凡是可以设定质权的动产,依《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7项的“兜底条款”,又可以成为动产抵押的客体;另一方面,《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所列的可以抵押的各项动产,似乎也没有被排除出作为质权客体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同一项动产上也就难免同时成立抵押权与质权。如何确定这两种担保物权间的效力顺位,着实给司法实务带来不少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9条第1款试图强行赋予登记抵押权的优先顺位,但二者均为合法、有效的担保物权,何以厚此薄彼,实难服人。〔28〕按该“司法解释”起草者的理解,其理由似乎在于防止担保人与质权人的恶意串通,参见李国光等:《“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284页。这分明是以意思表示瑕疵问题混淆物权效力制度。前述《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改弦更张,以各物权设立之先后定其效力顺位。这固然是对物权基本法理的回归,但其疑惑依然存在。疑惑之原因在于,动产抵押采登记公示方法,动产质权以占有或交付为公示要件,从而在其中一项物权设立在先,尤其动产抵押设立在先时,对于后来者尤其是后位的质权取得人而言,在动产抵押的客体范围如此宽泛的背景下,如何能知道欲设立质权的该项动产上已然存在一项先位的抵押权,进而防避自己的质权效力风险呢?更有甚者,此类动产仅就抵押权设立采取登记公示制,并非以登记为其物权公示的一般性手段,从而不仅在质权设立情形,在该动产所有权转让情形,对其所有权取得人来说,如前所述,同样存在难以防避的风险。一物之上同时成立多项物权,固然为《物权法》的物尽其用宗旨所鼓励,但一旦以牺牲交易安全为代价,则所引发的风险与纠纷必然会反噬制度目的。
综上所论,同一个物权只能采一个公示手段,即公示手段唯一性原则;一物之上若允许成立两种以不同手段公示的物权,则立法者应尽可能明确可登记动产的种类与范围,以此可明确地提示物权取得人,就该动产的物权取得除占有公示外,还应查阅相应的登记,以避免可能存在的物权交易风险。
三、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的构成
公示要素嵌入物权变动构成无非是通过两条路径,要么构成其生效要件,要么以其对抗要件的面目出现。在我国现行法上,前者构成原则,后者仅为例外。但是,公示要素在物权变动中为何有这样的构成,以及在这两种嵌入路径中何者更契合物权公示思想,学界并未有太多讨论。占据我国物权变动构成理论核心地位的,乃是否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争议,相形之下,公示要件在其中只是处于边缘地位,其相关问题也就未得到充分的揭示。
(一)公示要素如何嵌入物权变动构成
物权变动依转让人是否拥有相应的物权,可区分为有权处分与无权处分两大类情形。若以物权取得结果为原点,逆向回溯其取得权源,则亦可对应地区分为“自权利人处之取得”与“自无权利人处之取得”,〔29〕这是德国物权法学理最常用的分类术语,例如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五十一章与第五十二章之标题。这一区分所隐含的理论价值详见正文下述。后者即为物权善意取得制度,旨在解决物权交易安全问题。这两种物权取得情形之间为常态与非常态、正面与反面的关系,故在规范顺序上一般是先规定前者,非常态居后。但这一规范体系上的顺序并不意味着在二者的要件构成上,尤其是公示要素在其中所发挥的功能上,也必须以前者作为构造的逻辑起点。
1.对“自权利人处之取得”的考察
权利变动之构成所遵循的是罗马法以来的法谚:“无论何人,不得以大于自己所有之权利让与他人。”〔30〕“nemo plus iruis ad alium transferre potest quam ipse habet”;就此参见前注〔10〕,鲍尔、施蒂尔纳书,第64 页;[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上册,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14页。而物权“自权利人处之取得”情形,恰恰是对这一法谚所体现的法教义学逻辑的遵循。更为重要的是,转让人享有相应的物权或“有权地位”,〔31〕具体来说,“有权地位”是指转让人就其所转让的物权,在事实上确实享有,而且其转让也不存在处分权限制。至于只享有处分权能而不享有包含该处分权之本权(如所有权),例如行纪人对委托物的处分权,则属于商事物权法上的特别问题,不在本文主题之内。此外,在先为他人设立他物权而后再转让所有权的情形,该所有权之转让按照物权法基本理论虽然不存在处分权限制上的障碍,但取得人能否取得无该项他物权负担的所有权,仍需依善意取得制度解决。我国现行法上关于抵押权设立后抵押物处分上的特殊规则,也就是《物权法》第191条所确立的须经抵押权人同意的规则(类似错误者,尚有第226条第2款“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的规定,第227条第2款“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后,出质人不得转让”的规定,以及第228条第2款“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的规定),是对抵押权追及效力的背离,在比较法例上殊为罕见;所幸前述《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已废弃该规定。所解决的不仅是物权变动的前提性要件,更会影响在该情形下物权变动要件的构成。具体来说,如同权利概念自身,权利变动也是法律思维的构造,属于精神世界范畴,从而只要满足转让人享有“有权地位”的前提,并满足法律行为上的一般性生效要件,即可导致取得人取得所预期的物权;既然“有权地位”的前提在逻辑上必然包含物权取得的结果,则对取得人来说,也就没有必要在此之外再节外生枝地植入一个外置性的公示要素;一言以蔽之,无需借助外部公示要件,转让人之“有权地位”前提,已使物权取得之结果意义上的交易安全确保无虞也!如此一来,在转让双方当事人之间,其物权变动采意思主义的构成模式似乎是当然的设计。
但是,这仅是着眼于转让人与取得人之间的关系所观察到的结果。观察视角一旦不再局限于该当事人之内部,而是扩展至关于该物之交易链条的其他环节,尤其是将转让人为二次处分行为的可能性考虑进去,〔32〕而取得人在取得物权后的后续处分行为,因为属于有权处分,对后续取得人来说,其利益关切与其前手取得人基本相同,故无特别考察的必要。则这一推论结果就有修正的必要。这是因为无论是物权转让(典型者如所有权转让),还是他物权设立(如设立抵押权),在与转让人或设立人的关系上,一旦取得人所采取的行动仅止于双方合意的完成,而将外在的公示要素(占有或登记)仍留存于转让人处,则必定会给转让人留下实施二次处分行为的机会。这种二次处分行为虽然在法律评价上属于无权处分,仅此行为尚不足以损及取得人已取得的物权,但恰因留存于转让人(此时已构成无权处分人)处公示要素的配合作用,才会引发下述善意取得或类似的善意第三人保护制度的产生,从而在结果上就会挫败取得人原有的取得预期。正因为善意取得等制度的存在,对于任何一个稍具风险意识的取得人来说,在与转让人之间的物权取得关系上,也就不会再满足于其间物权取得合意的达成,而是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步骤。这一行动步骤就是使公示要素也发生相应的变动,即移转占有或变更登记,使得转让人处不再留存相应的公示要素,从而不再给转让人实施能引发善意取得等结果的二次处分行为的机会。
如此一来,公示要素自然也就需要嵌入物权变动的构成之中。但由此尚不能得出其嵌入方式是采取生效要件式还是对抗要件式的明确结论。
2.对“自无权利人处之取得”的考察
转让人不享有相应的“有权地位”,则按照上述罗马法谚的反面逻辑,即自始欠缺权利变动的逻辑前提,本不会产生物权取得的效果。〔33〕关于无权处分所引发的各种可能性结果,可参见 Wilhelm, Sachenrecht, 4. Au fl., 2010, S. 387 f.善意取得制度之创设则是逆此逻辑而为,以法政策考量为理由,为善意的取得人提供取得可能,以消除其物权取得上的风险。而善意取得制度的构造逻辑,又在于以取得人主观上值得保护的善意信赖弥补转让人客观上所欠缺的“有权地位”要件。〔34〕Vgl. Weber, Gutgläubiger Erwerb des Eigentums an beweglichen Sachen gemäß §§ 932 ff.BGB, JuS 1999, S.1 f.因此,取得人的善意信赖在何时并在满足哪些要件时方值得立法者保护,就成为善意取得制度构造的核心。
回归至权利变动的自身逻辑,如上所揭,转让人享有“有权地位”是最能保障取得人取得预期的逻辑前提。转让人是否享有“有权地位”是一项客观事实,是取得人方面无法改变的事实,取得人在作出交易决定之前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调查并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与证据,以判断该逻辑前提之真伪。但吊诡的是,在具体的物权交易情境中,在转让人之有权或无权被证实之前,也就是在真相被揭示之前,取得人所获得的信息与判断永远处于不确定之中,亦即取得人陷于无知之幕的困境。取得人在此之前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也就只能是获得自己的主观判断,建立自己的主观确信。
问题是取得人如何才能确信自己所建立的“主观确信”已经很充分,达到要求立法者为其提供保护的程度。答案似乎很简单,即按照立法者所提供的行为标准实现其全部行为要件的要求。这是因为只要立法者所提供的行为标准明确,取得人就可以判断自己是否已达到该行为标准,亦即取得人在其主观上可以完全掌控行为要件的满足程度,进而也就可以判断自己所建立的“确信”是否已达到受立法者保护的程度。但是,立法者又是依据何种考量确立该行为标准呢?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与取得人不同,立法者此时无需面对无知之幕的困境,直接以转让人之“无权地位”作为事实前提。在此情形,立法者所面对的是对立冲突的两种利益,即取得人的物权取得利益与原物权人的物权保有利益,前者代表抽象的交易安全利益,后者则代表静态的权利不受侵犯与剥夺的利益。〔35〕就这一对利益冲突的阐述,参见 Hager, Verkehrsschutz durch redlichen Erwerb, München 1990, S. 2 ff.双方所争夺的物权只有一项,最终只能由一方胜出。对善意取得人施予保护,必然会以原物权人丧失其物权为代价,以牺牲原物权人之物权成全取得人之物权。〔36〕正因为会触动原物权人最根本的物权保有利益,对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的追问甚至会超出私法范畴而上升至宪法层面,即是否已背离保护私人所有权的宪法原则。关于这一诘问在德国学界的讨论,同上注,Hager书,第9页以下。面对这样的矛盾该如何作出抉择,实是对立法智慧与技术的考验。取得人方面仅在信赖基础上达成物权变动的合意,显然不足以支撑使原物权人承受丧失物权之结果的正当性。因此,能够支持取得人胜出的要素必定是合意之外的客观要件。而在整个物权变动构成中,合意之外的客观要件除公示要素外,别无其他的可能选项。
思路一旦至此,那么立法者所面临的选择似乎也就变得简单,在取得人与原物权人两者中,考察公示要素已掌握在哪一方。这一标准若着眼于取得人视角,也就是考察取得人是否已取得对公示要素的掌握。因为按照前揭论述,一物之上的物权公示手段应具有唯一性,或至少应具有明确性与可靠性,故而一旦该公示要素已为取得人取得并为其掌握,那么就意味着原物权人已丧失其对该物权公示手段的掌握。这也意味着只要取得人在物权变动的合意要件之外进一步完成物权公示要件的变动,那么也就建立起自己的确信:不仅自己已取得所计划的物权,而且除自己之外,再无其他主体会经由公示要素而染指自己所取得的物权。唯有如此,也才能说明使原物权人丧失其物权的合理性。〔37〕须说明的是,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历来是物权法乃至整个私法中最富争议的议题。本文只是自公示要素在其中的作用以及构造可能性视角,试图就善意取得制度在其内在构造上提供一种新的阐释。限于主题与篇幅,本文不便就善意取得制度之正当性理论基础展开论述,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王立栋、任倩宵:《日耳曼法的权占、“以手护手”与〈德国民法典〉的善意取得》,《中德私法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纪海龙:《解构动产公示、公信原则》,《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但疑问仍在于在这样的框架下,取得人之取得公示要素究竟是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还是作为其对抗要件。
3.生效要件抑或对抗要件:公示要件三项功能之间关系的辨析
由上论可推知以下两点。一方面,公示要素之嵌入物权变动构成,并不能完全由常态的有权取得情形推导,而应将其反面情形作为思考的起点;换言之,公示要素之嵌入,其要旨在于确保物权取得之安全,即要么防止他人的善意取得对取得人取得预期的挫败,要么确保取得人自己的善意取得。但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对“自权利人处之取得”的考察,还是对“自无权利人处之取得”的分析,均不能说明公示要素嵌入的必然模式。对于这一疑问,通过再次系统考察公示要素所承载的三项功能之间的关系,或许能找到祛疑的启示。
学理上一般认为,物权公示要素具有三项作用或功能,即转让功能、推定功能与善意取得功能。〔38〕在德国法中此为通说,参见前注〔10〕,鲍尔、施蒂尔纳书,第61页以下;同前注〔33〕,Wilhelm书,第18 页以下。我国物权法在学理上亦大体承此学说。转让功能说明的是公示要素在有权取得情形中的作用,善意取得功能是无权处分情形中公示要素所承担的取得人善意信赖基础的功能,而推定功能则是公示要素在维护物权人之物权地位时所发挥的证据功能。从适用范围上看,这三项功能畛域分明,各司其职,彼此之间似无关联。〔39〕学者间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认为三者间为“相互勾连、浑然一体”关系者,如常鹏翱:《再谈物权公示的法律效力》,《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反之,就动产物权领域的占有或交付的这三项功能,以解构进路否认其彼此间关联的,参见前注〔37〕,纪海龙文。但在本文看来,这三项功能之间的彼此配合功效仍不容忽视。而其关键则是公示要素之转让功能的定位。
不妨先从公示要素在有权取得情形仅承担对抗功能观察这三者间的关系。〔40〕在《德国民法典》中,无论是占有还是登记,所承担的均是相应物权变动中的生效要件功能,故而以其作为对抗要件的情形,几无讨论的理论契机。可资比较的情形,乃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于2008年所引入的股权善意取得制度,恰建基于在股权变动中仅充当对抗要件的股权登记,由此引发学理上的强烈质疑与反思。相关讨论可参见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一,若作为对抗要件,则在转让双方当事人之内部,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时间与公示要素的变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差,从而使得公示要素所承载的公示功能不可避免地发生断裂,因为至少在此时间差里,公示要素所表征出的物权归属状态与真实的物权关系之间并不一致。第二,公示要素所承载的推定功能乃以如下经验事实为基础,即权利被推定之人在获得公示要素时,一般也伴随着相应的物权取得事实。〔41〕其中关于占有推定的内容,可参见王洪亮:《物上请求权的功能与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3页。但是,一旦在物权变动环节公示要素与物权变动效果之间发生脱节,那么至少在基于法律行为方式之物权取得中,亦即在物权变动之最为重要、最为常见的领域,也就无从建构该经验事实,其结果则是公示要素的推定功能要么严重减损,要么必须另行构筑其制度基础。〔42〕法国法上的占有虽然也有推定功能,但其构造逻辑似有不同,参见前注〔30〕,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书,第265页、第632页以下。第三,一旦将公示要素定位于对抗功能,也就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功能,则在这一规范思路的引导下,取得人的重点就在于击破外部第三人的主观善意,而其击破手段又非以公示手段为唯一,其他一切可用之手段或方法均应涵盖在该对抗制度的逻辑范围内。这样一来,不仅善意取得制度会被对抗制度所消解或覆盖,统一的物权公示制度或思想能否得以维持就更值得怀疑。
反之,一旦将公示要素在有权取得情形的功能定位为生效要件,则上述对抗制所内含的不足似乎均可迎刃而解。首先,生效要件的定位,无疑是最能真实、最能严丝合缝而无任何时间偏差地对外表彰物权变动的动态实况。其次,这一定位也为公示要素之物权取得意义上的推定功能提供最坚实的制度支持。最后,生效要件的定位也与善意取得制度的构建彼此无违,因为对取得人来说,生效要件的定位同样甚至更可使其确立自己已有效取得物权的确信,更能使其确信除自己外,其他任何人再无取得其物权的可能,哪怕仅仅是合意意义上的物权变动。
综上,公示要素嵌入物权变动构成的最佳路径是充当其生效要件,即学理通常所说的“设权要件”功能。颇为吊诡的是,尽管这一结论所针对的是有权取得情形的物权变动构成的设计,但如上所论,该结论却并非完全源自有权取得情形自身逻辑的推导,毋宁是其所承载的善意取得功能的反射结果。质言之,即使是有权取得情形之物权变动要件的设计,其目的仍在于应对无权处分情形的解决,以达到确保或实现物权交易安全的功能。
在此也有必要回应本文第一部分的中间结论。该中间结论以物权交易安全为物权公示原则提供法政策理由,且指向的是方便取得人获取转让人所转让物权的信息。但这一抽象论证一旦落实于具体的制度设计,也就是如何嵌入物权变动的要件构成之中,则其功能指向已发生变化:尽管凭借公示手段获取转让人方面的物权信息仍不失为其一项重要作用,但这一作用毋宁是附带性作用,其核心更在于使取得人取得唯一的或确定的公示要素,以建立其物权取得的确信。
既然是最佳设计,也就表明这不是逻辑的必然与唯一选择,仍然属于利益考量的法政策范畴,从而针对特别情形例外性地采取其他设计,应为法政策所不排斥。现行法就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的设立与变动采登记为其对抗要件,不循登记强制的常规思路,就是基于特别的利益考虑的结果。〔43〕同前注〔39〕,常鹏翱文。不过须明了的是,一旦采取登记对抗制,则该种登记也就难以承载相应的推定功能与善意取得功能。
(二)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公示原则
在不动产物权中,如前所述,因充当公示要素的登记具有近乎完美的公示能力,故以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之生效要件的设计,几为物权公示制度的典范,不动产登记制度也因此常常成为私法领域中设计其他权利登记制度时被借鉴或被效法的对象。相形之下,以占有作为公示手段的动产物权公示制度自始就伴随着致命的缺陷,且受其连累,也使得整个动产物权公示制度处于备受质疑的漩涡之中。〔44〕如纪海龙教授所质疑者,虽为占有的公示功能,但仍以整个动产为其论文标题,行其解构之说,参见前注〔37〕,纪海龙文。
1.公示原则、交付原则抑或其他
因为占有为“不说话的事实”,故而即使在最简单的以直接交付转让动产所有权的情形,显现于外部的也仅是占有的移转,即物由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但这一位置的移动并不能明白无误地告知外部第三人此时正发生一项所有权的转让。直接交付尚且如此,则《物权法》规定的三种所谓“观念交付”情形,即第25条中的简易交付、第26条中的返还请求权转让以及第27条中的占有改定更是毫无公示气息,因为在这三种情形之下,物自始至终就未发生移动,其占有关系(亦即间接占有关系)自身尚且需要凭借言语或其他手段揭示于外,遑论由该占有关系对外公示其上的物权关系!〔45〕至于这四个条文尚未涵盖的其他情形的动产所有权转让方式,其公示问题大体类似,不再赘述,具体参见前注〔6〕,Shuanggen Zhang书,第82页以下。
既然占有或交付的公示作用难副其实,那么以其为生效要件的动产物权变动也就无法再以公示原则作为其法教义学构成的基础。〔46〕德国法上的相关讨论,可参见Staudinger/Wiegand (2004), Vorbem 19 ff. Zu §§ 929 ff.有学者主张以“交付原则”替代“公示原则”作为阐释基础。〔47〕同前注〔37〕,纪海龙文。这一思路虽能说明实证法上交付规则的内容或构成,但似乎无法阐释何以存在交付要求。在本文看来,交付作为生效要件,一旦被揭去通常意义上公示功能的外衣,那么其正当性可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使取得人能取得与其所取得之物权相匹配的对物的占有权能或占有关系,从而不至于在其物权权能上有所欠缺,保障正常且有序的物权归属秩序得以实现。〔48〕同前注〔6〕,Shuanggen Zhang书,第 115页以下。第二,能够加强取得人在物权取得上的确信,因为占有具有排他性,取得人通过自己对物占有之取得也就可以确信地排除他人对该物之物权取得的可能。只不过如前文所论,这一意义已不再单纯体现于《物权法》第23条、第25~27条所规定的“自权利人处之取得”情形,而主要见于动产善意取得领域。而且,此种意义上的占有概念,也不能类同于德国法的做法作无节制的扩展,而只能体现为直接占有,至多只能包括取得人方面新创设的间接占有。〔49〕就此已涉及极其复杂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内在构成,具体参见前注〔6〕,Shuanggen Zhang书,第183页以下。
2.非以占有为公示手段的动产物权公示问题
动产物权一旦能够以登记作为其公示手段,那么只要在法政策考量所容许的范围内,自无否认其公示原则之理,问题仅在于践行公示原则的程度,亦即如果仅赋予登记为其物权变动对抗要件的效力,则就该登记难以同时构建其推定功能与善意取得功能。其理已如上揭,不再赘述。
更值得关注的是,为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最近几十年来,动产担保交易制度在各国的发展极为迅猛,甚至有国际化的趋势。这无疑会构成未来物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动产担保制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随着科技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动产担保制度的统一登记在技术上成为可能。〔50〕最新的相关研究,可参见高圣平:《统一动产融资登记公示制度的建构》,《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6期;邹海林:《动产担保物权的公示原则表达——以民法典物权法分编的制度设计为样本》,《法治研究》2017年第6期。尽管在具体的技术设计方面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大体可以断言,随着登记手段对占有的替代,物权公示思想在动产物权领域,至少在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方面有渐渐收复其失地的势头。
四、结语
物权公示原则的奥义尽在于物权交易安全的保护。而保护物权交易安全又是物权法规范的首要目的,因此在物权公示原则之外,物权法中尚有诸多制度也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保护物权交易安全的功能。其中与物权公示原则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物权法定原则。〔51〕同前注〔10〕,鲍尔、施蒂尔纳书,第7页以下。功能的重合也就意味着制度设置的重复。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就有学者主张以物权公示制度松动物权法定原则,直至建构出新的财产权体系。〔52〕最具代表者,如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再探内地民法典的可能性》,载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以下。此论是否信然暂不必论,但物权公示制度的重要性已然“公示”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