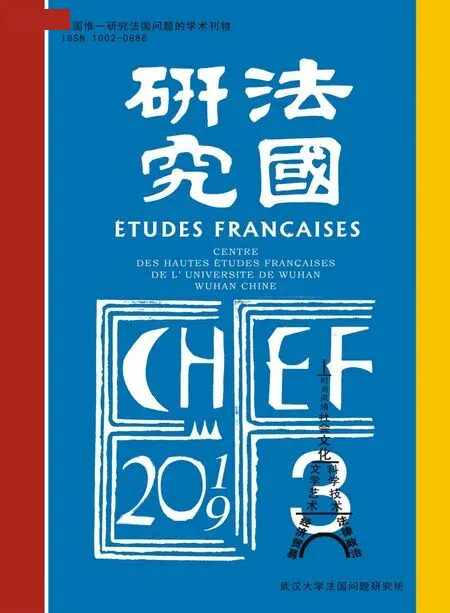亨利·米修的“中国式务虚”
——从《一个野蛮人在亚洲》透视米修眼中的中国形象
张珣
在不少法国作家眼中,相比于西方艺术精确再现的“务实”,务虚的中国艺术非常懂得“表现”,作品具有“羚羊挂角”式的灵动轻盈;但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却常常为了追求某种超越此在的抽象价值,而忽略自身的切实需要和思想感受,显得“缺乏必要的自我意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也落后于西方。这种拆分出“艺术中国”与”实践中国”两个优劣分明形象的“二分法”,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作家当中可谓流行。而亨利.米修在其中算是特例,因为米修看中国时并不“二分”,而几乎抱以一以贯之的批判态度,认为中国人在艺术上的卓越和在实践中的笨拙,都来自于同一种高度抽象的思维模式、和把对象简单化的倾向。中国人虽然具有高超的象征能力,但同时也缺乏全面把握复杂对象的能力。
一、“能力”还是“无能为力”?
虽然米修对中国的艺术和社会实践都抱以一以贯之的批判态度。但对中国人的“升华能力”还是忍不住不时赞叹。从称“中国人具有对符号的天赋”①Henri,Michaux.Un barbare en Asie.Paris:Ed.de NRF,Gallimard,Paris,1933,p.180.本文中的中文翻译皆由笔者提供。,到夸赞“只有中国的戏剧是精神性的戏剧,只有中国人懂得怎么真正的去“表现”(Michaux,1933:181)”,米修对中国艺术“高于现实”的特点由衷认可和钦慕。中国艺术家摒弃客观追求精神、以某种“理念真实” 来代替客观对象的审美倾向,在米修看来与西方致力于光影、空间和质感的准模拟手法完全不同,有时甚至显得更胜一筹。书中这样描述中国风景画:“物体的动势都被明确展现,却不是通过具体的厚度和重量,而是某种线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中国人善于把‘客观存在物’简化为‘存在物的象征’,就像某种数学或代数思维。各种质素先被打散解构,紧接着再被碎片重构,好像人们解代数题时所作的那样(Michaux,1933:156)”,而“欧洲人总是想要摸在手里,他们的画里连空气都是密实的。即使是圣经题材,裸体们也总是满载肉欲。激情热度、性感肉欲,仿佛总在摆弄着西方人的一只手(Michaux,1933:180)。”其实欧洲的宗教绘画中,裸体并不见得总是呈现出强烈的肉欲色彩,女裸们的神色通常是庄严而圣洁的。米修这种颇有几分偏见色彩的评价,显然是因为感受到了中国绘画所暗示的那个精神性世界脱离“现实”和“世俗”的轻盈,从而对西方绘画如高仿品般真实呆板而感到失望。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米修像他同时代的其他法国作家一样看好中国艺术,是因为在米修看来,中国书画艺术中体现出来的高度精神化,既是一种“升华原型”的能力,同时又是一种“效忠原型”的无能为力。在本书中米修曾明确指出,“即使中国人只是要呈现一个客观对象,他也会很快的就把那东西先变形,再简化(Michaux,1933:158)。”至于这种变形和简化到底是纯粹的审美偏好,还是含有无力准确直观地描摹对象的因素,我们不妨来看个例子:同样解剖尸体,中国的先行者和欧洲同行画出来的骨骼图却大相庭径。南宋地方小吏宋慈所著《洗冤录》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其中的“检骨图”所描绘的骷髅,头部没有眼眶鼻翼牙齿,脊椎没有生理弯曲,骨头缺乏具体形状、肋骨形如菊花辬而臂骨腿骨形如火腿肠。手指脚趾的关节则是一堆九宫格一般小方块列阵;而制造了人类第一具骨骼标本的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在其著作《人体构造》中,则已经绘制出了非常精确、类似于现代骨骼解剖图的骷髅。不仅骨骼形状逼真、关节比例正确,更有一定的肌肉附着其上。两相对比,以图形描绘对象的能力高下立判。也许有人要说《洗冤录》诞生于1247年而《人体构造》写于1543,其间有将近三百年的差距。但请不要忘记中世纪前的欧洲是不允许解剖的,宋慈和维萨留斯几乎都是各自文化中最早接触到真实人体骨骼的人。他们看到的的对象也相同,都是人组合在一起的206 块骨头。但务实的西方人能看到骨膜、关节和韧带,务虚的中国人却立刻把骨骼抽象变形成为菊花瓣和小方格。不要说宋慈只是为了示意,如果你去细数就会发现那一堆菊花瓣表达的肋骨真的有24 条,九宫格小方块也真的对应手指脚趾的节数;也不要说维萨留斯的时代绘画技法大有进步,透视法等已经成熟。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1771年所作的《鬼趣图》显示当时的绘画已经有了透视和空间,但他笔下的两个骷髅依然呈现为平面组合的菊花瓣和小方格。并不是中国人认识不了、或者描画不出形状准确的骨头,而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偏好于认识到骨头的“抽象性状”就截止,没有在“筋膜”、“韧带”等复杂细节上深挖细剖的习惯。“菊花瓣”表达了骨头的数量、方向和排列方式,刚直的笔法大概也能体现骨头的硬度。对于“中国式务虚”而言这些信息已经足够承载“骨骼”的内涵。要继续深化认识就因没有方向而显得乏力。米修在谈论中国字时总结道:“(中国人)缺少一种禀赋来认识纷繁细致的整体,也缺少(要去开发这种禀赋的)自觉。(Michaux,1933:157)。”后一句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只是某种思维习惯薄弱,很可能是兴趣或者天性的偏好使然;但如果长期意识不到建立这种习惯的必要性,就多半是某种能力欠缺了。
除了“高度精神化”之外,米修认为中国在诗、画、和书写文字中都表现出数学一般的高度抽象特征。而“高度抽象”的同时也很容易形成“高度主观”,使得中国人建立的规则很难具有稳定统一的普适性。米修就援引欧文在《中国书写文字进化史①G.Owen.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Writing:The Inaugural Lecture of the Michaelmas Term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Publisher:Horace Hart.1910,p.8.》中的例子,说仅仅是大象的“象”字,在几个世纪内就变了八次,以证明中国式抽象的随意(Michaux,1933:158)。在《中国的表意文字》一书中,米修更是开篇就表示,中国象形字在构字规则上,“缺乏明确可操作的原则来规定字符的简化、统一、和推演。②Henri,Michaux.Idéogramme en Chine.Paris:Ed.Fata Morgana,1972(broché),p.9.”在米修眼中,中国人实行“抽象”时,对对象的直观模拟度过低:“两千个汉字里大概能有五个是能一眼看出意思来的,这和埃及象形文字的‘好认’恰恰相反(Michaux,1933:157)。”站在我们中国人的立场很可能一时难以理解这种指责,毕竟在我们看来甲骨文具有很高的象形程度,并且立刻就会想到我们作为构字原则的“六书③分别是象形、会意、假借、转注、指事和形声”。六书从音、形、意三个方面为字符和客观世界建立联系,同时还兼顾了一定的哲学理念和图画美感,怎么会不好认、怎么叫没规则呢?那么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初学象形字的时候,我们能理解“臣”字为什么像一只竖起来的眼睛吗?能明白为什么一堆波浪就是“水”、而不是“江”、“河”或者“海”吗?学六书时又能完全分清哪是“会意”哪是“指事”吗?能回答哪种情况下用形声而哪种不用吗?的确,六种之多的不同规则体现了中国人对符号的“天才”,但这些规则之间的界限、不同规则的选用逻辑,却显得十分暧昧不清。因为我们并未要求按照同一稳定逻辑建立统一普适规则。我们的“抽象”方式并不限于“建立逻辑”,还包括凭着“灵悟”和纯粹的“感受”去捕捉某种精神气质上的亲和。这种“建规”方式更为宽松,为“奇思妙想”提供了更多空间;但宽松的规则不可避免的就使“结构”松散,从而导致“系统”内部缺少可靠的稳定性。当然,不能简单就说我们中国人这种具有主观随意性的抽象方式不好,“灵活性”和“系统稳定性”往往不可兼得。中国人的思维偏好虽然高度抽象,但米修也曾写道:“中国人从来都不是空想家。他们虽然没有超验的系统性规则或‘灵光一闪’什么的,但却有非常独特的思维能捕捉到一些无法简单量化的实用价值(Michaux,1933:171)。”
米修对中国书画艺术的态度非常有趣,他明确指出了中国式务虚的手法和特征,在提出批评的时候也努力让自己客观地去承认其中优点。但有时明明是同一种审美偏好在不同领域的体现,他却显得颇不通融,言辞激烈的一褒一贬。被他称为“最擅长表现、最精神化”的中国戏剧,为了避免直白浅陋通常使用回避本意、婉转暗示的方法,米修似乎充分理解。甚至还向他的欧洲读者们解释说:“当中国戏剧需要表现出空间辽远时,演员们就做出远望的样子来示意。这很好理解,如果没有空间,谁会没事望那么远呢(Michaux,1933:182)?”这种抛开具体场景,仅以暗示来邀请别人联想的手法,此时似乎还显得是一种高级手段,比欧洲“只晓得把一切都搬上台面,啥都不落下(Michaux,1933:181)”的做法要高明得多;但一旦转移到文字领域,象形字对客观对象多做变形、回避直接模拟本体,在米修看来则变成了中国人“喜欢遮蔽”的陋习。在《中国的表意文字》中,米修写道:“那种掩藏的特性影响着中国人的造字……把含义隐藏起来令中国人愉快,他们的书写符号因而也被‘密隐’保护了起来,一种只有内行之间才能心照不宣的密隐(Michaux,1972:13)。”诚然文字符号所采用的暗示会比戏剧要晦涩得多,但仍是同一种舍弃表象模仿内核的手法。能欣赏中国人“符号天赋”的米修应该不难领会到这种“得其意而忘其形”的审美追求。他自己就曾表示“胡子”加上“疼痛的膝盖”比其他一切关于“老”的词汇和体态都更能传递年迈体衰的感受(Michaux,1933:157)。更何况对于汉字他自己也算得上是“行家”,并非不能领会其中的寓意之妙、传神之趣。却是什么阻止了他把对戏剧手法的理解扩展到别的领域,从而像其他大多数研究中国艺术的法国作家那样、全身心的享受这其中的抽象之美呢?细看上文就会发现,米修在分析中国“艺术”的时候,却常常用一种近乎苛刻的眼光指责它不够“科学”。掌握细节也好建立系统也罢,作为科学实践的原则非常实用,用来批评艺术却显得过于求全责备。米修之前的伏尔泰(Voltaire),米修同时的马尔罗(André Malraux)等人,在欣赏中国书画戏剧时都把艺术和实践分得很开,为什么米修偏要如此严厉的把两者合为一体,甚至借着务虚偏好的某些缺失上升到中国人的“品性”上来呢?
他的有一句话也许能为我们解惑:“欧洲人(日耳曼、高卢、安格鲁-撒克逊人)的中国热啊!人们简直恨不得说一切都是中国人创造的!嗯!但好玩的是,欧洲人的的确确总能再加深中国人的研究,总能重新发明中国人的发明(Michaux,1933:167)。”其中的“嗯”字在原文中单独成句,后面的句子提行书写,显然米修说这话时情绪颇浓。而这情绪不外两重:其一,其他欧洲人把什么创造都归功于中国;其二,我米修认为欧洲人的创造力事实上就是要优于中国人。这两重情绪加起来,明确的表达了一种“抵制中国、捍卫西方”的意图。这种“捍卫”并不仅仅属于米修,它属于一个时代,整体上对抽象意义的“中国”都带有某种含混的敌意。“中国”作为遥远东方的代表,经常为欧洲的“自我调适”扮演着一个被动的他者:中世纪后期出于对宗教特权的反叛,欧洲需要自我否定的时候,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作为“宗教”的对立物被高度颂扬、以表明宗教思想之外仍然有高级智慧。中国以一个“制度优越者”的身份刺激着急需制度改革的西方;而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的现代化制度和人文主义思想日趋成熟,整个欧洲需要自我肯定和巩固了,中国就更多的被描述为一个“发展水平落后者”,孔子思想更是僵化刻板的代名词和“民主”的对立面。本书成书于1933年,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正如周宁先生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自省与自我批判的精神开始重新塑造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①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卷,北京:北大出版社,2006,371 页。”整个西方社会再次出现以中国为参照进行自我否定的思潮。然而大战后的惨痛激发出自强精神,必然要对这种整体性的自我否定有所反抗。1927年亨利.马西斯洋洋洒洒一篇《捍卫西方》,激发出一场浩浩荡荡的、一直持续了三十年的“捍卫西方”政治运动。捍卫,即保护一方免受另一方的伤害;既然捍卫西方,那么东方理所当然就是那个假想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米修的敌意是克制的、有所反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一以贯之批判中国的基调下还时常以一种客观的口吻承认中国式抽象的高明之处;但这种化入了潜意识的敌意往往又是最强大的,它能让一个高度理智的人对自己的敌视对象莫名、但却全面的抵触。我们无意说米修的“一以贯之”全是出于敌视,这里面既有客观因素又有文化隔阂。但不可否认这股淡淡的敌意始终存在。
二、“无为”还是“不得不为”?
在包括米修在内的法国作家眼中,中国人在艺术领域之外的务虚态度,则表现为忽略个人感受、漠视实际收益、放弃主观意志,只一心一意追求在伦理上“合规”。中国民众满脑子都是被灌注的抽象价值,自我意识十分淡漠。甚至有一种主动丢弃个性,抹除自我的自觉。而这种自我抹除,则被法国作家们归因于中国的“无为”思想。
这里提的“无为”事实上已经不是老子所说“去功利、去执念”的清静无为,而是一个在法国的道家思想研究过程中、被文化隔阂异化了的概念,演变成了“不作为”的同义语。“无为”从传入法国起,就跟十七世纪盛行的灵修学派“寂静主义(quiétisme)”混为一谈,被认为都是要人“放弃主观、取消意志”。只不过前者把人交给虚无缥缈的“道”,而后者交给寄托幻想的“神”。本质上都是否认现实、拒绝行动的消极态度。“无为”最早的法语翻译“non-agissant”见于1831年积约姆.波提埃(Guillaume Pauthier)的著作②Guillaume,Pauthier.Mémoires sur l’Origine et la Propagation des trois Religions ou Doctrines.Paris:Imprimerie de Dondet-Dupre,1831,直译就是“不活跃、不好动”。而后来常见的“non-agir”和“inaction”③著名汉学家勒内.格鲁塞(Réné Grousset)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东方哲学史:印度、中国、日本》中,以及著名东方学家莱昂.德.赫斯涅(Léon de Rosney)在其代表作之一《道家思想》中,都使用“non-agir”这个翻译。在解释这个概念时也都用到了“inaction”这个名词。米修使用的就是“inaction”.,更是索性就直接变成了“不行动”,把“不做不错”的消极倾向演变得更加激进,而老子思想中“因势利导”和“顺时而动”的精髓消失殆尽。直到1922年汉学家莱昂.维热尔(Léon Weiger)才发明出一个能够贴切“顺应”精神的对译“laisser agir①Léon, Weiger.Histoires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 Pékin:Imprimerie de 献县,1922,p.151.维热尔在发表他本著作的“中国天主教献县教区”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对中国思想文化有着深厚的本土体验,理解十分深刻。”,即“任其自为”。但这个说法在西方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人文主义语境下,很容易就被打上“放弃自身意志”的标签,成为中国人“自我意识淡漠”的罪证。中国人把自己主观思想的塑造完全交给“榜样”,自身则采取不作为态度的做法,显然让米修感到震惊。在本书中米修不无惊叹的写道:
中国人对于“模仿”的偏好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可以毫无痛苦、自然而然的就对那些让人极不舒服的“榜样”屈身适从。这种怪癖在中国人身上植根深入,以至于哲学家们几乎在(“模仿”)的基础上就建立起了他们的全部伦理——“榜样”伦理。中国的书籍会教你:“一个公正而智慧的王子可以让四海臣民模仿他的言行。他只要履行好他对父亲、儿子和兄弟的义务,然后人民就会好好模仿他(Michaux,1933:174)。
原文中“人民就会好好模仿他”被加了大写强调,显然对中国的“人民”放弃自主权的做法大有意见。因此尽管他称老子“是真正的智者”、“触摸到了本质”(Michaux,1933:184),但仍然说“无为”就是“撤销(annihiler)自己的存在和行动”,是“抹除(effacer)自我”(Michaux,1933:185)。
然而自我强调是本能。既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思考,人就会积极主动的维护自己的想法和利益。如果能够使得绝大部分普通民众都自发约束本能,就绝不可能仅仅是某种思维偏好的影响,而必然在其时代和社会有着深刻的原因和合理性。在笔者看来,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太大,不可能被“周全细致”又“整齐划一”的一体处理;而这个合理性,则在于榜样-模仿链条本质上是一种“分类-建模-推广”的抽象思维。“父子-兄弟”的模型确立了农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义务关系,那么以“王子”这个统治者的身份来建模,用父子关系表征君臣关系,就把政治义务嵌套进了血缘义务当中。如果强调个人、家庭、和社会之间分级隶属的关系如同确立函数,那么榜样明确出个体职能则是在刻画变量,使得整个社会的各种力量能够铰合一体,协作运动。为了更便于理解,这里不妨用米修自己提到的一个现象来稍加解释。米修说当一场战争不得不爆发,中国人却并不真的打仗,甚至也不演习,而只是示意、表演出战争的样子(Michaux,1933:156)。在西方人看来,这种车马列阵摇旗呐喊的场面,这种城下人山人海列成方阵,只有两员大将在阵前捉对厮杀的“古君子之战”实在怪诞得仿佛舞台剧。但是如果放弃“表演”而采取西方式肉搏,以中国的人口数量和当时的武器水平,只怕足够交战双方厮杀上半个月,而且最终也只能以“杀尽对方每一个”这样原始而惨烈的方式来分出胜负。在农业社会,人口和时间都极其宝贵,这样的战争成本实在过高。而“君子之战”乍看荒唐,实则对双方的“战力指数”出了非常科学的细分展示:车马是辎重水平,代表着游击能力和运输能力;士兵展示出武器水平和人员基数。厮杀的大将体现最高战力,甚至吹的号、摇的旗都表现出纪律水平。把一场战争抽象为辎重、装备、人员数量、战斗素质和纪律水平五个方面加以展示较量,已经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胜负预期。而结果却可以大大的降低战争成本。这就是“分类-建模-推广”的好处。虽然分类的时候难免挂漏,建立的模型(榜样)难免过于理想化,推广的时候也难免武断,但一个疆域过广的统一国家要想建立起均一的制度似乎却只此一途。这就像井田制,作为一个主观性极强、以理念代替实际的土地制度,它显然不具备太多科学性;但在一个丈量统计水平极其落后、幅员极其辽阔,水文天候肥力等自然条件差距极大、劳动力数量有限、土地分配极其不均的社会,恐怕再找不出一种比井田制更能够安排整个社会土地关系的制度。向“榜样”让渡自主权“不是中国人不作为,更多却是社会背景下的不得不为。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人本主义精神发展较晚,主流文化里也确实存在某种淡化个体、推崇伦理的微妙引导,老百姓的自我意识水平的确不高。但如果把原因解释为米修为代表的法国作家们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务虚偏好”的自我抹除,则未免武断。
结语
总的来说,米修的这种批判态度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他者视角。如果转换成西方实证主义视角,就不难发现米修对于中国人的批评有“简单化对象”的倾向是不无道理的。其次是文化隔阂。从对中国的熟悉程度来讲,米修虽然游历过中国(这一点强过他很多从未到过中国却写出大量中国游记的中世纪前辈,如曼德维尔之流),但毕竟不是汉学家,对中国的漫长历史和复杂社会状况缺乏认知,难免对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架构方式难以理解。再者还有时代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西方,其整个时代风气对中国文化既有“有意识拔高”又有“无意识恐慌”。在抵触拔高和保护恐慌的双重需求下,米修不可避免的对中国式思维产生了排斥乃至厌恶。而这份厌恶依附在看似客观的对“中国式务虚”的批判上,对西方人而言又显得那么的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