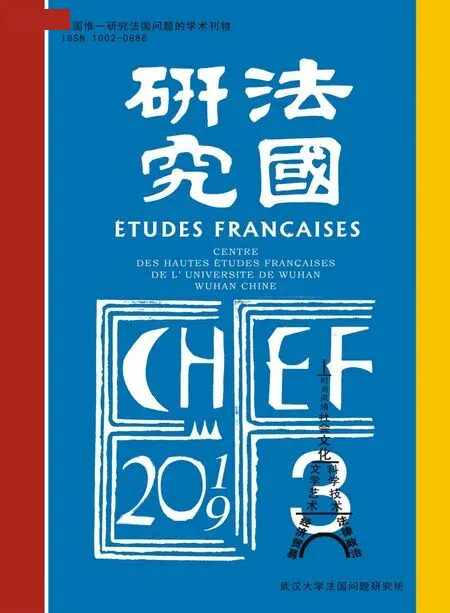反诘哲学之肇端:兼评博纳富瓦《反柏拉图》
唐毅
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是当代法国诗坛的巨擘。他出生于1923年,自青少年时代起,先后经历了世界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法国五月风暴、苏东剧变等。作为生命个体,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带给他复杂而丰富的人生体验,促使他毕生关注社会、现实世界和人类命运等重大主题。2016年,博纳富瓦离世,生前已出版的20 多部诗集,70 余本论著以及多部译作成为他留给法国文学的宝贵财富。《杜弗的动与静》(Du mouvement et de l’immobilité de Douve)、《刻字的石头》(Pierre écrite)、《昨日大漠一片》(Hier régnant désert)、《在门槛的圈套中》(Dans le leurre du seuil)、《雪的始终》(Début et fin de la neige)、《弯曲板》(Les Planches courbes)等诗集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反柏拉图》(Anti-Platon)创作于1946年①根据1980年博纳富瓦《致让·E·雅克松的信》(参见1981年出版的博纳富瓦《关于诗歌的访谈录》第134 页)可知,博纳富瓦于1946年创作完成《反柏拉图》,但该作发表时在诗名后标注1947年,应指首次出版的时间,后又于1962年删节再版,本文采用的是删节后的版本。,是博纳富瓦在成名之前的“练习写作”①[法]伊夫·博纳富瓦:《论诗歌的作用(上)》,吴康茹译,载《诗探索》1999年第4 期,176 页。时期完成的一部诗作。这首诗透露出诗人对待哲学的基本态度,表明博纳富瓦在诗歌创作生涯中一以贯之的诗学原则,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呈现其“在场”(Présence)诗学的思想来源。
一、《反柏拉图》的创作内涵
《反柏拉图》是博纳富瓦在诗歌创作上的早期尝试,虽然它没有像诗集《杜弗的动与静》(1953年)一样为诗人扬名立万,但时值与超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之际,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青年博纳富瓦的思想倾向,他表示“布勒东在梦想着他的思想而不是思考他的梦想”,因为“我们都是具有双重性的生物,既是语言的也是存在的”②Bonnefoy,Yves.Entretien sur la poésie.Neuchâtel:Les Editions de la Baconnière,1981,p.132.。他逐步转向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舍斯托夫(Chestov)的存在哲学,开始致力于艺术、诗歌表现真实的最初探索,这与他的求学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1940年二战的硝烟依然笼罩着法国和欧洲,在外省就读中学的博纳富瓦已开始接触到超现实主义诗歌,他的哲学老师从巴黎带来乔治·于盖(Georges Hugnet)的《超现实主义诗抄》(Petite Anthologie du surréalisme),博纳富瓦从中了解到布勒东(André Breton)、艾吕雅(Paul Eluard)等人的前卫思想。1944年至1947年间,他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数学,其间到地中海沿岸和美洲旅行。在这一时期,博纳富瓦广泛涉猎了波德莱尔、克尔凯郭尔、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并于1946年结识了布勒东。在与超现实主义短暂接触后,博纳富瓦认识到这一思潮脱离现实,玩弄技巧,他认为“超现实主义者们是一群只顾玩耍的孩子”(1981:118)。此后,从小有志于写诗的博纳富瓦毅然走上了文学道路。194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钢琴家论》(Traité du Pianiste)。由于此时受到超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这部作品具有自动写作和杂乱无章等特点。1946年完成的诗作《反柏拉图》,后于1962年删节整理后再版,是博纳富瓦逐渐摆脱超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品,展示出他对哲学与诗歌的独立思考,在他的诗歌生涯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成就为西方后世思想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之源。作为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构成,他把诗视为教化手段,“诗人以集体的名义,通过诗歌来塑造观众的灵魂,以求让后者遵循集体价值观”③王柯平等:《柏拉图诗学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8 页。。鉴于诗歌在城邦时代的非凡力量,柏拉图企图不动声色地“让哲学取代诗歌成为文化权威”(王柯平等:45),以至于在《理想国》中不留情面地谴责并放逐诗人。出于特定的政治时期和社会考量,柏拉图选择以哲学改造诗歌,这引起亚里士多德、尼采、康德、荷尔德林、克尔凯郭尔等后来者围绕哲学与诗歌关系问题的持续论辩,他们从不同向度相互驳斥,可谓众说纷纭。二战后的法国哲学是“各个充满自由思想创造精神的哲学家的多元、多质、多极的文化生命体,各自体现了明显的思想个性”①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4 页。。与萨特、德里达、拉康和福柯等人相比,博纳富瓦不算是成就卓著的哲学家,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和艺术家。在认识世界与寻找真理的道路上,博纳富瓦洞悉哲学的弊病而转向以诗歌改造哲学的路径。在诗歌创作的初期,他将以哲学改造诗歌的柏拉图作为反诘对象,意在拓展诗歌的新天地,建构起回归真实的诗学思想。
《反柏拉图》包括九个诗节,采用交替展开的叙述策略,铺陈虚构与真实相混杂的事物,表明博纳富瓦在某种意义上仍遵循超现实主义在梦幻中恣意想象的原则,但也尝试着“抵达更大的现实——在具体存在和日常真理中的现实”②Bonnefoy,Yves.L’inachevable:Entretien sur la poésie(1990-2010).Paris:Albin Michel,2010,p.354.,这与他主张像兰波一样直面“粗糙的现实”保持一致。博纳富瓦指出这首诗的名称是模仿“恩格斯所写的《反杜林论》(Anti-Dübring)”(2010:354)而来的,客观上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对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博纳富瓦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与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种现当代哲学思潮合力催化的结果。从创作手法上看,从“用木料和纸片建造的这座城市”到“柳树、皮毛和石头的国度”,再到“留声机上的蜡做的女人脑袋”③Bonnefoy,Yves.Poèmes.Paris:Gallimard,2012,p.33.,博纳富瓦在创作早期对诗歌意象的选取带有比较明显的自动写作和恣意拼贴等特征。诗人还精心设计了诗歌内容的排列形式,让单双数诗节交错但意义相对独立地展开。单数诗节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贯穿整个情节,主要以“他”和“她”两种人称为叙述主体,从虚幻意象中映照古典哲学的谬误,提出以诗歌改造世界的新主张。双数节则主要以“我”、“你”和“我们”的视角进行对话,“时间很可能消逝在你的颈项之上”(Bonnefoy,2012:34),似在向彼此倾诉对死亡的认知,又似在“血的国度”里探索虚实或时空的二维关系,“我听见你在夏天的另一边呼喊”(Bonnefoy,2012:40),既有诗意的追思,又有美好的愿景。整体而言,博纳富瓦运用这些人称的指代技巧,意在营造一种和谐共融的诗化世界,无论是死亡或重生,还是怪诞或纯真,始终在“我们”(nous/on)的周遭,与现实和真理同在。
博纳富瓦主张“潜心研究昭示有限性的此在和现时(ici et maintenant)”(1981:134),并且应促使诗歌语言反映这一属性。“夜之身躯在这里开始/虚无之路在这里被覆盖”(Bonnefoy,2012:36),诗人对“此在”④诗中译作“这里”,法语词为ici,哲学上通常译为“此在”。十分重视,诗中的“这里”指的是城市、国度、嘴还是路途,不必准确定义,但可明悉为是世界某个角落的“真正的场所”(le vrai lieu),是诗人热切盼望通向的未知之地(l’inconnu)。在诗的最后一节里,“只对塑造敏感,对经过敏感,对平衡的颤抖敏感,对已经从四面八方爆发的确认了的在场敏感”⑤[法]伊夫·博纳富瓦:《杜弗的动与静》,树才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1 页。,这首诗最终归于“在场”,同时透露出一种变化性。由此可见,《反柏拉图》开启了博纳富瓦以诗歌反映“在场”进而探求真理的创作道路。
二、叩问哲学,反诘哲学
博纳富瓦在一次谈话中被问及“是哲理诗人还是诗意哲学家”时,他表示:“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位诗人。诗人本身包含着一切。”①葛雷:《法国当代哲理诗人:伊夫·博纳富瓦》,载《国外文学》1993年第3 期,123 页。博纳富瓦对自我身份的定位表明诗歌在其心目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崇高位置,而哲学,虽是他青年时代汲取思想养分的沃土,却也成为后来终其一生不断反诘的对象。受黑格尔、海德格尔、雅思贝尔斯、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等人的影响,博纳富瓦对时间与空间、存在与表象、生命与死亡等问题进行哲理性思考,但他并未流连于此,而是向更本真的诗的范畴靠近。从与超现实主义决裂起,博纳富瓦投身到战后法国诗歌复兴的事业中,日益关注当代意识如何从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分离出来,以及诗歌和艺术在当下可实现的功能。因此,他拒绝了专门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转而创作诗歌,开展诗学批评,译介西方经典诗人和作家,投入诗歌和美学领域以便发现这个鲜活、具体的生命世界。正如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一样,在博纳富瓦的诗学思想中,哲学话语具有双重性:既塑造了他青年时期的思想,又困扰着创作之初的诗人自身。荷尔德林一生信奉诗高于哲学,并宣称终有一日“诗又将像在开端一样成为人类的教师;不再有哲学,不再有历史,唯有诗歌艺术超越其余所有的科学和艺术而长存”②李永平:《荷尔德林:在诗与哲学之间》,载《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4 期,187 页。。博纳富瓦未尝不是如此,他曾希望在当下“人文主义面临危机之际,通过诗歌让世界回归人类纯洁的伊甸园”,并通过诗歌“看到一次新的文艺复兴”③沈大力:《伊夫·博纳富瓦:一个“现实的梦幻者”》,载《文艺报》2016年7月15日。。在荷尔德林和博纳富瓦看来,诗歌终究是最有用的济世良方,诗人既要学习和思考哲学,更应叩问和反诘哲学,从而达到哲学真实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诗性真实。
对诗人而言,在写作初期,“普通的语言可以描绘平淡无奇的经历”,而更高层次上,“语言—意象相结合的形式可以细说对某一问题的抽象认知”,最高的层次则是“诗歌语言能够触及最震撼人心的个体体验”④Thoret, Yves.Le poète Yves BONNEFOY et la rencontre.Intervention à la table ronde “ Culture, loi et santé mentale”du Colloque Franco-Américain de Psychiatrie,“Psychiatrie et Environnement bio-psychosocial en 1996”,Paris,13-17 mai 1996.。《反柏拉图》是博纳富瓦的早期作品,诗人试图发挥语言的魔力,在稍显稚嫩的文笔和已然深邃的思维之间,他把抽象和永恒赶下神坛,以真实和在场为武器,反思自古希腊以降的哲学思想史。
博纳富瓦在诗的开篇将马的头和口鼻与城市、街道拼合在一起,将一个女人的脑袋和留声机拼接成一幅看似怪异的景象。如波德莱尔所言,“美是古怪的、令人惊奇的”⑤参阅朱立元编《西方美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229 页。。博纳富瓦运用了现代绘画艺术的具象思维,通过诗歌重新编排简单的日常事物的空间顺序,从而到达一个高于朴素现实的真实的审美境界。柏拉图则认为日常所见的世界是低劣和虚假的,真实存在的事物只是形式或模板,如同“洞穴里的囚犯所见的影子”⑥出自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意在阐述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区别等问题。本文引用该理论侧重于形式和表象对人的主观判断的影响。。在《反柏拉图》里,诗人竭力呈现由柳条、石头、斧子、卡片、土地、桅杆、桶、沙、螳螂等事物的诗意内涵。柏拉图重视形式的实在性,因而认为意象具有真实性,并称诗人和艺术家都是骗子。博纳富瓦则明确反对意象,指出“意象必定是谎言”①Bonnefoy,Yves.La Présence et l’Image.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3,p.34.,他主张“用几何学家的方法接近表象世界,就必须设置日常行为使用的三个轴向,而有限性是其法则”②[法]伊夫·博纳富瓦:《隐匿的国度》,杜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19 页。。因此,《反柏拉图》中的简单事物构成博纳富瓦诗歌的实在元素,它们受语言魔力的驱使,流露出反诘古希腊先哲的野心。
三、关于相似性与无限性的思考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到荷马关于“蜡”与灵魂的相似性的说明,可能是因为蜂蜡和心灵两词在古希腊语里的同源关系。这一描述为后世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柏拉图“摹仿说”的影响下,“蜡”被抽象为一种相似性。对诗人来说,“为了给虚构的存在赋予生命,并且召唤‘来世’,诗人或吟诵者首先要构建一个故事,通过语言描绘另一个世界的存在物”(王柯平等:148),这是柏拉图时代对诗和诗人的话语模型的误释。在《反柏拉图》中,“一个男人用蜡和颜色制作一个女人的模型,所有相似之处,使之存在,……血肉之塑像在其中重生、裂变,在蜡和颜色的激情中”(Bonnefoy,2012:35),博纳富瓦对相似性问题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诗歌不是模仿现实的产物,而是基于现实事物创造的新现实,需要利用诗人的天赋和语言的魔力来完成。在他的诗学思想里,“诗不仅是用想象力将一种现实浓缩,更主要是通过语言所创造的形象、韵律和诗学效果使人从现实走向一种高层次的现实——即含有一种超验性的新的更为开阔的现实”(葛雷:123)。因此,柏拉图指责诗歌乃至文学艺术的相似性和模仿问题是有失偏颇的,只有当身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回归到诗人的身份里,诗性真实的面目才会再次生动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经历世界大战又与超现实主义决裂后,博纳富瓦将这首诗的矛头直指柏拉图也许有其特殊的意图,表现为他在诗与哲之间的重新抉择。在《反柏拉图》中,“你”这个人称的使用值得探究,“智慧的你,您挖掘的是/人群中的高光/你倒在暗淡的死亡之国的门槛上”(Bonnefoy,2012:36),抑或“而你石状的头颅被交给风的帷幕”(Bonnefoy,2012:40),倘若将全诗看作与先哲对话,那么“你”应指的是柏拉图,与之相对,“人们称作我的那个人,当天色暗去/门被打开,人们谈论着死亡”(Bonnefoy,2012:38)中的“我”和“我们”可能就是个体的人或全体诗人。柏拉图的“理念说”使哲学陷入形式与无限性的泥沼,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宇宙应是有自然边界的,乃至当代哲学仍在用一种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探讨此问题。作为诗人,博纳富瓦明确反对哲学主张的时间、空间与现实的无限性,而认同一种“基于语言无限性的现实的有限性”(1981:132)观点。他认为“诗歌揭示的种种存在经验能被他者领会,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生命的有限性,从而更好地体验生命的丰富性,最终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①曹丹红:《诗意是翻译中不会失去的东西——兼评伊夫·博纳富瓦的翻译诗学》,载《外语教学》2015年第6 期,94 页。。通过《反柏拉图》中的对话模式,博纳富瓦指明当代诗歌的思想边界不存在于诗歌与哲学之间,而在于诗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之中。
总而言之,“当诗是哲学的起源时,哲学也反映在诗中,它在诗中找到了具有相同真理的共鸣”(王柯平等:121)。柏拉图的智慧最初与诗歌密切联系,苏格拉底也称诗是其“意义的水库”,施莱格尔(Schlegel)倡导“包罗万象的诗”②周国平:《诗人哲学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3 页。,博纳富瓦则颇为神秘地表示“诗歌包含一切”。在这个机器人可以写“诗”的时代,西方哲学跟随科学技术的脚步进入到后现代的话语语境里,而博纳富瓦敢于直面现代性危机造成的被动局面,反诘柏拉图并叩问哲学,力图借助诗歌重新发现诗和诗人的本质,反映科学与数字遮蔽下的更为鲜活、丰富的生命世界。
四、建构“在场”的诗学伦理
二战后的西方社会凋敝颓废,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焦点是现实的走向和人类的命运。初出茅庐的博纳富瓦尚未彻底脱离超现实主义的梦境,不过他早已发现残酷的周围世界需要青年人来重建。他尝试以诗歌改变现实,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由此,博纳富瓦致力于建构一种维系诗歌、现实和生命世界的诗学思想,“在场”是它的精神内核,从源流上对其考证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博纳富瓦“在场”诗学的发生史以及他以诗歌取代哲学从而完成思想求索的艰辛历程。
作为反对概念化、抽象化的诗人,博纳富瓦从未就“在场”与“真实”等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在《反柏拉图》中,“这个”(ce,cet,cela)、“这里”一类的指示词被频繁使用,诗歌的言说对象被定格于当下的个体生命和“真实的场所”。博纳富瓦创作的不是模糊化的表象,而是活生生的真实,这种真实指涉“在场”,即“诗人将尚不为人所知的本原,经过自己的思考,用简练的话语陈述出来的真实”③李建英:《反映“在场”,诗歌不可终结的使命——博纳富瓦诗学研究》,载《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1 期,198 页。。“赋予这个怎样的涵义”(Bonnefoy,2012:35),“在这块石头周围”(Bonnefoy,2012:41),诗人的语言从不含糊,“这块石头”指向自然界的每一块独立有形的石质物,但“这块”反映它具体的“在场”形态,它不在于无法触及的别处,而是呈现为“此在”。朱光潜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④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627 页。。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曾反驳老师“真实存在于形式”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说明一个事物是什么,必须说出它的本体,一切其他的范畴都是附着于本体,是本体的属性,不能离开本体的”①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7 页。,因而从本体意义上肯定了真实的事物如树木和羊群是完全存在的、基本的且唯一的东西。与之相似,博纳富瓦明确反驳柏拉图的存在理念,但他更胜于亚里士多德和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既反对诗歌‘模仿’现实,又反对将诗歌艺术等同于现实;既反对以概念代替现实,又反对将形象当作现实,他的现实是所有鲜活生命关系的总和”(李建英:208)。亚里士多德承认真实的实在之物却极力明确其定义,存在主义哲学把文学艺术当作话语工具,都与博纳富瓦主张的真实和在场相疏离。因此,在《反柏拉图》的最后一节里,“仅对平衡的微调、过渡和震荡以及在全面的爆裂声中被证实的在场显得敏感”,诗人让“在场”这一术语在复杂的感官体验之间出场,并且迎来全诗的尾声,表明诗人在创作早期已经敏锐地察觉哲学无法拯救当下的现实,而诗歌可以通过“抵偿哲学的先天缺陷”②Campion, Pierre.Poésie et philosophie:Étude du poème d’Yves Bonnefoy «Aux arbres».L’Information littéraire,1991(4).再现丰满的世界。
在《反柏拉图》的第五节中:“一个男人在混合卡片。一张上写着:‘永恒,我恨你!’另一张上写着:‘让这一刻拯救我!’在第三张上,男人写道:‘必不可少的死亡。’”(Bonnefoy,2012:37)博纳富瓦在诗里表示出对永恒的敌意和对死亡的批判。柏拉图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开端,关于死亡,他在《理想国》里“从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出发,运用宗教式的布道方式,通过上天入地的灵喻,表述了古希腊业报轮回的朴素思想”③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4 页。。受时代的局限,柏拉图认为有永恒不变的现实存在,死亡也能以理式的形态获得永生。博纳富瓦在诗作中直截了当地驳斥这种永恒的理式说,直言“永恒的贩子”(2012:33),这是他后来主张认识有限的生命世界的肇端。又如,“桅杆断裂的面貌,遇难的样子”(Bonnefoy,2012:39),海难是西方死亡主题的表现形式之一,或许能让人联系起苏格拉底时代的第一位智者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逃离雅典却在海上遇难的事件。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哲学摆脱不了对死亡的认知局限,因此,博纳富瓦在创作早期便倡导打破对死亡的概念化理解,让诗歌自由地吟诵生动的死亡,去欣赏“芬芳的草丛和枯死的树木”④Bonnefoy,Yves.Les Planches courbes.Paris:Gallimard,2017,p.33.,发现“侵入死亡的纯真”(Bonnefoy,2012:41),抵达“另一种死亡之岸”⑤[法]伊夫·博纳富瓦:《博纳富瓦诗选》,郭宏安等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9 页。。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后者认为“真实的生活不可能由抽象的概念体系所包含,反对用抽象的、普遍性的概念、思想、体系去代替具体、特殊的个人”⑥[丹]克尔凯郭尔:《颤栗与不安》,阎嘉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 页。,并表示“凡事都有终极的时候”(克尔凯郭尔:217),死亡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反柏拉图》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对无限性和死亡等问题的质疑,博纳富瓦力图以诗歌发现真理——一种现实和激情催生出的诗性真理。
博纳富瓦忠实于描绘最简单的世间万物,他表示:“询问诗歌,我的一生都只反映最自然之物,别无其他,因为在过去几年的诗歌经验里,在我看来已经出现了矛盾和担忧。”(1983:23)这些“最自然之物”首先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进而连接成社会现实,最终概括为整个真实世界。博纳富瓦擅于运用诗语言展示世间万象,他热衷描绘的事物群体庞大,如大地、荒漠、道路、城堡、火焰、云朵等等,尤其是“石头”这一物体在其诗歌里比比皆是,如“白日之酒倾倒,蔓延在石板上”(2002:51),“我们的家具如石头一样简朴”(2017:354)。而在《反柏拉图》中,“挖开这一小片疏松的土地,它的脑袋,直到你的牙齿重新找到一块石头”(Bonnefoy,2012:41),博纳富瓦吟诵“柳条、皮毛和石头的国度”(2012:33)并用“牙齿重新找到一块石头”,尽管他反对任何暗示,但其作品中“石”的物象与他毕生追寻的真实和真理在美学意义上显得格外接近。当然,“诗人只是采集人类自身重要的真实现状的信息,并使那些信息在此时、此地产生联系,使之成为思考的材料”(李建英:205),因而无论是“刻字的石头”、“石碑”还是“山岩”,只在诗作中展示“在场”的真实面貌,因为“物体的真实性独立于我们,因为它是什么不依赖这个人或那个人,不依赖他的思想、他的语言,甚至也不依赖他的知识”①[比]米歇尔·梅耶:《如何思考实在》,史忠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41 页。,至于真理,同样无法由诗人直接讲述,它也存在于意象和语言之外的客观、具体的事物中。在诗作结尾处,“触及这块石头后:世界之灯旋转,神秘之光涌动”(Bonnefoy,2012:41),博纳富瓦也许在写作之初便期待诗歌实现其抱负,但他并未就此驻足不前,他谙熟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等人的思想,却转向诗歌的领地去寻觅真正的道路,卡夫卡(Franz Kafka)称这条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②卡夫卡的经典语句,参阅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fefa0e0102wni8.html。。诗歌铺就的道路是丑陋、艰难和粗粝的,路尽头的真实也未必是美好的,但博纳富瓦从《反柏拉图》出发,像荷尔德林说的那样,“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四方”③[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唐译编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194 页。。
博纳富瓦认为“语言既是一种交流,也是一种多方面的探索,它也是人类共同意识变化更迭的反映”(1999:177),因此,他摒弃空洞的哲学而投身诗歌创作,渴望发挥语言的魔力,追索由生命个体组成的整体现实。博纳富瓦在创作《反柏拉图》时已蓄积着反诘哲学、拥抱诗歌的意愿,以“在场”收束起全诗的思想内核,既明晰了语言、诗歌和哲学的关系,又开启了当代诗歌焕然一新的诗学理念。这首诗无疑是研究其早期诗歌创作思想的重要作品,“在场”诗学以此为发轫,逐步完成对传统诗学的反拨,进而抵达诗高于哲学的更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