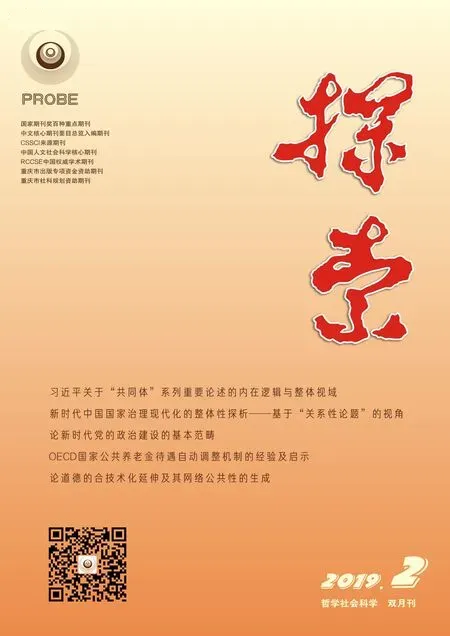OECD 国家公共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经验及启示
林 义,蹇滨徽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成都611130)
目前我国发展正面临结构性转型、GDP 增速放缓、物价持续上涨的风险。这可能导致基本养老金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方面的功能弱化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压力的增大。建立有效的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是合理应对策略之一。自动调整机制(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AAMs)是根据预先设定的一系列参数自动进行养老金调节的方法[1]。1922 年丹麦通过了第一部在国家养老金计划中实施自动调整程序的法律,将养老金待遇与政府雇员薪资水平的变化联系起来,以应对物价上涨;二战后,冰岛、卢森堡、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也陆续建立了自动调整机制[2]。为应对养老基金财务危机,在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发展完善过程中也考虑了财务平衡的需要。相较临时无规则的调整,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有以下优势:其一,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根据相关可测量指标的变动自动调整,具有可预测性;其二,较高频率的自动调整减少了对制度大幅调整的需要,降低了制度变革成本,减轻了对社会带来的不利冲击。
1 养老金自动调整机制的结构
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可解构成三个部分:一是调整参数,即待遇调整的参考依据;二是适用范围,用以确定自动调整机制何时运行以及何时停止运行;三是调整频率。
1.1 调整参数
调整参数是待遇调整的参考依据,决定待遇调整的幅度。养老金待遇调整幅度主要依据三类指标来确定,即待遇水平、待遇享受资格和缴费率。
待遇水平可以通过待遇指数化、收入的变化以及反映预期寿命的改善或资金短缺状况的相关指标进行调整。待遇指数化是将待遇水平与工资或物价挂钩。德国、加拿大、日本、葡萄牙等国家采取了这一形式。养老金待遇也可依据收入的增加情况而调整,如在DC(Defined Contribution)制中,投资收益的高低会自动影响待遇水平[1]。在实行名义账户(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NDC)计划的瑞典、意大利、波兰、挪威、拉脱维亚等国家,预期寿命的增加会自动降低养老金待遇[3]25。待遇水平还可依据预期寿命的变化而调整。在芬兰、葡萄牙等国家,养老金待遇通过“预期寿命系数”或“可持续因素”与退休时平均余命的提高相关联。
待遇享受资格参数中,退休年龄是被广泛使用的自动调整参数之一。退休年龄一般基于预期寿命的变化或养老基金状况的变化而调整,退休年龄的调整会影响缴费期和待遇领取期的长短,进而影响退休待遇。丹麦每5 年对退休年龄进行审查,并在考虑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财务状况下,可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捷克当前每年将退休年龄延长2 个月。法国则依据维持经济活动期与退休期的比例于2/3 至1/3 之间的标准调整退休年龄[1]。
缴费率通常较少作为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参数,原因在于缴费率不宜频繁变动。缴费率的频繁变动不仅使企业和个人难以适从,增加企业负担,还会增加运行成本和管理成本。另外,在老龄化程度加剧的趋势下,缴费率下调空间有限,所起作用不大。大多数国家通常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和公共养老金计划的持续性压力,暂时或长期改变社保缴费率。但仍有一些国家引入了该参数。在加拿大,如果法定费率低于持续性所需水平且政府未出台旨在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其他措施时,缴费率将增加。
1.2 适用范围
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适用范围由触发指标和触停指标确定。触发指标指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开始运行的条件;触停指标是其停止运行的条件。
触发指标依据其是否已实际发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预测变量,该变量并非已发生,而是基于过去情况对未来的预测,当该预测变量达到某一状态时,自动调整机制将被触发;另一类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状态变量,该指标测量的是已经发生的实际状态,当其达到某一预定状态时,就触发自动调整机制。例如,基于未来某段时间内预期CPI 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就是根据预测变量进行的调整;基于过去某段时间内CPI 的实际变化而进行的调整则是根据事实状态变量进行的调整。两种方式都能达到触发的作用,但各有缺点。基于预测变量进行待遇自动调整的机制需要良好的反馈机制和较高的管理能力,以便能及时更正预测情况与事实状况的差异;基于事实状态变量的待遇自动调整是对当前状况的一种滞后调整,可能会减少自动调整的实际预期效果[1]。
自动调整机制还需要确定触停指标,明确自动调整机制停止运行的条件。当自动调整机制的调整参数处于不合理变化水平时或养老金计划本身存在问题时,自动调整机制的运行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例如,将通货膨胀挂钩自动调整机制的待遇调节幅度与通货膨胀相关,当处于高通货膨胀时期,调节幅度可能较大,较高幅度的待遇调整不利于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稳定运行,特别是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待遇自动调整机制运行的代价会极大。为实现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平稳运行,防止财务状况受相关指标急剧变化的影响,需要规定自动调整机制的触停指标,确定其适用范围。当超出该范围时,自动调整机制应暂时被其他审慎决策所取代。
1.3 调整频率
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调整频率可以由法规固定下来,也可以由调整机制自动确定,即当触发指标的变化达到一定预期水平时,调整机制自动运行。较低的调整频率会使待遇水平与退休养老的实际需要产生较大差距,这种差距越大,需要较大程度的制度调整或改革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基于小步微调、循序渐进的原则,调整频率不宜较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墨西哥等国家每年调整一次,瑞士则是两年调整一次。
2 养老金待遇调整的动机和方式
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在结构上大同小异,但在触发指标、调整参数选择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主要源于不同的调整动机。概括而言,调整动机主要有以下两点。
2.1 保障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
保障退休金不受通货膨胀侵蚀是待遇调整的最重要目的。通货膨胀会降低养老基金的增值速度,拉高名义工资,增加养老消费支出,致使养老金贬值、替代率降低。应对通胀侵蚀最直接的方式是在自动调整机制中引入物价指数。另外,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生活水平,养老金与工资水平挂钩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这是目前OECD 国家广泛采用的方式,但各个国家具体调整幅度和调整方法略有差异,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直接依据物价指数或工资水平的变化进行待遇调整。挪威养老金待遇的调整是在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基础上减去0.75%。美国通过生活成本的调整(Cost-Of-Living Adjustments,COLA)以确保社会保障和补充社会保障待遇不被通货膨胀侵蚀,COLA 依据劳工部劳动统计局确定的上年度城镇工薪阶层和文职人员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Urban Wage Earners and Clerical Workers,CPI-W)来测算,如果CPI-W 没有增长,该年则没有COLA[4]。斯洛伐克收入关联计划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与平均收入增长和通货膨胀情况挂钩。从2013 年到2017 年,斯洛伐克养老金待遇以固定数额增加,收入增长和通货膨胀在指数化中的比重由2014 年的40 ∶60 逐渐变为2017 年的10 ∶90。2018 年起,养老金待遇变化完全根据消费品价格而定[5]332。其二,利用物价指数或工资水平确定待遇调整的最低或最高限额。西班牙规定每年1 月份按照包含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的一系列重估指数进行调整,养老金待遇最低年增长率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的0.25%,最大值为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值加上0.5%。波兰规定个人账户的名义收益率不能低于通货膨胀率。荷兰的基本养老金则根据最低工资的变化进行调整。其三,从物价指数、工资变化率和其他指标变化率中取最高值进行调整。英国国家养老金待遇每年从工资增长率、物价增长率和2.5%三者中选择最高值进行调整。冰岛则从工资变化率和生活成本指数两者中选择较高者为依据进行待遇调整。
按照物价指数或者工资水平进行待遇调整能够保证养老金购买力。这种调整方式更适宜于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经济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如果物价和工资常年连续大幅增长,则会加剧养老基金的财务压力、有损制度可持续性。因此,需要适当降低这些指标的权重,配以有利于基金收支平衡的指标进行调整,才能更有助于在维护制度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削弱通货膨胀的影响。
2.2 缓解财务收支平衡压力
目前,OECD 国家大都面临人口高抚养比,并且这一比例将持续攀升。2015 年,OECD 国家老年抚养比①此处老年抚养比为65 岁及以上人口占20 至64 岁工作人口的百分比。平均值为27.9%;预计到2025 年,该比例的均值将达到35.2%;2050 年更将高达53.2%,此时,比例最低的以色列也高达32.1%,而意大利、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均超过70%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2017 修订版,http:/ /dx.doi.org/10.1787/888933634306.。随着老年抚养比逐年攀高,养老金系统财务压力加剧,进而危害制度的可持续性,限制相关政策的调整空间。缓解公共养老基金财务压力、实现养老金财务平衡便成为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重要目标之一。由此采取的措施是将反映平均寿命、制度赡养率、养老基金资产负债比率等状况的指标纳入自动调整机制。
近半数的OECD 国家将与寿命相关的指标作为调整参数之一[6],但具体方式有所不同。第一种方式是用平均余命直接计算养老金。挪威在62 ~75 岁之间实行弹性退休制度;退休时,用累计养老金除以平均余命,得到年度养老金。波兰用名义账户的累积资金除以退休时的平均余命来计算养老金。第二种方式是将平均余命纳入包含其他调整参数的“可持续因子”当中。西班牙计划于2019 年在待遇调整中纳入可持续因子,该因子计算了退休年份时67 岁的平均余命相较于五年前67 岁的平均余命的变化。芬兰在达到退休年龄时,依据不分性别的生命表计算并指数化预期寿命,以作为养老金待遇调节的重要参数。瑞典公共养老金初始待遇水平根据账户积累总额除以年金因子,年金因子包含特定人群的平均余命、退休年龄等因素。第三种方式是将预期寿命与缴费挂钩,间接达到调整待遇的目的。法国将最低缴费年限与预期寿命挂钩,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最低缴费年限也逐步增加,以此来保持养老金支付期与工作缴费期比例的稳定。
依据制度赡养率调整待遇水平是指养老待遇依据制度内缴费人口与待遇领取人口的比例进行调节。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退休人口逐步增多,缴费人口持续减少,这会对基金收支平衡造成巨大压力。在纳入制度赡养率的调整参数后,随着制度赡养率的上升,待遇上升趋势将放缓。并且,相较于单纯地依据预期寿命进行待遇调整,考虑了制度赡养率的待遇调整机制更加强调代际责任共担原则。在日本,待遇调整中的修正指数除了退休时的平均余命外,另一重要参数就是公共养老金制度缴费人数下降率。德国待遇调整的可持续因子中也包含了制度赡养率。
如果说将预期寿命和制度赡养率作为自动调整机制的调整参数是通过缓解因预期寿命延迟和缴费人数降低而带来的财务危机,那么将养老金制度的资产负债比率作为待遇调整参数则是更为直接地维持基金财务平衡的方式。瑞典将这种方式运用于名义账户制,当养老金负债增长率高于资产增长率时,便降低积累阶段的名义记账利率和待遇发放阶段的调整指数,以恢复收支平衡。
根据预期寿命、制度赡养率、养老基金资产负债比例进行待遇自动调整无疑会减轻财务压力,增加制度的可持续性。但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制度赡养率的上升会使养老金待遇水平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制度的保障功能。特别是在那些以公共养老金制度为主要支柱的国家和地区,当制度赡养率较高且养老基金资产负债比例较低时,采用这些指标进行待遇自动调整将会极大降低国民的退休收入。
3 OECD典型国家公共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
待遇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也能缓解基金财务压力,增加制度的可持续性。但基于某单一指标的待遇调整机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特定目标的特定方面问题。财务压力和养老金购买力受多种因素影响,且各国面临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因此OECD 国家多综合采用各种指标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待遇调整。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其运行机制,下面重点分析瑞典、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四国的公共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
3.1 瑞典的自动平衡机制
20 世纪90 年代,瑞典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基础养老金(Guarantee benefits),保障最低养老待遇;二是现收现付制的名义账户养老金(Inkomstpension);三是基于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制缴费确定型养老金(Premium Pension)。前者资金来源于税收,后两者的基金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形成,合计缴费比例为工资的18.5%,其中16%进入名义账户,2.5%进入基金积累制账户[7]。
2001 年,瑞典引入自动平衡机制(Automatic Balance Mechanisms,ABMs),通过一整套“评估—触发—调节—再评估”机制来调节名义账户的劳动者养老金待遇。ABMs 使用平衡比率(Balance Ratio,BR)作为触发参数。平衡比率反映了养老基金的资产与负债状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当平衡比率大于或等于1,处于财务平衡状态,养老金待遇依据平均工资增长率(简称“收入指数”)而调整。当平衡比率小于1 时,意味着养老基金负债超过资产,自动平衡机制启动,名义账户的记账利率将被缩减,记账利率变为平衡指数(Balance Index,BI)[8]。BI 的计算公式如下:

BIt是t年的平衡指数,It+i和It+i-1分别是(t+i)年和(t+i-1)年的收入指数,BRt为t年的平衡比率[9]。
瑞典自动平衡机制的建立使得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波动风险在缴费者和领取者之间自动分摊,有利于养老金的长期稳定,但也存在调节幅度波动太大和造成养老金待遇充足性下降的问题[10]。
3.2 德国的可持续因子
德国的养老金制度体系包括强制性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自愿性养老保险。强制性养老保险是德国养老金体系的第一支柱,也是覆盖范围最广、最为重要的养老金计划。强制性养老保险采用现收现付模式,当期企业和个人缴费用于支付当期退休者的养老金。养老金待遇公式为:

Pt,i表示退休者i在第t年的养老金;PVt表示第t年的养老金现值;SYi指退休者i的缴税年限;AFi为调整因子;EPi指i在工作期间积累的收入点数,是个人年度报酬对所有受保人年度平均报酬的倍数[11]。
PVt的大小取决于可持续因子(Sustainability Factor,SF)。PVt和SF 的计算公式为:

PVt表示t年养老金给付现值,Anwt-1和Anwt-2分别表示(t-1)年和(t-2)年的缴费人口平均净工资收入,Pqt-1和Pqt-2分别表示(t-1)年和(t-2)年的养老金待遇领取人口/(缴费人口+失业人口)的值。如果人口老龄化加重,Pqt-1/Pqt-2大于1,养老金给付减少。α是调节缴费者和领取者的责任分配指数,固定为0.25。如果α=0,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所有压力落在缴费人口身上;如果α=1,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所有压力落在领取人口身上[9]。
德国养老金的待遇调整与平均工资、制度赡养率的变动和责任分配系数相关,能够根据经济状况和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制度赡养率的提高及时调节养老金待遇水平。责任分配指数的引入有助于在保证养老金替代率维持一定水平的前提下,不至于使缴费率有过快增长的压力。
3.3 日本的“宏观经济指数”
日本的公共养老金为现收现付的待遇确定型,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收入关联养老金两部分组成。2004 年的日本养老金改革引入“宏观经济指数”(Macro Index),建立自动调节机制,根据缴费人数和预期寿命调节养老金待遇。养老金待遇变化率的计算公式为:

ΔP(t)是t年养老金的变化率,ΔW(t)指t年在职职工工资的变化率,ΔL(t)指t年缴费人数的变化率,μ是预期寿命的变化率。t*是通过计算得出的养老金达到可持续标准的年份。在养老金达到长期可持续发展水平前(t≤t*),根据工资、缴费人数和预期寿命的变化调整养老金待遇;在达到长期可持续发展水平后(t>t*),根据工资变化率调整养老金待遇[12]。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缴费人数将不断减少,而预期寿命的延长也会增加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限。受此影响,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运行可能使未来养老金的支付水平持续下降。为防止自动调节后的养老金替代率过低,日本设置了最低养老待遇水平,即在下一个精算评估前,如果替代率跌破50%,将停止使用宏观经济指数进行修正。另外,如处于通缩期间,宏观经济指数也暂停运行。
3.4 西班牙的自动调整机制
2013 年,西班牙专家委员会结合德国和瑞典的自动调整机制应用经验,提出在西班牙建立可持续因子(Factor de sostenibilidad,FS)和新的自动平衡机制(índice de revalorización,IR)。
西班牙将可持续因子作为一个乘数项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待遇计算公式中。该因子将初始养老金待遇与退休时的平均余命关联起来,t年的可持续因子可表示为:

自动平衡机制则将养老金待遇指数调整与养老基金财务状况联系起来,而不再与通货膨胀关联。养老金待遇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

是养老金领取者数量的增长率,是由于新老更替导致的平均养老金待遇的增长率,是缴费的增长率,It和Gt分别为养老金总收入和总支出[13]。
为解决调整幅度波动过大问题,该调整机制通过三种方式对待遇调整幅度进行平滑处理:一是使用所有增长率的11 年移动平均值;二是使用It/Gt的11 年几何平均值;三是只修正养老金总收支不平衡规模的一部分,一般为1/3 ~1/4。同时,西班牙设置了养老金待遇调整的上下限,2013 年确定的养老金待遇名义增长率不得低于0.25%,不得高于0.5%。平滑调整和调整幅度的限制是对瑞典ABMs 的改进,能够减少待遇波动和缓解养老基金的充足性问题[13]。
4 OECD国家公共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经验
4.1 设置最低待遇标准,保障基本生活水平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趋势下,纳入预期余命、制度抚养比、养老基金资产负债比等因素的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有助于缓解由预期寿命延长和待遇领取人口比例过高引致的财务收支平衡压力;但这也会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削弱养老金保障老年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为实现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基本目的,保障老年基本生活水平,一些OECD 国家设置了养老金最低待遇标准。最低待遇标准的设置方式可概括为两类:一是直接对养老金的增长率设置下限。如西班牙设置了养老金的最低名义增长率,以保障养老金水平。二是依据能反映养老金实际购买力的相关指标确定最低待遇标准,包括反映通货膨胀情况、工资水平以及维持生计水平的相关指标。墨西哥享受最低养老金需要满足缴费年限等标准,其具体水平每年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进行调整。日本按照替代率的50%来确定最低待遇保障。2017 年希腊的最低养老金在平均工资的20%以上[3]25。斯洛伐克规定,自2015 年起凡是满足一定条件退休人员可以享受最低养老金待遇;其标准的计算与维持生计水平相联系,且对全职工作人员和自雇职员采用不同的标准[14]240。
4.2 注重制度的可持续性
受经济发展放缓和养老金待遇福利刚性的影响,各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压力加大。设置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缓解养老基金财务平衡压力。在该动机下,将可持续因子纳入养老待遇计算公式是近年来公共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因子包含对养老基金收支情况、制度抚养比状况和人均寿命延长等方面的考量;引入可持续因子的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将弱化这些变化对养老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有利于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瑞典依据养老金制度的资产负债比率的变化改变名义账户的记账利率,当资产负债比率小于1 时,记账利率由收入指数改为具有缩减效应的平衡指数。德国的可持续因子直接纳入制度赡养率,根据制度内待遇领取人口与缴费人口的变化进行财务平衡的调节。日本、挪威、波兰、西班牙则根据预期寿命的延长适当调节养老金待遇,以缓解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期与待遇享受期的比例变化带来的财务压力。
4.3 平滑调整幅度
相较于待遇临时无规则调整和养老金制度整体性改革,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优势之一是小步微调。频率较高的小步微调有助于减少养老金待遇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性,减少对制度大幅调整的需要,降低制度变革成本。但在一般的待遇自动调整机制运行下,仍然存在待遇较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波动较大情况下,引入宏观经济指标或与宏观经济状况关联度较高的指标的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可能引致养老金待遇调整幅度过大。因此,一些国家在待遇自动调整机制中对养老金待遇的波动进行平滑处理。平滑处理的方式通常是取较长时期内相关调整参数的平均值,以减轻由调整参数在某一段时间内剧烈起伏引致的养老金待遇大幅波动。例如西班牙的可持续因子中余命的计算以5 年为周期进行平滑处理,自动平衡机制中的增长率采用11 年的移动平均值[13]。
4.4 确立调整机制的适用范围
尽管平滑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缓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引致的养老金待遇大幅波动,但当自动调整机制的调整参数处于极度不合理变化水平时或者养老金计划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时,自动调整机制的运行将有损制度的稳定性。如前所述,养老金待遇下降幅度过大会削弱保障水平,降低参保人对制度的信任,因此一些OECD 国家设立了最低待遇标准。此外,设置待遇调整的上限同样十分重要,与物价或通胀挂钩的待遇调整机制在极端情况下会急速拉升养老金支出水平,造成养老基金收不抵支,损害制度可持续性。为此,部分OECD 国家设置了养老金待遇调整的上限。上限设置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限定养老金的增长率,如西班牙规定了养老金待遇名义增长率的最大值;另一种是依据工资水平等指标确定,如土耳其规定了养老金替代率的上限。
4.5 待遇调整机制的设计依国情而定
由于各国的经济、人口结构、养老基金等状况差异较大,OECD 国家的待遇调整机制设计不尽相同,其待遇调整机制的目标各有侧重。因此,在调整参数的选取与待遇计算公式的构建上呈现出较大差异。德国调整参数包括制度赡养率,日本纳入缴费人数。将制度内人口因素纳入是因为两国都面临着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2015 年,德国老年抚养比①此处老年抚养比为65 岁及以上人口占20 至64 岁工作人口的百分比。为40.9%,日本则高达45.6%,皆位居OECD 国家前列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2017 修订版,http:/ /dx.doi.org/10.1787/888933634306.。此外,德国在待遇调整公式中纳入责任分配指数,强化其现收现付制的代际分配功能。相较于德国,日本经济发展势头较弱,因此,日本在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设计中,计算出养老基金达到可持续标准的年份,以此确定待遇调整方式。瑞典、西班牙、挪威等人均预期寿命较高的国家也都将预期寿命作为调整参数纳入待遇自动调整机制中,以应对本国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引致的养老基金财务风险。
5 对我国的启示
为保障养老金购买力,增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使参保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2018 年1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出要建立激励约束有效、筹资权责清晰、保障水平适度的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在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本文就完善和优化基本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提出如下政策思路。
5.1 建立最低待遇标准机制,保障基本生活水平
我国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基本目的就是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调整要体现保险的互济性与保基本的功能目标[15],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预期寿命逐步延长的情况下,引入预期寿命、制度抚养比等调整参数的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可能会导致养老金待遇的下降。如果下降幅度过大,不仅难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还有损民众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因此,需设置最低待遇标准机制,确定最低养老金待遇。当在自动调整机制运行下的养老金待遇低于最低待遇标准时,采用最低待遇标准。这样做不仅是保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目标的需要,也有助于体现政府的养老责任。可借鉴日本按照养老金替代率的一定比例来设置标准,亦可通过计算当期生活成本或相关综合指标来确定最低养老金待遇。
5.2 引入财务可持续性指标
受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影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抚养比持续攀升;加之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养老金待遇领取期的增长,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断攀升,财务平衡压力巨大[16],制度运行面临长寿风险和持续发展风险。当前,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以增强激励性为导向,较之OECD 国家,缺乏对养老保险基金长期财务可持续性的考虑。待遇机制的设定较少考虑长寿风险及其影响,原有的精算平衡对长寿风险估计也相当保守[17]。我国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需要立足当前,也需要兼顾长远发展。逐步纳入有助于基金平衡的可持续性因子或相关调整参数,以强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具体而言,可以在挂钩调整中引入预期寿命、长寿风险、制度抚养比、退休年龄、基金偿付能力等调整参数。配合实施兼顾预期寿命、缴费年限为基础的弹性退休制度,将极大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抵御长寿风险的能力,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18]136。另外,可以考虑调整与上年度养老金水平挂钩的办法,采取与平均工资水平或者物价指数挂钩方式。与上年度养老金水平挂钩尽管能够体现其保障养老金购买力、防止通货膨胀的目的,但待遇调整机制在该情况下纳入预期寿命、缴费年限等参数后,会具有很强的福利刚性。强调与平均工资水平或者物价指数挂钩,不仅有利于保障养老金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还使待遇调整机制的福利刚性相对较弱,更具弹性。
5.3 明确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适用范围
当引入工资水平、物价水平、预期寿命、长寿风险、养老金制度财务收支状况等调整参数后,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还需明确适用范围。调整参数本身可能在某一时期会处于不合理水平,此时待遇调整机制的运行会使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不确定性。并且,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调整频率通常较高,未考虑长期状况的调整参数反映的是短期变化,这意味着待遇自动调整具有“短视”的缺陷。调整参数短期内的大起大落会导致待遇的大幅升降,从而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稳定性。需要明确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适用范围。当超出这一范围时,调整机制停止运行,再进行审慎决策。在确定适用范围时,应根据待遇调整机制所纳入调整参数的合理变动范围、制度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要求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的适宜替代率水平综合考量。
5.4 同步但差异化“城职保”与“城居保”的待遇调整机制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种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简称“城职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到这种制度差异。尽管《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但国家层面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过去三年未作调整,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居保”的建立到两大制度的整合及发展过程中,基础养老金仅在2014 年调整过一次;而“城职保”则每年都调整。两种制度待遇调整的不同步进一步拉大了职工与居民养老待遇差异,有损制度公平性。因此,需要积极探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调整的新机制,以减少物价波动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者实际生活水平的不利影响,使农村老年人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由于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差异,需在最低待遇水平确定、调整参数选取等方面采用不同指标,在保证制度稳定性情况下满足不同居民生活水平的需要。
5.5 优化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
多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调节都是由中央政府依据调整原则,确定大体调整水平;各地依据自身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实际状况出台具体调整办法,确定具体调整幅度。各地高低不同的调整幅度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有其合理性,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进一步优化。无论确定什么样的调整比例,都需要强调调整的科学依据,强调优化机制对提升养老金调节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作用。定期量化通货膨胀和物价波动对养老金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优化现有的养老金指数调节机制,妥善处理价格、工资与养老金之间的联动关系,尽最大可能维持养老金实际购买力,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经济生活[19]。积极探索制定加大对生活困难城乡居民缴费补贴力度的相关办法。同时,应进一步优化调整比例的制定依据和测算公式,增加透明度,使人们有清晰、稳定安全预期,化解社会公众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不信任[20]。
5.6 完善基本养老基金预算管理
完善基本养老基金预算管理是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基础。目前,我国基本养老基金的预算管理还有待完善,各地区预算编制不规范,执行约束力较差。需要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能力,建立起科学有效的预算管理体制和养老金精算管理与审计披露制度,强化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的精算平衡能力和制度运行的风险预警能力。只有在科学有效的基金预算基础上设置适宜的养老金自动调整机制的触发条件,才能更好发挥自动调整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