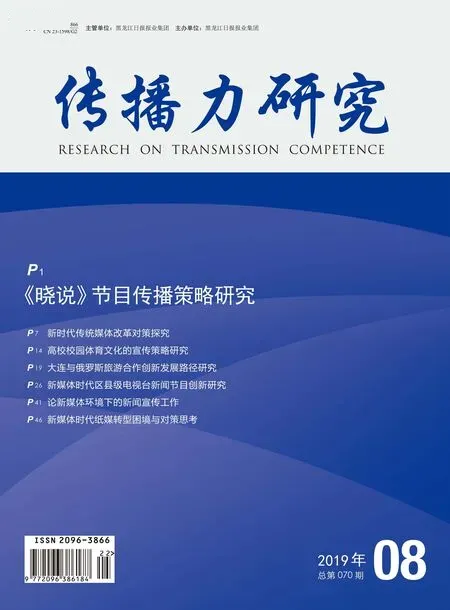新媒体对科技传播的影响研究
赵昂 工人日报社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受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这样的改变也影响到了科技信息的传播效果。
科技知识的复杂性,加之目标受众群体学历、学科背景不同,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在相应学科方面充足的科学知识,使得在科技传播过程中,过去“教科书式”纯文字的表述方式,以及传统的示意图方式,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甚至会带来反效果,让受众对科技知识和信息产生畏难情绪,让普通受众感觉,科技知识和信息距离自己越来越远。正因如此,如何利用新媒体,做好科技传播工作,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科技传播的难度和必要性
进入21世纪后,科技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科技知识数量增加,难度也在增大,这就使得科技知识的传播效果受到影响。
一方面,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养者比例较低,使得大部分媒介受众对于较复杂科学知识的理解有难度,根据中国科协公布的第10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8.47%,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结果也显示,2017年6岁以上人口中具备大专以上文凭者仅为13.87%。另一方面,由于新闻工作者中,文科专业背景者占比例较大,理工专业背景从业者较少,使得部分新闻工作者对复杂自然科学知识的科学表述能力有限,对于专业名词的解释仅能复制粘贴百科内容,难以润色,影响到了传播效果。
二、新媒体提升科技传播效果
将复杂科学知识以图像、声音、视频等形式阐释,可以有效提高传播效果,在这一点上,新媒体工具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仅以短视频为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科学报社与字节跳动联合发布《知识的普惠——短视频与知识传播研究报告》显示,短视频打破了知识在传播和接收中存在的固有壁垒,以社交为纽带进行知识共享,将个体学习转化为大众分享和参与,让知识可以触达更多的人。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短视频降低了知识接受的门槛,拉近了知识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普通群众能够通过短视频,以新奇、有趣的形式接触到高深的专业知识。
以地图学中的墨卡托投影原理为例,一般受众只看纸上的普通地图,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各国国土面积实际大小,和世界地图上画出来的不一样,但在短视频中,制作者将格陵兰岛的轮廓直接拉到巴西上,效果一目了然。与此同时,新媒体表现方式的趣味性,也能增加受众对科技信息的兴趣。
三、人人都能成为科技传播者
由于新媒体信息发布门槛较低,使得个人也能成为科技信息的传播者。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自身,也能在网上发布信息,与此同时,科普爱好者也能通过微博、微信、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发声,进行科普。
短视频平台快手与中国科普所联合研究项目发现,2018年快手平台上的科普内容已超过360万条短视频,并获得80亿次播放和150亿次点赞。这些短视频,绝大部分来自个人,其中既包括科技工作者,也包括科技爱好者。这些短视频制作者的资源不及科普机构,也使得其素材大多因地制宜,比如黑龙江鹤岗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王野虓,在拥有16万粉丝的“水果医生”快手号上,通过给水果“做手术”,向不了解临床医学知识的普通受众传播基本医疗知识,比如“腹腔取物”就是从给车厘子“做手术”的视频来展示的。
大量由个人发布的科技知识和信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受众并不了解相关科学知识,对于个人科普的真伪难以辨别,监管机构也无法查证每一条信息的来源以及准确性。
四、新媒体影响下科技传播的未来
尽管科技机构、科技工作者和新闻媒体,都可以利用新媒体进行科技传播,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最重要的科普阵地,依然是校园本身。教育机构有必要利用新媒体工具,向学生进行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科技知识传播。
随着教育改革深入,80后、90后乃至00后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在提升,整体科学素养也在提升。科技谣言的传播受众,大多集中于中老年人,特别是通过社交平台上的文章进行传播,标题危言耸听,内容环环相扣,没有受过严格科学训练且具备一定自然科学素养者难辨真假,科技机构和媒体应当学会使用新媒体手段和新媒体语言,并提升工作人员的科学素养,以通过新媒体手段,传递准确的科学知识和信息,并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我国科学进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