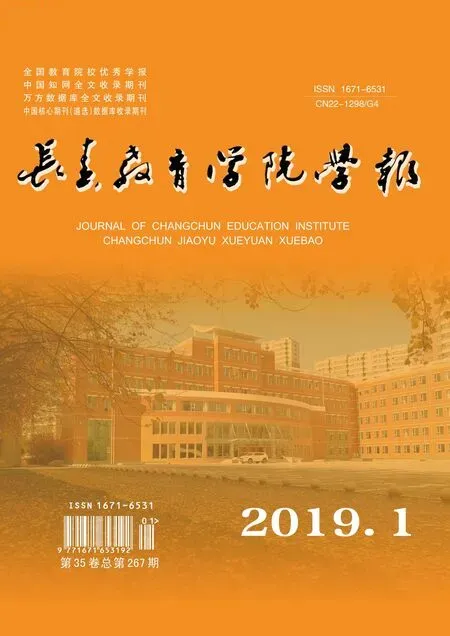他者评论因素对文学重译的影响
——以刘重德三译《爱玛》为例
刘婷婷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学翻译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出现重译本。如简·奥斯汀的作品《爱玛》,虽并未及奥斯汀另一部作品《傲慢与偏见》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但却被认为是其艺术的巅峰之作。自传入中国以来,《爱玛》已经出现了很多汉译本,如刘重德、张经浩、孙致礼、祝庆英、祝文光等都曾经对其进行过翻译,其中刘重德先生于1944年始译,并由重庆正风出版社于1949年出版的是《爱玛》汉语首译本;1981年刘老对该译本略加修订并于1982年由广西漓江出版社再版;此后,1993年,刘老又对其进行了重译,由广东花城出版社第三次出版。《爱玛》是世界文坛的瑰宝,刘重德先生翻译该书经历了翻译——修订——重译的复杂过程,那么促使其重译的动因是什么呢?
一、重译动因研究综述
古往今来,重译现象普遍,国内关于其动因研究方面的成果颇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现代新闻记者、出版家邹韬奋[1]指出,重译属“不经济”的行为,认为重译既浪费人力又浪费出版资源,并主张译者去翻译从未被译过的作品。针对该观点,其他学者相继展开反驳,提出重译是必须的。如鲁迅[2]认为,对于译界中存在的胡译乱译现象,唯一的好方法就是进行重译;且即便有了好译本,重译也是必要的;文言译本经过重译,改为白话译本;有了白话译本的,也可以重译出更好的译本。梁实秋[3]也对重译予以肯定,提出“有翻译价值的书,正无妨重译。有了很多的译本,译者才不敢草率从事”。此后,对于文学译作有否定本,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定本,即最完美的、无需再修改且适应各个时代需求的译本。方平[4]和许钧[5]都指出翻译不可能有定本,肯定了文学作品总是需要经过多次重新翻译,才能获得更好的译本。罗新璋[6]最初坚持从以往实践来看,翻译完全可能有定本,不过,谢天振[7]于1996年明确提出“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的看法时,说明了其看法文章是与罗新璋两人讨论之后的结果。叶君健[8]并未站队一方,他认为任何译者都不能称自己的译本是定本,不过译作中的“精品”确实存在。郑诗鼎[9]将重译原因归为四点:译者对原著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有比旧译更理想、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出现新的翻译方法以及为适应译语读者期待。罗蓉蓉[10]与陈爱华[11]两人同时从重译出版角度出发,就重译现象的实际情况,指出其是现代图书编辑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的重新阐释,是对传统重译现象研究的一种继承。
现阶段重译动因研究多由西方理论指导,属跨学科研究。如,谭秀梅[12]运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重译本展开描述性研究,分别从历时与共时两个角度对重译本和旧译本之间的关联展开细致分析;陆颖[13]则借助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对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飘》的重译展开了分析;并于2014[14]年从文化角度出发,研究社会文化语境转变与译者主体成长对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的动机、目标和过程的影响作用。
纵观国内重译动因研究,主要涉及的动因包括:旧译本特质,旧译不完善,为了不对追求完美的译本;适应译语文化语境;译者个人成长等。那么是否存在其他动因呢?本文将以刘重德三译《爱玛》为例,探究主流动因之外的他者评论隐喻对于文学重译的影响。
二、他者评论因素与重译
1989年,刘重德[15]在《译诗问题初探》一文中讲了一个小故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收到一个未曾谋面的青年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附有青年自己的文章。文章主题是关于文学翻译的,青年谈及Fletcher翻译的《春怨》中一些不当之处。刘重德先生对这篇文章评价很高,同时也肯定了其对《春怨》翻译的看法。
笔者之所以将这个小故事置于此处,即是想要说明刘重德先生珍视评论意见,无论意见出自何人,他乐于仔细分析,并表明自己的看法。正如他[16]在谈及外国文学翻译和外国文学翻译评论关系时指出的,翻译是评论的依据,评论则对外国文学翻译起着净化和提高的作用。对于重译,刘老在1993年《爱玛》重译本自序中表明,其重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多方学者评论,诸如李德荣、翁凤翔及宋淇等人评论的影响。他们均通过对比刘老1949年或1982年译本与他人译本,在指出刘老译本优点的同时,也对其中的不当之处进行了说明。
李德荣发表于1987年的文章《〈爱玛〉两种译本比较》首段,有评价简·奥斯汀及《爱玛》的文字。他认为女作家简·奥斯汀在英国文学界独树一帜,在中国亦是广为人知。她创作的《傲慢与偏见》《爱玛》《理智与情感》等作品作为英国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在世界范围内为读者们喜爱,盛名不衰。翻译这样一位名家的作品是非常有意义的,又极富挑战性。[17]从最后一句总结不难看出,李德荣对《爱玛》的译者们既有肯定也存在担忧。他对比了刘重德1982年《爱玛》译本与张经浩1984年的译本,认为“刘译许多地方,不仅译得忠实流畅,且与原文辞气相符,风格相近。不过,又觉得两种译本在不同程度上均存在一些问题”。他指出:“刘译比较倾向于直译,译文风格与原作比较接近……存在一些理解错误……不要把直译当作译文可以生硬造作的理由。”尽管刘重德在重译本自序中提及自己在翻译《爱玛》时并未特意采取何种翻译方法,不过译本中有些重译确实受到了李德荣建议的影响。
1991,翁凤翔在硕士毕业论文《功能对等与小说翻译——<爱玛>的两种中译本比较研究》中,比较了张经浩《爱玛》译本与刘重德《爱玛》译本。论文[18]中提到:由于直译,刘教授译本的显著特点是成功地传达了原文结构上的美;同时,由于太重视原文结构与字面意义,就难免出现“搭配不当”“有欠通顺”的情况;但是,尽管出现了一些错误,但仍然掩盖不了译本的优良品质。
刘重德教授翻译实践经验丰富,又对翻译理论相关研究成熟,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时已经提出“信达切”新三字原则、翻译过多本外国文学名著的人,在1993年重译《爱玛》时,确实受到翁凤翔这位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论文的影响,并接受了他的相关意见。在1993年重译本自序中,刘教授提到作出了怎样的改变,他说:“对于那些过于直译,有欠通顺的词句,或重新措辞,或重新组织,使它们比较容易上口和理解。”[19]可以看出刘重德先生严谨治学的翻译之德、翻译之风以及对待翻译评论的那种“闻过而喜”之态。
香港著名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宋淇,在《为珍·奥斯汀叫屈:谈改译与抄译》一文中,对刘重德1949年《爱玛》译本与夏颖慧1988年译本进行了比较。虽然,此文的重点在于指出后者对刘老译本不正当的抄译与改译行为,但其中不乏对刘老译本的得失评论之处。通过译例分析,宋淇提出了他对《爱玛》译本的两点意见。首先,关于翻译单位问题,他指出翻译单位应该是整句,甚至是整节,反驳了以字词为翻译单位的观点;同时,以整句为翻译单位,指的是译者将句子“消化、分析、拆开,最后再把各成分融合在一起的翻译过程,甚至有时候为符合汉语语法习惯而颠倒词句的顺序也是必要的。[20]其次,他还指出刘老1949年的译本存在未脱离对词和词典的依赖问题。对于翻译工作者应如何利用词典这一辅助工具,他认为学界谴责的是一味查字典进行翻译,盲目拿来词典义的行为;而翻译工作本身并非完全不能查词典,因为有些词语属一词多义或者说意义过于偏僻古旧,就必须仔细翻阅词典,结合上下文语境,进而选择最恰当的词义进行转换。[20]
刘重德在其1993年《爱玛》重译本自序的结尾处说:“认真考虑了李德荣、翁凤翔以及宋淇等同行的宝贵意见。”[19]通过上文可知,三位学者指出的刘重德旧译本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可归结为:理解错误;过于直译造成的搭配不当、有欠通顺;未注意翻译单位问题;未能够灵活运用词典。笔者将结合刘重德译本中的具体译例来观察上述评论意见是如何影响译者重译的。
例1 She was the youngest of the two daughters of a most affectionate,indulgent father,and had,in consequence of her sister’s marriage,been mistress of his house from a very early period.Her mother had died too long ago...and her place had been supplied by an excellent woman asgoverness...[21]
1949年译文:她是一位最娇爱的父亲所有两女儿最小的一个,而且,由于姐姐出嫁,她很早就做家里的女主人了。她母亲去世太早了……而且母亲的地位也早已为一位作家庭教师的杰出女子所代替了……[22]
1982年译文:她是她父亲最娇爱的两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由于姐姐出嫁,很早便当了家里的女主人。母亲去世过早……而且母亲的地位也早由一个杰出的妇女——家庭教师填补了起来……[23]
1993年译文:父亲最疼爱两个女儿,由于姐姐出嫁,她这个小妹很早就当了家。母亲去世过早……而且母亲的地位也早已由一个优秀家庭教师取代……[19]
简·奥斯汀自19世纪初期成名,但其作品的文字语言等却仍是18世纪的英语书写特点。该节选的首句中,首先,“the youngest of the two daughters”在18世纪的英国是很常见的说法。在两个旧译本中,刘重德先生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分别将其译为“所有两女儿最小的一个”和“两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正如宋淇所述,“读起来绕口,不像中国话”[20],不符合汉语习惯。通常“最小的”中的“最”多指三者以上之一。而原文中爱玛只有一个姐姐,因此,旧译并不恰当。其次,对于后半句中的“mistress”,刘老1949年译本将其译为“女主人”,1982年译本保留了这一翻译,颇像是过于欧化的汉语表达,1993年重译本中将其译为汉语日常用语“当了家”。最后,两个旧译本对首句的翻译十分相似,且都保留了原文的词序结构。正如宋淇所述,是以词为翻译单位。1993年重译本则进行了较大的改变,结合下文以整句为单位,同时采取意译法进行了重组,将“the youngest”与“been mistress of the house”合并翻译,译为“她这个小妹很早就当了家”,不仅是地道的中文表达,且用词更为经济,为佳译。第二句较长,重译本做出较大改变之处在于后半部分“her place had been supplied by an excellent woman asgoverness”的翻译。旧译本遵循原文语法结构,将“by an excellent woman asgoverness”分别译为“做家庭教师的杰出女子”和“一位杰出的妇女——家庭教师”,而重译本则将其译为一个“形容词+名词”的结构,即“优秀的家庭教师”,十分简洁。此处,关于“excellent”的汉译,据宋淇分析,当人们听到“杰出女子”或者“杰出妇女”时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女英雄,或是某个领域内做出突出贡献的女性,这里用来形容一位家庭教师似乎并不恰当,相较而言,他认为“优秀”更加合适。我们可以看出,刘老在重译本中确实接受了他的评论意见,采用了这一译法。
例2 Sorrow came—a gentle sorrow—but not at all in the shape of any disagreeable consciousness.—Miss Taylor married.It was Miss Taylor’s loss which first brought grief.It was on the wedding-day of this beloved friend that Emma first sat in mournful thought of any continuance.The wedding over...her father and herself were left to dine together,with no prospect of a third person to cheer a long evening.Her father composed himself to sleep after dinner,asusual.[21]
1949年译文:悲愁来临——一种缓和的悲愁——但并非以任何使人觉得可憎的形式而出现的。泰勒小姐结婚了。第一次带来了悲伤的是泰勒小姐的离去。那是在这位爱友结婚的一天爱玛才第一次的愁坐终日。婚礼完毕……只剩她父亲跟她两个人来一块吃饭了,一个第三者来助一个漫长黄昏的兴是没有希望了。晚饭后她父亲照旧的静息入睡。[22]
1982年译文:悲愁,一种不太厉害的悲愁,终于来临了。但并不是以任何令人觉得可憎的形式出现的。泰勒小姐出嫁了。正是泰勒小姐的离去才第一次带来了哀伤。也正是在这位爱友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爱玛才愁坐终日。婚礼完毕……就只剩下她和父亲一道吃饭,不能指望再有一个人来共同欢度这漫长的夜晚。饭后,父亲照常安静入睡。[23]
1993年译文:悲愁,一种淡淡的悲愁,终于来临了,但并不是以任何令人觉得不快的形式出现的。泰勒小姐出嫁了。正是泰勒小姐的离去才第一次带来了不幸。也正是这位密友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爱玛才第一次独坐良久,愁思绵绵。婚礼完毕……就只剩下她和父亲一道吃饭,不能指望再有一个人来共同消遣这漫长的夜晚。饭后,父亲照常安静下来去打盹儿。[19]
该段同样节选自第一章,李德荣与宋淇均对此段的翻译进行了讨论。首句,从结构与形式来看,原文中的破折号在后两个译本中删去了,同时,将1949年译本中的句号变成了逗号,并按照原文的形式,将其合并为一个句子。从内容来看,两个旧译本将“a gentle sorrow”分别译为“一种缓和的悲愁”和“一种不太厉害的悲愁”,这两个翻译均是过于欧化的表达方式,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宋淇提到“淡淡的哀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颇为常见的一种表达方法,用在此处十分恰当,尤其能够传达原文意义。再看重译本,刘老确实采用了宋淇的意见,将该段语译为“淡淡的哀愁”。旧译本中对后半句中“disagreeable”的翻译则显得有些过分,均将其译为“可憎的”。汉语中,“可憎的”蕴含着强烈愤怒的情感色彩,用在此处不当,毕竟原文场景是泰勒小姐的婚礼,是非常开心的喜事。此处,用“disagreeable”只是为了表达爱玛因为泰勒小姐即将离开他们,无法每日常伴而感到伤心不快而已。因此,重译本才将其译为“令人觉得不快的”。第四句中的“the beloved friend”,两个旧译本均译为“爱友”。宋淇认为,刘老此译法是硬搬词典义的行为。“beloved”有“dearly loved”之意,英语尚可如此使用;然而,在中文中,表达朋友之间关系亲密的有如“契友”“挚友”或“密友”,但通常不会使用“爱友”这种表达方式。刘老两个旧译本均将第三句中“sat in a mournful thought of any continuance”译为四字结构“愁坐终日”,而李德荣与宋淇对此有不同看法。宋淇认为“愁坐终日”非常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而李德荣则认为此处译文存在过分之嫌。爱玛这天是去参加泰勒小姐的婚礼,因此完全不至于会愁坐终日。同时,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试译,即“独坐良久,愁思绵绵”。刘老重译本采用了此译。“...a third person to cheer a long evening”,两个旧译分别是“一个第三者来助一个漫长黄昏的兴”及“有一个人来共同欢度这漫长的夜晚”;宋淇认为“助兴”一词很好,但译本中将两字分开太远;而1982年译本中的“欢度”,宋淇认为属过度翻译,他提议改用“打发”一词来翻译原文中的“cheer”。刘老重译为“有一个人来共同消遣这漫长的夜晚”。最后,“her father composed himself to sleep after dinner,asusual”,李德荣虽未具体指出此处译文错误,但指出旧译本中有些地方存在理解错误;而宋淇则认为刘老此处完全是理解错误。两旧译形式上忠实于原文表层内容,但实则表达的都是“父亲饭后去睡觉了”,然而,原意并非如此。对此,宋淇[20]指出了几点原因,第一,阅读原文全文可知,伍德豪斯家每天是两餐(上午10点及下午4点),尽管伍德豪斯先生是位老人,却也不至于睡觉那么早。第二,正如奥斯汀其他作品,小说中的家庭在晚餐之后会有一个茶会。而这也是伍德豪斯先生的第三餐,更不至于当时就去睡觉了。据此,他给出了自己的试译,“他收拾一下,照常舒舒服服地自顾自打一个盹”。刘重德1993年重译本将该句重译为“父亲照常安静下来去打盹儿”,总体上参照了宋淇的意见,且与其试译相比,刘老的译本更加简洁经济。
刘重德旧译本出版之后,许多学者进行比较研究,因刘老在其重译本自序中未提及其他意见,笔者此处仅从李德荣、翁凤翔和宋淇三人对刘老旧译本的评论出发,结合译本中具体实例展开了分析。这同时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在阅读刘重德1993年《爱玛》重译本自序时,笔者发现,其中提及重译受到了他者评论影响的文字;而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至今未有从他者评论因素分析重译动因的研究。正如刘重德对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与翻译关系的论述,翻译评论于翻译而言尤为重要,能够敦促约束译者,促进翻译质量的提升。重译也是翻译,他者评论因素对重译影响深远。因此,对于译者而言,若要使翻译受到更多关注,更好地完成翻译工作,就需多加注重翻译评论,注重他者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