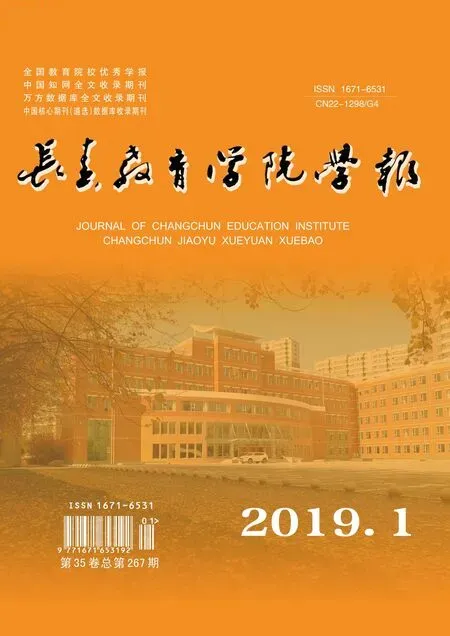不可能的爱情
——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观”解读《情人》
冯 霞
《情人》是法国当代最负国际知名度的女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小说为她赢得了国内国际声誉,并获得当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为法国新小说的集大成者与创始人之一,这部小说则是其新小说的扛鼎之作。它打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诸多创新手法在当时令文艺界耳目一新,并为后来者所效仿。首先她以第一人称咏叹式的叙述为主,间或以他者自居。时而似在旁观,时而似在自省,让读者如临其境又很难辨识作者是在讲述自己还是杜撰。其次,她打破小说叙事的时空概念,顺叙、插叙和倒叙交错并用,信息流在过去与现在的隧道里自由穿梭,意识转化成梦语般的文字被碎片化记录。再则,故事情节随着时空顺序的转移而转换,小说回忆了15岁那年,女主人公在原法属殖民地越南西贡的成长经历。她以碎片化的语言,跳跃式的主题切换,时而讲述她的家庭和家人,时而讲述她的学习,时而讲述她的心路历程,时而讲述她的爱情故事。但这看似松散的情节背后仍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她的初恋,抑或早恋。这段恋情是起于15岁那年,她在码头邂逅一位三十几岁的中国富家子弟,由此展开的一段性爱、伦理与金钱交织的不伦之恋。杜拉斯轻描淡写的语言背后实则暗藏对这段绝望爱情的追忆和惋惜,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情人》是杜拉斯在中国拥有最多读者和研究者的作品,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学者们多对作品进行历时性分析或就小说的某一主题展开研究,诸如女权主义、新小说等,鲜有人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小说的爱情主题进行剖析。本文拟运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二元对立”观对该小说进行解读,以求窥探这段爱情注定不可能的深层原因,从而领略小说的文学价值。
一、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于20世纪初,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认知观的影响,伴随结构主义运动而诞生。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本身即存在多个理论体系,如共时/历时、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句段关系/联想关系等,故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也无唯一标准,从不同视角去透视文学作品,则会出现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但它们均是在结构主义框架下探究文学文本,必然有其共性。根据不同文学批评观的特征,再结合结构主义的特征,可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概括为: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为理论基础,以文本本身的内在结构为研究对象,以共时为主兼顾历时性研究的文学研究方法(李广仓,2006,p.121)。形式研究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一大特色,它为文学研究开创了一条新道路,“使文学研究具有了所谓的“文学的科学”之特性”。(李广仓,2006,p.175)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运动发展达到顶峰,涌现出大批结构主义思想家,诸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等等,他们通过结构主义的理论,对各自从事的领域重新予以定义和解读,为人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结构主义公认的集大成者首推列维·斯特劳斯,这位人类学家用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观探究神话学的方法不仅颠覆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也使文论家大受启发,将其广泛用于文本结构分析,用以解读文本意义、主旨和深层内涵,为文学批评开辟了新天地。
二、“二元对立”模式对揭示文本深层意义的影响
“二元对立”的思维是人类最基本最简单的结构思维。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认为:“在二项对立的所有过程里,对立成员必然在我们头脑里,我们利用双方进行比较,比方说,判断大的就不能不考虑小的概念。没有贵的意义,贱的意义就不可思议,二项对立的价值就在于此。”(罗曼·雅各布森,2001年,p.287)“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是“当研究对象被分解为一些结构的成分后,研究者就可以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相互联系的排列、转换等关系,而这些关系或结构又总是体现为两事物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形成区别和对比,从而产生另一层次上的各自的意义,研究者因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对象结构的复杂性”。这一思想在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先生(Ferdinand de Saussure)研究语言系统时已经使用过,我们上文提及的结构语言学的重要概念均是以二项对立模式呈现的,如能指/所指,语言/言语等。而后,列维·斯特劳斯将这一模式用于解读神话,并将其发挥到极致。比如他认为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野性思维与经文化塑造后的逻辑思维,野性思维/逻辑思维就是一种二元对立关系。结构主义文论家也将这一模式用于解读文学文本,其主要代表为罗兰·巴特,他认为“通过找出文本中其他的对立双方以及分析这些对立双方是怎样相关的,结构主义学家就能解构文本并解释其意义”。[1]他运用二元对立结构分析拉辛剧本中悲剧人物的复杂性,从而摆脱了拘泥于作家与作品关系的外在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情人》这部小说也是利用一系列的冲突,即“二元对立”,将作品的主题慢慢展开并进行深化,从而让读者感受到这段恋情的绝望。笔者将对小说中影响这一爱情悲剧的几组二元对立关系分别予以阐释。
(一)二元对立冲突让情人关系得以建立和维系
1.高贵与卑微的二元对立。小说中的“我”是生活在印度支那的白人,家庭虽然穷困潦倒,但硬撑着也要雇佣当地人干活;“我”每次往返学校与家之间,母亲都会找专车接送,并嘱咐师傅保护“我”的安全。这是因为在殖民地的种族等级里,白人血统比当地黄种人更高贵,殖民者比被殖民者高一等。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哪怕遭遇生活的磨难也不曾磨灭。反观“我”在湄公河码头邂逅的中国男人,他的家族富甲一方,财富让他的社会权势很大,但是作为黄种人,面对白种人总归低一等。“我”精神的优越感和他骨子里的自卑感是种族地位决定的,根深蒂固、不可改变。所以,初次相遇他给“我”递烟时,手分明在颤抖,而“我”明白了这种身份的高低悬殊正是自己的筹码。“我”放大了自己的优越感,他放大了自己的自卑感,从而使“我”在初次交锋中首先占据了优势,并坚定了征服这个中国男人的信心。
2.富有与贫穷的二元对立。根据小说的叙述,“我”一开始并没有对中国男人一见钟情。在当时的种族歧视下,白种人与黄种人恋爱,于家族是耻辱,于外人是笑柄,这是绝对的禁忌。那么,卑微的中国男人是如何打动高贵且未动心的“我”的呢?从女方而言,这种关系要成立和维系,卑微的一方必须有高贵的一方可索取的东西,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爱情,男人还能吸引女人的则只剩下金钱。正如台湾作家亦舒的作品《喜宝》中女主角喜宝说的,女人需要很多很多爱,如果没有爱,那就需要有很多很多钱。[2]“我”虽然并未爱上这个中国男人,但是他恰好拥有“我”以及我的家庭所需要的金钱,这无疑是他对“我”最大的诱惑力;对男人而言,富有的一方也必须能从贫穷的一方有所得,方能心甘情愿为其花钱,而“我”的青春、美貌、早熟的韵味和异域风情恰恰调动了中国男人所有的征服欲。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Walser)在他的小说《布景和导演》中讲道:“只要是成功的爱情都是一种交易,或交换,我给你,你给我,你给我越多,我给你越多,然后不断升级。”如果把爱情看作一场交易,那么“我”和中国男人的情人关系开始其实是金钱与美色的交易。
高贵与卑微的对立,让“我”在心理上占据主导,让中国男人对“我”产生征服欲望;富有与贫穷的对立则让中国男人有了赢得芳心的可能。看似来自两个对立世界的男女,因为各有所需,各有所得,情人关系得以确立并维系。
(二)二元对立冲突让情人关系难有结局
1.世俗与反世俗的二元对立。小说的主线即是一个贫穷的白人小女孩和一个富有的殖民地中年男子的爱情。中国男人对“我”一见钟情,“我”只是希望从中国男人那里获得金钱,但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也逐渐爱上他,两个人从情人变成了恋人,中国男人甚至想娶“我”为妻。但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用在他们身上的每一组形容词都是对立不相容的:“我”是来自出身高贵的白人家庭,而中国男人是卑微的黄种人,无论他有再多的财富,我的家人都鄙视他。所以我的家人欣然接受他的财富和宴请,但从不正眼相视,更不与之有任何交流;“我”是穷人阶级,而中国男人富可敌国,在中国男人的家族眼里,这绝对不“门当户对”。所以中国男人的父亲极力反对,并以“你若敢娶她,我就没你这个儿子”的狠话相威胁;再则,我是一名15岁的少女,而中国男人已三十几岁,在所有世俗的眼里,这段爱情有违伦理道德,是一场赤裸裸的“钱色交易”,不仅不为家庭所容,更被他人所唾弃。“我”被所有人认为是贪财的妓女,甚至学校的老师不再允许其他同学和我交流,不再过问我是否回学校上课和睡觉,我被彻底地孤立和遗弃。这段恋情就双方的种族和地位而言是反传统的;就双方的年龄而言,是反道德的。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评判,这场恋情都是反世俗的。世俗力量的抗议为这段感情的夭折埋下了伏笔。
2.女性意识与男性权威的二元对立。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股风潮对她小说创作的影响。《情人》中的“我”的原生家庭环境很恶劣,虽然是殖民地的白人,有着优越的种族地位,但是家庭环境不仅落魄不堪还乌烟瘴气:破旧的房子矮小、昏暗、闷热;父亲在我2岁即去世,父爱过早缺失;母亲盲目偏爱,劳苦一生,丧失了所有的温柔和慈爱,变得冷漠和神经质;大哥哥游手好闲还凶狠残暴耍流氓;小哥哥身体羸弱,性格亦软弱无能,成为大哥哥的出气筒。这个家庭没有钱,没有欢声笑语,没有温柔关爱,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斗争,或是窒息的沉默,抑或绝望的冷漠。在如此缺爱环境下长大的“我”,心中的女性意识则在潜滋暗长。“我”想摆脱传统的、怨妇般的母亲的阴影,“我”想制服大哥哥、保护小哥哥,“我”想向偏心的母亲证明“我可以”。这种抗争和独立的意识,在“我”15岁的年纪,得以实现的唯一的资本是青春的美貌,而唯一的捷径则是依傍有钱人。为此,我总是打扮得大胆前卫而艳丽,希冀吸引某位有钱人的目光;当这位中国男人被成功引诱后,“我”全然不顾我们年龄、身份、种族的差异,不顾他人的耻笑,成为了他的小屋情人。在我们的恋情中,无论是床笫间的欢愉,还是恋情的发展,“我”始终是主导者,我甚至敢于表达自己的身体诉求,大胆地说出“我要”。在女性身体被遮掩、欲望被抑制的时代和社会,如此大胆的言行和举动可谓离经叛道。所有颠覆传统的行为,实则是“我”内心的女性意识在这绝望的生活中被唤醒,“我”所有的行动不过是想挑战男权社会下,认为女人应该隐忍、贤惠、矜持、洁身自好的论调。“我”希望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自由释放内心的渴望。正是因为“我”觉醒的女性意识,家里的恶魔大哥哥对“我”敬畏三分,“这个哥哥只怕一个人,有这个人在,他就胆怯,这个人就是我,他就怕我”。也因为“我”强大的女性意识,在与中国男人的交往中,我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不仅让他愿意主动给“我”钱,请我的家人吃饭,最重要的是,女性意识让“我”跟随自我的意愿和需求,尽情享受身体的欢愉。“我”并不认为“我”是在出卖肉体换取金钱,相反,我是在享受性爱的美好体验,并借以忘却生活的磨难。然而,“我”的女性意识是否能主导这段恋情的结局呢?中国男人对“我”的爱已达疯狂,他想娶“我”,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家人—他的父亲。但是,这个社会终究是绝对男权社会,我的反抗行为本身即是暗示了当时社会男性的主导权。母亲偏爱大哥哥,任由他为非作歹;大哥哥称王称霸、飞扬跋扈,这都是对男权社会大背景的暗示。虽然大哥哥怕“我”,中国男人对“我”俯首称臣,这小小的胜利并不能说明“我”就能掌控一切,因为这两个男人各有各的软肋,他们并不代表这个社会最高的男性权力。“我”和中国男人的恋情,“我”不能操控结局,中国男人也无法做主,因为我们的背后还有更强大的男权——他的父亲。父亲代表了这个社会最高的话语权,而且这个父亲还有权威、有财富,他才是真正可以掌控一切的王者。“我”的女性意识在这位父亲面前,显得势单力薄;而中国男人离开了父亲更是一无所有甚至无法生存。女性意识到底抵不过男性权威,我们的爱情不被男权社会接受,这再次为爱情的悲剧结局做了铺垫。
3.独立与依附的二元对立。如果说身份的高低、财富的多寡、世俗的抗议、家族的反对都只是造成爱情无果的客观原因,那么男女主人公性格的冲突则是最重要的主观原因。中国男人在外地位显赫,呼风唤雨,但他的钱权不是自己所创造,而是他父亲所提供。没有他父亲馈赠的一切,他不过是一个身体羸弱、沉迷鸦片与美色、一无所有的无能庸人。为了不失去现有的富足生活,并能继承父亲的家业,他绝不敢挑战父亲的权威,只得惟命是从。当他意识到自己真正爱上这个白人小女孩,并想娶她为妻时,尽管他鼓起了勇气试图说服父亲,但是当父亲威胁若要娶这个白人女孩,就不再认他这个儿子时,他彻底害怕并开始权衡:与失去这个女孩相比,他更怕失去父亲能给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他不能与父权抗衡。正如“我”所言:“要他违抗父命而爱我娶我、把我带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的父亲的金钱。”在父权压制下的中国男人天性懦弱,依附父亲就是他此生的命运。反观“我”,如上所述,“我”是一个女权意识觉醒的独立女性形象,尽管“我”看起来在“依附”于中国男人,享受财富和性爱,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各取所需。尽管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这个中国男人,但是她知道他的父亲坚决反对;她也知道这个男人离不开他父亲的财富,而她是如此的独立和自由,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所以最终她不愿让这个男人为难,毅然选择离开。这个独立于任何人,只属于自己的女性,和这个依附于家业的男人,他们爱情的结局归根结底是性格使然,且因这种性格在性别上错了位。倘若独立和依附二字的主角换位,即女依赖,男独立,那么结局可能是灰姑娘的华丽转身抑或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双殉情,但是这个故事必然陷入前人的套路,失去滋味。杜拉斯让贫穷的女孩独立有骨气,富有的男子懦弱而依附,这一性格错位带来故事的另一种结局,颠覆了读者的传统认知,这也正是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冲击性魅力。
世俗的反对与不可抗的男性绝对权威是他们爱情道路上的外在障碍,而决定他们未能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男女主角错了位的对立的性格冲突。
“二元对立”架构了《情人》的内容和主线,通过对文本中对立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方法有助于促使小说整体结构中的诸多关系项得以明晰化,在“二元对立”的作用下形成鲜明的对比。理顺各组对立项从而帮助我们直击小说的深层结构与深层内涵,从而使读者明白,这段爱情之所以能开始,得益于两人地位、财富和性格的反差,反差在最初是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也正因这种反差造成的冲突无法抵御,注定了这段爱情的不可能。杜拉斯也正是巧妙地利用这种二元冲突,使得故事大胆颠覆,细节引人入胜,结局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