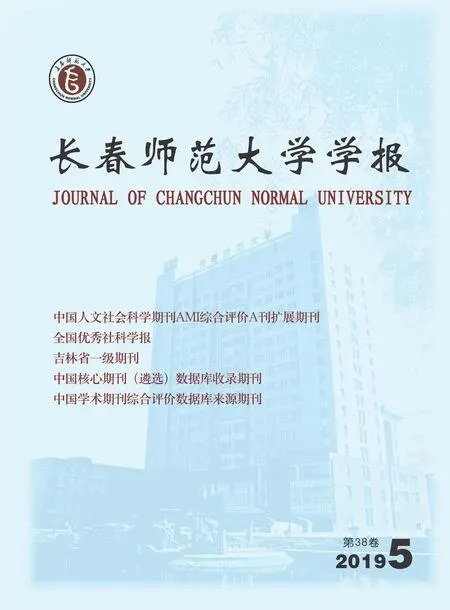文学伦理学视域下《永别了,武器》解读
仇 慧,张 琳
(东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永别了,武器》也成为20世纪初反战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亨利对战争的态度由最初的热情转向最终的厌弃,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他与凯瑟琳的爱情关系从萌芽到确立以及最终的幻灭也充满波折,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战争的冷酷无情及其对人类的残害。
小说中,美国青年亨利响应政府号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前往意大利参战,担任救护车驾驶员,其间,他与战地医院的英国护士凯瑟琳相遇相识。凯瑟琳悉心照料受伤的亨利,两人随之相爱,并在米兰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亨利伤愈后不得不离开已经怀孕的凯瑟琳返回前线,却发现意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亨利在执行撤退任务过程中被狂乱的意大利军队袭击,继而受到意军拦截并被战场宪兵随意判处枪决。亨利在最后时刻跳入河中逃脱并隐藏身份逃往米兰寻找凯瑟琳。后来,两人逃到中立国瑞士度过了一段平静幸福的日子。然而,凯瑟琳最终死于难产,婴儿也未能幸存,留下亨利一人独自面对世事的冷酷无常。
一、写作背景
文学伦理学认为,“伦理环境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1]一战时期欧洲的动荡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亨利的悲剧。
《永别了,武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场为背景,本为同盟国成员的意大利背信弃义,投入协约国的阵营,而其本身的军事力量又不足以抵抗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军队,因此不得不在协约国其他成员国的帮助下勉力维持。在双方力量几乎消耗殆尽、战局明显向协约国一方倾斜的时候,美国宣布参战,站在协约国一边。美国总统威尔逊号召本国年轻人“为了结束一切战争,去欧洲打仗”。海明威作为美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参加了开赴意大利米兰的野战救护队。《永别了,武器》中的主人公亨利的经历则是基于海明威战时遭遇的本色创作。战争结束时,意大利惨胜,伤亡人数超过160万,其中60万阵亡,22万终生残疾。
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战争与爱情成为这部小说最主要的两条线索。两条伦理线交织在一起,时明时暗,在揭示战争的丑陋残酷的同时讲述灰暗战争背景中的爱情故事,亨利的形象也更为鲜活。
二、伦理秩序的破坏
美国在战争初期向战争双方兜售武器大发战争财,而后为了更大的利益直接参与了战争,但是在对内宣传时却将自己置于道德高地,鼓励年轻人为了自由和平而战。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亨利对战争的观点在不断地变化,这个起初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的热血青年渐渐地认识到战争的本来面目,并最终决定与战争单方面“媾和”。
小说的开头并未涉及惨烈的战争场面,只是平直地描述了亨利所观察到的萧条景象和战友间无聊的调侃。这时的亨利身在战场,怀揣着捍卫世界民主的梦想,但对战争本身似乎知之甚少。“祖国需要我时,我就去了,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什么都做,那不过是我的义务。”[2]亨利起初恪尽职守,充满责任感,他“仔细检查车胎,看看有没有划破或石头蹭破的地方”,“这一揽子事情的顺利运作,很大程度上要靠我个人”。随后,他意识到个人不会成为战场上的决定因素,“那儿有我没我并没多大关系”,甚至连最初入伍的目的都开始模糊起来。当凯瑟琳问起他为什么身为美国人居然进入意大利军队时,他回答:“我也不知道,并非每件事都能说清楚的”。当护士长问起相同的问题时,亨利的理由不过是因为会讲意大利语。此时,战争对于亨利而言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跟我毫无关系”,不过是为了完成祖国交付的任务换了个地方工作而已,死亡也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因此,他和战友要么不按规定配枪,要么枪支在手却无法击中目标,“我知道我是不会送命的。这场战争不会要我的命。就像电影里的战争一样,对我本人没有什么危险”。这时的亨利虽然对战争的目的不甚明确,但仍然将之当作自己应当完成的责任,乐观以对。
在战场上奔波的过程中,亨利接触到各个阶层的军人。从与他们的对话中,他渐渐意识到战争的另外一面。美国原本是战争的中立方,利用售卖武器聚敛了大笔财富,这种不参与到实际战场上的行为对普通民众影响不大。但在战争后期,美国政府为了获得战后瓜分世界的资格,打着维护世界秩序的旗号向德国宣战,也不可避免地将大量美国青年带入了战争的旋涡。而意大利政府在一战中的角色也并不光彩,叛出同盟国加入协约国的行为使意大利军方的决策蒙上了不忠不义的阴影,这些也必然会影响到意军参战人员的信心和士气。美国和意大利出尔反尔的行为使两国政府在道德层面上出现瑕疵,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战士对决策者的信任危机。亨利在战场上遇到的各型各色的人无不对这场战争抱有抵触的情绪:弄丢了疝带而导致病情恶化的士兵告诉他有人会故意生病或受伤来逃避上前线;一起执行任务的司机们更为尖刻地指出有的士兵要靠枪毙来逼迫才会出击,甚至是由于惧怕家人被株连而被迫冲锋陷阵;最终,他们作出“人人恨这场战争”的结论,并敏锐地感知到统治阶级的荒谬无能,“一个国家有个统治阶级,这统治阶级是愚蠢的,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得。因此就有了这场战争。而且他们还借此发财”。士兵们意识到了政府所谓的正义根本站不住脚,不过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欲望而置广大战士于危险的境地。战争的残酷被赤裸裸地揭露在亨利的面前,士兵同军官及政府的对立情绪使他越发地怀疑他参加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一战是欧洲列强重新瓜分欧洲之战,与美国何干?”[2]
随后,血腥的战斗场面愈发加重了亨利的疑惑。他和司机们休息的掩体遭到了敌军迫击炮弹的袭击,一个战友在他面前挣扎死去,他试图救治其他人,但发现自己也受了重伤,这时,亨利亲历了战争可怕的一面,“我看着我的腿,心里非常害怕”,他真切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
“我使劲呼吸,可又无法呼吸,只觉得灵魂冲出了躯壳,往外冲,往外冲,我的躯壳始终在风中往外冲。迅即间,我的灵魂全出了窍,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如果以为是刚刚死去,那是大错特错。”[3]
战争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残酷的,士兵会随时面临死亡,陷入战争的百姓随时会有生命财产的损失。对于对战双方政府来说,一场战役的输赢未必会影响整个战局,但是对于士兵和百姓来说,任何伤亡损失对他们都是决定性的,决定他们能否继续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进行这样一场伤亡惨重的战争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亨利觉得“不知道美国跟奥国有什么势不两立的”,同样,跟其他国家的矛盾也是这样,对于普通士兵来说,这种模糊的参战目的是遥不可及或难以理解的。
在随后辗转救治的过程中,亨利再次体验到了战争中产生的混乱。军医在为亨利检查时说,“值勤时受的伤。这样一来,军事法庭就不会说你是自残了”,这一说法更加印证了疝气士兵所描述的军官对于士兵的不信任,同时也反映出士兵对于政府的猜疑和对逃离战场的渴望。同时,转运的过程中亨利发现位于他上层担架的士兵不断地流血,而司机在听到亨利的示警求助后仍然无动于衷未加任何援手,最终那名士兵失血而死。军事法庭、救援人员是政府在战场上的代言人,而原本应承担起支持和救援责任的他们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多疑和无情的卑劣嘴脸,他们给予战士的不是应有的信任和支持,而是不知所谓的怀疑和对伤患遭遇的漠不关心。亨利通过自身的经历再次确认了战争中政府同士兵之间关系的崩塌,同时也对战争的本质加深了怀疑。
在野战医院中,昔日的战友里纳尔迪前来看望亨利,他试图帮助亨利回忆或“创造”受伤时的英勇事迹,希望能够借此为亨利申请一枚银质奖章,而亨利对此却反映平平,似乎得不得奖章对他来说无所谓。荣誉和勋章原本是战士最值得骄傲的东西,然而在一战的意大利战场上,荣誉可以通过虚构和作假来取得,为此亨利不得不怀疑他为了这样的政府和友军在战场上拼杀是不是值得。至此,亨利的心中对于所谓荣誉、正义等等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越来越模糊,亨利甚至对战争的意义和军人一直引以为傲的荣誉都充满了怀疑和鄙视。
如今观察了这么久,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事,那些光荣的事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那肉不再加工,而是埋掉罢了。
什么神圣、光荣、牺牲、徒劳之类的字眼,我一听到就害臊。
诸如光荣、荣誉、勇敢、神圣之类的抽象名词,若跟村名、路号、河名、部队番号和日期放在一起,那简直令人作呕。[3]
战场在亨利的眼中等同于屠宰场,深陷战争的人们就是屠宰场里待宰的羔羊,他们的牺牲没有任何意义,而所谓的荣誉在亨利看来不过是给了屠杀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场帝国之间分赃不均所引发的战争打破了人们对于正义的幻想,消磨了士兵对政府的信任,也摧毁了战士对荣誉的信仰。
撤退的过程更加混乱,亨利等人面临的不仅仅是德军的威胁,“意大利人对我们的威胁比德国人还要大”,被吓坏的意大利人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对什么都害怕,看到什么都乱开枪,一同撤退的战友艾莫就这样死在自己军队的枪下,他们的遭遇使亨利对这场战争丧失掉了最后一点希望,“不但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退却”,回家成了他唯一的期盼。之后遇到的意大利战场宪兵更是令亨利绝望,也成了压垮亨利军人梦想的最后一根稻草。亨利因为无辜被抓而试图反抗,随后受到“毙了他”的威胁;因为外国口音被怀疑是“穿着意大利军装的德国人”,他不得不等待面对“愚蠢的审问”;目睹撤退中的中校被诬“叛国”而被枪决使他意识到形式上的审问最终的判决全部是枪决……最后一丝活着离开战场的希望也破灭了,亨利乘人不备跳入河中逃离了可怕的战场,他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也与战争脱离了干系。“愤怒和责任一起,都在河里被冲洗掉了。其实,早在宪兵伸手抓住我衣领时,我的责任就停止了。我洗手不干了。这不再是我的战争了。”[3]
亨利亲眼见证了战争所导致的伦理秩序的土崩瓦解,在战场上他经历了捍卫世界理想的破灭,目睹了统治阶级同战士间信任的消失,也深切体会了军人荣誉感和信仰的崩塌,他从一个盲目的参战者成长为认清了战争本来面目的消极战士,并最终毅然决然地远离战争,最终完成了对战争本质的深刻认识。
三、伦理秩序的重建
亨利在战场上从蒙昧到清醒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战争中大部分的伦理秩序都陷于混乱,本应成为军人精神支柱的参战目的、政府权威、荣誉感和信仰都被破坏,他需要另一种秩序来稳定和填补他的精神世界。亨利在与凯瑟琳的情感在战场上伦理秩序不断坍塌的时候渐渐明晰起来,爱情的力量重建了亨利心中的情感秩序,从而使他趋于内心的平和。
小说开篇的亨利对战争懵懂,对爱情同样一知半解。整天混迹在军营的亨利不可避免地听战友们随意地谈论女人,他们当中很多人缺乏对女性的最基本的尊重。身处这样的环境下,亨利同凯瑟琳最开始的交往不过是逢场作戏,没有付出任何的真心。他在与凯瑟琳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试图亲吻她,可笑的是,不是因为喜欢或者爱,而是因为觉得凯瑟琳长得很美。当凯瑟琳反复问起他会不会对她好时,亨利的反应居然是“该死”。恐怕这时的亨利只是把凯瑟琳当做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负担,连朋友都算不上。
第三次见面的时候,亨利对凯瑟琳对他执行任务的关心略显不耐烦,这表明亨利不想凯瑟琳太过介入他的生活,她是“别人”而非“自己人”。当凯瑟琳问他是不是说过爱她的时候,他违心地撒谎答“是的”,但是心里面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不过是场游戏,不比打牌更郑重。同时,凯瑟琳也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是战争中的消遣,是一场“戏”。尽管如此,他们的相处还是在亨利的生活中留有痕迹。当想见凯瑟琳却未见到时,亨利会觉得“孤单又空虚”。亨利与凯瑟琳之间的交往没有任何规则的约束,其关系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还没有触碰到爱情的门槛。
亨利与凯瑟琳的再见就是发生在受伤修养期间的米兰医院了。亨利一个人躺在陌生的医院,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心中满是对伤情的忐忑,而熟悉的战友又不在他的身边,这时,凯瑟琳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就像一道阳光给了他抚慰和希望。“我一看见她,就爱上了她。我神魂颠倒。我爱她爱得发疯了。我不敢相信她真的来了,便紧紧地抱住她。”[3]此时,凯瑟琳成为亨利在伤痛和陌生环境中的唯一精神依靠,亨利清楚地知道,正是这次受伤促成了他和凯瑟琳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爱情初露端倪,“上帝知道,我本来是不想爱上她的。我也不想爱上任何人。但是上帝知道我已经爱上了她。”[3]养伤期间,亨利和凯瑟琳的感情一日千里,任何短暂的分别都像是一场长途旅行,每次见面都是久别重逢,在他们心中,他们就像是真正的夫妻,“她到医院的头一天,我们就算是结婚了”。在遥远的异国战场上,身负重伤的亨利正处于最为迷惘和无助的时候,凯瑟琳的出现带来了“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而她悉心的照料恰好缓和了亨利由于参战目的和意义动摇所引发的冲击,情感秩序的初步建立弥补了战场上伦理秩序缺损导致的心理伤痕。
这段时间是战争中亨利和凯瑟琳一起度过的最安静美好的一段时光,他们一起出去吃饭,一起郊游,凯瑟琳对亨利细致入微的照料给他带来了家一样的感觉。亨利也渐渐地对凯瑟琳越发关心,越发能够体会凯瑟琳的心思变化,他渐渐地从一个情场上玩世不恭的浪子变成了一个有责任心的爱人。不久之后,凯瑟琳怀孕了,然而离别也随之而来,亨利伤愈后很快要重返前线,以前对生死不屑一顾的亨利郑重其事地买了枪,这是亨利对自己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凯瑟琳的负责,他不想凯瑟琳再一次经历未婚夫阵亡的惨痛经历。离开前他们在旅馆的相聚是他们对家的全部憧憬,旅馆的房间就像是曾经的病房,就是他们的家,里面有甜蜜温馨和他们浓浓的情谊,以及他们对家的渴望。在这里,他们依依惜别,亨利决定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承担起来,家庭伦理秩序在他心中初见雏形。
重返战场的亨利时时想念着凯瑟琳,哪怕做梦都惦念着她,他们的感情融入到亨利的生活中不可分割。独自逃亡的时候,亨利仍然不由自主地想起凯瑟琳,心里充满对她的想念和愧疚,生怕“想她却没有把握见到她”。
当亨利辗转找到凯瑟琳时,亨利对侍者称凯瑟琳是他的妻子,家的概念在亨利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了。对亨利来说,凯瑟琳是他的一切,有凯瑟琳的地方就“像是回到了家,不再感到孤独”,“其他事情都不真实了”。从此,他们决定再也不分开,哪怕面临被逮捕的风险,他们也一起冒险横渡湖区逃往中立国瑞士,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彼此鼓励彼此关怀,亨利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一个丈夫应该承担的保护妻子的责任,并最终在瑞士建立了自己的小家,也端正和确立了爱情和家庭这一伦理秩序。
生产前,亨利和凯瑟琳在一起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两个饱受战争磨难的人暂时脱离了战争的阴影,可他们还是“丝毫不敢浪费在一起的时光”。好景不长,凯瑟琳在生产时出现了难产的迹象,亨利在忐忑不安的等候,一方面心疼“可怜巴巴的亲爱的凯特”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另一方面又担心现有安定生活的破灭。亨利在脑海中反复九次提到“万一她死去可怎么办?”这里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凯瑟琳生死间的挣扎,也包含着亨利对未知结果的深切恐惧,最终在医生提出剖腹产时,一句带着感叹号的“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将亨利的恐惧推到了顶点。万一凯瑟琳死了,爱情赋予亨利的精神支持消失殆尽,依附其上的家庭伦理秩序随之破灭,他的整个生活将重归无秩序状态,毁于一旦。最终,孩子死了,凯瑟琳也没能活下来,亨利同凯瑟琳告别,“就像跟石像告别”。从此以后,亨利的生活灰暗一片,如一潭死水不起波澜。他们还是没能逃脱战争的影响,恶劣的生存条件打破了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秩序,重新将他们推入了可怕的灾难,打破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一切幻想,“任何人的死亡,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都是没有意义的。在战争中死去与在恋爱中死去,结局都是一样的。”[2]
四、结语
在战场上,亨利目睹的是秩序的破坏和崩塌,在爱情之路上,亨利努力地寻找方向建立秩序,然而这一切努力,放在战争的环境下,显得那么的弱小和无助,最终都会灰飞烟灭。“亨利的迷惘是别无选择的必然结果和时代的悲剧。”[4]亨利的遭遇就像战后老兵遭遇的写实,他们在悲惨的现实世界中很难愈合身心的伤痛,战争的打击对他们而言是摧毁性的,因此,“迷惘的一代”的出现,归根结底,是战争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