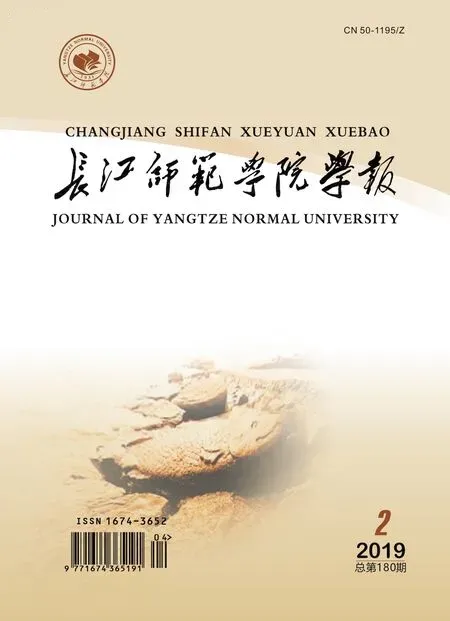从厉鹗著述看浙派诗人群体的“尚宋”特征
王小恒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8100)
厉鹗作为清代浙派中期的领袖和诗学巨擘,一生嗜于著述,创作繁丰。由于其生前不求仕进闻达,又无处显位者为之鼓扬,逝后无子嗣,荒凉寥落,著述湮灭删轶者甚多。然而就我们现在可见的材料,从文学创作和史地研究两个方面来说,其诗词创作走的是“尚宋”的路径,而其史地研究则将焦点对准了两宋尤其是南宋。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中期,文人动辄以文字被祸,厉鹗及其同仁与宋代人文的这种“隔代同音”,决不是偶然的,基于厉鹗在浙派诗人群体中的地位和影响,这种“隔代同音”也不是个别现象。本文拟从厉鹗文学和史学两个方面着手,对其撰著加以系统考察,同时对其“尚宋”①本文的“尚宋”不仅指传统诗学意义上的“宗宋”,还包括浙派诗人在文学史地撰著中,常常把历史时段锁定在两宋。这不但体现了其创作、治学的兴趣所在,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他们身处清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某种情感寄托,或者说是此种情感寄托的曲折表达。特征略加剖发,以期抛砖引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下文中不少撰著的编撰者虽标为厉鹗,但实际上是浙派主要成员集体合作的产物,如《宋诗纪事》就是这样,另外不少也是厉鹗和其他浙派成员的合著,如《绝妙好辞笺》。因此,这些撰著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浙派诗人总体的倾向和偏好。
一、厉鹗的文学创作及著述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初字雄飞,号樊榭,又号南湖花隐,是清中期浙派诗人群体的巨匠和领袖人物。厉鹗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凡是诸种传统文学体式如诗、词、曲、赋、散文等,均有涉及。厉鹗在文学创作及史地研究方面的著述,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在宋诗学领域的贡献,更为学者所称道。
(一)《樊榭山房集》三十九卷
厉鹗的《樊榭山房集》基本收集了他的绝大部分诗歌、散文及词曲创作,计有诗歌作品1 400多首,序跋等数十篇,词作200多首,以及散曲之类作品近百首,是研究厉鹗创作最需要注意的本子。某种意义上,《樊榭山房集》还为我们提供了浙派诗人群体发展到中期阶段的种种线索,例如通过其诗词曲文等创作,可以大体考证其交游、唱和的情形,如查为仁、查礼、万光泰、陈章、“扬州二马”、楼锜、刘文煊、符曾、易谐、商盘、朱稻孙、张世进、汪孟、闵华、汪沆、王昶、方士偼、钱载、蒋德及陈兆仑,等等。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樊榭山房集》(全三册),这一版本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但有陈九思的标校,而且在标校时加进了清人董兆熊的注释,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厉鹗的诗词创作具有鲜明的“尚宋”特征,其突出表现就是诗词中大量引用宋代故实。由于这个原因,不少论者批评厉鹗诗词创作“掉书袋”、堆砌材料,但这恰恰是厉鹗创作“尚宋”的体现。由于“尚宋”,厉鹗的诗“难读”,所以清代人董兆熊专门为厉鹗诗做了注释。厉鹗诗及董兆熊的注释,内容异常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一起构成了浙派宋诗学研究的一大渊薮。
(二)《南宋杂事诗》七卷
《南宋杂事诗》是雍正初年(1723)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厉鹗、赵昱和赵信及七人合著的诗集,集中每人各写100首(符曾101首),总数为701首。对于这部诗集,《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书以其乡为南宋故都,故捃摭轶闻,每人各为诗百首,而以所引典故注于每首之下。意主纪事,不在修词,故警句颇多……采据浩博,所引书几及千种。一字一句,悉有根柢。萃说部之菁华,采词家之腴润。一代故实,巨细兼该,颇为有资于考证。盖不徒以文章论矣。”[1]可谓要言不繁。关于《南宋杂事史》的创作主旨,查慎行所为《序》云:“吾杭自建炎南渡,号称帝都,虽偏据规小,顾历七朝百五十余年间事……大抵绚者如霞锦,淡者若云烟,领异标新,目不暇给。而今而后,于故都旧可无舛漏之憾矣乎。”[2]此语颇耐琢磨,而言下之意是非常清楚的。事实上,当人们审视《南宋杂事诗》中所吟咏的朝堂景象、宫廷逸事、时尚节气、山川遗迹时,就可以看到,各卷都不约而同地对两宋之交的惨况,南宋立国的繁盛,直到最后灭于“异族”铁蹄之下的史事,都有反映。诗中大量篇幅还写到至死难忘故国的南宋遗民谢翱、汪元量等,透露出华夏人文惨遭践踏、甚至毁灭的巨大哀痛。很明显,厉鹗诸人是借写南宋史迹,表达胸中难言的惆怅和对兴亡的感慨。正如严迪昌先生指出:“《南宋杂事诗》既是一部寄寓特定群体心魄的咏史诗合集,又缘其所征引文献近千种,附录之引用书目中不少已散佚,所以,《杂事诗》不仅是清代宋诗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典籍,同时也为南宋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文献资料以及足资校勘的文本异文。”[3]
因此,我们讨论浙派诗人群体的“尚宋”特征,《南宋杂事诗》颇具代表性。首先,《南宋杂事诗》的作者群体汇聚了清代中期浙派初起时期的大部分核心成员。其中,沈嘉辙、吴焯论年辈资历都在厉鹗之上,和厉鹗在亦师亦友之间,对于启导厉鹗走上诗坛、产生影响具有一定作用;陈芝光虽材料匮乏,不能确考,但大体可以判断,年辈也在厉鹗之上;符曾有《春凫集》传世,他曾学诗于查氏门下,与清初浙派与中期浙派的过渡性诗学大匠查慎行有师生之谊;赵昱和赵信是手足兄弟,敬爱一生,形影不离,不求仕进,时人称为“二林”,他们不但是浙派诗人群体的核心成员,更为重要的是,其家小山堂不仅藏书十分丰富,而且是浙派诗人群体成员的读书与论学之处。考之相关资料,赵氏兄弟是赵宋后裔,其母又与明清易代之际山阴祁彪佳有姻亲关系,而其小山堂藏书又以倾其财力搜寻祁氏澹生堂逸本为职志①详见拙文《从全祖望与杭郡赵氏两世交谊看其盛世“遗民”心态》,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文中对赵氏兄弟家世及藏书宗旨有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这样的家世背景,这样的进退出处,在清代中期这样一个政治、文化生态均极为吊诡的时代,“离立”之意甚明。要之,据有关资料显示,厉鹗等浙派诗人集体创作的《南宋杂事诗》的诞生地就在赵氏兄弟经营的春草园,其鲜明的“尚宋”特征固不必说,这一诗人群体对当朝的立场和态度也不难揣度。
(三)《宋诗纪事》
“纪事”体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特殊体式,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所纪之事不限一体,诗、词、曲、文各体皆具。这些“纪事”大多以作者为中心,他们的生平事迹、轶闻趣事,以及对具体作品的点评、研究资料等都汇集于此。唐代孟棨的《本事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部专述诗歌本事的著作,是“纪事”一体的直接源头,同时是诗话的肇始之作。此后,诗歌纪事代不乏其作,著名的有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八十一卷,近代陈衍的《辽诗纪事》十二卷、《金诗纪事》十六卷、《元诗纪事》二十四卷,陈田的《明诗纪事》一百八十七卷,今人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以及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文的纪事有清代陈鸿墀的《全唐文纪事》一百二十二卷,词的纪事有清代张宗的《词林纪事》二十二卷,今人唐圭璋的《宋词纪事》,曲的纪事有王文才的《元曲纪事》,都可谓洋洋大观。在诸多纪事体著作中,厉鹗的《宋诗纪事》一百卷是对后世影响较为特出的一部。
厉鹗对宋代文化极为爱好,对宋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研究有极深的造诣。雍正三年(1725),他与好友合作,欲效计有功《唐诗纪事》体例,搜罗鉴录宋诗,但因故罢去,后来得到大盐商、大藏书家兼至交“扬州二马”兄弟的大力援助,于乾隆十一年(1746)编成《宋诗纪事》这部煌煌巨著。《宋诗纪事》收宋代诗人三千八百多家,各卷以诗人为中心进行编排,卷一是帝王皇后,卷二至卷八十一是按时代编排的各家诗人,卷八十二至卷八十三是时代无考的诗人,卷八十四至卷九十九是宫掖、宗室、降王、闺媛、宦官、外臣、逆流、释子、女冠尼、属国、无名子、妓女、卟仙女仙、神鬼,卷一百是谣谚杂语,各家之下附有小传,有时在传后有作者评论。厉鹗在《宋诗纪事·自序》中说,宋诗“迄今流传者,仅数百家,即名公巨手,亦多散逸无存,江湖林薮之士,谁复发其幽光者?”[4]正是有感于此,《宋诗纪事》中收录了众多宋代诗人遗作,更可贵的是这部巨著以诗存人,有宋一代许多名位低微的诗人借此为后世所知。对于《宋诗纪事》的贡献,正如钱锺书所说:“没有他们的著作,我们的研究就要困难得多。不说别的,他们至少开出了一张宋代诗人的详细名单,指示了无数探讨的线索,这就省掉我们不少心力。”[5]《宋诗纪事》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搜集材料非常丰富。厉鹗对宋代的笔记、杂史、小说及诗话等文献非常熟悉,可以说是当时对宋代文献掌握的最充分的人之一,因而他能驾轻就熟地把这些材料加以钩辑整理,使之归于各家或其诗之下,为后人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宋诗纪事》重视考证订误。厉鹗曾说:“胡元任不知郑文宝、仲贤为一人;注苏诗者不知欧阳非文忠之族;方万里不知薛道祖非昂之子。以至阮宏休所纪三李定,王伯厚所纪两曹辅之类,非博稽深订,乌能集事?”[4]由此出发,厉鹗订正了不少前人舛误,故纪昀等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评厉鹗“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6],诚为确论。《宋诗纪事》虽然招来诸如“重出”“失收”“失考”之类的批评,但毕竟瑕不掩瑜。
《宋诗纪事》最早的版本是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厉鹗生前已经刊刻。此后,清代陆心源撰《宋诗纪事补遗》一百卷及《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四卷,又有宣古愚、罗以智、屈弹山等的《宋诗纪事续补》三十卷。这些都证明了《宋诗纪事》问世后在清代的影响。今人孔凡礼辑撰的《宋诗纪事续补》,“积二十余年之功”[7],辑录厉鹗、陆心源二书未收作者一千五百多人,按时代先后编为三十卷。孔著主要从一些地方志中广加搜罗,诚为厉氏功臣。另外,钱锺书所著《宋诗纪事补正》也于2003年问世,但该书一出版,立即受到不少批评[8],其学术地位尚待进一步探讨。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存的《宋诗纪事著者引得》,有一定参考价值。
《宋诗纪事》编者一般标为厉鹗,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据相关资料显示,浙派诗人群中的“扬州二马”即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不但亲身参与了《宋诗纪事》部分内容的编纂,且其家“小玲珑山馆”丰富的藏书是《宋诗纪事》资料获取的主要渠道①关于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和其他浙派诗人群体成员与厉鹗共同编纂、出版《宋诗纪事》的若干细节,可参考拙文《论“扬州二马”的图书收藏事业及其文化贡献》,载《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这部煌煌巨著编成之后,由于卷帙巨大,主要编纂者厉鹗又是寒士,根本无力刻板行世,不得已厉鹗发布《征刻〈宋诗纪事〉启》谋求赞助,最后还是“二马”兄弟慷慨解囊,助成其事。因此,这样一个大部头的著作,若不是当时及时刊刻,广为流布,能否传世还是个问题。因此,这部著作不但鲜明地体现了浙派“尚宋”的倾向,也是广大浙派同仁集体编著、出版的结果。
(四)与查为仁合笺的《绝妙好词笺》七卷
《绝妙好词》七卷,是南宋词人周密所编。周密曾辑录宋代文献、家乘旧闻为《齐东野语》等书。周密《绝妙好词》的编选意图,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样:“不无荆棘之悲,用志黍离之感。”[9]《绝妙好词》七卷,收录了南宋一百三十二家词人作品近四百篇,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选词标准以婉约清丽为主,以姜夔、吴文英等人词风为宗。
《绝妙好词》作为一个重要的宋词版本,元明时已湮没无闻,清初藏书家钱曾述古堂藏有手抄本,柯煜(钱曾族婿)与其从父柯崇朴对抄本加以校订纠误,镂板以传。厉鹗、查为仁所笺之本即柯、高之本②《绝妙好词》厉鹗题跋云:“《绝妙好词》……幸虞山钱遵王氏收藏抄本。禾中柯孝廉、南陔钱唐高詹事江村校刊以传,是书乃流布人间矣。近时购之颇艰,余最有倚声之癖,吴丈志上掇残帙以赠,仅得二卷,又借于符君幼鲁,属门人录成,乃为完好。”。由于《绝妙好词》版本稀缺,关于它的一则轶事,兹录于此,足资一证。吴焯《读书敏求记》跋云:
绛云楼未烬之先,藏书至三千九百余部,而钱遵王此记凡六百有一种,皆纪宋板元钞及书之次第完阙古今不同,手披目览,类而载之,遵王平生之菁华,萃于斯矣,书既成,扃之枕中,出入每自携,灵踪微露,竹垞谋之甚力,终不可见。竹垞既应召,后二年,典试江左,遵王会于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燕,约遵王与偕,私以黄金翠裘予侍书小吏,启鐍,豫置楷书生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成而仍返之。当时所录,并《绝妙好词》在焉。词既刻,函致遵王,渐知竹垞诡得,且恐其流传于外也。竹垞乃设誓以谢之。[10]
厉鹗为《绝妙好词》作笺,一方面从词风及作词宗旨上,他与周密及《绝妙好词》所选诸人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是他秉承了周密作为南宋遗民选辑此集的特有心态,实不愧周密的异代知音。当他于乾隆十三年(1748)入都铨选县令、途经天津查为仁水西庄,见“莲坡之辑,颇有望洋之叹”,并将自己以前所搜集的有关资料“举以付之,次第增入”③今《绝妙好词》有厉鹗所撰之序,对笺注此集缘起述之甚详。详见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7页。,是一个质量很高的笺本。厉鹗和另一位浙派诗人群体重要成员查为仁④关于查为仁的生平及在浙派诗人群体成员中的地位,详见拙文《论津门查氏的遭际、心态及其水西庄的营建——以查为仁为中心》及《论查礼在浙派诗文化活动中的东道主地位及其贡献——兼论浙派宗主厉鹗的水西缘》,分别见《图书与情报》2013年第5期、2016年第4期。合笺周密《绝妙好词》与其编撰《宋诗纪事》的宗旨完全一致,就是要借以保存两宋诗学、词学文献,并给两宋时期名位低微的诗人、词人应有的地位。鉴于浙派诗人群体成员在清代中期的特殊处境,他们不屑仕进,甚而与王朝隐然处于“离立”的状态,这种“隔代呼应”使得他们在撰著上的“尚宋”情结中渗透了一种莫名的悲情成分。
严格地讲,《绝妙好词笺》并不算注本,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对字、词、句的注疏,而是把各种参考资料加以汇编,以保存资料为宗旨。在内容上,它分为作者小传及资料、词的背景及解题、词的评价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词人的小传及相关资料,这一部分内容很重要,因为《绝妙好词》所选相当一部分词人都“士生隐约,不得树立功业,炳焕天壤,仅以词章垂称后世,而姓字犹在若灭若没间”[11],因此,要给处于“若灭若没”之间的词人作传是需要一番勾稽功夫的。第二部分内容较少,有时连录几首词而不着一字,但这部分提供的资料仍具有一定价值。第三部分是对每位词人的总体评价。总评大多先征引《词旨》的《属对》《警句》二章,摘录出该词人的好的属对及警句,广引诸家点评,有时还附录其他词作。
乾隆十五年(1750),查氏自刻《绝妙好辞笺》问世,道光八年(1828),有杭州徐氏(徐懋)刊本,光绪间又有翻刻徐氏本。民国又有《四部备要》本,较精善。1957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据《四部备要》重印单行本,是目前最善而又全面的本子。
二、厉鹗的史地著述及其他
厉鹗是一位文学巨匠,不但在文学上有理论、有创作、有选集、有笺注,而且在史学方面也堪称大家。与文学创作与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尤其是南宋)相一致,他在史地领域对宋代也极为关注,除《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不是直接涉及宋代之外,像《东城杂记》《湖船录》《南宋院画录》等,均把研究的视点倾注于南宋,因此,厉鹗的史地著作与文学著作共同构成了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景观,给人一种富于形式感的无穷意味。由于当时文字狱盛行,文化“高压”酷烈,士人抱无限怨抑,无由也不敢抒发其内心所感,厉鹗的著作创造了独有的表述方式!这种方式的曲折与幽深恐怕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其他时代都是相对少见的,它“冠冕堂皇”而又意在言外,它让人能隐然心会又觉得“无迹可寻”,正是在模棱两可之间,某种特定的而又难以释怀的情绪得到另一种意义上酣畅淋漓的表达。
(一)《辽史拾遗》二十四卷
是书《四库全书》已著录。关于《辽史拾遗》撰写之缘起,樊榭自己说:“宋、辽、金三史,同修于元至正间,秉笔者多一时名儒硕彦”,而“宋史失之繁,《辽史》失之简”[12],并认为明代王圻所作《续文献通考》所及辽事,“条分件系,不出正史,尝病其陋,而叹辽之掌故沦亡也”[12],有感于有辽一代掌故、文献的散轶,厉鹗发奋拾《辽史》之所遗:《辽史拾遗》对正史材料作了注疏,使之更加详明;对正史疏漏不及的史实,则参考各种文献补充于后。若与正史记载互有差异的材料,就进行论证排比,加以按语,以说明作者的意见。又对其中时间错乱及舛误,多有补正。同时又在文条之后补辑辽之四境方位、物产及风土人情,使之更加完备。厉鹗在搜集史实上下了一番苦功,正如其所云:“暇日辄为甄录,自本纪外,志、表、列传、外纪、国语,凡有援引,随事补缀。犹以方域幽遐,风尚寥邈,采篇咏于山川,述碑碣于塔庙,短书小说,过而存之。”[10]所以后来人们对这本名著评价很高。《四库全书总目》云:“鹗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皆采辑散佚,足备考证。”[13]梁启超热情称赞“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14],严迪昌也推许厉鹗为“有专攻的史学家”[15],这里的“专攻”就包括《辽史拾遗》一书的撰著。而厉氏自己对此书也颇为得意,曾吟诗曰:“旧史临潢新注就,不知谁肯比松之(时注辽史成)。”[16]完全以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的史学成就自命,“亦不诬也”[13]。
比厉鹗稍后,杨复吉有《辽史拾遗补》。杨氏认为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虽“博采旁然,粲然大备”,但材料方面仍“异置孔多,不免语焉弗评之憾”[17],遂考以《旧五代史》《契丹国志》《宗元通鉴》三书,增益《辽史拾遗》四百余条,成《辽史拾遗补》五卷,实为厉氏辽史研究之功臣。
(二)《东城杂记》二卷
《东城杂记》二卷,《四库全书》已著录。厉鹗家住杭州城东一个叫东园的地方,是宋代古迹,《宋史》曾载其名。可见此书之撰也是厉鹗著述一贯“尚宋”的一个例证。对于杭州东城,厉鹗生于斯,长于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极为熟悉,且怀有极深的感情,正所谓“举目皆古迹”(全祖望语)。其自序曰:“杭城东曰东园,地饶水竹蔬蓏,修然清远,先君子因家焉。小子生于是,居已三十余年,凡五迁,未尝离斯地也。”由于要“考里中旧闻遗事”,而苦于“志乘所述廖廖无几”,所以厉鹗一方面四处访朋问友,获得材料,一方面又“从故籍参稽,每有所得,辄掌录之”,有朋友也建议他“古杭事綦繁,何不推广成书”①厉鹗《东城杂记》有《自序》,此段文字见于其《自序》。厉鹗《东城杂记自序》未见收于其文集中。其《东城杂记》常见的的本子有清嘉庆二十五年汪氏振绮堂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等,诸本稍有不同。。因此,在厉鹗的不懈努力下,《东城杂记》于雍正六年(1728)三月撰成。
《东城杂记》记载大抵略古详今,补《宋史》所未记载的内容八十五条,分为上下两卷。内容精博而典核,有些内容就连地方专志如《浙江通志》和杭州的旧志也未涉及。在体例上有“小传”(灌园以后)之设,对后来修地方志极有帮助。难怪《四库全书总目》称道云:“是书虽偏隅小记而叙述典雅,彬彬乎有古风焉。”[18]为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把它列为参考资料之一,1958年以《粤雅堂丛书》作底本排印出版。
(三)《湖船录》一卷
《湖船录》一卷,是杭州西湖画船之总录,共八十多条,其中不少涉及南宋史迹。早在清初,浙人朱彝尊就有《说舟》一书,厉鹗的《湖船录》就是在《说舟》基础上增益而成。虽然亦是寥寥小记,但叙述雅洁,非独骚人之结习闲情,对吴自牧《梦粱录》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等书也补充甚多。西湖志乘多记园林之盛,而西湖画船实亦应为此类著作必不可少的内容。正如厉鹗所云:“西湖风漪三十里,环以翠岚,策勋于游事者,唯船为多。”[19]此书成后一百多年,有杭州人丁午撰《湖船续录》,其自序称,其先祖丁敬曾撰有《湖船续录》一卷,曾载于《杭州府·艺文志》。丁敬与厉鹗实为终生至友,也是浙派重要诗人,亦为浙派印学之鼻祖。今观丁午之《续录》所辑画船近一百条,其数量超过了厉鹗的《湖船录》,但是有些船名似嫌牵强附会,如“卖鱼船”等。
(四)《增修云灵寺志》八卷
乾隆九年(1744)成书,《四库全书》存目。云灵寺原名灵隐寺,是浙江第一大寺,位于今杭州西湖湖畔。在两宋时期,最高统治者与此寺渊缘颇深,南宋高宗和孝宗更是经常至寺进香。康熙时,玄烨南巡,“驻跸山中”[20],御书“云林”二字匾额,遂改名云林寺,灵隐之有志,历史相当久远,“前此之有志也,始自昌黎白珩子佩氏,近则仁和孙治宇台氏、吴增子能氏相继重修”,但是“天文焕烂,佛日重光,曷可无纪?前志虽三属草,脱漏尚多,曷可无述?”[21]因此,当时的云林寺主持高僧巨涛和尚请樊榭主修寺志,张曦亮协助。作为杭人的樊榭自然慨然应允。新志在体例门类上,仍沿旧志,重点是补前几部旧志之未备,未几,书成,共八卷。
(五)《南宋院画录》八卷
此书《四库全书》著录。南宋自偏安临安,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越发歌舞不休,吟咏太平。除此之外,还效仿前朝宋微宗赵佶故事,设立御前画院,并有相应的专职官员,画院官员所作就是院画,实为官方主持设立的专事绘画的机构。当时院画名家有所谓刘松年、马远、李唐、夏圭等四大家之目。在画院设置之初,由于某些画家与北宋画院存在师承渊源,尚能取得相当成就。但总体上,由于画家生活体验有限,因而所作偏于精工细琢。然李唐等人造诣较高,正如厉鹗所云:“如《晋文公复国图》《观潮图》之类,托意规讽,不一而足,庶几合于古画史之遗,不得与一切应奉玩好等。”[22]
《南宋院画录》第一卷为总述,第二卷到第八卷记载自李唐以下共96位画家,详细地勾勒画家的生平事迹,后附以诸书所藏的真迹题咏,内容既丰富又详明,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称:“征引渊博,于遗闻佚事殆已采摭无遗矣。”[23]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是由于厉鹗本来就对宋代文献极其熟悉,所以征引起来左右逢源。二是由于他不满足于《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对院画作者的粗略记载,而是别据《图绘宝鉴》《画史会要》等书画专书加以勾沉提要,并“编搜名贤吟咏题跋,与夫收藏赏鉴语,荟萃成帙”[22]。可见,厉鹗又是一位杰出的书画鉴赏家。
通过以上考察不难发现,厉鹗及其浙派同仁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史地研究,多集中在两宋时期,体现出突出的“尚宋”特征。清代中期严重的政治和文化高压是“尚宋”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他们有意识的文化选择。两宋作为华夏文化“造极”的时代,又为元朝所灭,因而生活在清代的士人在意识和感情上高度认同宋代,他们在创作和治学两个领域凌跨元明、追步两宋是相当自然的事情。这种文化认同处处又给人一种意味深长、曲折莫名之感。通过这种方式,清代士人某种不便言明的情绪得以畅达地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