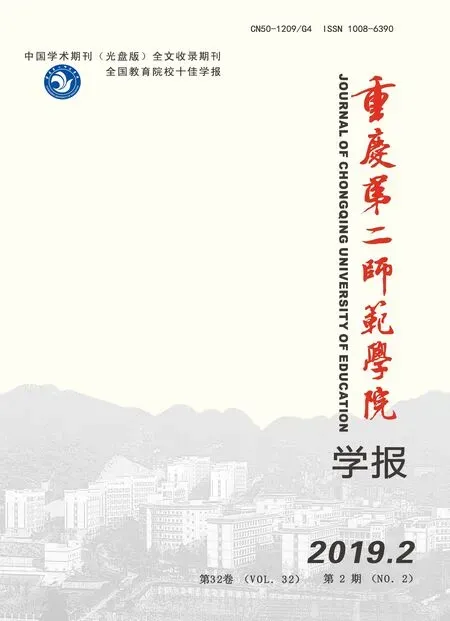论克尔凯郭尔的叙事反讽
——以《一个诱引者的手记》为例
王文勇
(南昌师范学院 文学院, 南昌 330029)
学界认识克尔凯郭尔的反讽概念基本上是基于其学位论文《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从存在主义哲学方面进行生存论的解读。较早研究克尔凯郭尔反讽的文章主要还是集中于其著作的文本解读,缺少把反讽概念放入其整个哲学、神学和文学创作中进行深层次认识的视野。“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反讽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1]“尽管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反讽的诠释从一开始立意就很高,但他对苏格拉底的理解总的来说还处在美学的层面”[2],或者仅仅把反讽视为一种间接沟通的方式,即“克氏的苏格拉底式沟通”[3]。近来,有学者逐渐在扩大认识克尔凯郭尔反讽概念的范围,“苏格拉底的反讽为伦理过渡到宗教做好了准备,他却没有完成这个过渡”[4]。也有学者发现“克尔凯郭尔的反讽是一种有伦理维度的存在论概念”[5]。
克尔凯郭尔在西方的哲学历史中搜寻到了苏格拉底的反讽立场。“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未知数、一个立场,这个立场证明是苏格拉底所特有的。我称此立场为反讽。”[6]193反讽是一种含蓄的立场,道出了西方反讽传统的历史精髓。而从《一个诱引者的手记》[7]则可以发现克尔凯郭尔文学创作的叙事反讽,这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人们对其反讽概念的认识。克尔凯郭尔一生醉心于反讽的生存策略。无论是就其生存美学而言,还是就其感官性创作本身而言,反讽是克尔凯郭尔叙事过程中屡试不爽的手法。
克尔凯郭尔在其小说叙事的过程中,频繁使用反讽的策略。《一个诱引者的手记》的叙事结构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在叙事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可靠叙事特征,人物、多层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立场呈现了叙事反讽方面的典型特征。“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所知道或感悟到的东西多于或少于另一个人,那么反讽就必然会在实际意义上或潜在意义上存在着。”[8]252所以,要理解克尔凯郭尔的叙事反讽,就应该抓住其小说中的人物和叙述者进行探析。
一、叙述者
《一个诱引者的手记》的叙述者不止一个,小说开篇的“我”(下称A)开启了整部小说的叙事。而A并不是讲故事的人,其只不过是抄写整理那本潦草的抄本。“此刻,我无法抑制我的躁动,无法掩饰我的焦虑,因为出于我自己的缘故,我决定把那份潦草的抄本整理清楚,那是我匆匆忙忙地在极度不安中偷抄下来的。”[9]121
叙述者A的躁动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充满焦虑?躁动似乎来自该日记的巨大吸引力,读来令人兴致盎然,躁动不安;焦虑似乎来自自己偷看别人的日记,导致的不道德感甚或焦虑。但是焦虑也有可能来自阅读(抄录)该日记的心灵体验。笔者倾向于后者的焦虑来源。因为A似乎并无故意偷看的意图,只不过被这本日记深深吸引住了。所以,A是一位作为抄录者的读者。
A的评述十分重要,常常显露出叙述者、叙述的作品以及其他叙述者的核心价值观。“现在看见了这日记簿,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用一种超自我的态度对自己及其处境的记述,这是一种真正审美的客观态度,这本日记的名称也是经过认真考虑选定的,它与所记述的内容完全吻合。”[9]122从该引文叙述者A评论这部小说的文字中,可以明白:第一,这部小说是具有审美意义的小说;第二,日记的叙述者是另一个人(下称B1),而且是“超自我”的叙述态度;第三,A对B1非常熟悉。从其后对B1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B1。叙述者B1追求一种诗意的生活,其写的日记不全都是事实,但也不全是虚构。这极为类似《红楼梦》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所谓事实与虚构的真假。
叙述者A评述了日记的材料来源和创作目的,评论极富美学意义。A似乎无意中透露了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创作准则,又似乎无意中告诉了读者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无功利性的,绝对不能为了出版而创作。不过,A是反讽式地说出这个意思。“从整个内容来看,这绝不可能是一部文学作品,他绝不会想到去出版。”[9]123所以,《一个诱引者的手记》的叙述者A不过是对小说的抄录而已,当然,间或也可以做一些评论。
如果进入这部小说的阅读中,读者就会发现原来小说的叙述人物均是“我”,但却是三个不同的叙述者:叙述者A、叙述者B1、叙述者B2。B1是所谓的诱引者约翰尼斯(出现在约翰尼斯的日记中,这是小说的主体);B2是约翰尼斯引诱的对象柯得莉娅(出现在柯得莉娅写给约翰尼斯的信中)。
上述三个叙述者承担了不同的叙述功能:A主要叙述小说即日记和书信的来源,同时进行叙述评论。若没有认真理解小说开头部分A的引导叙述,则很容易被小说的主体引入歧途,产生对小说的误读。B1承担了小说中日记的叙述者角色,是小说的主要叙述承担者;B2承担的叙述相对较少,主要是承担柯得莉娅写给约翰尼斯的信的叙述。
二、叙述分层
所谓叙述分层指的是叙事性文学作品,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呈现出故事套故事的多层次叙述特征。赵毅衡先生从广义叙述学的角度,对叙述分层描述为:“上一个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下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或叙述框架。”[10]264叙述的层次性特征表现为每一个层次讲述的是一则较为完整的故事,或者每一层次的故事是不同的叙述者重复叙述同一个故事。显然,叙述分层的依据是叙述者的切换和故事框架的完整性。
就克尔凯郭尔的小说《一个诱引者的手记》而言,由于该小说采用三个不同的叙述者,故而必然要在叙述的过程中,呈现出叙述分层的特征。A叙述故事的由来,即抄录B1的日记和B2的信件,以及对故事的评论干预,是第一个叙述层次;B1在自己的日记中叙述故事,是第二个叙述层次;B2在给B1的信中叙事,与B1同属第二个叙述层次。
A首先叙述小说的由来,是偶然的机会使然,自己遭受到了内心的煎熬和道德的谴责。“异乎寻常”的偶然性机会显示出B1对于自己的日记是作为隐私看待的,一直严密保管,不希望被别人看见。然而,偶然性的机会给予了A,A在排除内心深处的偷窥性焦虑和道德上的谴责之后,拥有了开启故事叙述的机会。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A重点介绍了下一层的叙述者B1和B2。A对下一层叙事的叙述者B1和B2均十分熟悉,这为下一层叙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且,A阐述对B1日记的理解,却又仅仅是A的观点而已。这很类似《红楼梦》中空空道人在青埂峰下一块大石头上“从头至尾抄写回来”《石头记》。
A是小说《一个诱引者的手记》的理想读者。其不但对下一层叙事的叙述者B1十分了解,而且对日记文本的事实与虚构部分均十分清楚。这样的叙述者真让人怀疑是不是B1本人。当然,这种怀疑是没有意义的。就小说叙事而言,A不仅具有叙述功能的意义,还有叙述分层的重要作用。没有叙述者A,该小说的分层不可能如此清晰。
A把自己比喻成搜查房间的警察。他不仅熟悉叙述者B1的现实生活和处境,而且对B1的心理境界也十分清楚。A向读者敞开了B1的心理状态,极大地提高了读者进行下层故事阅读的兴趣,促进了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A还非常了解叙述者B2。B2主要是在写信给B1的过程中进行书信体叙事,其叙述的内容远没有B1的日记多,但在整个小说中却必不可少。事实上,由于B1和B2的第二层次叙事涉及不同的叙述者,如何将两者叙述的内容组织在一起就是一个叙述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依赖叙述者A,当然,其前提是A对下一层叙事的两位叙述者均十分熟悉。A和B1彼此认识,而且关系密切,这不仅为下一层叙事做好了铺垫,而且为第二层叙事(即主叙事层次)中B2的信件来源提供了依据。
A详细叙述其创作的过程,构成该小说的后设叙事层面。学界普遍把这种后设叙事称为元叙事或元小说。“小说自己谈论自己,就是‘元小说’。”[10]299所谓“元”来自英文“meta”的前缀使用。笔者赞同傅修延先生的观点:“metafiction在台湾被翻译成‘后设小说’,本人认为这种译法是很有见地的。”[11]37有后设叙事就必然有叙述的分层。A的叙述是后设叙述层; B1和B2的叙述同时存在于另一叙述层上,构成了小说中日记和书信共存的主体叙述结构。
还有一个叙述层次不得不提:在A组织整理B1叙述的日记和信件,以及B2叙述的信件的过程中,存在一处叙述干预。小说在A叙述之后,进入第二层次叙事,该叙事包含两个部分:一是B2柯得莉娅的信件(只有三封短信);二是B1约翰尼斯的日记和信件。就在同一层次叙述的不同叙述者之间转换之际,小说文本插入了第三者的叙述干预:“假如说柯得莉娅没有她所爱慕的约翰尼斯的那种音域,那么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柯得莉娅具有同样的音色。这音色显然渲染在她的每一封信中,尽管她在表达上还不十分清晰,她的第二封信尤其如此。在这封信中,人们与其说是了解到不如说是猜测到,她想表达什么。然而在我看来,这不清晰的地方正是它的感人所在。”[9]132
上述叙述夹在B2的信件和B1的日记、书信之间,成了小说阅读过程中的另类。从叙述的内容来看,该叙述者显然不是B2,因为叙述中的“她”指的是B2;也应该不是B1,因为上述引文中提到B1时直呼其名,且B1是男性。所以,上述引文中的“我”应该是叙述者A。而A的叙述是不可能存在于第二层叙述之中,因而引文只能构成对第二层次叙述的评论干预,具有跨层叙述的色彩[10]276-280。
《一个诱引者的手记》收录在克尔凯郭尔的假名作品集《非此即彼》中,在该集的前言里,作者用假名维克多·艾莱米塔又虚构了一个后设叙事,用于叙述该作品集的来源。这或许可以成为“后后设叙事”。“我最好还是先讲述一下,我是怎样获得这些文稿的。”[12]2这些文稿来源于维克多七年前买的一张陈旧的文书写字柜,偶然的机会在这张柜子里发现了后来出版的《非此即彼》上下卷。可见,维克多不过是这些作品的整理者而已。但是这也构成了该小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叙事层面。
三、不可靠叙述
正是由于多个叙述者的设置,产生了叙述分层的结构。这种叙述结构充满了张力,经常会导致不可靠叙述的局面出现。“叙述不可靠性,指的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10]228可见,不可靠叙述指的是由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价值距离,导致了叙述者的价值选择与隐含作者的价值选择互相冲突。就《一个诱引者的手记》而言,叙述者A存在于后设叙述的层面,主导了元叙述的所有内容,其作用不仅是元叙述与叙述分层,而且该小说借助A道出了主层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他(B1)过着一种太精神化的生活,以致不可能成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诱惑者……他的踪迹是如此模糊不清……他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滋生剂,吸完之后就把他们丢掉,就像一棵树木抖落它的叶子一样——叶子枯萎凋谢了,而他却依然青春常在。”[9]126
叙述者A基本上可以代表隐含作者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其对B1的评述之中。隐含作者并不认可B1约翰尼斯是一位诱惑者,因为其实际上也是被诱惑者。因为B1自己过着太精神化的生活,例如宗教信仰,并不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而是远离我们的另一个世界。甚至,B2也难以判断B1是不是诱惑者,因为他的踪迹实在是太捉摸不定了。树木的比喻说明了B1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信仰义士,在目睹芸芸众生的感性生活之后,其毅然摈弃了这种生活。作为叙述者B1的约翰尼斯存在于真实世界之中,又不属于这个世界。
可见,在主层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存在于克尔凯郭尔所极力宣扬的宗教信仰之中,而不是俗世社会中感官性的审美生活。克尔凯郭尔对感官性的审美生活持否定态度,这也与主层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价值观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在《一个诱引者的手记》的后设叙事中,叙述者A似乎很担心读者不明白小说中隐含作者的价值观,花了很大篇幅继续阐述这个问题。A在信仰层面探讨了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
然而,小说主叙述层的主叙述者B1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在叙述层日记开始部分,B1有浓厚的市侩气,很会照顾女人,很容易取得他人的信任,似乎是一个蛮可爱的人。但是,其想做马车夫或仆人的欲望是出于得到美人抱入怀中的目的,则彻底暴露出叙述者B1的土匪习气、庸俗不堪。而且,B1是一个在黑暗中猥琐的偷窥者,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引诱女人的高手,似乎很类似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西门庆”。
显然,叙述者B1与隐含作者之间存在非常大的距离:前者是拈花惹草的猥琐男;后者是追求信仰人生的精神义士。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判若云泥,不可同日而语。B1的价值追求存在于俗世社会的形而下层面;隐含作者的价值观是“另一个世界”的形而上层面。可见,该小说的主叙述层次一开始就呈现了明显的不可靠叙述的现象。
四、叙事反讽
克尔凯郭尔没有给予反讽概念一个完整的定义,“若有人想找到一个明确的阐述,那却是徒劳的”[6]195。其反讽概念似乎是一个动态的主观性立场。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相关论述,反讽是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的选择,所选择的立场是主观性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尽管自己知道自己是知道的,但假装自己不知道,这是反讽的;同样反讽的是,尽管自己知道自己并不知道,但假装自己知道。反讽也可能以一种较为间接的方式通过对立关系出现,例如,反讽选择单纯、头脑简单的人,不是为了嘲笑他们,而是为了嘲笑有智慧的人。”[6]205在叙事作品中,全部或局部存在这三种反讽:第一种是带泪的笑,第二种是滑稽,第三种是嘲讽。
《一个诱引者的手记》的叙事反讽来自多个叙述者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叙述者A站在小说的框架之外,承担后设叙事,与隐含作者具有较为相似的人格。叙述者B1和B2处于叙事的框架之内,承担了主叙述层的故事讲述,承担故事的见证者叙事。“见证者这一手法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加以运用。他的眼睛既可向内转,从而使其自身成为叙述内容;抑或向外转,从而使得其他人物或社会事件成为关注的重点。”[8]267日记和书信体是见证者叙事的典型代表。B1在主叙事层经常“向内转”叙述自己的心境,又会“向外转”叙述自己的所见。
两个叙事层次的叙述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两个方面的叙事反讽:一是叙述者与作者之间,二是多个叙述者之间。“当叙述性人物有别于作者之际,便会出现一种反讽性差距;而当叙述者人物有别于自身作为事件的参与者时,则又会出现另一种反讽性差距。”[8]267小说叙事反讽来自叙述者自身的局限,只能存在其所属的叙述框架之内。但是《一个诱引者的手记》设置了多个叙述者来解决这个问题,故而将叙事反讽转化为叙述者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叙述者B1和B2存在于主叙述层面,专注于两人之间的生活境况之中,具有较为独立的世界体系。叙述者A主要存在于小说的第一部分,承担着日记来源、人物介绍和叙述干预等叙述功能,是后设叙事层的主宰者。A介绍B1的人格,本质上是在投射自己的人格,因为B1的人格主要存在于主叙述层面。当读者进入主叙述层面时,会惊讶地发现B1的人格并不是A所认为的那样。A认为B1不是一位真正沉迷于感性生活的人。而在主叙述层面,B1对女性的执念与挑逗却又呈现出典型的诱引者特征。孰是孰非?如此巨大的分歧与悖论,呈现了强烈的反讽特征。
然而,克尔凯郭尔似乎十分喜欢这种悖论,因为这种叙述者之间的分歧与悖论构成了令其神往的反讽意义。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存在许多截然相反的悖论:不幸与幸福,不要与想要,激情与绝望,恐惧与狂热,等等。在小说《一个诱引者的手记》中,A对B1的评价是一个精神纯洁高尚的人,而B1的自我呈现是一个专注于感官欲望满足的人,至少在日记的开始部分是如此。克尔凯郭尔在此放低了自己的姿态,冷眼观瞧两者之间的看与被看,不做任何对与错的评述。当然,这一方面来自小说叙述自身的局限或悖论;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似乎以此方式显示了生活悖谬的真理——存与在的隐与显。如果说A是一个隐在的理性,那么B1则是一位显在的感性。如此看来,小说《一个诱引者的手记》的叙事反讽,是克尔凯郭尔有意为之的。
不得不提,不可靠叙述在《一个诱引者的手记》中随着主叙述层面的不断推进,似乎在不断缩小,直至最后逐渐接近了可靠性叙述。主叙述层面的叙述悖论最为强烈,故而反讽的否定性效果也最为明显。A在后设叙事层阐述了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和人格——过着一种高度精神化的生活,不可能成为纯感官性的诱惑者。如果读者进入主叙述层面就会发现:B1对异性的挑逗与引诱,正是其纯感官性诱引者的症候。主叙述层一开始的不可靠叙述显然十分强烈,叙述悖论十分明显,反讽的否定性十分突出。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B1成功诱引了B2。这时的不可靠叙述达到了巅峰,叙述的悖论冲突不可调和,反讽的特征几乎要翻转叙述者的故事。事实上也是如此,故事在叙事反讽的顶峰之后走向了翻转。
小说《一个诱引者的手记》叙事反讽的翻转节点是“八月三日”的日记,也是该小说主叙述层最长的一篇日记,几乎占据了整个小说篇幅的一半。这足可看出,就小说叙事的架构而言,叙事反讽的翻转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从订婚到“尽一切可能安排使婚约破裂”[9]199,似乎就在一念之间,B1的价值观与人格发生了逆转,显然,这与A所认为的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一致。后来,故事在B1想方设法促使B2解除婚约的意图中展开,婚约的确解除了,B1获得了“精神化”的生活,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一致,不可靠叙述逐渐消失,叙事反讽的张力也近乎为零。尤其是在那些叙述者A所谓的“远距离作业”(即叙述干预)中,在婚约解除之后,B1否定了诱惑者的纯感官性追求,走向“精神化”的生活。叙事反讽也顺其自然地自我解除,克尔凯郭尔重新回归到寂静的夜晚,聆听莫扎特的歌剧《唐·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