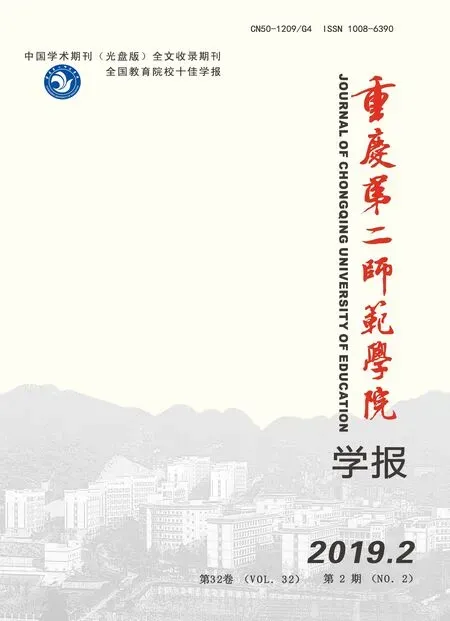立德夫人与清末反缠足活动研究
吴 敏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南京 210024)
立德夫人本名艾莉西亚·比尤伊克·立德(Alicia Bewicke Little),是19世纪英国一位重要的旅行作家。她1887年随其丈夫、英国富商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来华,至1906年归国,在华居留长达19年。在华期间,立德夫人除了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写作之外,还致力于反缠足活动,成为研究晚清时期妇女身体解放的一位重要人物。目前,学界对于立德夫人的相关研究不多,一般将其反缠足活动归于基督教传教士与“天足会”的活动中进行考察,忽视了立德夫人作为一个西方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关怀,她所代表的西方寓华女性群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被历史大潮湮没。事实上,立德夫人及寓华的西方女性在清末曾全力帮助中国设医院、恤灾民、立学塾,致力于破除女性缠足陋习,以不同的文化视角审视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外籍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说:“为今日中国计更有重且要者,则女子之缠足也……有道之士,深怜痛惜,大声疾呼,冀图挽救于将来,藉起疮痍于一旦,则有如立德夫人者。”[1]18798因此,探讨立德夫人反缠足活动之概况、特点及影响,反思西方寓华女性群体所起的独特历史作用,以及中西女性文化在清末对接时给中国女性社会带来的影响,自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立德夫人反缠足活动之概况
立德夫人1887年随夫来华之初,便从一个作家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在与中国女性接触的过程中,立德夫人对女性缠足的习俗大为震惊,之后便致力于破除这一陋习。1897年,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天足会”总会,禁止妇女缠足,提倡妇女放足。立德夫人联合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的夫人们首先在南方各省设立分会,进而扩展到全国各个地区。立德夫人设立此会的目的是专注于劝诫妇女缠足,使中华大地上的妇女有一双天然之足,获得身体上的解放。立德夫人采取刊印书册,至各地演讲,游说上层官员和地方绅士,宣传妇女放足的意义和方法来开展反缠足活动。
立德夫人曾将提倡放足的宣传书册、劝诫文告等发放到各个地区。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天足会所刊印的宣传文书种类颇多,有示谕文告类、通俗读物类,甚至有绘图本类,约30余种。这些提倡放足的宣传文书对中国民众特别是妇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立德夫人还到各地发表演说,宣传放足。从现存的立德夫人的演讲文稿中,可以发现提倡放足之初在中国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重重阻力。面对中国时间久远、根基深厚的习俗之一,立德夫人感到了废缠足的不易。她认为,这件事对她来说十分陌生,就像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里的感觉。立德夫人在一次演讲中直言:“有的官员架子大得像是把天地间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看到这我的心就凉了……站在这些听众面前,我才彻底意识到,与中国官员探讨最敏感的话题——女人的脚,而且是一个妇女与他们讨论,对他们来说有多么不可思议,这是闻所未闻的事。”[2]302作为西方女性,立德夫人没想到她关于“解放妇女的脚”的演讲在中国闻所未闻,这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不过是笑料罢了。这体现了中西方对待妇女问题的差异,西方女性认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中国社会却认为女性维权像是一场滑稽剧。这样的态度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中西方女性文化的巨大落差,反缠足遭遇的阻碍可见一斑。
随后,立德夫人意识到社会上层引导的重要性。立德夫人在《成都天足会近况》一文中提到,资州一位母亲在前任川督发出严禁缠足的告示后,给她的女儿放了足,在看到现任川督就职后没有重申严禁缠足一事,她又把女儿的脚缠起来了,可见官方立场的重要性。鉴于此,立德夫人开始游走于上层社会,并得到了张之洞、李鸿章等大员的支持,把有关禁止缠足的公告印成小册子发放,以官方话语带动百姓。这一招在社会上层产生了作用,“一位军官到这里来好像只是为了研究张之洞的文采,对我的演讲毫不理睬,不过最后还是签名加入了我们的天足会”[2]302。立德夫人还直接寻求皇帝对严禁缠足的支持。1896年,天足会曾通过美国公使田贝将一份建议书“循礼转交总理衙门,代为进呈”,建议书被驳回后又“拟再力请”,“必以此事得以上闻而后已”。立德夫人及其同盟者认为,废缠足一事“其权固操诸君上”,若“蒙明降谕旨,民间必自禀遵”[3]1757-1759。上行下效,立竿见影。《天足会纪事》提到,在李中堂的太夫人和李伯行的夫人及女儿放弃缠足的情况下,李筱荃的孙女也不肯继续缠足,要求放足。因此,立德夫人提倡的放足首先是从社会上层开始突破的,她游说上层官员和夫人来共同商议废缠足的事宜,从而形成了上层影响下层的一股新的社会风气。
立德夫人认为,缠足“不过事成习惯,一家之中,姑母如此,妯娌如此,父母之心以为吾女不如此,则择配联姻,必致贻门楣羞。推此一心,使天下之为母者,一乡也,一邑也,一国也,遂莫不如此矣”[4]889。可见,废缠足的根本阻力是中国传统风俗习惯,而缠足陋习绵延如此之久的原因是儿女婚配问题。由此,她主张民户之间相互约定并实行经济制约。《戒缠足丛说》记载,重庆有殷户二百五十多家互相之间约定,家里的女儿不缠足,儿子不娶缠了足的媳妇,如果有违背约定的人家,就自罚银两,并将这些银两分给贫苦人家中的女子,助其妆盒。此外,立德夫人在男校演讲时提倡男学生娶天足女生并对此怀有乐观的态度,“女校约70名学生,隔壁的男校学生更多,所以,为姑娘们找婆家没有一点难度”[2]286,使天足女子的婚配问题有了解决之道。立德夫人还鼓励兴女校,她认为在女学堂中上学的女生,其接受能力和开放程度是高于普通女子的,她们可以做到寻常姑娘所做不到的,“此等学生来学时即可渐渐劝其放足”[5]18。更为重要的是,女校能够使她们获取知识,培养其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由于女学兴起,妇女思想逐渐开化,女子婚配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加上政府及上层人士的引导,天足会的鼓励和提倡,社会风气开始有所转向,男子开始乐意迎娶学塾中的女子,出现了“问何娶乎尔?曰:娶其大脚而读书尔”[6]19428的现象。
综上所述,立德夫人的反缠足活动,主要以劝诫为主,辅以经济惩罚。《天足会陈词》说:“欲民间之渐除此害,莫若使之捐税而由天足会经理其事。凡会中不缠足之妇女,即任稽查。”[7]19083逐渐开始由劝导向禁罚转变。另外,立德夫人认为,缠足陋习虽然在中国女性中兴起,但根本原因却来自男性。所以她每到一地举行反缠足演讲集会前,总会“为上层社会的年轻男人们举行一次集会”[2]291。她向中国的士人发出了深切的期盼,希望取得他们的帮助,“……诸君子情殷谋国,且家中各有妇女,所望各立良法,与天足会相得益彰,将贵国一半之人,是受其赐,岂徒喜吾道之不孤哉”[6]19430。立德夫人在反缠足活动中非常注重方式方法的运用,以著书作论,广泛印发于各地作为敲门砖,四处奔走演说,将不缠足活动广为传播;以劝令长官、绅士带头反缠足,作为权威引导,最大限度将反缠足的言论扩展开来,身体力行,一度成为启发中国妇女身体意识觉醒的漆室微光。
二、立德夫人反缠足活动之背景
立德夫人作为一个西方女性,她为什么要反对中国的缠足习俗呢?她又有怎样的独特条件能将活动开展下去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19世纪的中国与西方社会背景大不相同,女性生活相差甚远,不同的文化视角和强烈的“道德教化”使命促使西方寓华女性开展反缠足活动。早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率先提出了“男女平等”,西方妇女问题自此已经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耕织一体的小农家庭经济结构和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却使女子依附于男子,女子只承担生育和家务的角色,只是男子的附属品。在清末孱弱的时局中,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凸显,立德夫人的反缠足活动是在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对接下做出的反应。在她看来,当时的中国是落后的,她回到天津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新修的铁路和火车头。同欧洲相比,这铁路和火车头只能算小孩的玩意,但仍使我们感到恍若穿越了好几个世纪”[2]1。面对落后了“好几个世纪”的中国,文明的优越性促使她以一个强者的姿态来劝诫弱者,帮助她们更好进步。这就是所谓“帝国的女人”所要承担的“道德教化”的责任。所谓“母性帝国主义”,即“当她们在殖民地时,与她们的男性同胞一样,相信身为演化程度较高的白种人的一分子,肩负着一种道德责任,理应协助在地社会产生文明蜕变,她们认为帝国的女人必须解放与她们同性别的殖民地的女人。换言之,这正是她们背负的白种女人的重担。”①虽然当时中国与印度的处境并不相同,但是在她们的意识中被认为是相同的。
立德夫人认为,近代中国正处于各大国“环而相瞩,各自谋其应得之利益”[6]19427的局势中,而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男女人口是否同心协力。如今,在国家孱弱之时,占据人口一半的中国女性因缠足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无法帮助男性有所作为,反而表现出愚昧无知。“中国女子,疲于精神,劳于猥贱卑琐之举,矫揉造作,以修容饰媚为工,闭塞文明,造成不识不知之现象。”[6]19427与西方女子相比,她们身上的缠足陋习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个国家文明的不合时宜。立德夫人在跨国视角中看到了巨大的文化落差,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重视妇女的,以之观照中国妇女,并为破除妇女缠足陋习而发声。国度背景的差异和“道德教化”的责任感是立德夫人决定反缠足的出发点。
然而,寓华西方乃至英国女性并非只有立德夫人一人,为何废缠足由她首先提出而又能够实行的下去呢?笔者认为,其中很大的原因来自她的丈夫阿绮波德·立德——这位第一个驾驶轮船通过长江三峡进入中国西部、成立重庆利川保险公司的英国富商,也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在中国最为风雨飘摇之际进入中国的外国商人。所以,立德先生身上带有帝国主义“霸权”的气味,他对于反缠足一事的态度是强硬的。他在《扁舟过三峡》一书中曾经提到:“如果我们有勇气推翻龙的宝座,发布一项从今以后不得毁伤孩子们的脚的禁令,我敢肯定,这项命令一定会得到遵守,开始可能有人不大高兴,以后他们会感激的。这样的做法从其他角度看,会认为不正当,但从人性角度来看,是完全公正的,在中国历史上,也常有不止一次发布赦令的先例。众所周知,满族人就曾对不情愿的人民强制推行留辫子,还强制穿着袖口裁剪得像马蹄一样的窄袖子衣服。”[8]160在他看来,只有统治者强行推行反缠足政策才可能改变这一现状。这无疑更加坚定了立德夫人反缠足的决心,以及她希望取得中国上层人士的帮助这一方法的实行,她拥有利用丈夫的商业网络拜访一些朝中大员和地方绅士并劝说他们支持反缠足的便利条件。由此,她所发表的演说才具有吸引力和话语权,使她和旅华的西方女性能够充当中国妇女的发言人。可见,立德夫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力支持是她能够发起这项运动的外在基础。
立德夫人秉承着世界女性同为一体的人文关怀,并有意将它落实,“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以终止缠足”[9],这也是她率先发起反缠足活动的原因。立德夫人早年游历中国,经常得到中国女子会的帮助,但是这些世家少女却往往“因缠足致伤而亡者,大抵十居其一……诸病丛生”[6]19430,有的人由于缠足而导致双脚溃烂,有的人因为解开裹脚布而导致双脚残疾,最后只能靠膝盖走路。她们不仅无法保持健康,甚至会丧失生命。在清末动荡的社会中,“在疯狂的团民以及肆无忌惮的俄国和法国士兵面前,缠足的妇女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柔弱的妇女死去,给了幸存的男性亲属以沉痛的教训”[2]344-345,中国女子虽同为女性却遭受着残酷的束缚,同情心使她萌生了帮助她们争取身体解放的想法。
此外,立德夫人发现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由于缠足而于百事不利。“以余所见,四川全省妇女,无不缠足,往往吸洋烟以止足痛,或借此以消永日之无所事事……妇女居室,百事漫不管理,则奴仆辈必成群嬉戏”[6]19427,家范不成。缠足妨碍妇女谋生。立德夫人在沪期间发现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大都不愿雇用缠足的妇女,因为妇女缠足使她们做事极为不便,这些妇女甚至没有办法进入纺纱局、轧花局、缫绦局等诸多需要女工的地方。中国的女子因为缠足的缘故,只能留在家里处理家务,将生计、生活之事全都仰仗男性,形成一种女子坐食拱手的现象。女子无法经济独立,人身与思想便不能从依附中独立出来,这样一来,自觉争取权利又从何谈起呢?在接触中国女子的苦楚后,立德夫人发出“今中华之待妇女,无故而苦楚其足,且不徒双足之苦楚已也,一肢忍痛,全体积衰,更为推而广之,全地,犹一身也。华女不安,西女即因之而不乐”[6]19426的感叹,可知她设天足会“力劝华女,保其天然之素足”[6]19426是出于将世界女性视为一体的女性同情。她热衷于女权的争取,认为一旦帮助中国妇女反缠足成功,她们树立的权威和道义形象,有利于她在英国所展开的争取妇女选举权和财产权的活动。因此,立德夫人此举是以一个不同于男性身份的女性视角思考问题的结果。
我们总是惯性地认为立德夫人反缠足是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事实上,她对教会的态度是若即若离的,她所提出的反缠足想法并不完全是对基督教义的阐述,相反,她在创会之初就极力将天足会单纯化,尽力冲淡基督教义的色彩。她在创会致辞里提到:“我们的宗旨,与其说是为了对抗一种原则,毋宁说是为了移除一种时尚。尤盼会中女士竭尽所能,根据自己的想法,从周遭开始,径行以自认最佳的方式,推动本会目标,无须等待委员会的指示。须知,我们只要说之以理,诉诸美好的品味与感受,那么,缠足这种毫无道理可言的时尚,是很有可能被扬弃的。我们的目标固然切合基督教的教诲;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广邀各界的协助与支持,不论其动机是出于伦理学的、医学的,还是经济学上的考量,或者纯粹出于对那些成千上万被迫受苦却无力抵抗的幼女的无比怜悯,我们都欢迎。”[10]598可见,立德夫人认为反缠足纯粹是移除一项鄙陋的“时尚风俗”,是为了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以便于扭转整个社会的风气,从而引领一种异国女性的时尚风潮,打开她们参与中国社会的空间。她意识到当时基督教基于教义会禁止信教的中国人参加祭祀等传统活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适应,这在《我的北京花园》中得到印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基督教,很显然,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的寺庙,其财务都一定会日益窘困,其建筑会日渐颓坍,最终这些寺庙会逐渐消失于中国大地之上,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见亦有意安排的吗?”[11]220-221这会使得中国人认为,与基督教密切联系的文明都是他们的威胁,并由此爆发排外运动,从而使得天足会失去很大一部分支持力量。从这一层面来说,立德夫人对于教会的态度是趋于分离的。
然而,立德夫人等西方寓华女性并不通中文,她们的活动范围也有限,如果没有传教士的帮助,根本无法深入更广大的地区,所以她们必须借力于各地教会,通过他们的翻译传达反缠足理念,利用他们已有的社会网络,将天足会的宣传著作和言论发放扩散到广大群众之中。因此,传教士又成为她们最为重要的喉舌。从立德夫人的游记中也能发现,她到各地演说时都会借助当地教会的各种资源——翻译人员、文画派发助手、会场、向导、食宿等,并且鼓励教会设立天足分会。毕竟,立德夫人与西方传教士拥有共同的文化、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分离的乡情,从这一层面来说,她对于教会的态度又是趋于亲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完全将立德夫人的反缠足活动归于基督教传教士反缠足活动中,传教士只是作为同社会各界人士同样的身份参与了这项活动。从根本上说,反缠足活动是由立德夫人等西方寓华女性发动领导的废除缠足陋习的 “风俗和时尚之属”[9]。立德夫人所秉承的世界女性同为一体的女性关怀是将反缠足活动持久进行并鼓舞中国妇女起来维权的最主要动力。同时,她热衷于女性权利的平等自主,有一个建立世界女性国际组织的目标构想,并希望在帮助中国女性身体解放的过程中得到初步实现。因缘际会,使立德夫人成为西方寓华女性群体中反缠足活动的发起者,这也是她不同于传教士反缠足的独特之处。
三、立德夫人反缠足活动之影响
立德夫人在建立世界女性国际组织的宏伟目标构想下,基于上述原因联合西方寓华女性开展的反缠足活动,扭转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缠足风气,助推了中国女性身体的解放,并唤醒了中国士人对破除社会陋习的自觉努力,是中国女性争取身体解放的漆室微光。立德夫人此举反映了中西女性文化在清末的激烈碰撞,以及西方寓华女性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审视中国古今未有之大变局之所以发生的新视角。
在立德夫人等西方女性来华时的清末,女性缠足陋习已经存在于中国社会数千年。至少从立德夫人等的认知来看,中国妇女甚至小女孩都是悲惨的,她们没有精神上甚至身体上的自由,女性角色被长期固定于一种奴性的状态。因此,立德夫人等带着母性的同情和道德教化责任的初心,开始了反缠足活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们极力打开不缠足风气的大门,吸纳更多人加入不缠足的队伍,成为中国反缠足持久战的重要力量。1900年,立德夫人在香港演讲时说,“今21处通商口岸,已设支会”,共有“会友30万人”[12]1678。直到1906年立德夫人归国前夕,中国天足会上海年会仍然吸引了不少人参加,“来者实多,虽多派数人照料归座,后至者仍无隙地也”[13]24962-24968,中国天足会的影响也达到了立德夫人任内的顶点。仅在上海一地,由天足会派送的反缠足小册子就有95000多本。虽然当时中国缠足的妇女依然很多,但不缠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风行各地。天足会各分会来函报告当地放足情况,皆十分乐观:“照现在兴盛之情形,似无须再设分会,因人心已经大动,咸以放足为乐也。”[13]24962-24968至1906年,中国缠足风气已经开始得到扭转,民间普遍接受了放足的思想,只是还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别。
反缠足活动唤醒了中国女性及有识之士的自觉,促进了女性身体解放的进程。立德夫人曾感慨:“妇女不仅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且是另一半人的母亲。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和抚养的儿子会与他们的母亲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缠足在中国蔓延开来以后,中华帝国从没诞生过一个赢得万民景仰的男人。”[2]345中国濒临危急局势,国弱种弱,文明败落,再不重视妇女的地位,将何去何从?这对当时抱有富国强兵愿望的中国士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们对妇女解放问题展开自觉的努力。郑观应对缠足作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认为中国缠足之习俗是“戕伐生质以为美观,作无益以为有益,是为诲淫之尤”。[14]康有为将缠足比作古之刖足,认为女子缠足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是中国独有的鄙陋之习。当时中国文人在甲午战败、国家内忧外患、自信心丧失殆尽的情况下寻找富国强兵的出路,却因为缠足的陋习常使“外人拍影传笑,讥为野蛮之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15]242
有识之士发起了对缠足陋习的大规模反对活动,开始思索中国的妇女问题。《记天足会演说事》载:“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该女士立德氏,创立是会以旋……一时豪杰之士附从其说,逢人说项,到处宣扬者,难以枚举。于是乎各省之分会设矣,督抚之告示张矣,缙绅女子多有相率不缠足者矣!”[4]889西方寓华女性所发起的反缠足活动,激发了中国士人、中国妇女对反缠足的自觉努力,积极创办不缠足会,星星之火势必燎原。正如明恩溥所说:“这种无用而残酷习俗的冲击来自在中国的外国人。而中国人自身的觉醒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可喜的是,当前在这个帝国的中心,这种觉醒已经开始。”[16]260但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首先是由男性领导发起的,这说明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妇女自主发起解放运动的条件。
“中国之所以积衰者,无他焉,只缘于才识之不到与见闻之不远耳。”[1]18799立德夫人鼓励书本发放和兴女学对后来的女性思想启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两项措施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客观上将西方平等自由的观点通过西式的教育和书本渗入了众多女学生的头脑。李提摩太对此评价说:“中国深居漆室,非朝伊夕矣,幸得一灯相饷,心目间遂启微光。”[1]18799林乐知当时敏锐观察到了中国女性社会的变化并指出:“最近奋激之现象,为前古所无者,莫如女界。彼欧美各国之女子,既以释放而大显其能力……乃东方之女子,数千年幽闭于一室者也,亦且相兴,抉网罗破藩篱而出,如迅霆,如惊涛,其进步之速诚可怖也。”[17]24973-24974在19世纪末,中国女性社会已经开始摆脱封建束缚的藩篱,正发生着“迅霆惊涛”般的变化。中国女界的进步离不开立德夫人等西方寓华女性的推动,正是她们在促使中国女界觉醒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李提摩太称赞立德夫人为“巾帼之伟人,海邦之益友也”,一些中国人称她为“第二个观世音菩萨”,这是对她极高的评价,代表了当时中国一部分思想开放的人对其反缠足行为的肯定。
四、结语
立德夫人的反缠足活动,不仅反映了中西女性文化在清末的激烈碰撞,更体现了清末西方文化已经渐入中国,并且逐步占有强势地位。立德夫人等西方寓华女性通过反缠足活动实现了在中国的社会参与,虽然她们这种反对中国陋习的思想产生于“母性帝国主义”的“文明教化”使命,不免会忽视中国本土社会的想法,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它是符合我们对于文明的要求的。毕竟,缠足习俗将女性桎梏在性和生育的特定位置和功能上,对中国妇女而言是非人化和不人道的。立德夫人等西方寓华女性的反缠足活动不仅推动了中国女性争取身体上的解放,同时也影响着她们自觉寻求思想上的解放。正如胡适在《慈幼的问题》中所提到的,基督教传教士虽然在我们看来是一群文化侵略者,但是至少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些许的新文明和人道主义,他们设立医院、开设学堂、提倡放足,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却是这一片天地的开拓者,他们把我们从迷梦中唤醒,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应该有所感激的。立德夫人等西方寓华女性虽不同于传教士的身份,只将反缠足活动作为“时尚风俗”之属,与教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却依然在中国近代女性社会文明中起到了启蒙作用。立德夫人等西方寓华妇女的反缠足活动启发了国人对女性社会的重视,根深蒂固的缠足陋习被逐渐拔起,中国女性不论在身体上、智力上、精神上都慢慢获得解放,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中国女性也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同时,渐渐跟上了近代世界女性前进的步伐。从女性社会变迁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化,以立德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寓华女性所起过的作用,不应被时间湮没。
注释:
①Antoinette M. Burton 认为,在“白种女人的重担”意识形态之下,就算19世纪末的印度女性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参与社会改革,在“母性帝国主义”的论述里,印度女性依然只是被动的、无助的等待她们拯救和解放的殖民客体,是她们彰显其帝国女性主义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