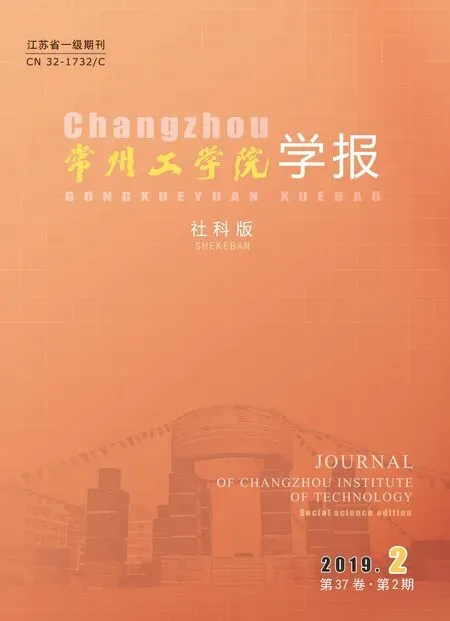论苏童小说的恐惧色彩
许萌,杨波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恐惧”写作的酝酿及生成
“在美学上色彩包含两方面内容:主观色彩和客观色彩,客观色彩的涂抹、渲染,可以造成一种特定的氛围、色调”[1],不同的文本色彩伴随着不同的审美感受,苏童的作品给读者留下的正是这样一种幽美诡谲、哀艳阴柔的审美感,在作者的蓄意架构中,字里行间充满恐惧色彩。与美国作家爱伦坡令人头皮发麻的恐怖小说不同,苏童虽然也有大部分作品涉及死亡、复仇、谋杀,却不是以制造凶杀为写作目的,因而在本质上与爱伦坡的恐怖小说不能比肩而论。恐怖义为害怕、畏惧,而恐惧“整体上是一种高于恐怖的情感……恐惧着力表达的是一种孤独的凄凉和庄严的沉重,一种细腻的受命运驱策的悲伤和宿命感”[2]。恐怖与恐惧仿似一对孪生子,但实质上恐怖往往倾向于描绘客观环境,恐怖带动着恐惧情感的发生,而恐惧则偏重主观感受,凸显环境对情节的推动,展露人物的内心。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苏童小说有意营造这样一种恐怖的氛围/人/情/事/物,塑造了许多令读者感到恐惧的形象。虽然作家的创作宗旨不在于专写恐惧,但行文中时时流泻而出的“恐惧色彩”着实为苏童文学创作的特质之一。有些评论家注意到了苏童小说中的恐惧色彩,如季红真认为《米》中五龙的命运“可以读出作者对人类本性中原欲的恐惧”,“叙事成为一种对窥视到的历史与人性残酷本相的恐惧感的宣泄”[3],王德威也曾评价“苏童的故事是可悲恐怖的”[4]。与此同时,也有些研究者认为苏童的作品普遍带有“颓废色彩”,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并不贴切,从作家的蓄意营造与接受者的阅读感受来看,实则是“恐惧色彩”作祟。但无论研究者们如何众说纷纭,归根结底还是要从知其人、论其世来探究其本源。
罗曼·罗兰在分析贝多芬、托尔斯泰等艺术家时说:“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为之戕害,内心为之破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5]对于苏童来说,这些生活的磨难在他的童年时期恰好都经历过。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只有4岁的苏童来说,“这意味着我逃脱了许多政治运动的劫难,而对劫难又有一些模糊而奇异的记忆”[6]。比如一阵阵的枪声、随处可见的“打倒×××”的标语、被批斗的人挂着纸牌在街上走来走去……“‘革命’、‘历史’在苏童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是残酷、血腥、暴力的印记,这样的童年记忆与经验对他后来的‘文革’背景小说产生了深远而潜在的影响”[7]70。除此之外,对作家影响最大的是在9岁那年患了肾炎和并发性败血症,在家休学养病的大半年里,“苏童没有吃过一粒盐,每天都是喝一碗又一碗的中药。生病造成的痛苦因素挤走了苏童所有的稚气的幸福感觉,九岁的苏童,便尝到了恐惧死亡的滋味”[7]71,正是童年时对死亡的深刻体验,使作家作品里随处弥漫着恐惧的气息、生命的脆弱以及命运的无常感。苏童自己也曾说:“我现在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描绘死亡,可以说是一个惯性,但这个惯性可能与我小时候得过病有关。”[8]这两段童年时期的重要经历影响了作家的性情和气质。青年时期的苏童前往北大读书学习,他一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一方面开始从事大量的诗歌创作,作家孤独冷睿、诗人般的忧郁气质也随之凸显。在后来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中,苏童又逐渐受到了以细腻见长的苏州评弹、浪漫浓厚的民间故事的滋养,同时又接触到现代绘画,并受西方福克纳(福克纳小说常以凶杀、乱伦、梦魇为题材,以挖掘人物内心来表现复杂人性的主旨)等的影响,这些都使苏童小说创作中的“恐惧色彩”愈加凸显和浓厚。
纵向来看作家的创作经历,从21岁的处女作《桑园留念》开始到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从中篇小说《罂粟之家》到大红大紫的《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后分别被改编为影视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茉莉花开》),即使是在完成了“《平静如水》《仪式的完成》《逃》等,被视为是转换了艺术视角——走出了枫杨树之后的作品”[7]74,苏童小说中都或显或隐地散发着“恐惧”的火石磷光。他后期的“香椿树”系列小说、“红粉”系列小说等依然保持并延宕了“恐惧色彩”这一文本特质。“文学创作是与作家心理紧密联系的一种艺术活动,恐惧在苏童的小说创作中是他心理和情感的一种情绪记忆,也是他审美情感核心内涵的体现。”[9]苏童将自己的思考及人生感悟汇聚在笔端,写人情世态,写别人,也写自己。那么,作者究竟在恐惧什么呢?在他诡艳生动的文字之下又隐藏着怎样的秘语?这需要我们在他常写的生死、命运、逃亡、人性幽暗等主题之中细细品咂。
二、“恐惧色彩”的多维展现
首先,在审美的主要对象,即小说的人物塑造方面,“枫杨树”故乡系列的代表作《米》中五龙的残暴,他对米的疯狂迷恋,对女人的变态掠夺,以及对敌人使用的复仇手段都令人不寒而栗。起初他是从乡村逃荒到小城镇的流民,是一个因为饥饿潦倒给地保跪地磕头的可怜者,进入米店后在强烈的复仇欲望驱使下,用毫无道德底线的手段打击报复身边的人。令人恐惧的除了五龙本身阴戾、极端、变态的性格和行为外,还有从受虐者到施虐者转变的整个过程中人性阴暗、人格分裂甚至变态心理的深层次表现。五龙这一人物是带有病态色彩的存在,他在整部小说中起到了加强恐惧、制造紧张、迎合读者期待视野的作用。另一部“枫杨树”故乡系列的代表作《罂粟之家》展现了乡村一个家族的淫乱和仇怨。地主刘老侠的剥削,被统治贫民陈茂的复仇,阴森森像鬼一样穿着一身白衣的刘素子,偏执又病态的刘沉草……这些人物共同营造了一种颓败死寂、古老沉重的历史气息。另外,乡村的贫困、疾病、土匪和仇恨都被苏童潜在地描写出来,在作者充满神秘主义和宿命论思想的叙述下,整部小说犹如浸泡在罂粟毒汁中一般,骨子里是恐惧冰凉的。再如苏童创作后期的“香椿树”系列小说代表作《刺青时代》,不同于前两部古旧气息较浓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小说,它的现代性较强,在篇幅和可读性上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它所呈现的人物形象给人的冲击会更大一些,如怀孕的母亲在小说开头就惨死于冰河上,暴戾无常的父亲王德基有诱奸女儿的嫌疑,去铜厂偷铜的大喜翻墙而死……最令人背脊发凉的是瘸腿少年小拐的阴冷和偏执,他被人推向火车而丧失一条腿,在成长中受尽欺凌却又不甘心忍辱偷生,最终靠着自己的血泪和武力成为地方一霸,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同五龙、陈茂一样,他一开始受尽屈辱,潜意识的“变态”层被开掘,再慢慢凭借自己的努力、心机或运气,完成由弱者向强者的转变,这个过程是撕心裂肺的,这种被压抑的人性一旦爆发,平静的生活将被打破,潜在的杀戮与血腥、暴力与恐惧也将浮出水面。苏童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性阴暗以及被异化的一面,在看似平淡冷静的叙述下慢慢酝酿,实则每个主人公的设置都煞费苦心,甚至他们在每个阶段应该呈现怎样的状态他都作了精心安排。苏童的小说之所以充满恐惧色彩,一部分与常写的“灾难、宿命、逃亡、暴力、人性的阴鸷、死亡、性”等主题密不可分,另一部分与作家对人性和灾难的思索、凝视和个人叙述风格相关。此外,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还有一个问题,即在作家众多的作品中关于正面的、讨喜的女性形象明显缺失,作家笔下的女性大多阴鸷凄惨,要么大胆泼辣,要么狠如蛇蝎,鲜少有温柔明朗、贤良淑惠、代表传统美德的那般女子,即苏童笔下的女性普遍缺少“真善美”,这样呈现出的文本自然少了温情对冷漠和残忍的消解,有意营造的恐惧色彩也愈加浓厚。如短篇小说《离婚指南》中,杨泊为了情人跟妻子离婚,使尽浑身解数却让自己越来越累,妻子表面的温顺、内在的刚烈,情人的冷漠和自私自利也十分具有张力,文中并没有家庭的温暖,也没有爱情至上的快乐,有的只是两个女人冷冰冰的对“猎物”的争夺和心理战术,自杀、毁容、打架等等,把现世生活中的人性之恶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中并无恐怖的情节或人物,但小说饶有深意地指出生活、婚姻的真谛,未免令人细思极恐,同时也表现了作家从生活层面到精神层面对男性和女性婚姻情感的忧思和恐惧。
其次,就审美氛围而言,苏童的小说无论篇幅长短,随处可见恐惧色彩的影子。小说的审美氛围离不开环境、色彩、语言、意象的有机结合,典型的如短篇小说《妻妾成群》中,以腐朽的陈家大院为背景,“痛苦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柴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残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10]。文中常提到的后花园枯井,也幽幽地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在封闭的空间里,小说的恐惧色彩更加浓郁,而作者直接描写:
她似乎就真切地看见一只苍白的湿漉漉的手,它从深不可测的井底升起来,遮盖了她的眼睛。……在又一阵的晕眩中她看见井水倏地翻腾喧响,一个模糊的声音自遥远的地方切入耳膜:颂莲,你下来。颂莲,你下来。[11]213
把恐怖氛围推向了高潮,颂莲就是长期在这种压抑、充满病态的生活圈内被活活折磨得精神失常。又如《园艺》中孔先生与太太争吵未归,后因一只金表被几个少年勒死埋在自家的花坛里。失踪一个多月后孔太太面对着她心爱的香水月季时,只见:
一朵硕大的花苞突然开放,血红血红的花瓣,它形状酷似人脸,酷似孔先生的脸,她看见孔先生的脸淌下无数血红血红的花瓣,剩下一只枯萎的根茎,就像一具无头的尸首……[11]26
在苏童的笔下,除了精心设计的恐怖情节外,连日常的生活、随意的散笔勾勒都充满了恐惧与不安。作者的审美偏好自然影响到审美意象的选择,比如湿漉漉的南方小镇,灾难重重的枫杨树村,暗红妖冶的红罂粟,塞在女人子宫里白花花的大米,漂着尸体的河流,阴森的枯井,神秘的梦境,冤屈的鬼魂,泛滥的洪水和瘟疫……这些都是作家小说里的常客,能集中并且有力地证明苏童小说中恐惧色彩的分量。除审美意象的择取外,心理描写也对审美氛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对病态人物的细致展现极容易引起读者情感与心灵的共鸣。除上述苏童笔下五龙的受虐与施虐,小拐的偏执与分裂外,还有精彩的剖析女性病态心理的小说。如在短篇小说《你丈夫是干什么的》中,孕妇和女友聊天,表面是和谐愉快的,实则暗藏心机,孕妇有意炫耀自己的幸福来可怜女友的离异,女友拐弯抹角地提示孕妇将遭遇家庭危机,小说又从两个女人的博弈转至现实生活中两性的婚姻问题,孕妇内心惶恐怕丈夫外出偷情,半疯半傻地把女友的杀虫王喷向熟睡中丈夫的脸。这样一出家庭闹剧正是千万个家庭、妇女、两性关系的真实写照,集人性的猜忌与攀比、阴暗与毒辣于一文,孕妇的心理描写推动情节发展,因而全篇笼罩着一种沉重、压抑、恐惧的气氛。
最后,从审美体验来看,曾经有读者因为读小说《米》夜晚被吓醒而谴责作家。在短篇小说《仪式的完成》中民俗学家抽到鬼符的场景同样令人毛骨悚然:
一个又一个八棵松人顺利地通过白发老人的手臂,人鬼迟迟未出现。民俗学家脑子里闪现过某个念头,但他想这种结局未免太戏剧化了。……民俗学家莫名地打了个寒噤,他把元宝交给老人,他想这不可能,这未免太戏剧化了。老人打开那只元宝后开始慢慢地朝上举,紧接着他清晰地听见老人的声音,充满灼热的激情的声音。
鬼。
鬼在这里。[12]
这种“拈人鬼”的仪式令审美者感到莫名的诡异,以及感觉到人与万物相关联的神秘力量,在苏童睿智、理性的笔下,往往一句话就令人心惊胆战,这归功于他的小说语言艺术赋予了读者强烈的心理体验和真实的审美感受,因为“对于指向外界刺激的感觉来说,感情是指向主体内心的一种主观体验,任何一种感觉,都会同时伴生这种心理上的内体验。对于这一点,感觉敏锐、感情丰富的文学艺术家更容易体会到”[13]。
苏童是位优秀且多产的作家,在他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其大量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这些颇受追捧的影视剧更加印证了其小说中所含的“恐惧色彩”这一文本特质。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原《妻妾成群》)中阴森诡谲的宅院,暗黑色调与大红灯笼的强烈对比,在午夜传来三太太梅珊幽怨的唱戏声,男权核心陈佐千只有声音却从未露脸的神秘……电影集声音、画面、色彩,流动性、文学性、艺术性于一身,这些直观的元素都在无形中增强了原著中已有的恐惧感。又如《茉莉花开》(原《妇女生活》)中,茉在半夜悄悄地偷窥女儿和女婿的私生活,莉对丈夫的变态占有欲导致了丈夫的自杀,阿花流产时鲜血染红了白裙子……除了电影镜头里阴森飘动的白布帘、黑暗中猛然出现的人脸等一系列刻意营造的恐怖效果外,茉莉花母女三代人无限循环的悲惨命运才是最令人心生恐惧的源头,影视作品正是通过层层设置的“外像”直扎到生活、人性的最本质,扎到人的心里去。《大鸿米店》(原著《米》)则更甚,为了凸显小说的主旨——人性恶和幽暗的一面,整部电影的色调都置于红与黑的交错中,尽显沉闷压抑,在视觉和心理上都形成巨大的冲击,这些改编的影视作品都较好地保留并呈现了苏童小说中“恐惧色彩”的原汁原味。
三、“恐惧”创作的共性与个性
“文革”后我国迅速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开天辟地的新纪元造成的颠覆与重塑局面使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受到较大的冲击,恐惧与迷惘更是当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态。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文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与“寻根文学”相继兴起,知识分子逐渐走出伤痛,把目光转向探索人生、挖掘人性上面,开始寻找新时期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随后,以苏童、余华等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群异军突起,“马原在1984年发表了《拉萨河的女神》后,紧接着残雪、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作家的作品也给中国当代文坛以巨大的冲击。这场先锋小说运动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批评家确认并广为接受的先锋小说的创作有着更为鲜明的‘文体’实验色彩”[14]。先锋作家在叙事、语言、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将生存与死亡、血腥与暴力作为笔下的常客(可参阅胡西宛的《先锋作家的死亡叙事》),尤为鲜明的是先锋作家的作品中普遍存在“恐惧色彩”这一文本特质,正如摩罗、侍春生所作的评价:“八十年代崛起的一大批作家,其文学成就的基本依托就是对这种令人恐惧令人绝望的精神逻辑和生存真相的揭示与演绎。”[15]以下将择取几位先锋作家探究其小说中“恐惧色彩”这一文本特质的共性与个性。
先锋作家叶兆言以“秦淮河”系列小说著称,然而在他温婉旖旎的江南风情背后,也有令人深感惊惧的刑侦系列小说。如《走进夜晚》《凶杀之都》《危险男人》《危险女人》《最后》等皆是作者有意识地趋向死亡与犯罪题材的作品,小说总体来看语句平淡且无蓄意营造的阴森气息,但却总有令读者冷不丁感到惊悸之处,如《凶杀之都》里展望刚走出机场,“迎面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用饱满的红漆写着血淋淋的大字:欢迎你光临温柔之乡”[16]……杀人不见血式的恐惧感夹杂着作者独有的“古旧”情调,使叶兆言的小说笼罩在一种特别的氛围中。作为先锋文学“射雕五虎将”之一的“北丐”洪峰,在早年的小说创作中也无一例外地涉及死亡与恐惧。如其代表作《东八时区》里写卢小红投海自杀的场景:“潮汐将她美丽的身体裹到深处,又在第二天黎明前推上沙滩,她的脸被鱼类啮咬得斑斑驳驳,黑洞洞的眼眶里缓慢地爬出几只拇指大的灰黄色蟹子……”[17]作者并没有用太过冲击的语言或情节去刻意营造恐怖的氛围,而常用贴切的比拟去修饰、夸大各种死亡的面目,这远比死亡本身更可怖。又如小说《湮没》《离乡》《奔丧》等,作者偏于将死亡和性爱混合在一起叙述,并且总会在出其不意中将读者带向恐惧的巅峰。北村的小说多半带有浓得化不开的哀伤,他善于把这股哀伤凝聚在主角身上作为叙事线索,如《伤逝》里的超尘和《周渔的火车》中的周渔,两个女主人公神秘感极强且麻木如死灰,她们虽然毫无杀伤力,却为文本奠定了幽诡的基调。又如《施洗的河》中难以言明的父子之仇、兄弟之恨等,刘浪把弟弟刘荡推进河里,回家后发现弟弟没死,“刘浪心惊胆战地经过弟弟身边的时候,刘荡冷漠地看着他,一边拧着湿漉漉的衣服,刘浪听到了刘荡手里发出的拧断一个人骨头的咔嚓咔嚓的声音”[18]。真实的恐惧往往藏于北村小说中常有的男女对立、父子/父兄对立这种极其危险与撕裂的复杂感情中,并不是敷于表面的。
除上述外,在小说的“死亡与恐惧”叙事方面还有一位重要的作家,即有“东邪”之称的余华,其作品尤其值得与“南帝”苏童的作品进行比较。余华的早期作品,如《现实一种》《西北风呼啸的下午》《死亡叙述》《古典爱情》等,无不体现了暴力、血腥、残忍和死亡,如《现实一种》中的某个片断,4岁的皮皮摔死了还是婴儿的堂弟:
他俯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是从脑袋里流出来的,流在地上像一朵花似地在慢吞吞开放着。而后他看到有几只蚂蚁从四周快速爬了过来,爬到血上就不再动弹。只有一只蚂蚁绕过血而爬到了他的头发上。沿着几根被血凝固的头发一直爬进了堂弟的脑袋,从那往外流血的地方爬了进去。他这时才站起来,茫然地朝四周望望,然后走回屋中。[19]
种种类似的对于死亡表象客观而冷峻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对生命、生存的看法,另一方面“这种冷峻和客观的姿态让人感受到冷意,他对人间的暴力和残忍有一种展示的欲望和解剖的快感,却缺少了对人类价值的思考和对世界应有的人文关切”[20]。与余华直面死亡的叙事相比,苏童侧重的恐惧则更加富有艺术魅力。首先,因为“恐惧是苏童小说创作审美情感的核心内涵,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情感流露,表现在主题的确立,意象的创造,情节的设置,氛围的营造等方面”[9];其次,与余华冷峻的“零度叙事”、具有游戏意味的姿态相比,苏童“马尔克斯式”的奇思异想,哀艳朦胧的古典情怀以及轻逸灵动的小说语言更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渴望一睹“恐惧面纱”背后的秘密……
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多把目光聚焦在“死亡、恐惧”上面,这和当时传入文坛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等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不仅是新时期文学及思潮推动了先锋作家对人如何生存的思考,对人性、心理情感的敏锐攫取,也为后进的作家创作提供了足以借鉴的角度和艺术深度。苏童小说中的恐惧色彩在诸先锋作家作品中颇有辨识度,无论是从读者的阅读感受、作者的书写风格来看,还是从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分析,抓住苏童小说的这一文本特色,有助于我们走近作家本人,走近其“恐惧色彩”背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