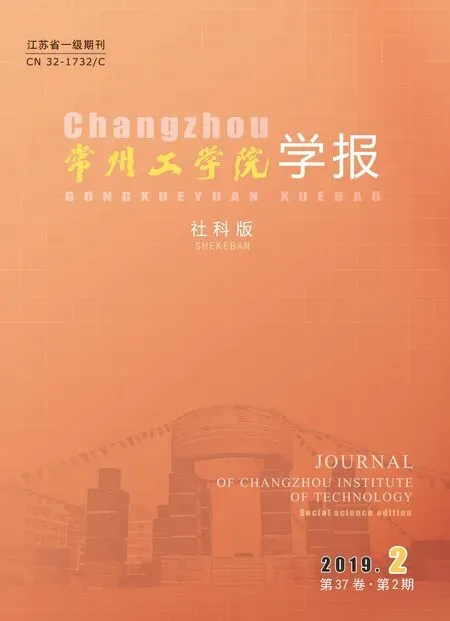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悲情城市》与《海角七号》叙事比较分析
张浩宇,张霁月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 多重转换的叙事时空
“热奈特在叙事学领域提出任何叙事都建立两种时间性:被讲述事件的时间和讲述行为本身的时间性。”此外,“大部分叙事需要产生接纳事件的空间环境,电影叙事的基本单元——画面,就是一种完美的空间能指,表现引发叙事的行动和与其相配合的背景”[1]104。影片《悲情城市》与《海角七号》采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叙事手法,将个人经验与历史经验相结合,引发了不同时期观众的共鸣。
(一)非线性叙事时空
在影片叙事中,《悲情城市》并非采用传统连贯的线性叙事,而是大量使用景深镜头与空镜头等缓慢节奏的叙事手法,反复使用相同场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掘更深层次的内涵。故事展开叙述的场景较为单一,如小酒馆、家、医院、渔港,主要为室内景,通过人物的行动揭示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悲剧命运。廖庆松采用气韵剪接法,“剪画面跟画面底下的情绪,暗流绵密,贯穿到完”[2]。两个画面中插入一段空镜头,不仅具有空间能指的意义,而且使整部影片有机地连结起来,充满叙事张力。因此空镜头的设置,在承接转场的同时为故事设置悬念,使缺憾的空间具体可感,成为情绪延宕的补充。下文以几个空镜头为例,进行非线性叙事时空的分析。
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气氛阴暗,台湾动荡的局势下人心惶惶。影片透过窗帘内产婆的虚像,让人观测女人生孩子的动态,随后林文雄的儿子出世,取名“林光明”。导演通过镜像观察事物的方式,“类似法国麦茨说的‘电影之爱’:观众接受并看着来自现实世界的影像铭刻在银幕上,而产生内在愉悦”[3]。与此同时,字幕交代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台湾将脱离殖民者的统治进入后殖民时期,但新生命出世的喜悦,仍无法改变悲痛事件的继续发生。画面进而转向一片静默、美丽的渔港,空旷的场景展示“二二八”事件爆发前九份的平静状态,有起承转合与设置悬念的效果。接下来的画面是,林家“小上海”酒馆开业,一家人沉浸在热闹的氛围中。衔接镜头依然是美丽的渔港,伴随着《流亡三部曲》的歌声,长达38秒的空镜头,承载着年轻一代台湾人对祖国强烈的归属感,思念的情绪与赤子之心寄托于美丽的大好河山中。画面与声音分属于不同区域,有声的抗日音乐与文清、宽美通过字条无声的交谈,构成影片内部的叙事张力。镜头自上而下摇移俯视渔港,雨声与雷声衔接下一个镜头,宽美在收拾医院的床单,文良被绑在病床上,眼神呆滞,残酷的战争剥夺了一位有志之士应有的尊严。画面视点进行了虚化处理,营造出深焦效果,借助渔港、天空等转场景物与富有情绪表现性的雷声、雨声交代叙事时空位置,呈现有层次的时间与空间的对比关系。小酒馆内的歌声与窗外雷声延展到医院,构建另一个空间,暗示时间的更替。紧接着黑帮势力找上门来,文雄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跑路生活,由林家客厅里女人们的谈话转场到文雄卧室,文雄仓忙逃跑后仅留下妻子和儿子。天空稀松的云朵将电线杆拉向远方,而近处房屋处于黑暗面,隐喻女人必须要坚韧地撑起半边天,完成家庭的重任,渴求未来的光明来代替眼前的黑暗。陈仪广播的同期声承接薄雾笼罩的山间,一只雄鹰在画面边框处盘旋,直至消失在山野中,隐喻人物在自然与历史中渺小的地位,老大林文雄是动荡的台湾黑暗势力的牺牲品。文清和宽美婚礼的唢呐声延续到白天,绿色的山野间时空的变化,暗示葬礼到婚礼的转折,空镜头代替时空流转,由悲转喜预示了台湾的未来终将是光明的。最后一幕是车站月台的空间场景,来往的列车不断却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归程,无论文清与宽美何去何从,始终也无法摆脱个人在历史进程中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无奈。整部影片以空镜头串联故事的逻辑性节奏,以非线性叙事结构表现叙事时空的同时,表现了台湾新电影画面诗意性的内涵意蕴。
(二)双重交叉的时空套层
“虚构”与“现实”为二元对立的概念,后新电影的去中心化赋予了台湾地景两种不同方向的表达。影片《海角七号》中,过去友子的故事与现在的友子在虚幻空间与现实性空间交替出现在同一画面中。除了现实生活中阿嘉与友子背离现代都市的空间外,另一种则是60年前由于历史造成的日本先生与学生友子分离的回忆空间。作为影片重要叙事线索的7封信,出现在阿嘉与友子两人感情发展的每个重要节点,将两代人的爱情跨时空穿插在一起。
“太阳已经完全没入了海面,我真的已经完全看不见台湾岛了。”日本先生作为叙事者以旁白的形式念出7封信,以日本战败遣返回乡为叙事背景,信中流露出遗憾、伤感等情绪,激发观众兴趣的同时引出现代青年人的感情,告诫人们要懂得珍惜。阿嘉在受到挫折时机缘巧合读到这封信,画面中闪现年轻友子的脸庞,时空交织以平行蒙太奇的手法连结起阿嘉和友子,使二者建立关系。日本先生乘船返乡与学生友子从此诀别,与此同时阿嘉受挫离开都市台北返乡,同样的离别,前者表现了日本先生与爱人分离的无可奈何,后者表现了阿嘉只能与梦想告别继续流浪。台湾人与日本人早在20世纪已有的情感纠葛,交错在现代时空中呈现发展,人物身份、处境也因此发生转变。阿嘉和友子第一次擦肩而过是在在地乐团甄选会上,看似不和谐的乐队组成,在7封信的穿插中,与信件独白者情感的波澜转折形成情绪共鸣。“友子,预计明天入夜前我们即将登陆,但愿这彩虹的两端,足以跨过海洋,连接我和你。”演唱会前夕的友子在阳光下看到了彩虹,阿嘉在送信的路上,踏着彩虹而来。银幕上呈现的现实世界与信件中构建的虚构世界的关系变化,如同镜像般相互对立呈现,又彼此嵌套。再者,当日本教师诉说因思念而日渐苍老的容颜时,镜头交错呈现友子若有所思地走在海滩边、邮差茂伯补送信件及阿嘉在海岸边的画面。“友子,我已经平安着陆,我会假装你忘了我,假装你我的过往,像候鸟一般从记忆中迁徙。”最后一封信,将他与友子的情感置于绝望的极端,正如同他将思念与忏悔化作7封情书,穿越60年的时空,依然无法送到信件中早已不存在的旧地址。究竟年迈的友子小姐是否读到这些信件,年轻的友子与阿嘉最终是否走到一起?“两个异质时空的段落相互切换,亦散发着一种过去未完、有待未来加以延续、承接并深化的意思。”[4]
7封信的套层空间将不同时空的故事交织剪辑在一起,日本先生与他的学生友子曾经真挚美好的感情因历史而断裂,只留下纯粹的回忆。阿嘉追逐音乐梦想以及与友子的爱情,借助旁白的方式,贯穿整个故事,相互照应与融合。双重叙事的时空套层结构,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经过片段式的拼贴,描绘出台湾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产生的焦虑现象,展现多元化语境下台湾的真实面貌。
二、个人经验折射集体经验
在侯孝贤的电影中,台湾的日式风格建筑被视为一个暂时性的过渡空间,通过不同角度的固定镜头,揭露了后殖民时期种种殖民残余的痕迹,以及战后国民党统治的戒严背景。“按照我们制定的体系,‘视觉聚焦’表示摄影机所展现的与被认作是人物所看见之间的关系。”[1]175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在这个具有文化意味的空间中呈现出来,透过家庭成员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以写实镜头聚焦多重叙事视点,充满后殖民时代的隐喻色彩。
(一)女性视角与旁白
《悲情城市》延续台湾新浪潮电影的美学风格,以人物关系折射出个人经验背后的历史建构,表达台湾本土身份认同的困境,追溯台湾的历史悲情。侯孝贤导演置身于“二二八”背景之下,呈现女性视角的多重叙事,以宽美的内聚焦视角和旁白为主,推动故事的时间轴叙事进程。
“旁白声音既是叙述的传达者和执行者,也是一种独立的存在,音色、质感、语气、腔调、节奏都暗示讲述者的‘听觉性格’。”[5]宽美的旁白是故事的直接叙述者,天皇和陈仪广播中产生的历史重大事件叙事乃是间接叙事,宽美与二嫂女性话语的讲述则呈现出循环往复的齿轮式历史时间,呼应空镜头中自然生命的不息与重生。整部影片由宽美的日记构成,通过与文清的交谈勾勒出历史背景下林家小酒馆里人物的生活,以日记为线索,将主人公的重担设置在一位聋哑人——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上。同时用字幕、旁白、广播、音乐等叙事形式,以宏观视角观照历史背景。片中宽美的日记是帮助观众了解叙事发展的关键,医院场景的出现频率仅次于小酒馆,医院是宽美工作的地点,通过宽美交代叙事情节。宽美在给阿雪的信中,提到新生的希望——阿谦在健康茁壮地成长,当初想要逃避到如今心态平和,再提到文清又一次被抓,生死未卜,以及面对未知的情况已然可以坦然面对,结局是导演将个人情怀转化为置于高点的宏观性观看与审视。影片最后设置了在林家客厅,林父与林家老三文良在正厅餐桌吃饭的场景,一个是日渐衰微的父权,一个是丧失正常人理智处于半疯癫状态的老三,在门框后一直忙碌的母亲与客厅中来回穿梭的孩子成为家庭的支柱与希望。宽美在信中提到要宽荣照顾好身体不便的文清,另外阿雪在写给宽美的信中,怒斥上天不公,连聋哑人都不放过,画面切入宽美坚定的旁白“天理有无我不管”,带出对文清的个人关怀以及对命运的呐喊。
多层次的声音片段,颠覆官方的独白式史诗叙述,细致描绘出从日本殖民转移到国民党统治的过渡时期台湾的真实生活。作为两次重要的旁白,天皇宣告日本撤离的字幕和陈仪的广播,带动叙事的发展。由于广播电台信号频率的缘故,天皇的声音微弱嘈杂,侯孝贤采用字幕的方式表述历史背景,也借此处理方式暗示日本的殖民势力在台湾已无话语权。第二个是广播中陈仪的讲话,以富有方言味道的“国语”讲述如何处置事变,以及宣布戒严。与天皇宣告日本撤离的声音微弱嘈杂相同的是,陈仪的广播同样频率不稳定,通讯受到干扰,国民党执政虽有些水土不服,却依然成为事实。不同的是,陈仪的广播有固定的听众,医生与护士围绕在桌子前,不管是否深入思想,仪式感是存在的,即使在做毫无意义的宣告。《悲情城市》中宽美的日记是片段式的、去政治化声音的一部分,广播和字幕则通过另一种旁白形式,讲述个人成长经验并折射出历史集体记忆。
(二)内聚焦视角叙事
热奈特指出:“内聚焦叙事是指有固定的内聚焦,叙事说明的时间仿佛是经过唯一一个人物知觉的过滤。”[1]177《海角七号》以阿嘉的视角为线索,展现现代年轻人的爱情观和人生观。阿嘉作为主要叙述人物,以其与行为人之间的互动,呈现台湾本体内部的多元文化差异与民族认同感。影片中“国语”“台语”与交杂的日语充斥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本土音乐、建筑、美食等文化生活均为最真实的写照。影片打破以往台湾电影以本省与外省矛盾为主的话语体系,探寻多民族并存、文化碰撞的复杂社会中人们身份认同出现的困境与焦虑。
影片开头,阿嘉骑着机车穿梭在城市与乡间,飞驰而过的台湾代表性建筑逐渐远去,镜头通过阿嘉的个人视野展示繁华、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机车后视镜中反射出的都市场景与即将通往的乡村田野逆向而行。阿嘉的行动构建出饮食男女的生存场域,也构成影片前后叙事空间的对比,通过对比凸显导演对台湾人生存主题的思考和观照。年轻人逐梦的理想屡遇现实的打击,都市似乎是乡村年轻一辈不可企及的存在,信件、内心独白、海边思考的静态镜头都以阿嘉内在的本我叙述主角的内心世界,使人物个性更加饱满。同时,作为讲述者,内聚焦叙事与外在的他者叙述相结合,使观众了解到位于乡村的台湾在地人的日常生活与欲望诉求:“国宝级”月琴弹奏者茂伯曾经的至高荣誉与现在被人遗忘沦为邮递员的生存困境;原住民交警对离世爱人的思念;憨厚的修理工人水蛙对已有家室的老板娘不敢开口的暗恋;辛勤奋斗的创业者纳拉桑终于收获人生的幸福以及天籁孩童大大代表祖国的希望等。叙事视角的不断转换,使观众在融入故事的同时,又能作为一名全知全能者,以客观冷静的距离审视整个事件与行为本身。影片以阿嘉的视角为基点,众分支线带动主线的发展,同时为主线铺垫,融入观众未知的世界,使观众感受导演所传达的意涵。
三、本土叙事书写人物身份
(一)本省人与外省人话语表达
《悲情城市》以外省人和本地人为主,穿插其间的多重话语,既展现了台湾由日本统治时期到新台湾过渡身份建构的复杂困境,又呈现出日本殖民势力的消长与接受大陆新文化所要克服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在政权交替的过渡阶段,台湾人在夹缝中生存,一边是日本殖民政府文化的深入渗透,一边是对大陆新政府的接纳,处境艰难又充斥着矛盾。是使用本土方言“台语”,还是标准普通话,又或是早已成为日常语言的日语?语言上的冲突在文清于车厢险些被捕的场景中达到高潮。文清被火车上一批手持棍棒的本省人围住,质疑其身份,这些人第一遍用闽南语质问,得到文清结结巴巴的“台语”“我是台湾郎”后,第二遍又用日语重复提问,得不到正宗的日语回答后欲施以暴力,幸得本省人宽荣解围。将此场景置于历史场域中,“二二八”时期,会讲“台语”的人不算是正宗台湾人,兼会“台语”、日语两种语言,方可成为合格的台湾人。不仅隐喻国族认同往往还伴随着外界势力的介入,也常常伴随着创伤经验,地道的本土特质在历史繁衍过程中沦为尴尬且不被认同的身份特质。
其中一场关于谈判的戏中,在印刷日本假钞票的事情败露之后,黑帮红猴被杀害,两派黑帮反目成仇,请来本地颇受尊敬的阿姐主持公道。她提出三分制解决办法,两边帮派一份,红猴年迈的老母一份,简洁明快地解决双方的争端,具有权威的主导性作用。另外一场关于谈判的戏中,老大林文雄为文良早日出狱寻求上海帮派的帮助,林文雄讲“台语”,手下翻译为广东话再转述为上海话,谈判语言的多元化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人物身份。由于双方在语言表达上存在障碍无法沟通,本是一衣带水的男人力量群体代表,有话语权却无法得以完善表达,谈判效果大打折扣,只得以借助外物的形式——罪恶的毒品使对方明了。另外,小酒馆的餐桌上,同样出现因语言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冲突。在场人物有台湾本地人、上海人,两组人马谈论走私生意,当本地人欲要说着一口闽南语的酒女来招待外省人时,上海人情绪激动且气愤,台湾人立即招呼酒女回自己身边。然而在听京剧时,这位上海佬又如痴如醉。为响应政府号召,医院聘请知识分子讲授“国语”,曾经以日语为母语的台湾人正接受母系文化的输入,从另一层面也反映出以医院的医生护士为代表的工薪阶层,对国民党执政的接受。影片中知识分子在宽荣家的抱怨,法院的院长、工作人员都由国民党的亲属要员组成,“法院是你家开的吗?”一句话点出国民党妄图一手遮天的资本家本质。脱离了殖民身份后依然面对不自由、没有话语权的社会,政权的罪恶带来知识分子对前途迷茫的担忧。
(二)多元身份的建构
相对于《悲情城市》小酒馆里圆桌吃饭的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冲突,《海角七号》则展现出社会族群的多元文化身份,日本人、台湾在地人、原住民、外省人等,来自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群像,其身份、族群、年龄、背景与职业都具有能指与所指的意涵,充分体现出导演的精心安排。
海滩演唱会中台湾本土音乐,阿嘉创作的流行歌曲,日本传唱度极高的民谣,通过混杂的语境,再现了台湾多族群的日常生活。倒车镜里出现的高大建筑物,从镜像中隐喻城市与乡村的背道而驰,影片中几位挣扎于人生苦海的年轻人:本是模特却沦为模特经理人的友子、离开霹雳小组的警察劳马、修摩托车的水蛙、努力的“小米酒”推销员马拉桑等,将在恒春小镇完成遥不可及的人生梦想。从《悲情城市》到《海角七号》人物身份多元化,情怀不同,激烈的身份冲突转化为具有包容性的日常叙事,由二元对抗呈现为多元对抗。极具象征力的恒春在地乐团是汇聚融合多元身份的包容性场域。中孝介以曾经的殖民者身份加入演唱会,与台湾在地人组成的乐团形成友好的平等关系,海滩演唱会不再以日本歌手为中心,本土身份得到认可且被接受程度大于知名日本歌手。作为他者介入的中孝介,以化解族群间积怨已久的矛盾、达到和解为任务,促进了台湾本土自我身份的觉醒。阿嘉与友子的感情出现破裂时,故事安排村民的一场婚礼,作为消解矛盾的催化剂,通过喜结连理的婚姻,达到缓解气氛并融解矛盾的作用。爱情的碰撞,乐团友情的身份,人性的温暖,促使看起来并不合群和拥有不同背景与身份的一群人,凝聚成团结的集体。他们热爱音乐,勇敢追求,为了同一个目标绝不轻言放弃,以实际行动诠释台湾精神,完成对台湾身份的嘉奖。
四、结语
首先,相对于侯孝贤《悲情城市》非线性的叙事表述,《海角七号》尝试了不同的美学实践,融合多元素的剪切手法,创造双重叙事的时空套层。其次,《悲情城市》借助旁白,通过女性视角反映历史现实,魏德圣导演则通过阿嘉的视角,观照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最后,叙事场景的选择在建构与观众之间或亲密或疏离的关系的同时,也体现出多元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处境。总而言之,相较于新电影的单一叙事,后新电影使用更为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都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新电影则更致力于本土化空间叙事。魏德圣导演作为后新电影导演的代表之一,在叙事手法上与以侯孝贤为代表的新电影导演产生一定的继承与背离,在肯定新电影写实主义叙事风格的基础上,将眼光投向多元族群与社会的不同阶层,开辟了后新电影的叙事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