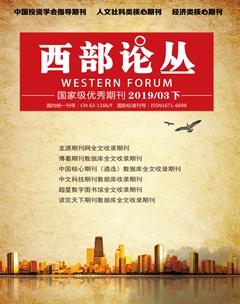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吕鹤霄
摘 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民族国家”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内部包含较多民族,当个体对自身族群的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并将次民族的认同置于民族国家认同之上时,就会出现国家认同危机并引发诸多政治性后果。解决多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关键在于塑造“民族”与“国家”的统一边界,强化各民族间共同的政治认同。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认同危机
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
Nation在西方语境中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它包含了民族与国家的双重内涵。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民族国家(Nation-state)通常以民族与国家有机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形成是为解决欧洲王朝国家内民族与国家二元对立问题。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家至高无上”原则,民族国家正式取代王朝国家成为新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实质上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自出现以来就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危机:
(一)国家认同危机出现的原因
首先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经常出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两者边界并不统一。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地球上存在大量潜在的民族”,潜在民族数字“可能比能够独立生存的国家的数字要大得多”。当个体对自身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并将次民族的认同置于民族国家认同之上时,国家认同危机出现。周光辉和刘向东称之为地方民族成员对次级群体的“狭隘的忠诚”,周平则将这种多民族内国家认同问题视为一种“集体忠诚冲突”。在成功创造国家后,统治集团必然会强化相应的单一民族意识,以神圣化国家的历史文化根源,当国家能力较弱而无法有效强化这种意志时,就会引发社会运动和革命。
其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不同类型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则是政治认同。民族是一种文化共同体,所谓的民族认同就是个体基于客观的血缘或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而对特定族群产生的归属感,基于民族文化之上的民族认同形成历经很长时间且难以改变;而国家是“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政治实体,所谓的国家认同个体感觉他属于特定的政治单位、地理区域和团体,将其视为予以强烈效忠、恪守义务或责任的对象以确定他属于哪一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是基于国内各个民族群体的认同,当多民族国家内的某个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较低,国家就不能从这里获得合法性。
(二)多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政治性后果
首先,国家的法律、政策往往会受到质疑,导致国家的合法性降低。在政治生活中,国家政策的实施和在社会中的政策效果往往会以迥异于国家初衷的形式告终,很多国家的统治范围甚至仅仅局限于城市甚至是首都附近。根源在于国家的统治建立在国民的忠诚、服从基础之上,如果国家内部存在较多民族群体不愿意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或对其抱有抵触情绪,就会导致国家统治成本过高、治理能力低下,尤其是在国家认同弱化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随时会产生各种社会与政治运动。
其次,引发民族间冲突和民族分裂运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大都伴随着激烈的民族冲突,那些具有鲜明族群中心主义而经济剥夺感强烈的少数族群群体,更容易陷入与其他族群的冲突。民族冲突可能采取从非暴力对抗到暴力冲突等多种方式,包括言论攻击、集体抗议、暴力斗争、种族屠杀等,不论何种形式其本质都是对现有政权的颠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民族分裂者长期利用民族、宗教等进行反动宣传,煽动民族间的对立、制造恐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各大民族间的隔阂、影响民族团结。即便是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苏联、民主法治最为成熟的美国,也面临着潜在的民族冲突与分裂运动。
此外,国内民族问题严重会给境外势力的介入国内事务提供可乘之机,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的完整。威胁主要来自于两大方面:一是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通过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获取反对国家政权的军事、经济等支持;二是外部国家会以民族自决、保护人权为由采取军事措施,悍然入侵。一个独立、稳定、繁荣的民族国家是赢得国际地位的前提,一旦出现国家认同危机,将导致综合国力的急剧下降。
二、消除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路径
多民族国家认同危机无法回避,抑制民族冲突、实现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必须借助国家政权,制定相应措施,对多民族进行有效整合,以保证国家稳定与发展。
(一)给予一定的民族自治权
自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治理方式,其实质是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一种制度保障。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许多国家开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民族自治作为国家层面的一项重要政策。民族自治的优势在于通过一定的政治权力分配与制度设计,可以将基于一定血缘纽带、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民族情感性意识引导到充满理性的政治认同中,实现民族成员对国家政权的认可并主动地进行政治参与,从而增强少数族群国家认同感。联合国大会于2007年通过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明文规定了“土著民族享有自决权”,他们可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谋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我国的民主自治政策始于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先后建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并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写入国家宪法,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塑造各民族间共同的政治认同
建构族群认同所依据的基础要素,主要来自于血缘纽带或族裔身份。从国家认同的塑造路径上看,个体首先在文化上对特定民族(例如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接受一定的政治制度安排,由此形成国家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主体是多样的,主要包括对国家政权、制度、政府与执政党、政治人物等的认同:所谓国家政权认同是对掌权者权力来源的认同,按照韦伯划分有传统惯例或世袭、他人崇拜与追随、法理基础三大来源;就制度认同而言,越来越多的经验表明,稳定、高效的制度设计是凝聚国民对国家向心力的关键;就政府與政党认同而言,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权力由执政党行使,对执政党的认同意味着对政府、国家政权的认同;政治精英认同是指人们对政治领袖、政治家产生的情感上的归属感。总的来说,人们之所以认同某个国家,是这个国家在政权组织、政治制度、社会政策等各方面能切实保障国民利益,能够让内部成员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对多民族而言,塑造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将会促成对国家的认同。因此较多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情感是一种盲目的国家优越感,它带有对外部群体的蔑视和排外倾向,并具有对外部群体的支配感,而爱国主义是一种健康的、建设性的、宽容的爱国情感。
(三)强化领土认同
按照国家的经典定义,现代国家就是在特定领土内成功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因此领土是构成国家的要素之一。江宜桦将国家认同分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不论国家采取何种建构模式,由于认同对象的不确定,始终无法消除国家认同危机,领土认同较之文化、民族和制度认同,最大特点是具有明确的物理边界,决定了领土认同可以成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客观基础,离开领土认同,制度认同会流于世界主义,民族认同也无法形成于地方性族群认同的合围之中,因而它们都不能起到塑造和强化国家认同的作用。多民族国家的领土认同往往会在国家面臨主权危机和国家安全的时候强化并最终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巩固。近代中国在对外敌的不断抗争中,民族意识在不断成长,并在全面抗日期间达到一个高峰:以“民族”一词为例,1911年年底前《申报》可检索出的条目为243条;到1925年、1928年、1936年、1939年,“民族”一词可检索到的条数分别增加到了502条、1119条、1507条、2369条,可以说外部势力的侵略催化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让中华民族这一文化概念逐渐被赋予了政治性,并成为了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基础。
三、余论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并非都能合二为一,能否在保持对族群忠诚和认同的同时培育对国家的认同,是学术界持续关心的话题。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问题不仅困扰着二战后走向独立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困扰着具有成熟民主体制的西方发达国家。只有保持“民族”与“国家”边界的统一,才能保持多民族国家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01):26-40.
[2] 江宜桦. 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国家认同.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1997(25): 83-121.
[3] 高永久等.民族政治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3
[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222.
[5] 黄道炫.战时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J].史学月刊. 2008.(05):16-25.
[6] 周光辉,李虎.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为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16.(07):4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