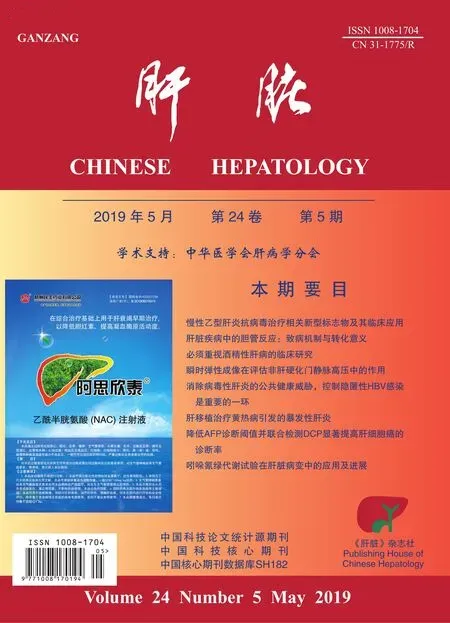调节肠道菌群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研究进展
卢双 沈天白 陈阳 王怡群 李莹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是全世界近年来非常常见的代谢性疾病,在部分患者中可进展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纤维化,并最终导致肝细胞癌和肝衰竭。NAFLD与肥胖、胰岛素抵抗和血脂异常有关。最近有一系列证据显示NAFLD与肠道菌群密切相关,亦有研究提示调节肠道菌群可以改善或治疗NAFLD,但具体作用机制和临床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与内脏肥胖和糖尿病相关。在一项对445位受试者进行活检评估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率的研究中,77.2%的受试者被证实患有NAFLD[1]。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在日本NAFLD患者和NASH患者的人数分别超过1 000万和100万[2]。NAFLD已成为美国慢性肝病最常见的病因,对大约12 000名居民的分析表明NAFLD的患病率为18.8%。据估计,NAFLD和NASH在肥胖患者中的患病率分别约为75%和19%,在病态肥胖者中可高达93%和26%~49%[3]。根据上海、北京等地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在10年中,普通成人超声诊断的NAFLD患病率从15%上升到31%以上[4]。
近年来,肠道菌群与NAFLD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有研究结果提示NAFLD可能与肠道微生物组成紊乱有关。特别是发现健康个体与NAFLD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成存在差异[5]。所以,本文主要就肠道菌群及其与NAFLD治疗的关系进行综述。
一、NAFLD的发病机制
现代医学认为NAFLD的发病机制多而复杂。1998年,提出了二次打击假说[6],这个假说认为脂肪变性是肝脏发生第一次损伤后,再次损伤才能够发展为NASH或纤维化。近年来,多重打击假说被更多人接受,并且多重打击假说认为在具有遗传倾向的个体中,有无数的因素以平行和协同的方式起作用,以解释临床观察到的不同表型。虽然从单纯的脂肪变性到NASH的进展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这两个临床亚组结果的显著异质性导致NAFL和NASH可能对应于两个不同的实体。因此,肝细胞损伤发生在NASH中时,会导致细胞死亡、局部炎症和纤维发生。
肝细胞损伤在疾病早期由多种不同因素触发和维持,如胰岛素抵抗(IR)、脂肪因子、营养因子和肠道菌群(GM),以及遗传和表观遗传因子。目前在已提出的多种NAFLD的发生机制中,胰岛素抵抗似乎是NAFLD和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的关键(因为NAFLD的发生与代谢综合征的发生都具有胰岛素抵抗的病理生理基础,所以它们有一些共同的机制)[7]。药物、毒物、胆碱缺乏、载脂蛋白B基因突变、胃肠外营养等因素单独或与IR共同导致肝脂肪变。并且IR还可以与细胞内游离脂肪酸增多、ATP储备耗尽、氧化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共同参与肝脏损伤的发生。胰岛素信号转导在肝脏脂肪变性中起中心作用。此外,脂肪在肌细胞中的积累导致了IR和成对的葡萄糖摄取。因此,外周IR和高胰岛素血症的发生有助于增加游离脂肪酸在肝脏中堆积。在肥胖受试者中,脂肪酸似乎被错误的从主要储存部位转移到了其他部位,如:骨骼、肝脏,被重新酯化为二酰基甘油,造成脂肪的堆积。
另外,饮食、肠道微生物群、遗传因素和脂肪生成之间相互作用通过对脂类转录因子的调节引起脂肪变性,脂肪变性通过激活IKKβ导致转录因子NF-κB信号增强。NF-κB的激活诱发炎性介质TNF-α、IL-6和IL-1β,这些细胞因子导致库普弗细胞被激活并调节NASH的发展[8]。
二、肠道菌群概述
在肠道中存在着数万亿的肠道微生物,它们有着帮助维护和平衡宿主健康的重要功能,包括免疫、营养状况和代谢功能[9]。大部分的糖类和植物多糖都不能被人体内的酶降解,而肠道菌群中最主要且数量最多的短链脂肪酸(SCFA)产生菌,在复杂的植物多糖初始降解和11种寡糖发酵释放SCFAs和气体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0]。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肠道菌群和慢性肝病密切相关。由于肝脏中70%的血供是通过门静脉来自肠道的,因此肝脏会不断地暴露在肠源性因素中包括细菌成分、内毒素和肽聚糖。包括库普弗细胞、窦状细胞、胆道上皮细胞在内的许多肝细胞表现出的先天免疫受体被称为病原体识别受体,这些受体对肠道中不断流入的微生物源性产物作出反应[11]。这阐明了肠道生态失调的本质、肠道屏障的完整性以及肝脏对肠源性因素的免疫反应机制。
此外,“代谢性内毒素血症”的假说证明了肠道菌群与高脂饮食引发慢性低水平炎症是相关的。饮食导致肠道菌群改变,使致病菌的数量有机会增加,减少了保护肠屏障细菌的数量,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这样进入血液的内毒素也会增多,慢性炎症反应就会发生,进而引起代谢失调疾病,如:肥胖、胰岛素抵抗等。肠道菌群通过对宿主能量代谢、免疫系统和炎性反应的影响,决定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发展。
三、NAFLD与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对脂质代谢(尤其是饱和脂肪酸的代谢)影响了脂肪在肝脏中的积累以及NASH患者肝脏炎症的发展[12],肠道菌群紊乱导致乙醇肠道菌群增多,这些菌群在肠道中的内生乙醇增多,过多乙醇在代谢中使过度消耗氧化型辅酶Ⅰ而使还原型辅酶Ⅰ增加,进一步导致高脂血症和脂肪肝。一些已经被提出的机制解释了这种特殊的失调对NAFLD患者的影响,如增加肠道通透性、改变某些饮食的代谢,导致单糖吸收增加,增加了肝毒性产品和内毒素的产生和释放。这些因素在易感宿主中将激活几个炎症介质,并导致纤维化和疾病进展。
人体中微生物为宿主提供必需的代谢和生物功能。脂肪多糖(LPS)存在于宿主血浆中,是一种来自肠道的细菌成分,被认为是几种疾病(如肥胖相关的代谢紊乱,包括NAFLD)的发生因素[13]。在健康的生物体中,肠道菌群通过一种共生机制有助于维持体内平衡,在这种共生机制中,细菌和宿主双方都是受益的,这种情况被称为“生态失调”。这种共生一旦失调可能对代谢和免疫反应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肥胖和与肥胖相关的疾病发生发展,包括IR和NAFLD[14]。有实验证明增加肠道通透性、细菌过度生长,特别是革兰阴性菌,增加了肝毒性产物如细菌内毒素(LPS)的产生,LPS被肠道吸收,可以进一步影响肝脏炎症;肠道完整性的破坏增加了肠道通透性,亦导致细菌易位,细菌内毒素渗入门静脉,通过激活肝脏炎性细胞增加NAFLD发生的危险[15]。肠道菌群也通过水溶性营养胆碱与NAFLD发生联系;后者既可由鸡蛋和红肉等动物制品摄入,也可由肠道菌群生物合成[16]。
四、调节肠道菌群与NAFLD治疗
NAFLD的治疗尚无特效方法,目前公认的治疗策略是改善生活方式和控制体重。NAFLD的小鼠的粪便移植在野生型小鼠中引起了获得性菌群失调的NAFLD,该研究结果也有助于证实肠道菌群在NAFLD的预防和治疗中的重要性[17]。益生菌的潜在有益作用已在一些动物实验研究中已得到证实,益生菌可以通过降低肠道通透性、调节核受体的表达以及纠正肝脏和脂肪组织中的胰岛素抵抗来保护NAFLD的发生和发展[18]。并且益生菌通过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抑制细菌易位以及入侵上皮细胞,它们可以诱导抗菌肽的生产,减少炎症,从而影响免疫系统;同时也增强了肝硬化的高动态循环状态,避免了肝性脑病的发生[16]。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姜黄素通过对大鼠肠道菌群系统的调节,可减轻肝脏脂肪变性[19]。研究发现NaB干预可以显著改善高脂喂养小鼠的肠道菌群,增强全身炎症反应,最终降低高脂饮食诱导的肝脏组织损伤。并证明黄连素是一种可以有效修复高脂饮食诱导的肠道菌群失调的药物。肠道菌群的正常化减轻了肝脏脂肪变性的诱发因素,从而保护宿主不受NASH的影响[20]。Daubioul等[21]进行了一项为期8周的交叉研究,随机抽取了7例NASH患者,让他们服用低聚果糖或麦芽糖糊精(用作安慰剂)。报告显示了胰岛素和转氨酶水平的改善。虽然这项研究受到小样本量和短期随访的限制,但它支持微生物修饰改变作为NAFLD和NASH患者的潜在治疗选择的作用。
五、展望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调节肠道菌群可以改善NAFLD的程度,并且在肥胖及其相关疾病(包括NAFLD)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证据大多来自于小鼠实验,研究中将肥胖动物的肠道菌群移植到正常动物的肠道菌群中,可诱发相关的代谢疾病。NAFLD病机复杂多样,通过改善NAFLD患者肠道菌群来治疗NAFLD的方法有待进一步探索,为临床治疗积累更多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