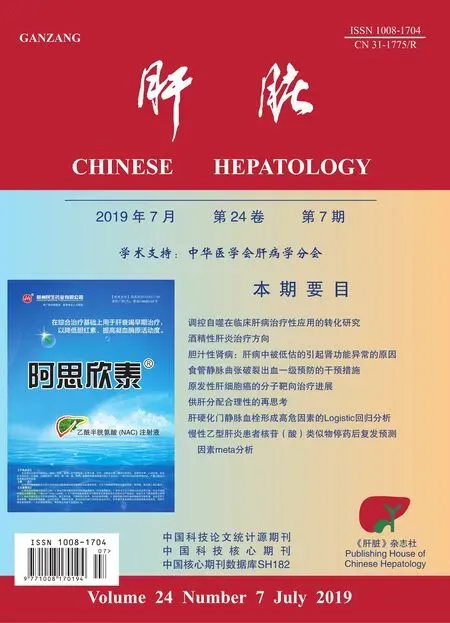整合素与肝纤维化
张荣 刘绍能
作者单位:100053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整合素是细胞与细胞之间、细胞与细胞外基质之间重要黏附受体家族成员,介导细胞与微环境之间的信号调节,在细胞存活、分化、生长、运动和凋亡等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整合素在不同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整合素在肝纤维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肝纤维化是肝脏对各种慢性刺激进行损伤修复反应时,是以胶原为主的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matrix,ECM)在肝内大量沉积的病理过程。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是肝脏损伤后最主要的致纤维化细胞,在各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下,不断地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产生大量的ECM,最终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1]。HSC增殖及细胞表型转化、ECM合成增多并沉积同时伴新生血管、炎症的形成是进展性肝纤维化修复重建中突出的病理表现,在这过程中整合素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整合素的分子结构和功能及其介导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作一综述。
一、整合素的结构
整合素是介导细胞黏附的主要跨膜受体,属于免疫球蛋白基因超家族,在脊椎动物中,迄今为止共鉴定出由18条α和8条β链结合成的24种非共价结合的异质二聚体[2],分别包含大约1 000和750个氨基酸。整合素家族成员在结构上都由一个较大的胞外区、短的跨膜片段、较短的胞内区组成。α、β亚基的胞外区为氨基末端,与相应配体结合,其胞外部分是纤维连接蛋白(FN)、玻璃黏连蛋白(VN)、层黏连蛋白(LN)、骨桥蛋白(OPN)、纤维蛋白原、胶原蛋白等ECM受体。胞内区为羧基末端,与细胞骨架蛋白相连。α、β亚基的不同组合决定着整合素与配体的结合特性及信号特征的专一性和多态性。不同亚基之间相互组合形成的整合素,其功能也不同,按β亚基可分为β1、β2、β3这三个亚家族,β1 亚家族又称为 VLA (very late activation antigen)家族,有 VLA 1~66种整合素;含β1亚基的整合素主要介导细胞与细胞外基质成分之间的黏附;β2亚家族主要表达于各种白细胞表面,主要介导细胞间的相互作用;β3亚家族称为细胞黏附素,含人玻黏蛋白和血小板的 GPⅡb/Ⅲa 受体,主要介导血小板的聚集,参与血栓形成。整合素β3 通过对同种细胞间信息传递的调控,参与细胞的凋亡过程。几乎所有动物均有整合素表达,目前发现参与肝纤维化的整合素亚型有α1β1、α2β1、β2、ανβ6、α6β4、α6β1、α7β1、ανβ1、ανβ3、ανβ5,ανβ6,ανβ8、α5β1、α8β1等[3-5]。
二、整合素的生物学功能
整合素介导细胞与其ECM之间相互作用,黏附主要基于ECM蛋白与细胞表面整合素配体中小肽序列或蛋白域的特异性。根据整合素识别配体的特异性,可以将整合素大致分为层黏连蛋白整合素、胶原蛋白连接整合素、白细胞整合素和精氨酶-甘氨酶-天冬氨酶肽(RGD)三肽序列整合素,这些组合在不同的细胞类型中表达各异。细胞间通过ECM整合素的黏附以及生长因子信号,控制细胞的生物功能。整合素在细胞中双向传递信号以发挥其生物学功能:①整合素的胞外结合活性是由细胞内部(由内而外)调控的。②ECM的结合引发外界信号传入细胞(由外而内)。在与ECM结合后,整合素聚集在膜平面上,通过与局灶性黏附激酶、Src激酶家族、踝蛋白、桩蛋白、α-辅肌动蛋白、张力蛋白、黏着斑蛋白等细胞骨架连接蛋白相连[6]。整合素同时参与Ca2+结合蛋白、RAS-Raf-MAPK激酶、黏着斑蛋白(FAK)、蛋白激酶C、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骨形态发生蛋白(BMP)、细胞外信号激酶(ERK)、整合素连接激酶(ILK)等信号通路的传导;另外也是表皮生长因子(E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CN2)、TGF-β等细胞因子的辅助受体,这取决于细胞表面整合素结合点的特异性[7-9]。细胞膜中整合素的表达水平不仅影响细胞的形态、增殖、分化、迁移和某些大分子合成,重要的是能保持组织和结构的完整性。整合素已逐渐成为细胞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和病理学的研究热点[10]。目前整合素多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炎症、血液病等疾病潜在治疗靶点的研究[11]。
三、整合素与肝纤维化
(一)整合素与HSC HSC有静止和活化两种细胞表型,在肝损伤激活后,静止的HSC变成活化的HSC,且活化HSC在肝纤维化进程中起重要作用。静止HSC和活化HSC中整合素亚型的表达存在差异,HSC表面有特异的RGD三肽序列结合位点,只有激活状态的HSC才能和RGD配基结合。整合素表达增加能够激活HSC,促进肝纤维化的发生[12]。James R等研究证实[13],整合素αν是玻连蛋白和纤连蛋白的黏附受体,通过与HSC中RGD三肽序列结合,维持HSC活化表型,激活TGF-β信号通路,促进纤维化发生。OPN、CCN2和CCN1是肝纤维化的促进因子,它们通过与HSC表面ανβ3整合素结合,调控其中整合素的表达,增加HSC黏附[14]。Chuan Y等[15]研究发现,HSC活化过程中整合素ανβ5明显被上调,其拮抗剂可明显抑制HSC黏附、增殖及胶原I的合成。可见,整合素在HSC活化中起重要作用,参与肝纤维化的发生和进展。
(二)整合素与ECM 活化的HSC分泌大量的ECM,在肝硬化中增加至多10倍[16],其构成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基础。ECM对HSCs的表型转化、增生以及凋亡等生物学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细胞内骨架蛋白通过整合素的外向信号传递调节细胞黏附、迁移和增殖等活动,另一方面,ECM分子通过整合素的向内信号传递调节细胞分化和分泌。整合素介导的ECM和细胞骨架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肌成纤维细胞分化,是维持细胞骨架的关键受体,整合素控制着HSC中的ECM产生和重塑[17]。ECM通过肌动蛋白细胞骨架重组以及Src激酶和ERK/JNK信号分子家族的激活来增加胶原的产生。ECM 的重要成分LN与整合素的相互作用使细胞在黏附过程中同时启动了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KP)和PI3K两条信号转导通路,可影响细胞的黏附、迁移、侵袭、增殖和凋亡。可见,整合素介导HSC与ECM相互作用,在肝纤维化的发生、进展等方面起重要作用[18]。
(三)整合素与血管生成 血管新生是多种病因引起的肝纤维化的共同病理特征,决定纤维化的进展和预后。ECM分子可能通过结合内皮细胞表面特异的整合素来控制毛细血管的形态,同时ECM分子(如纤维粘连蛋白)通过改变表面整合素Na+/H+抗转运系统的位点来调节毛细血管的生长。Ras-Raf-MAPK系统的激活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诱导的血管生成所必需的,在缺乏整合素的情况下,激活FGF的通路减少,从而使FGF的表达下调,血管生成减少。目前所知,至少有8种整合素(α1β1,α2β1,α3β1,α6β1,α6β4,α5β1,ανβ3,ανβ5)参与血管生成。在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等慢性肝损伤中都发现了血管新生的证据。在大鼠纤维化模型中发现整合素ανβ3表达与肝纤维化进展一致,随肝纤维化的加重,α-SMA和CD31表达增加,提示肝纤维化进展中整合素ανβ3表达水平增加与HSC活化和血管新生有关,并与间质重建程度平行。大鼠肝纤维化模型中给予整合素ανβ3、ανβ5特异性抑制剂西仑吉肽,能减少肝脏中血管生成[19]。正常肝组织有少量的新生血管,但几乎检测不到整合素ανβ3,而在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肝组织中,整合素ανβ3的表达明显增加,伴有明显血管新生及VEGF、CD31的表达增加,且这种作用能被VEGF抗体所抑制[20]。可见,整合素与肝窦微血管生成相关,导致肝窦毛细血管化,促使了肝纤维化的进展。
(四)整合素与炎症 免疫活性细胞对肝脏组织的侵袭是人类肝脏疾病和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之一。通过对PSC患者组织中胆管周围单核浸润物成分的研究,发现B淋巴细胞和T淋巴细胞浸润后整合素α4β7呈阳性。α4β7整合素通过与黏膜蛋白细胞黏附分子(MAdCAM)相互作用,在胃肠道淋巴细胞的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肠道和肝脏MAdCAM表达升高与胃肠道疾病(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和丙肝)有关[21]。iNOS是一种在PSC患者中表达并与胆管增生和纤维化相关的促炎性巨噬细胞生物标志物,研究发现靶向整合素αMβ2结合区域,可抑制巨噬细胞iNOS的表达,减轻纤维化的发生[22]。在肝硬化外周血白细胞中整合素CD11a(αL)、CD11b(αM)、CD11c(αX)和CD49d(α4)表达升高,并随着肝功能衰竭的进展而进一步升高,如果阻断CD11b和CD44则降低单核细胞的附着[23],同时在动物模型中如果CD39缺失,则可加重肝损伤和肝纤维化[24]。整合素参与肝损伤的炎症反应过程,并与肝纤维化的产生密切相关。
四、展望
由于肝纤维化是继发于感染、免疫、毒性和代谢原因导致的慢性肝损伤,目前治疗主要是消除致病诱因,虽然许多研究表明消除诱因可能会阻止纤维化进展甚至导致纤维化逆转,但是并非所有患者都对病因治疗有效,有些仍需要抗纤维化治疗,故寻找有效的肝纤维化的防治方法有着积极的意义。整合素介导调节血管生成、HSC活化、ECM的降解,并参与肝损伤的炎症反应过程,与肝纤维化密切相关,因此,以整合素为靶点开发新型抗肝纤维化药物是防治肝纤维化的一条重要途径。由于整合素受体在许多细胞类型上均有表达,不同细胞类型中的配体可能竞争相同的整合素受体,因此靶向干预整合素过程中,必须权衡利弊,以防止未知的临床不良反应的发生,临床中需要确定抗体-药物偶联物进行细胞特异性靶向拮抗整合素治疗的精准医学(包括 RGD模拟物、特异性整合素拮抗剂等)[25],以阻止或逆转肝纤维化,同时避免抑制生理性反应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