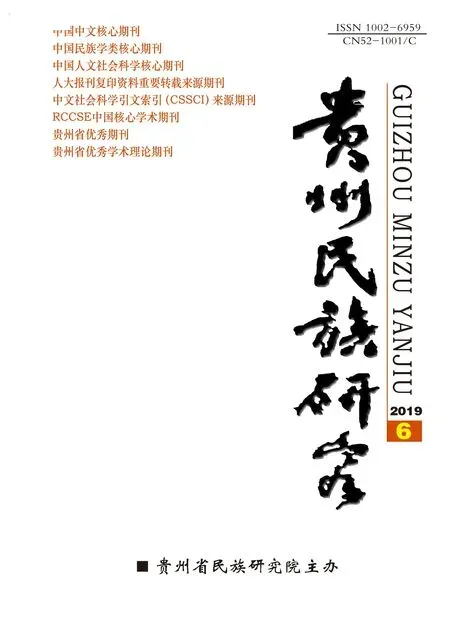民族传统音乐中的人文情怀透析
曹 晖
(淮阴师范学院,江苏·淮安 223300)
人文情怀的学科勘边定界始终是文化追索的哲学化思辨。一方面人类活动对自我价值的定位与追求是人文情怀的主旋律,任何抛却自我价值塑造的意识表达均是对人文情愫的亵渎;另一方面人文情怀虽然是宏观的价值精神,但是始终游离于人与自然、社会的三维一体建构中,并以个体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为切入点;民族传统音乐作为民族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在音乐旋律的波动中倾诉着音乐艺术化意识形态的人文情怀,在人的自我价值实现中,民族音乐通过祭祀、祈福曲调,寄托着歌者祈福避祸的诉求;比如:瑶族《娱神歌》以愉悦神灵,寄托歌者祈求丰收的意愿。进而以合乎个体社会性和自然性本能反映承载音乐艺术生存文化、人伦文化、礼乐文化的基本人文情怀释放。因此,在探究民族音乐人文情怀的释放时,要以人的基本诉求和本能为依托,在人与自然、社会的三维一体中审视音乐的人文情怀,才能在跨艺术机制的音乐范畴中,实现民族音乐的再认知。
一、民族传统音乐中人文情怀凝聚的表现
(一)“人的潜在诉求”
人文情怀核心在于突出人的价值,音乐作为主体化社会艺术,在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始终承载着音乐艺术的文化本位与主体诉求的艺术表达。加之民族群体注重自我张扬的秉性,使得以即兴演唱为主的民族音乐在自我诉求的表达中显得极为彻底,音乐艺术的人文情怀的表达也尤为显著。首先,崇尚真善美,注重音乐对美好事物的描述。民族传统音乐对万物的音乐礼赞,映射着民族群体崇尚真善美的基本人文情怀。比如:东北地区赫哲族音乐《伊玛堪》是专门反映群体憎恶扬善的音乐,词曲普遍具有崇尚真善美的情感韵味。其次,民族传统音乐在演绎中承载着歌者祈福庇佑的夙愿。比如:畲族传统音乐《打徨》主要在人患疾病久治不愈时表演,意在驱邪治病。而独龙族传统祭祀音乐主要以歌者的祈祷为主,在自然灾害面前,祈求五谷丰登;在天灾人祸中歌舞并用,承载歌者祈福庇佑的情感诉求[1]。再者,民族传统音乐通过叙述性曲目的演唱,承载着特定价值的追溯。比如:瑶族传统音乐《盘王古歌》《开天辟地》等音乐表达了瑶族群体追溯人类起源的基本情怀,裕固族歌颂格萨尔王的音乐,体现了民族群体对英雄气概的歌颂与缅怀。
(二)“人的社会本能”
“人的社会本能”是构筑音乐人文情怀的关键,在个体社会活动中,满足个体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是民族传统音乐人文情怀不断凝聚的过程。在民族传统音乐的人文价值移植中,个体的劳动行为在人文情怀的凝聚中不断增添释放人性的改造,比如:瑶族劳动歌《舂米调》《挖地歌》以独具特色的号子,诠释着劳动创造幸福、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达斡尔族山歌《扎恩达勒》通常在放牧、劳作之时歌唱,在劳动中缓解疲惫的即兴音乐哼唱成为彰显民族群体热爱劳动、在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塑造的人文情怀。“在能歌善舞的民族群体眼中万物都是音乐的表达体,在民族音乐品鉴者思绪中民族音乐始终保持了简单音乐的复杂文化表达。”[2]因此,民族传统音乐人文情怀的艺术表达,贯穿至群体的社会生活当中;或以曲示俗,展现群体在民俗风情中对个体自我价值的再塑造。比如:独龙族传统音乐《习俗歌》将“卡雀哇”等传统节庆融于音乐当中,从而洋溢着群体认同的民族自豪感,歌舞齐驱,承载着民族群体对社会是非曲直的评判,彰显着个体对社会真善美价值的群体认同与礼赞;载歌载舞,表达着个体独特的审美思维和朴素的艺术追求。
(三)“人的自然属性”
“人的自然属性”是民族传统表达人文情怀的重要一环,人的自然属性与民族群体个性张扬秉性相互碰撞,无疑为民族音乐人文情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载体。在“人的自然属性”展现中生老病死是重要支柱,民族群体在生老病死的音乐表达中必然透露着相关联的价值追求、情感表达。
一是民族传统音乐对出生与死亡的观念的情感释放。生与死是人的最直接的自然属性,音乐对个体自然属性的表达,形成了民族独特的艺术情感。比如:哈尼族传统音乐《迷煞维》作为丧葬音乐的典范,展现了哈尼族群体平静乐观的生死观。而土家族丧葬音乐《跳丧舞》则以祖先崇拜、着重来生表达其独特的生死观。二是民族传统音乐在疾病抗争中以社会习俗承载疾病自然性的情感[3]。一方面在疾病的音乐表达中,民族群体通常借助超自然力量的颂唱,企图借助神秘色彩驱除痛苦;另一方面在与疾病斗争中,彰显群体祈福避祸的音乐表达。比如:畲族传统音乐《打徨》主要在人患疾病久治不愈时表演,意在着驱邪治病。三是民族传统音乐在婚嫁情爱的表达方面,承载着敢于追求、直白朴素的情感价值观。哈尼族传统音乐《然咪比》作为婚嫁音乐,反映了哈尼族直白简朴的婚恋情怀[4]。当然,民族传统音乐在人文情怀的聚焦中以婚姻为支点,崇尚个人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反对转房婚等婚恋陋习,在强烈音乐呐喊中呼唤人的本性。四是民族传统音乐在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注重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人文情怀凝聚中,典型音乐艺术的表达。比如:藏族、鄂温克族在民族传统音乐中以歌颂自然的形式,绽放着草原民族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人文情怀,特别是藏族群众禁止杀生的人文精神,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5]。
二、民族传统音乐中人文情怀释放的载体
(一)“个体”——民族音乐人文情怀释放的出发点
人文情怀旨在弘扬个体的价值,主张个性自由、注重个体社会价值。民族传统音乐在以人为中心艺术塑造与演绎中极为注重人的本能价值,音乐的旋律、主题定格都以歌者个体的审美情趣为出发点。就民族传统音乐的发展来看,民族传统音乐是体现人本主义、推崇个体社会价值的重要艺术形式。一是在民族音乐的起源中,即兴音乐占据着相当比例,特别是民族地区语言文字不对应的趋势下,使得即兴音乐艺术完全释放了群体的天性,注重自我、追求自由的人文情怀被释放得淋漓尽致。二是在民族音乐的传承方面,民族音乐多以口口相传为主,音乐的传承过程成为民族群体释放自我价值过程中的重要一环[6]。就民族音乐艺术的形态而言,一方面民族音乐艺术始终将“娱神乐鬼”“祭祖拜神”音乐艺术以群体独特的审美形式表达,或者说民族传统音乐是借“娱神乐鬼”“祭祖拜神”满足自身需求的艺术。比如:土家族群众在《跳丧舞》中载歌载舞、欢天喜庆,以顺应自然生死的乐观情怀审视生死。另一方面民族音乐在婚嫁、待客方面,不断渗透着音乐潜在的人文情怀,并将人文情怀情感化,比如:佤族在婚嫁、待客方面极力映射人文情怀,《迎客歌》《待客歌》将佤族群众注重自我地位、自我尊重的情感歌唱得活灵活现,仿佛身临其境[7]。从民族音乐的时代转变而言,推动民族音乐接受时代洗礼始终是民族群体对自我价值、自我社会价值的肯定。因此,不论民族音乐对人文情怀进行何种承载与表达,人的情感总是人文情怀最佳、最显著的载体。
(二)自然、社会——民族音乐人文情怀释放的载体
民族音乐艺术在人的价值诉求下通常以“自然”“社会”为载体,借助自然、社会表达个体独特的人文情怀。换言之,在民族传统音乐艺术人文情怀的释放中,自然与社会是根本性载体,是双重性载体。一方面个体在音乐艺术属性的锻造中势必要以自然、社会为载体。比如:蒙古族音乐《马儿马儿快快跑》、京族音乐《采茶歌》都是群体通过自然、社会实物,来开展音乐艺术表达[8]。另一方面在民族音乐艺术人文情怀的释放中,自然、社会则成为具体人文情怀承载的载体,比如:瑶族音乐《创世纪》以说唱的音乐形式告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将遭受自然惩戒的自然法则。总之,在民族传统音乐人文情怀的透析中要始终以人与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载体为基础,承载人文情怀的文化内涵。
三、民族传统音乐中人文情怀的基本反映
(一)生存文化——民族传统音乐人文情怀的起点
生存文化是人文情怀价值追索的前提,是个体人文情怀转化的基本体现。生存文化是衔接人与社会的过渡点。个体对生存的认知,确定了其大致的社会轨迹。可以说,生存文化是民族传统音乐人文情怀的起点。
首先,民族传统音乐对生存文化的反映,体现在音乐对人与自然同根同源观念的表达[9]。比如:仡佬族通常祭祀神树,在问答式古歌号子中,仡佬族群众将禁止乱砍乱伐的生态意识融入至音乐词曲中,彰显着群体朴素的生存之道,蕴涵着仡佬族群众简朴而深邃的人文情怀。此外,在藏族、门巴族早期宗教音乐中,音乐表演对禁止杀生、人与自然万物同根同源观念的诉说,也是对民族传统音乐基本人文情怀的有效补充。
其次,民族传统音乐将生存文化具化为“自然敬畏、感恩自然”的情感表达。少数民族群体依山傍水、逐水草而居的自然生活习性成为音乐表达群体自然生活的重要载体[10]。自然敬畏是体现民族群体适应社会、改造社会的价值标尺,在音乐艺术中通常以双向对比的形式演绎民族音乐来释放人文情怀。比如:瑶族音乐《创世纪》以说唱的音乐形式、告诫人与自然需和谐相处,否则将遭受自然惩戒的“自然敬畏、感恩自然”情怀在音乐表演的形态中无限放大,使之成为一种禁忌。再者,民族传统音乐对生存文化的表达,表现为民族民歌对朴素生态习俗的歌颂。比如:鄂伦春族群体对禁止捕捞、砍伐幼苗的生态习俗,以山歌的形式世代歌唱传颂。
(二)人伦文化——民族传统音乐人文情怀的纽带
一是民族传统音乐对婚嫁习俗中人文情怀的承载,特别是部分民族传统音乐在婚嫁习俗的人文情怀释放中,不断将特定的音乐形式定格于婚嫁文化当中,成为民族婚嫁文化的重要见证和有机组成部分[11]。比如:仡佬族音乐“顶翁罗”是群体对自由恋爱、尊重女性婚嫁自主等人文情怀的强烈表达,而《哭嫁歌》则是出嫁姑娘对父母、家庭依依不舍的情感表露。
二是民族传统音乐对家庭文化和家庭美德中人文情怀的音乐汇聚。家庭文化是人伦文化的核心,是人伦文化的最终归宿,在民族传统音乐的人文情怀释放中,音乐所摄入的主要是孝道文化、家庭中个体关系、家庭美德;一方面民族地区普遍盛行“族长制”,在家族式村寨的艺术中,音乐艺术所承载的人文情怀基本与社会对人文情怀的认定无异。另一方面在家庭美德的音乐礼赞中家庭伦理关系成为民族人文情怀释放的基础,苗族、侗族等族群繁多的民族,山歌、古歌多以反映群体喜闻乐见的家庭天伦习俗[12]。
三是民族传统音乐对丧葬习俗中人文情怀的归宿性释放。个体生命的尽头是人文情怀的最终落脚点,音乐艺术对人伦文化的解读,蕴涵着民族群体独特情感的价值追求,即民族音乐对丧葬文化的吸收。
(三)礼乐文化——民族传统音乐人文情怀的主体核心
在人文情怀的表现形态中礼乐文化是最为核心的层次,礼乐文化是音乐艺术人文情怀对社会制度准绳的音乐艺术性摸索[13]。首先,民族音乐对礼乐文化的人文情怀承载弘抑结合形式开展,在正面弘扬、歌颂的同时又借助音乐的表达方式,以民族禁忌、禁止性行为的劝勉浓缩民族传统音乐对人文情怀的承载。比如:仡佬族音乐《戒烟歌》《戒赌歌》以诗歌化的音乐艺术将社会道德规范以妇孺皆知、通俗易懂的方式承载,活化了民族礼乐文化的传播[14]。其次,民族音乐对人文情怀中礼乐文化的萃取,以民族群体喜闻乐见的礼仪习俗为切入点,通过礼仪习俗的倡导,释放群体大众认同的、彰显个体价值需求的人文情怀。比如“打亲敬酒舞”与盘歌等音乐是从仪式性习俗中衍生而来的关乎社会礼仪的音乐,在音乐演绎中附带着群体赖以遵循的礼仪法则。而阿昌族音乐《蹬窝罗》从音乐的角度审视着阿昌族群众喜庆之余的礼仪性举止。再者,民族音乐艺术对人文情怀的凝聚和释放,以区域性社会制度为基石,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歌舞化表达,反映歌者用制度衡量评价自我价值,从而以制度的侧面凸显音乐艺术的人文情怀。比如:毛南族“榔规”作为早期社会法制制度,至今在毛南族《叙事歌》中都有提及,目前依旧是村寨基层组织内部衡量是非曲直的尺度[15]。
音乐是人艺术化的意识反映,人文情怀的音乐表达是民族音乐艺术的精髓。以人、自然、社会三维一体的音乐载体为基准,以民族音乐生存文化、人伦文化、礼乐文化为切入点,剖析民族音乐艺术的人文情怀成为整合民族音乐文化,构建民族音乐文化共同体——人文情怀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