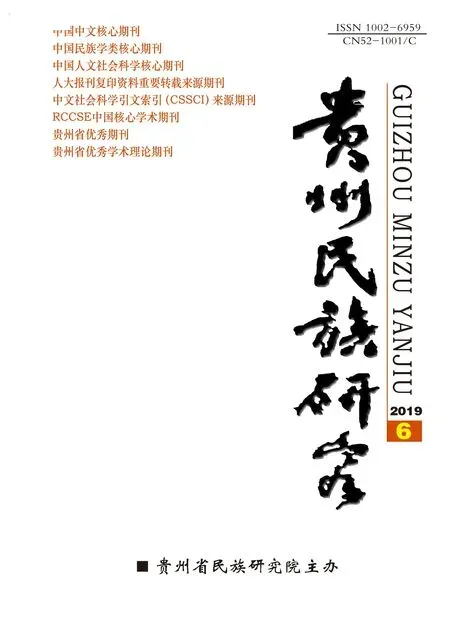边境多民族口岸社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
——以中缅边境片马口岸为例
李智环 司文一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504)
从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学者对于口岸的研究起始于殖民地的开辟,选择合适的口岸开设地点、探讨如何利用口岸掠夺殖民地资源或输出本国商品等是早期口岸研究的主要内容。与之相对应的是,近代以来列强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地区及通商口岸所展开的各类所谓学术考察和研究成果多属于入侵中国的情报资料。而国内的口岸研究方面,主要体现在自清政府被迫将沿海沿江城市列为通商口岸至今(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独立主权的国家环境令口岸制度得以向健康方向发展完善),学者们从历史、区域经济以及地理学角度对口岸的功能进行分析和讨论。总体而言,现阶段与边境口岸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物流、旅游业、卫生检疫以及管理等方面,其中对于电子口岸的研究可谓近年来的热点。并且,侧重点多在于“事”而忽略“人”,缺少针对口岸区域内毗邻国家民众间互动交流的“深描”和文化阐释。在非传统安全的视角下,关注边境口岸区域及边民的研究成果则更为鲜见。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边境并非处于隔绝状态,事实上存在着丰富而紧密的个人、家庭和多种经济关系。”[1]
而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在涉及云南的相关研究时亦不乏颇带“保守色彩”的观点,即云南是出“和谐经验”的地方,“问题研究”相较于前者的重要性要小。但笔者认为,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新的时空背景下,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都日益频繁,特别是边境口岸区域内民族间各种内容的交往历史悠久,连通相邻国家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及民族关系的文化内涵更显突出,因之边境口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边民是边境口岸区域内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政治互信的主体和人文基础,更是边境安全语境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目前以和平发展为主流的边境地方社会中,相较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逐渐拥有更多“话语权”,所以对于口岸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更显迫切和必要。
一、田野点:片马口岸及相关社区简介
片马,在世居于此地的茶山人(景颇族支系)语言中就是“木材堆积的地方”,历史上即是中国与缅甸北部的交通和商业要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环。并且,片马及其附近区域更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西南边疆危机中的抗英事件,以及作为“二战”时期中国与盟军主要的空中通道——著名的“驼峰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闻名于世。此外,1948年缅甸独立后片马即被缅甸实际占领,直到1961根据中缅两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规定,片马、古浪、岗房地区才归还到中国。据片马镇政府2017年12月向笔者提供的信息,片马是隶属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乡镇级行政单位,全镇辖片马、古浪、岗房、片四河4个村及景朗1 个社区共14个村民小组、5个居民小组。镇域内居住着汉、景颇(茶山人支系)、傈僳、纳西、白(勒墨人支系)、彝、壮、怒等8个民族,共有820户3246 人。其中农业人口1901人,城镇人口1367人。同时,片马镇还有近5000人的流动人口。
笔者将片马口岸作为典型来探讨,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片马作为国家领土边缘地带的历史悠久。其二,片马口岸区域的欠发展程度较深,不但区域经济自生能力较为欠缺,其所依赖的边境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也是众所周知的国家级贫困地区。其三,其战略位置十分突出,片马地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坡腹地,也是滇西北地区通往东盟国家的唯一陆路通道。云南省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格局中被定位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作为滇西北最为重要的国家级口岸——片马口岸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更是“兴边富民”战略工程在滇西北地区实现的窗口地带。
二、片马口岸社区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人类学调查
(一)生态安全问题
边境地区的生态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边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同时也可能成为影响边境地区社会稳定发展以及相邻国家间边民生存安全的障碍性因素。而现阶段片马口岸区域内存在的生态安全问题带有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特征即非军事性、跨国性和动态性等,主要表现在几乎每年都要扑灭来自缅甸的山火问题上(即当地人俗称的“打火”)。
片马与缅甸接壤的缅北山区,人们至今还有烧山耕种(刀耕火种、燃烧秸秆等)的习惯,每年冬季就是他们的烧山季节。因此,缅甸的山火烧到中方一侧是常有之事。自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设立以来,片马当地群众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森林保护工作,但“打火”却是其中最为紧急和耗费精力的事情。每当缅甸的山火快烧到界桩时,片马镇政府就要在短时间内组织边民们上山“打火”,每个家庭都要出一个劳动力,且要保持手机等通讯设备的畅通。火势小时用水浇灭,一周左右可结束。火势较大时,大家会紧急挖掘出几公里的隔离带,有时甚至会在山里“工作”一个月。
虽然“打火”通常发生在当地人的冬歇时段,但边境口岸地区的多数男性在此期间因参加打火同时“消失”到山里,对于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无疑具有消极影响,如果缅甸山火烧到中国境内,则更会对中国边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形成直接威胁或造成现实的经济损失。
(二)人口安全问题
“缅甸媳妇”和重组家庭数量较多是目前片马地区存在的主要人口安全问题。
一方面,“缅甸媳妇”数量不少。事实上,妇女外流现象在云南的中缅、中老以及中越边境地区都普遍存在。而与笔者在怒江地区调查过的其他村寨状况所不同的是,片马镇的“光棍”数量却并不多——原因是“缅甸媳妇”填补了本地妇女数量减少的“空缺”。多位村民对笔者表达过类似内容的信息:“我们这里不缺女人,没媳妇的一般只有身体不好的,一个村子没几个(光棍),缅甸多的是女人,她们都愿意嫁来中国。”笔者在田野工作中也发现,片马镇的“缅甸媳妇”数量要较怒江沿边的其他村寨多。此种状况不能不说与片马作为口岸区域,交通上的便利为国境线两侧边民的“亲密往来”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有利条件有着直接关系。虽然对于片马镇的主要民族傈僳族和茶山人(景颇族支系)而言,娶过来的“缅甸媳妇”不会存在多少“文化适应”问题(多是同一民族、语言相通且都信仰基督教),但娶“缅甸媳妇”的风险还是有目共睹并且对于其中的多数人来说是可以预见的。“缅甸媳妇”在中国没有户籍,无法享受到相应的政策性保障(土地分配、“新农合”的医疗保险、扶贫优惠等)。而这样的家庭往往又是国家人口管理的“盲区”,易出现超生现象(四胎、五胎的情况往往出自于有“缅甸媳妇”的家庭),其中“缅甸媳妇”和“超生无户籍孩子”在医疗方面的花销会占去部分家庭经济支出中相当大的比例。
另一方面,重组家庭数量较多。笔者通过田野工作了解到的情况,将其中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两方面。其一,中国边境地区相对内地和沿海较为贫困的现实,加之手机微信等社交软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普及,令当地部分已婚的中国籍妇女因向往浪漫爱情和现代化的生活而抛弃家庭。比如,笔者在片马村湾草坪组曾参加过一个重组家庭的婚礼,夫妻皆因前任伴侣出轨而婚姻破裂,当笔者问起男方儿子的感受时,这个11岁的傈僳族少年的回答虽然平静却充满了怨气“现在不想和她(指妈妈)说话,她跟那个年轻的男的去上海……”。其二,非法跨境婚姻家庭稳定性较弱。多数缅甸妇女嫁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无外乎经济和情感两大因素,但前者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许多夫妻感情基础不牢固,而在缺乏国家法律认可和保护的状况下,家庭易破碎。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嫁入中国的缅甸妇女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较低,又不能享受到中国边民的各项福利,导致其中少部分人通过出嫁实现美好生活的梦想破灭而重回祖国,而还有少部分妇女会选择再嫁来提高其个人的生活质量(比如,以片马为跳板再嫁到中国其他地区)。
众多“缅甸媳妇”的存在,反映出的是片马口岸区域由于当地男女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引起的男性单身群体扩大的人口安全困境。而几乎成为“平常现象”的重组家庭问题,既与非法跨境婚姻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也与当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特点有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家庭破裂的原因是什么,对于作为下一代的孩子的伤害却是不可逆的。因此,人口安全问题不但会在目前影响到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伴随“问题家庭”中孩子的长大其惯性作用还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段里持续。
(三)经济安全问题(口岸区域经济自生能力欠缺)。
笔者认为,经济安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动态和谐状态,是在某一区域具备较好的经济自生能力基础之上实现的。换言之,经济自生能力欠缺,则不可能在“一带一路”的开放背景下拓展起航,甚至时常会因为“内部故障”频现“安全警报”———事实上,作为在片马口岸区域生活的主体——边民们对此是最为“缺乏安全感”的。片马镇至今常住人口只有两千多,之前的木材贸易给这一口岸小镇带来了车水马龙的繁华,外界对木材的需求和几万流动人口在此地日常生活之需是片马镇快速发展的动力。但当木材贸易日渐萧条、外需接近不存在时,片马地区的发展一下子陷入泥潭、举步维艰。简言之,就发展现状而言,片马作为滇西北边境地区重要的陆路口岸,不但没有发挥出口岸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这一地区的人们似乎还处于“贫困中观望等待”的状态。笔者将片马口岸区域遭遇的经济发展困境归结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自然地理及气候环境的客观制约。一方面,气候条件相对恶劣。整体而言,片马镇平均海拔较高,并且多为超过25度的坡地,雨水霜冻期长,不适合多数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另一方面,交通条件相对落后。云南省省会昆明市距离片马口岸730多公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六库镇到片马镇也需要3个半小时的车程(96公里多为崎岖山路),这不仅增加了片马人民的生活成本,而且路途的艰辛(尤其是在风雪丫口附近,冬天积雪,夏天时常会有滚石和泥石流)也增加了外来人员投资的风险。
(2)片马地区的多数边民,处于不想墨守成规却又不知如何改变现状的困境中。长期以来,重重大山令此地的人们生活在几近封闭的环境中,因而也造成了他们思想保守,缺乏长远眼光的思维方式。笔者在此引用一位当过村干部的景颇族大叔描述那时多数人的状态:“能从缅甸运木材的时候,他们(指村民)就每次帮外地老板运几天,拿到钱就休息,等这笔钱花光了再出去干活,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木材有用完的一天!”而笔者在片马国门小学与老师们的接触过程中,也得到了相关的佐证:虽然片马之前经济繁荣,但是多数片马人并没有把繁荣之时所得的金钱以及精力投入到教育中来,所以现阶段多数在读学生的家长仅为小学学历,对孩子们的学习基本没有辅导能力。
(3)基层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缺乏灵活性。很多政策的执行没有切实考虑到该区域的实际情况,给边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在此仅举一例:当笔者对于一位村民在短短几年内建好的两处新房面露疑色时,这位村民的解释也颇带怨气:“我这房子刚盖完没多久嘛,去年政府‘精准扶贫’又有了建房的政策(和补助),本来是好事嘛,我就想在原来的房子上加盖一层,可他们(基层干部)非要我重新盖一栋……”可见,由于政府基层工作人员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过于刻板、教条,并没有收到理想的帮扶脱贫效果,进而对于增强片马口岸区域经济自生能力的作用不明显。
三、中缅边境欠发展口岸社区非传统安全问题解决之策
片马口岸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可以说在中缅边境口岸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根据笔者近年来在中缅边境多个口岸区域的田野工作了解到的情况,事实上,中缅边境除了德宏州内距离较近的三个口岸姐告、畹町以及章凤,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有形成多口岸整体性运作的系统趋势外(即使是畹町、章凤口岸,区域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余口岸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都处于落后状态。而由于沿边村寨少数民族妇女外流现象不断,所以“缅甸媳妇”在中缅边境地区是具有普遍性的人口问题和现象。生态安全方面,即使不是缅甸的越界山火,也存在林木盗伐或随意燃烧生产生活垃圾而造成空气污染等问题。因此,只有切实地解决上述问题,才能真正实现“边境安全中的口岸发展”。
(一)通边
笔者曾撰文指出:“边疆政策既要充分发挥边界在国家交往中‘通’大于‘堵’的功能,又要兼顾政策本身的惠民性,避免因强调国家利益而淡化、稀释地方社会和当地人的利益。”[3]然而,在解决边境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时候,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一国之力。中国国家政策的效力仅限于国内,口岸“通达”以及边疆地区的发展同样需要相邻国家间在相互理解并不断接触、协商的基础上扫清障碍性因素。但另一方面,中缅边境在很大程度上与“硬边界”的代表类型——美墨边境(美国和墨西哥)的情况相似,即国家间力量对比差距明显,在多种合作方面有互补发展的需求。所不同的是,缅甸国家地方武装割据的现实状况,导致国家间的沟通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协商来弥补——这也显现出以口岸为代表的中缅边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来。
以片马口岸区域为例,“打火”与“跨境偷盗”问题长期困扰边民的生活。客观而言,现状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处于被动地位,而中国边民在某种程度上则可以说是“受害者”。从“当地人的视角”观察,目前无论基层公务员还是普通边民尽管对此都颇有抱怨,但在公共场合中却很少提及。笔者在私下曾询问过部分人,官方与民众的回答很一致即担心会对中缅两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讳疾忌医”的做法。笔者认为,针对“打火”问题,中方应与缅方(主要指克钦邦政权)在保持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向缅方提供帮助。当缅甸山火形成难以控制之势,缅方及时通知中方,中方不仅要提供较为先进的灭火器具,必要时还应向缅方派出专业灭火队以有效防止缅甸山火烧至中国境内。由此可见,加强中缅两国的沟通协商机制是“通边”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二)“实边”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实上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同时进行的,因此习近平同志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地理位置处于国家领土边缘地带的口岸区域。而本文所指的“实边”与历史上中央王朝通过移民巩固守卫人少地袤的边陲之地的涵义已大相径庭。现代中国的边疆地区,虽然与内地相比依然可以说是地广人稀,但在国家军事实力日渐强盛即传统的军事安全有确实保障的情况下,大规模地将人口移至边境地区的情况已不再需要。与此同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更加受到各国及其人民的关注和追捧。所以,本文提出的“实边”主要是指在全面了解边民主观想法和行动选择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质量,以抑制边境地区人口外流,为边境民族社会有“活力”的发展即“兴边”奠定坚实基础。
一方面,从经济生活层面上“互嵌”。片马口岸区域历史上盛产各种中草药和经济作物,有着“片马无穷山”的美誉,长期以来世居于此的人们依靠采摘中草药、木耳、菌类等山珍到市场交易而得以实现民族社会的延续发展。只是由于历史与社会条件的局限性,并没有在此地形成一套真正科学完整的运行机制。但盛极一时的跨境木材贸易,却令当地人很快习惯于依赖“快餐式的生财之道”而将传统的生计方式抛于脑后。然而,经过近十年的“沉寂—痛苦—探索”,这一地区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建立在山地立体性气候基础上的“三圈共同体”的生计方式格局,即中心的商业圈、以旱地种植为主的中间圈、以及以水田和经济林木种植为主的外围生计圈。并且,由于片马当地的民族分布与地理海拔存在一定的联系,所以生计方式的“互嵌”也与当地居住格局上的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结构有一定的重合。
具体说来,中心圈囊括了外来流动人口以及景朗社区、片马村飞机场组的边民,其主要构成民族为汉族和白族。古浪和岗房两村(以傈僳族和景颇族支系茶山人为主)由于气候相对温暖,当地政府组织村民种植草果和核桃(据两村村委会提供的数据,古浪村草果2500亩、核桃4000亩,岗房村草果3680亩、核桃7360亩),目前村民们的辛劳已获得相对充裕的回报。但片四河村(以傈僳族和白族支系勒墨人为主)受地理条件的制约(距中心商业圈较近,但气温较片马其他地区低、无霜期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笔者认为,如果片四河村能够在仓储、加工等领域有所突破,事实上会与片马的其他村寨形成口岸区域经济发展的互补、连动之势,从而实现这一地区的“一盘棋”效应。
另一方面,从知识技能层面“充实边民”。如前所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振兴边疆民族地区的系列优惠政策,比如,“精准扶贫”“兴边富民”以及“一带一路”等,笔者在多次调研过程中亲见,片马人能够切实感受到国家政策的力度也获得了部分收益,并且表现出了希望借助政策之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愿望,但多数人对于具体如何去做却不知所措。而当地基层政府的扶贫措施也部分因教条、刻板的工作方式而收效欠佳———这些“人”的问题无疑是需要“转动脑筋”才能解决的。其一,进一步加大片马口岸区域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不但要不断增强国门中小学的师资力量,提升教师群体的基本素养,还需根据边境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实际情况调整教育方式,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令孩子们热爱学习,不至于因厌学而辍学;其二,针对初中毕业生以及中青年劳动力,每年都要开展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劳动技能短期培训(比如,农技知识、农产品加工、民族刺绣技艺等),帮助边民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实现生计方式多元化的转变;其三,不仅要令基层公务员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学习先进的行政管理经验和知识),还要定期在他们中间组织工作实践的成绩展示与宣讲,令其尽量避免因工作缺乏灵活性而出现不良效果。
笔者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口岸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亦有“人口实边”之效。片马口岸区域存在的“缅甸媳妇”和重组家庭数量较多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当地妇女外流引起的,但其实质是中国沿海、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的对人口流动的“拉—推”之力所致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客观地说,边疆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缩小了,人口外流现象即会从根本上得到抑制。而笔者在怒江其他沿边村寨所做的调查中也发现,由于国家政策和资金对边疆地区的倾斜及大力扶持,目前怒江外流少数民族妇女(以傈僳族为主)已出现了“回流”现象。
(三)兴边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审视口岸功能特别是文化功能对富边、固边、民族融合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4]笔者对此的理解是,文化作为国家重要的“软实力”,在口岸地区应成为国家间经贸交流互动中所承载的主要内容。进言之,边境口岸除了拥有自然资源及通商功能外,口岸所在的边境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拥有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和风俗风情,历史、人文景观丰富——是多民族文化的富集地。文化是口岸未来发展的核心内容与方向——文化在戍边、守边的基础上,更应发挥其富边、兴边的重要作用。
就现状来看,文化产业的作用在目前片马口岸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片马口岸区域自古以来即是茶山人、傈僳、勒墨人、彝、怒、纳西以及汉等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人们的文化、宗教在此地碰撞、交融。因此,片马已形成了具有本地特点的边境地域文化模式,而其特色的文化内容与形式应在未来的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边境文化旅游产业是其合适的路径选择。正在建设的“国门第一村”不仅要突出茶山人的文化,还要融入傈僳、怒等当地其他世居民族的特有文化形式。并且,长期以来多民族、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相处也是片马口岸区域的吸引力所在。蕴含着丰富抗战历史文化且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驼峰航线纪念馆”,同样是片马口岸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所以,在“怒江大峡谷国家公园”的建设规划中,除了怒江秀美旖旎的高山峡谷自然风光之外,作为滇西北边境最为重要的陆路口岸——片马口岸的民族风情文化游应成为其中重点打造的品牌之一。
而我们亦可以预断,当口岸地区的特有文化以产业的形式存在,并成为边民提高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时,即是文化富边的展现。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化软实力的助推,从而实现边地口岸区域经济腾飞、人文交往互动频繁,生机勃勃的场景,并由此证明文化能够兴边,振兴口岸必须依靠文化的力量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