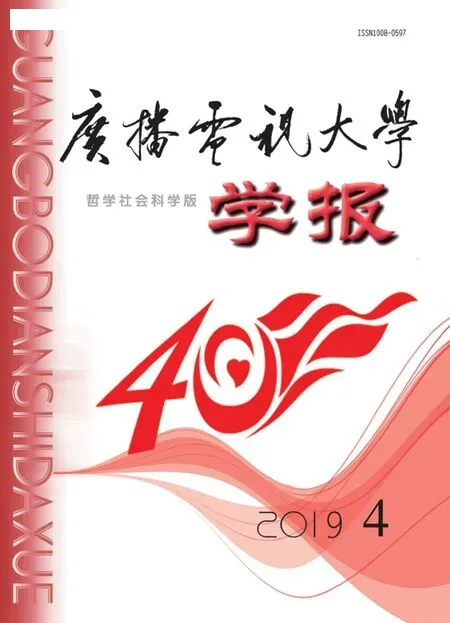诗非悟不灵
——周珽“诗脉说”简析
陈颖聪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香港 999077)
周珽(1565—1645),字无瑕,号青羊,海昌硖川(今浙江海宁硖石)人,为明代嘉兴府博士弟子员,然一生未仕,循其先祖之训,过着吟诗写画的乡居生活。隆武元年,清兵攻入硖川,周珽自缢,以示对朝廷的忠贞。周敬,号澹斋,是周珽的曾祖,仕履未详,曾编有《唐诗脉》,未及付梓,即遭倭寇洗劫,稿件散佚。[1]P440
周珽在其选编的《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以下简称《评林》)《凡例》中告诉我们:
余自髫年醉心诗学,思缵先志。适检家藏破笥,拾一未刻时剩稿,披阅间觉比古今诸家选实为精细,可称全璧。恨纸久烸爛,前後次第殊多乱阙。嗟乎,以先人手泽沉沦百十年,复沐馀波,岂可再使泯灭耶?因加删补,仿先伯亭山公注杜集意,著为《会通》。[2]P440
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评林》,是周珽在其先祖所传残稿的基础上,重新选编而成的一个唐诗选本。其中“诗脉”之说,是周珽沿其先祖周敬之说,而又有所删补所成。[1]P441
对“诗脉”之说,明人陈继儒在为《评林》撰写的“序”中是这样理解的:
此选直从《素问》、《灵枢》中来,不望气视色,不执古人之僻论禁方,而但以精察脉络为主,运用于心手,工巧之间,针砭汤液无所施而不合。诗之脉亦然。[2]P418
可见陈继儒是以中医的特点和术语,解释周氏“诗脉说”的特点。诗之脉,有如人之脉,是生命之所系,是诗的综合素质的集中反映;所谓“不望气视色,不执古人之僻论禁方”,则是说周氏对诗歌的理解和鉴定,不重其表象,而重其脉络;不轻信前人的结论,而是有所参详辨证,一句话,就是来自于自己对诗的感悟。
陈继儒对周氏所说的“脉”的理解,是深得周氏本意的。周敬就说:
彼(按:指诗)其映古今,光宇宙,而与世罔极者,不徒摛章饰句,而直有一脉以神行其际也。[2]P419
又说:
唐诗虽沿制于藻绘,原有一种神理不可磨之处,斯能跨绝时流,永垂不朽,而周秦以后于斯为盛也。[3]P435
在这里,周敬对“脉”有了十分明确的说法,这个脉就是“神”,或者说是“神理”。他是以唐诗为例,说明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风格的诗,都永远存在着一种“神”或“神理”,这种“神”或“神理”的作用,使诗不断承传、发展。而在承传、发展的过程中,时代可以不同,诗的风格、体裁也可以各异,但其中的“神”或“神理”是贯通的。所以要研究诗、认识诗,就要把握诗中的“脉”,即要领会诗中的“神”或“神理”。
那么,周氏所说的“神”或“神理”指的是什么呢?周敬没有留下进一步的说法,但显然,他所强调的是“理”,就是自然、本然、不为人力所可以改变的内在属性,也就是诗的本质属性。这点,我们可以从周珽的叙述中体会得到。
周珽对诗歌曾有这样的要求:
诗先气格,气格既具,性情所到,一往遂成。意不在奇,语中不在异,自然韵度宫商。……若古诗,以风调高古为主,其道在神情之妙,不可以力雄,不可以材骋,不可以思得,不可以意致。……律诗全在音节、格调、风神。[4]P168
在这里周珽是从“气格”、“性情”、“韵度”、“风调”、“音节”、“格调”、“风神”这些方面去认识诗的本质,认为这是诗中不可缺少的属性。但周珽谈得更多的,是“性情”与“神”或“神韵”。他在评论李峤《侍宴甘露殿应制》(“月宇临丹地”)这首五言律诗时说:“格调亦整,特乏神韵。”[4]P178在周珽看来,这首诗,从格律的要求看,是工整的,然而全诗只是简单地罗列出侍宴的场面及过程,其中并无可以让读者感触的情趣,更无可使读者足以神驰的想像空间。这样的诗,是缺乏神韵的,算不得是上乘之作。对贺知章《送人之军中》(“常经绝脉塞”)这首五言律诗,周珽又说:“昔人赏其奥,吾更赏其韵。”[3]P431这首诗句句是景,亦句句是情;句句是作者随遇所感,亦句句是古今游子、亲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思念。这种景中之情,情中之景,活生生的印象,引起读者各自不同的联想与感怀,在这首诗中作者之情与读者之情很容易就融洽在一起,收到了神会、通感的效果。周珽认为贺知章这首诗中的精华,在于其诗所表现的这种独特的韵味。
所以,周珽引用并赞成黄子肃关于“第一等句得于天然,不待雕琢,律吕自谐,神色兼备”[2]P419的说法。诗句能具有自然天籁之声,天真素朴之情,就是最好的诗句。这一种“律吕自谐,神色兼备”的境界,就是周珽追求的“神”或“神韵”。周珽是把周敬所说的“神理”,直接改变为“神韵”的说法,从强调诗之本质所属之“理”,具体化为诗之审美本质的“韵”。那么,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呢?
先看周敬对诗的本质的看法,他认为:
两汉、六朝名流辈出,骚赋古词体裁迭换,无非争妍于句字,竞丽于篇章,而精意消歇,孰能登坛主盟而上符三百篇之旨哉。[2]P419
出于推崇盛唐的原因,在周敬的眼里,汉魏的诗是逊于盛唐的,这方面我们暂且不论。笔者认为,在这句话中,透露给我们的应是,在“字句”、“篇章”与“精意”之间,周敬所重的是“精意”。而这个“精意”,周敬则认为是经作者“极虑精研,意在笔先”[5]P3而表现于诗的,也就是说的,是在下笔之先的意念。可见他认为,诗人之所贵者,不在于字句篇章,而是在先于字句篇章,而又充溢于字句篇章的“意”。用周敬的话来说,这就是诗的“神理不可磨之处”。
很明显,周敬关于“神理”的基础,是诗中“意”的提炼和形成。而这个“意”,在古代诗论中,又多理解为“志”。《毛诗序》曰:“在心言志”,《广雅·释言》:“诗,志意也”,宋人丁度在《集韵》中更是直接说:“志,《说文》:意也”。在传统训诂家看来,这个“志”与“意”,是二而一的,其具体表现则是“情”。所以郭绍虞先生指出:“唐孔颖达早已看出,‘志’与‘情’是一个东西,‘言志’与‘缘情’并无本质区别。”[5]P67又说:“《序》中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是二而一的东西。”[2]P291
周敬关于“神理”的基础,是以“情志”为表现的“意”,则这个“意”就充溢着使人感动和回味的内容。所以,他有时又把“神理”说成为“神韵”。在论卢照邻《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这首诗时,周敬曰:“通篇格局雄远,句法奇古,一结更饶神韵。”[2]P431此诗写尽权贵如浮云,不可长驻,而唯不变者乃自然之生生不息。全篇在尽数史上之权贵如浮云后,只在诗的结尾处,轻轻用“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袭人裾”两个句子,不动声息地点出荣华富贵并非长久可靠之物,唯有自然生生不息者乃得长盛不衰。诗中末两句表面上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花开花落的景色,而在全诗衬托下却含有无限的情。读者通过自己的体会而感悟其情,而与作者取得了通感,领会其意,品出其味。此中的“意”、“味”,周敬称之为饶有“神韵”。
从周敬的表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神理”与“神韵”,在周敬的认识中是并无二致的,当他说诗的本质、诗在流传中所表现出的生命力时,偏重的是“理”;当他说诗所产生的意象、情境,读者对作品的回味、感悟等等时,偏重的则是“韵”。而其中始终起作用的则是“神”。对于这样的“神”,周敬没进一步的说法。
但周珽在接过其先祖的话头时,这个“神韵”或“神理”的内容就得到展开了。
他在提出自己的说法时,先引证了前贤的几段文字,黄子肃曰:
妙悟者,意之所向,透彻玲珑,如空中之音,虽有所闻,不可仿佛;象外之色,虽有所见,不可描摹;水中之味,虽有所知,不可求索。洞观天地,眇视万物,是为高古;剖出肺腑,不借语言,是为入神。[2]P433
他肯定了黄子肃关于“妙悟”的说法,并描述了所以“妙悟”的状态,这就是一种若有若无,若存若亡的状态,这种状态并不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触感而获得,而只能通过情志的共鸣、心灵的感悟。这个“感悟”就是“神”。
他又肯定了揭奚斯关于“味”的说法:
今人作诗,收拾好语,襞积故实,枰停对偶,迁就声韵,句缚于律而无奇,语周于意而无馀,语句之间救过不暇,均为无味耳。[2]P434
刘宾客谓诗者人之神明。谓当神而明之,大而化之,如林间月影,见影而不见月;水中盐味,知味不知盐。[2]P470
这是以“味”而说诗必须给人以无穷想像的空间,所以诗之优劣,不在于它写什么,而在于它在读者中所引起的感悟,所产生的效应。这就有如我们可以尽量享受林中宜人的景色,但不必追究月之圆缺;在品味水中的盐味时,不必问盐的由来。揭奚斯认为这种于无影无形中,给人以影响,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人们觉得诗“神而明之”的缘故。可见所谓“神”就是不露声色,而又使人产生感悟之处。
于是周珽概括了自己对“神韵”的理解。他首先比较盛唐与中唐诗的区别:
盛唐人寄趣在有无之间,可言处常留不尽;中唐用意好刻好详,色相不能俱空;是以有分耳。然和平婉厚,如钱、刘、皇甫、司空、郎、李、韩、卢辈,各出手眼,自成机局。虽觉正始神韵渐微,而盛时典型尚厉。[2]P470
他认为,盛唐诗与中唐诗最大的不同,在于盛唐诗能做到虚实相生,似有若无,留给读者足够的想像和发挥的余地。换言之,就是能达到蕴藉、含蓄的艺术境界。而中唐诗则着意刻画,务求逼真,读者难以在其中找到发挥的余地。因此,周珽明确地说:
是故知诗之妙处正不必说到尽,不必写到真,而欲写欲说者,自然可想。虽可想而不可道,斯得风人之义。[2]P439
这种“可想而不可道”的诗意,就正是诗的妙处。那么,这一“妙处”如何可以领悟呢?于是周珽说出了“悟”的意义。他说:
俾兴味情辞,一本于了悟焉耳。
又说:
论诗如论禅,禅道在妙悟,而诗非悟不灵。作律诗如行兵,兵法在变化。律固有定体,而图变透悟乃称善律。悟即变也,变即悟也。
总见诗要有天趣,不可凿空强作,当饱参然后臭味乃同。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法所宜先,而悟弗容已也。[6]P19
诗中的“天趣”,是通过“悟”而体会,而这个“悟”则是“禅悟”。显然,这是直承严羽的说法。郭绍虞先生指出:
沧浪以盛唐为第一义,而复以盛唐为透彻之悟,其说原不枘凿。就其有差别处言之,则此后格调派即宗沧浪第一义之说,而神韵派所取于沧浪者,又在透彻之悟。[3]
周珽诗主盛唐,以“悟”识诗、论诗,从而得诗中的“趣”,因此,他说:“夫禅之道,当下便扫;不立文字,便是文字,此禅诀也,亦诗诀也。”[7]这种无迹可求,惟有通过“悟”感受到的“趣”与“味”,就是诗人与读者,今人与古人“神会”之处,亦就是自古至今存在于诗中的“神理”,或“神韵”。所以郭绍虞先生又认为,古人往往通过言“味”,表达对“神韵”的理解[3]P435,这对我们理解周珽所说的“趣”与“味”是很有启发的。
周珽不但指出“若古诗以风调高古为主,其道在神情之妙。不可以力雄,不可以材骋,不可以思得,不可以意致”[3]P435,肯定古诗的优势乃在于“神情之妙”,这种“妙”就是因“悟”而得的“趣”。在《评林》所选的诗中,我们亦经常看到有带“○”,带“△”,带“、”的诗句。周珽告诉我们,带“○”的诗句,是“取其蕴藉冲和、微妙玄通,令人读之可思而不可言也。”带“△”的诗句,则是“取其简雅清深、优柔婉丽,无中生有,巧夺天工也。” 带“、”的诗句,则是“取其雄奇俊逸、雍容正大,平淡中有文采,诵之不觉舞蹈也。[3]P423”这些“可思不可言”、“巧夺天工”、“诵之不觉舞蹈”的诗句,妙趣横生,充满韵味,令人回味无穷,而又只可神会。这是周珽所着重肯定,着意引导读者欣赏的字句,从这些字句中,可以感悟诗中的“神理”,理解作为“诗脉”的“神韵”之妙。
周珽以“韵趣”、“妙悟”说诗中不可磨灭之“神理”,而最终则又落到了“情”上。他同意陆时雍以“离象得神,披情着性”[4]P33。去概括王维的诗,这是因为王维的诗景外有情,言外有意,所以其情其意,均非作者强加于读者,而是由读者体会,在体会中达到了与作者的感通,达到了“神会”,所以这是一种自然、真挚的情意,能够生出各种韵趣的情意。
如前所述,他强调:“诗先气格,气格既具,性情所到,一往遂成。”所谓“气格”,是指诗中的风格、品位,他认为“性情”与“气格”是同样重要的。不同的诗人,自有其不同的风格特点,这些风格特点是该诗人创作的基础,但这个基础不是空设的,必须有诗人的真实情感充实其中,运用一定的艺术风格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才能成为“诗”,才能成为“好诗”。所以周珽在选诗时特别看重诗中的“性情”。他说:“凡经在选,但取其有当于性情。”[4]P109他在对张籍的《野老歌》(“老翁家贫在山住”)作眉批时又说:“诗以清淡为佳,不以苦刻为贵,固矣。然情到真处,事到实处,音不得不哀,调不得不苦。诗以清淡为佳,不以苦刻为贵。”[6]P24这里所谓的“清淡”,是指朴素自然,不事雕琢的文字风格,这个风格的形成,靠的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靠的是对事物实事求是的反映。诗中的格调,韵律的哀、乐,都是因作者在诗中抒发的真实性情而形成的。
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6]P10又说:“诗道亦在妙悟。”[6]P30郭绍虞先生指出“沧浪之兴趣说和他谓的妙悟,是分不开的。”[6]P42而在周珽看来,“吟咏性情”是诗的根本,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通过诗的语言,诗的意境,而传达出了能让读者产生感悟的“趣味”,而产生出诗中不可磨灭的“神理”或“神韵”,于是周珽把“性情”、“趣味”、“神韵”构成了一个整体,以“神韵”的说法表达了对严羽“禅悟”的见解。后来清人张宗泰说:“(严氏)所谓别材别趣正谓真性情所寄也。”②我们虽然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张宗泰与周珽有什么关系,但不可否认,他们对“情”与“趣”的认识是接近的。
以“性情”为基础,以“兴趣”为审美追求,通过“妙悟”而领略诗意、沟通前人的“神韵”,就成为了周珽对诗的基本认识,支持着他的“诗脉”说。
周珽生活在明末之际,他对“神韵”的理解,自然离不开其前人,如胡应麟、陆时雍等的影响。但胡应麟主要是以“韵味”,“情趣”,补格调诗论的不足,其意义在于透露了“格调”向“性灵”的接近,或转化。至于陆时雍,虽然大体上摆脱了格调诗派的影响,“性情”在其对“神韵”的理解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但其所偏重的主要是诗中的“韵趣”,诗中的审美享受,目的则是把“韵趣”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34]周珽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但把“神韵”看作是诗歌的审美追求,同时把“神韵”看作是作者与读者沟通的桥梁,这是今人与古人得以在诗中实现“神会”的缘故。周珽认为,这就是贯串古今一切诗中的“脉”。周珽关于“神韵”的主张,成为了明代“神韵说”向清代“神韵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注 释]
①所谓“诗脉”,其根本的意义是在于确认诗中具有贯彻于一切时代、一切体裁、一切作品的最本质的属性。这则是理论家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例如刘勰就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文心雕龙·情采》);“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巻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文心雕龙?神思》)他看到了辞藻、声韵、性情、思理是一切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内容,是贯彻一切作品的最根本的属性。从这方面而言,则是与“诗脉”的说法颇为接近的。但刘勰却未能有意识地把把它提升到“脉络”的高度,去概括文学作品的本质特点。以后的理论家亦主要是沿袭或发挥刘勰之说。到明代周敬、周珽才从“脉”的属性去认识诗的本质。
②周维德《全明诗话·前言》:“《诗镜总论》的作者陆时雍提倡神韵,把神韵作为品评作品优劣的标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