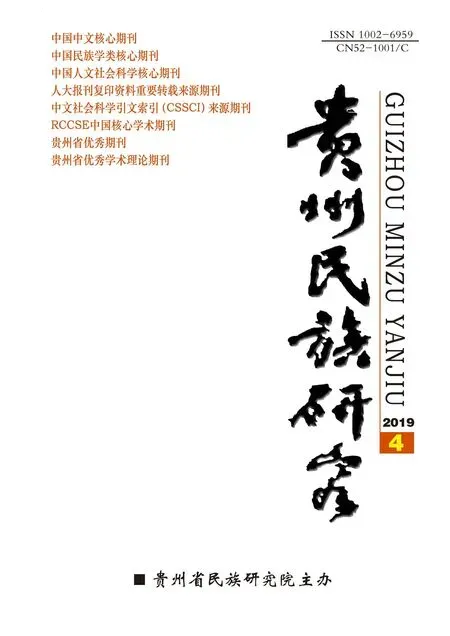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空间探究
刘尧峰
(湖北民族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恩施 445000)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变迁的不断加剧,我国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展现出的文化场域逐渐式微,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许多弥足珍贵的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正悄然淡出人们的视线。文化场所作为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得以存活的关键场域,一方面使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得以产生并世代沿袭,另一方面也给予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得以保存和再现的文化土壤,失去了文化场域也就失去了存活的依托。本文以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空间为对象,探究其文化空间的类型及其表现特征,对于守护民族文化基因,保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及其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武术文化空间的界定
“文化空间”亦称“文化场所”,是传统文化得以产生、存活与传承的时空场域,拥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属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空间是同一类文化所在的生存空间及场所[1]。武术文化空间作为武术文化的依托,是武术文化所赖以存在的时空场域,它是在“文化空间”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根据相关学者的描述,武术文化空间一般特指“某个集中展示武术文化活动或武术文化元素的地点,或确定在某一周期举办与武术文化有关的一段时间。”[2]包括时间性武术文化空间与空间性武术文化空间两种类型。
二、西南少数民族武术的文化空间
根据文化空间及其武术文化空间的界定,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空间主要包括西南地区的传统节日、宗教祭仪、传统赛事等时间性武术“文化空间”,以及庙会、村落及其学校等空间性武术文化空间,两者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寄寓的主要文化场域。
(一)西南少数民族时间性武术文化空间
1.西南少数民族武术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素有“节日之乡”的美誉,拥有众多传统节日,诸如彝族的火把节、虎节,傣族的泼水节、送龙节,傈僳族的盍什节、刀杆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苗族的花山节、赶秋节,土家族的舍巴节、龙袍节,白族的三月街、绕三灵等节日,不胜枚举。
传统节日是展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大观园”。“千百年来,各种民族民间艺术在这里展现、交融、竞争、锤炼,从而铸造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艺术珍品,流传后世。”[3]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各种民俗活动传承与发展的载体,而其中的某些节日更是为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提供了展演的舞台,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传统节日上,往往都会有精彩绝伦的武艺展示,抑或是富含武术技击动作的传统舞蹈表演。例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上就有精彩绝伦的景颇刀舞,其单刀舞和双刀舞均有成熟的套路,景颇刀舞威猛迅疾,刚劲有力,充分展现出景颇男子勇猛彪悍的英武形象。傈僳族于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的刀杆节上,亦有“挑花、点刀、抹刀、耍刀、上刀、折刀”等传统刀术绝技展演,刀风嗖嗖、刀光闪闪,刀花如万朵梨花一片;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每年农历六月的火把节上,一般都会举行赛马、摔跤、射箭、拳术表演及其上刀梯等绝活。苗族赶秋节上,苗族勇士光膀赤脚如履平地般攀爬上高耸入云霄的刀梯,并在刀梯上表演单飞燕、倒挂金钩、观音坐莲、大鹏展翅、古树盘根等惊险刺激的武术动作。土家族“龙袍节”上也会安排各种耍拳、打飞棒、使刀枪、舞流星锤等武术展演活动。由此可见,传统节日作为时间类武术文化空间,成为了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重要继承方式之一。
2.西南少数民族武术的宗教祭祀类文化空间
受历史发展及其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是一个巫风浓烈,原始宗教盛行的地方,素有“巫风野火出西南”之说。西南少数民族的宗教祭祀仪式繁多,而其中的巫傩祭仪和丧葬祭仪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武术文化元素。宗教祭仪不仅是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发性要素,同时也是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场域。
巫傩祭仪作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流传的一种原始宗教形态,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西南少数民族巫傩祭仪中除了常规的祈祷以及供斋蘸神等仪式外,还有较多的武术打斗场景,亦武亦巫,巫武结合是其特色。例如纳西族原始巫教东巴跳中就有各种单打、群打、刀对刀、剑对剑、三斗打、四破门、五佛跳,擒勾术等带有浓郁民俗色彩的武术表演,每当祭风、消灾、祭山神与龙王、除秽、开丧、走荐、求寿等七大道场时,一般都要进行东巴跳。尤其是在云南巨甸一带传统集会上,几十乃至上百个东巴手持刀、剑、斧、叉、盾牌、矛法杖和降魔杵等武器和法器,进行对打、掷刀、飞矛、投叉等各种练武动作,整个表演气势如虹,威武雄壮。土家族苗族还傩愿的祭仪中巫师往往都要进行各种上刀梯、踩地刀、趟铧犁、翻叉绝技以及套路武术的展演,在驱(杀)鬼仪式中,巫师“围绕某种假想敌——‘鬼魂’来表演各种攻防搏杀的技巧与场景”[4]。又如贵州安顺地戏(跳神)仪式中,场上演员手持刀、枪、剑、戟等兵器,进行各种惊险刺激的打、杀、劈、刺等武术动作。
西南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承载着丰富的武术文化内容。其祭仪往往以武事活动为媒介,例如彝族、哈尼族葬仪的送葬仪式中,为了祛邪驱鬼,让死者平安到达天国,就有武艺队挥舞双刀、大刀、小龙头等边走边演练。[5]云南罗平彝族的闹丧活动中,亦有各种大刀、大鞭、连枷、金钱棍、奇门棍等庄严激励的练武场面。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丧葬仪式中为悼念亡灵而进行的各种跳武丧、打廪、绕棺表演等,则是将歌舞与武技交汇在一起的一种古老葬俗,武丧表演中的“猛虎下山”“燕儿衔泥”“犀牛望月”“鹞子翻身”以及绕棺舞的典型动作“弯弓射月”“懒龙翻身”“换边拳”“倒立竖”等,动作粗狂豪迈,刚柔相济,不乏武术文化的踪影。而打廪过程中唱跳的动作和内容亦全是反映军旅征战、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等古老战舞,是其民族武术文化的另类表达。丧葬习俗作为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特殊留存方式,为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
3.西南少数民族武术的赛事文化空间
武技竞赛历史久远,相关典籍记载颇丰。从战国庄周《庄子·说剑》:“日夜相击于前……好之不厌”,到三国曹丕《典论·自序》:“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再到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两人出阵……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6]及至民国时期,在“强国强种”的时代语境下,各级各类国术竞赛接踵而至,使得流传了千年之久的中国武术真正登上了体育竞技的大雅之堂。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武术竞赛的开展如火如荼,武术比赛业已形成了一整套科学规范、系统完善的赛事体系。
当前,少数民族的武术赛事主要集中于全国及其各省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武术比赛中,而全国少数民族武术比赛作为单项赛事的发展步伐则较缓慢。作为时间性武术文化空间,各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少数民族武术提供了文化交流与技艺展演的平台。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更是借助于各级民运会的大舞台来展示自身独特的魅力,例如在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就有《布依族猫叉》《巴子刀》《孔雀棍》《仡佬族武术》《哈尼族武术》《龙渣瑶拳》等精彩绝伦的西南少数民族武艺展演。而在湖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土家族武术运动员所表演的《土家白虎拳》《土家扁担拳》《土家板凳拳》《土家降魔棍》《土家鸡公铲》《土家羊角叉》等珍贵稀有的原生态武术拳械,其原始古朴的技术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对传播与推广土家族武术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全国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各省市举办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固定时间类文化空间,成为了当今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交流、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文化空间场域。
(二)西南少数民族空间性武术文化空间
1.西南少数民族武术的传统庙会文化空间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古老的民俗活动,多在春节和元宵节等节日内举行。传统庙会活动期间往往都会举行各种祭神、娱乐及其商贸活动。建国后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庙会曾被视为是滋生封建迷信活动的温床而被禁止,失去了在公共场合存在的合法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以及文化需求的不断升温,各地庙会再度兴盛起来,“现今的地方庙会大多已经发展成为集民间文艺表演、民间武术、民间手工技艺、商贸旅游为一体的民间传统盛会。”[7]庙会已经成为传统民俗中的一种地方性文化标志。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宗教信仰最为普遍,宗教品系最为齐全的地区,不仅保存有各少数民族的特色宗教,诸如东巴教以及各种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等宗教信仰,同时还有汉族流传而来的宗教,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宗教文化特征。由于宗教品系的繁盛,伴随而来的便是庙宇林立,各种庙会活动兴盛的独特景象。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庙会活动不仅在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增强乡土意识、推动地区贸易、繁荣市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形形色色的乡村庙会也为各种民俗活动提供了展演的舞台,各种杂耍绝活、舞龙舞狮、武术展演等大都借助传统庙会这一平台得以亮相,并成为庙会活动中最能吸引眼球的活动。例如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庙会上舞狮掷绣球者,开场前往往都要表演“四门架子”“苏公背箭”“猛虎跳涧”“五虎群羊”“八虎拳”“白虎拳”等土家族拳术。而云南民族村滇池庙会上,一般都有水族套吞口、苗族吹枪、傈僳族射弩等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武艺展示。又如拥有千百年历史的云南大理白族“三月街”庙会集市,期间除了常规的物资交流以外,还有赛马、摔跤、射箭、打拳等精湛绝伦的传统武艺展演,使得整场演出高潮迭起。在过去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某些江湖艺人会将传统庙会视为自己的“金饭碗”,庙会表演成为他们赚钱养家糊口的良机。为了寻觅演出机会,他们对地区传统庙会的时间与地点了如指掌,逢会必演,正是在这样的天地里,少数民族武术得以留存与承传。传统庙会作为地区民俗文化交流的载体,为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空间场域。
2.西南少数民族武术的村落文化空间
村落作为传统农村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与社会结构单位,是广大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活空间,同时也是滋生各种村落文化的根本领域。村落武术作为村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村落组织的文化代言,而村落则为村落武术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是村落武术的文化空间所在。
长期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延存,同样离不开传统村落这一特定的文化空间,乡村拳场是人们练拳习武的重要场域,在村落这一特定的时空场域中,村落武术作为慰藉情感精神与维护乡村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西南少数民族村落中不断地传承和绵延。例如梅山武术作为在梅山当地农村广为流传的乡土武术,就属于典型的村落武术,拥有浓厚的群众基础。当地民间很早就有“设厂习武”的传统,村落拳师一般会在农闲之际开厂授徒,“忙时耕田、闲时练拳”已成为地区村落的一种文化生活模式。与此同时,村落在一些重大喜庆节日中往往都会组织一班拳套人马进行武术表演,各村落拳师还常常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梅山武术成为了地区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村民个人身份的象征。又如湘西花垣县麻栗场镇金牛村,作为西南地区一个偏远的苗民聚居村落,其村民尚武之气蔚然成风,无论男女老幼都会耍上几套拳脚。该村世代流传着一种苗族上古拳术蚩尤拳,自清代乾嘉苗民起义以来,金牛蚩尤拳即声名大震。上百年来,蚩尤拳在金牛村村民中世代承袭,成为村落文化的一大特色。平日里,无论田地村头还是屋角院落,往往都有练习蚩尤拳的村民身影,而到了农闲时期,武术爱好者更是立堂开练,切磋技艺,练拳习武成为了金牛村村民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村落作为空间性的武术文化空间,使得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得以世代存续和绵延。
三、结语
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空间为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提供了生存与展演的平台,正是具备了各种文化空间的载体,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才得以拥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世代承袭。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商业经济的发展,在多元型现代文化的冲击下,西南少数民族武术赖以生存的原始文化土壤不断消失,文化活动场域逐渐呈现出衰微的景象。因此,在社会变迁日益加剧的当下,加强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空间的保护与传承已成刻不容缓之事,这就需要发动地方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双驱动联合力量,在保护现有文化空间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间。唯有这样,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路才能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