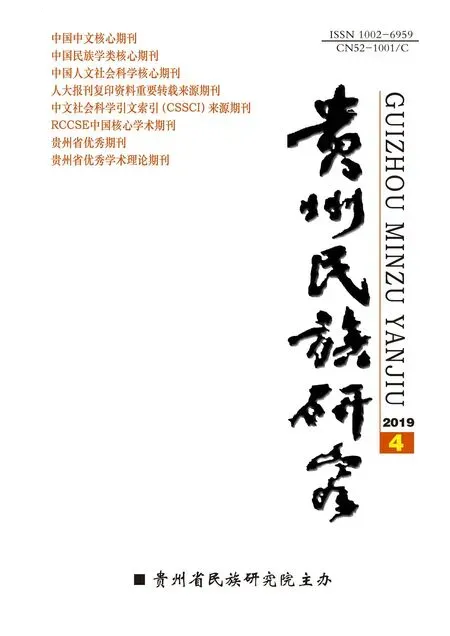多民族村落视野中家族成员的行为逻辑考察
——基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水村的田野调研
张露露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村落是由一个个家族共同凑聚而成的微型邦国。家族成员以村落为生活基地,在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中集聚而成为一个个命运共同体,他们的公共活动既使村落呈现出稳定、共识与和谐的一面,也使之表现出变动、强制与冲突的一面,由此深刻地影响着村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变迁。作为现实生活中宗族现象的抽象化表达,已有的宗族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存在着家族系统、鬼神系统和国家系统三种权力支配系统[1],而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2]。马克思·韦伯又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家族结构式的社会”[3]。这些经典观点是对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特征做出的基本判断和精准概括。总起来看,有关宗族的学术成果汗牛充栋,但从政治学学科视角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宗族治理的相关研究还较为稀少。笔者在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在多民族聚居的水村,各种社会关系共存并且错综复杂,宗族势力是维系村庄稳定与发展的主导力量。尤其是当遭遇冲突时,不同家族的竞争态势和势力对比会愈发凸显,家族成员也会做出不尽相同的行为选择。本文在分析水村村治模式的基础上,采用关键事件法,着重通过“牦牛圈”和“牛角羚”两个冲突事件的深描和分析,来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一、宗族治村:水村村庄治理模式考察
水村位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A州,海拔2400多米,全村实际居住人口有1000余人,其中农业人口756人。笔者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先后进行三次入村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据悉,水村有1000多年的历史,逐渐形成了以羌族为主的“羌、藏、回、汉”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格局。全村姓氏繁杂,居前四位的是李、孙、王、许,分别占17.2%、8.9%、7.6%和5.0%。按照村落与家族结合类型的划分,水村属于复主姓村,即50%的村庄人口由两个以上的大家族共同构成。这种姓氏分布状态使水村呈现“四大家族”并存的特征,也对村庄的治理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村庄的政治舞台上,村支书和村主任是村落公共权力的主要掌控者,因此他们是观察水村村治模式的一个良好透视角。在此,我们结合最近五任村干部的家族背景(如表1)来进行具体分析。

表1 水村最近五任村干部的宗族背景
由表1可以看出,在最近五次的村换届选举中,共有8位候选人成功当选。除了外派的X和Y两位之外,其余6位均源自本村。在村支书的任职中,李一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担任了22年的村支书。在村主任的任职情况中,李二担任了30多年的村主任,最近三任分别为王一和王二,其中王二连任两届。特殊的是,李一和李二是堂兄弟关系,王大与王一、王二为父子关系,其中王一是王二的兄长。村民中也广泛流传着“王李有权,许有钱,给孙家气得没办法”的说法,这是对长久以来大姓家族尤其是李、王两大家族共同执掌村落政治局面的一种真实写照。可见,水村复杂的家族关系缠绕交织在村落的公共权力之中,村干部换届选举已经成为大姓家族获取村落公共权力的重要渠道。这使水村的村落政治表现出明显的“宗族治理”特征。

表2 水村村治模式与其它类型的差异
水村的村治模式与当前我国农村地域存在的一些其他村治模式存在明显区别(如表2)。这些村治模式在主导因素、实质和基层民主实现程度上存在诸多差异。其中,恶人治村是一种极端形式,意味着基层民主的失序。宗族治村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双面性,关键在于村治主体的治理行为是否良善。宗族治理其实是家治的延伸与拓展[4],是家治突破家族的私人场域,延伸到村落公共空间的一种活动表现。这种村治模式为我们深入分析村庄冲突事件中家族成员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基本前提。
二、强与弱:“牦牛圈”事件中家族成员的行为表现
水村三面环山,高原牧场水草肥美,共有20多户牧民放养牦牛。A州为改善牧户设施条件,减轻牧民的劳动强度并提高防疫工作的精确性,计划投资488万元建设61个牦牛多功能巷道圈,每个牦牛圈示范建设项目可获财政补贴资金8万元。水村获得了一个指标,但围绕着牦牛圈的资源配置问题产生了分歧,进而引发了冲突。
“上边这个指标是给我们这些有牦牛的,王某没牦牛却把这个(钱)给占了,那就得给我们修。本来应该是修在后边沟里头,结果他们就要修到他们地里去,我们就不同意,因为我们的车子开不上去,装不了牦牛。然后就找王主任,找他差点打起来。因为争吵起来了嘛,结果他就把他的弟兄们全部叫出来,他兄弟们就出面了。我们惹不起,唉,为村里的事情他们就是这样。”(牧民马某,小姓家族)
马某的说法在其他牧民那里得到了印证:“都知道是他们不对,不应该拿了这笔钱。唉,你意见很大你也没办法,你没文化,你要把他得罪了他就收拾你,因为他弟兄多嘛。”
在“牦牛圈”事件中,冲突的双方是以马某为代表的牧民和以王某为代表的王家人。事情的起因是牧民的牦牛圈修建资金被侵占,牧民在与村主任商讨的过程中发生言语争吵,进而导致冲突局面的形成,并以牧民的维权失败而告终。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同家族成员的行为逻辑。
一方面,以马某为代表的牧民在维权过程中变成了弱势群体。首先,马某等牧民养殖并售卖牦牛的年均收入约为4万元,是他们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牦牛圈的选址和修建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具有强烈的维权动机。其次,当牧民得知王某侵占了他们的合法利益时,他们最初并未过多顾虑王某的大姓家族身份,而是采用协商方式,但对方的方案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进而找到村主任以期解决。最后,在王主任和王家人的共同压制下,马某等牧民最终选择了忍让和放弃。可见,无权并且来自小姓家族,是牧民维权失败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王某是事情的引发者和获利人。王某没有饲养牦牛却获得了补贴资金,是对牧民合法利益的侵占。在第一次协商中,王某提出的方案实际上是一种托辞。在第二次协商中,王某与王家人合力迫使牧民最终放弃了应得的利益。利益的驱使、来自大姓家族以及家人是村干部,是王某做出这种不法行为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王主任在整个事件中是化解冲突的关键,但他却从仲裁者变成了家族成员利益的袒护人,最终侵害了牧民们的切身利益。
由此可见,在“牦牛圈”事件中,马某等牧民既缺乏公共权力和权威资源,又来自小姓家族,使他们在村落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是他们产生默认行为并无奈放弃合法利益的主要原因。相反,王某和王主任等大姓家族成员,一旦获取了公共权力就成了村落里的强势家族。这种强势地位助长了一些家族成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也使个别村干部在处理村庄事务中遭到了掣肘,从而造成了村落公共权力的家族化,侵害了其他村民的合法利益。
三、良与痞:“牛角羚”事件中家族成员的行为表现
“牛角羚”事件是我们探究家族成员不同行为逻辑的另一扇窗口。据村民讲述,自2010年以来,随着国家惠民政策对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倾斜,水村的村级资金也日益充裕起来。这不仅提高了村庄公共设施的供给能力,也诱发了一些村干部的贪腐之心。已经退休的老书记李一,军人出身,性情刚直,当他感知村级财务资金将有遭受侵占的风险时,就要求不定期进行财务公开,因此得罪了某些村干部。机缘巧合的是,有一天,李一和几个村民在后山偶遇一只牛角羚(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把它猎杀并抬回村里食用了。后被人举报,他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法律惩处,李一也因此被判刑五年。当刑满返村后,李一从家人和村民们那里得知村级资金被严重侵吞的事情,要求查账并发现了问题,之后上访反映此事。最终,涉案人员被处罚,退回赃款21万多元,其中X书记和村主任王一被撤职,开除党籍。
我们这里来着重分析一下涉事人员的行为逻辑。事情的起因是一些村干部有了贪腐的动机,但碍于李一的监督无从下手。整个事情的转折点是“牛角羚”事件,李一因此而入狱五年,实际上为这些村干部侵吞村级资金提供了可趁之机,涉事村干部也最终受到了处罚。问题在于,为什么李一敢于查账、检举并揭发违法乱纪行为呢?而涉案村干部为什么会在李一入狱后采取行动,又在他出狱后才遭到惩罚?
一方面,李一在整个案件中,他的心理动机和行为表现很明显是为了维护村庄的公共利益,因而他的行为是良善的。这种良善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有三个:一是李一性格使然。他为人正直,面对村庄的不公正行为敢于申诉。二是李一是退休的老支书,口碑良好,20多年的村干部生涯使他难以容忍村庄的不法行为。三是李一的文化水平高、法律意识强,他懂得依照村庄规则来查账、要求信息公开,并采用检举、揭发等方式而不是违法手段来促成事情的解决。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李一来自村庄大姓家族,并拥有良好的村落威望。
“老书记回来后,我们就赶紧给他说这个事。他也看不惯,他家族大,人又多,他就敢去村里说,去村里查,一查不就查出来了?”
——村民A
“他们都气我气得很,好几次在村上见了面,都想动手。我是大姓人,他们不敢惹我。不过要是我在村上势力弱一些,他们早就下手了。”
——李一
可见,李一基于家族势力和良好的声望而采取的良善行动,既使他成为弱小家族成员的利益表达渠道和代言人,也进一步为他赢得了村落威望。李一这类家族成员以“在野”的身份,对任职村干部的行为起到了监督和制约的作用,有助于村落公共权力的有序运行。
另一方面,涉案村干部选取“牛角羚”事件后采取行动,是因为李一在村落里的“不在场”,为他们解除了最大的外部监督力量,力量微弱的小姓家族也难以对他们形成有效的制约。权力一旦脱离制约,就极易诱发违法乱纪行为。李老书记的归来使外部制约和监督力量得以重塑,最终促成了事情的解决。王主任等村干部的“痞化”行为,直接损害了水村村民的切身利益,也遭到了应有的惩罚。可见,家族势力与村落公权力的叠加,既能增强村干部为民谋利的力量,也可以成为一些村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的助推器。
综上可知,大姓家族成员利用自身的威望而做出的良善行为,不仅能增加个人名望和家族威望,也发挥了监督制约和利益代言功能,从而使村落公共权力朝着为民谋利的方向运行。但大姓家族成员利用村落权力做出的“痞化”行为,不仅会弱化自身的家族权威,也常常会使村落公权异化为私权,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四、结论与讨论
在水村这一多民族聚居的村落中,通过“牦牛圈”事件和“牛角羚”事件的深描,对家族成员的行为逻辑进行解析,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水村是一种“宗族治村”的村庄治理模式。家族力量、权力、权威是三种重要的村落政治资源,家族成员对这三种资源占有量的不同,是他们产生不同行为表现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小姓家族在缺乏村落权力和权威的条件下会更加凸显自身弱势地位,当遇上冲突时倾向于采用默认、妥协或放弃等行为“消灾”。大姓家族与权力或权威的结合会使其成为强势家族。家族成员尤其是强势家族成员的良善行为,能够赢得村落道德权威,并发挥监督制约和利益表达功能,使村落公共权力沿着有序的轨道运行。相反,他们的“痞化”行为也会弱化自身村落权威,进而导致村落公共权力的私化或家族化。水村给我们的基本启示是:在多民族村落视野中,家族成员在不同道德观的引导下展开的公共活动,既可以制造矛盾,引发冲突,也可以化解分歧,整合利益,从而使村落呈现出两张截然不同的社会面孔。诚然,强势家族成员之间的角逐甚至冲突,有消极的一面,但也可以激发村落活力,成为村落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在水村,宗族治村遵循的是自治逻辑,权威实质上是一种德治资源,而村落里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显露出了法治力量的疲软。因此,在健全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进程中,如何在多民族聚居的村落里强化法治的力量,发挥法律对违法乱纪行为的约束功能,并促进法治认同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深度耦合,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