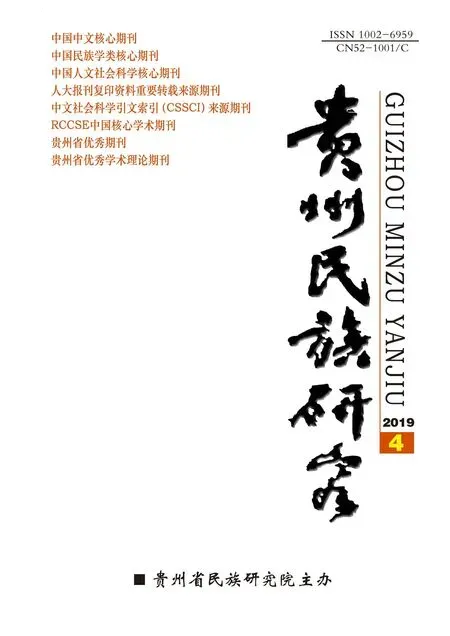相生相合:传统侗族社会的两性制度安排及现代启示
粟 丹
(浙江工业大学 法学院,浙江·杭州 310014)
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传统侗族女性在这一关系中的地位如何?笔者以为,传统侗族妇女地位具有流变性,在她们一生当中,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会随着女儿、妻子及母亲等社会角色的变换而变化。同时家庭具有整体性,妇女地位问题其实是社会、家庭及个体需求的混合表现。
传统侗族社会的两性制度围绕“天地人和”这一理念来建构,和谐作为古已有之、东西横贯的发展理念,直接塑造了侗族社会两性制度,社会两性制度又进一步激励和约束了女性的行为。基于“观念—制度—行为”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对传统侗族社会女性观念进行介绍,其次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对传统侗族社会两性制度安排进行梳理,进而对侗族妇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制度实践进行描述和分析,最后从立法角度反思我国当下婚姻家庭立法,并对新型两性和谐关系及和谐家文化制度建设进行思考。
一、和谐是传统侗族社会两性制度的观念基础
(一)传统侗族社会的和谐观念
侗族长期居住于湘黔桂三省区毗连的大山之中,是典型的山地民族。侗族多聚居在依山傍水的地方,他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注重保护的山水和树木。侗族的鼓楼、风雨桥、侗族大歌便是绿色文化的代表。同时,侗族是一个喜欢月亮的民族,侗族地区的许多文化事象都与月亮有关。青年人集体谈情说爱叫“行歌坐月”,晚上男女单独约会叫“凉月”,全村集体游乡做客叫“月也”,月亮负载了侗族人民丰富的文化内涵。基于绿色文化和月亮文化的审美情趣及自然观念,尊重自然、维护自然成为了传统侗族的最高精神价值。和谐观念也直接影响了侗族人民的性别意识,既然和谐是世间万物生存的根本法则,男女关系也应该如同自然界一样符合阴阳之道,应该是一种合和关系。阴阳思维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之一,《易经》的“阴阳两仪”思维模式是其典型代表。它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方面,世界上万物无不由两两相对的“阴”“阳”这对矛盾构成;另一方面,这对矛盾不是对立排斥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互动过程中守中致和[1]。阴阳两仪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模式和生命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阴阳和合则“生”,阴阳隔离则“息”[1],即天地合而万物生,男女合而后有子孙繁衍。
(二)和谐型构了传统侗族社会的共享观念
“和”在传统侗族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和现实意义,其直接型构了传统侗族社会的共享观念。共享观念是指被人们神圣化、自然化了的基本理念,是人们毋庸置疑就加以接受的天经地义的道理[2],有如西方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法则、自然理性的含义。共享观念对于一定社会制度的建构和运作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其构成了制度的公义基础,是制度得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稳定性保障。共享观念对于侗族社会的制度运行和秩序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虽然侗族女性在宗教信仰、生计劳作、文化娱乐等方面与男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这并不代表女性与男性完完全全平等,在她们生活中仍然存在众多性别隔离和禁忌。如补拉制度中对妇女财产权的否定,“萨岁”和“月也”活动对孕妇的禁止,生活中女性不能从男性前面走过,忌夫妻在娘家同房,禁媳妇到娘家生育等等,这些“人为”的规范被套上“自然”的外衣之后,变成了天经地义又合乎情理的自然法则。于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在这些自然法则中得到淡化甚至消解,使他们为和谐这一共同价值而变得克制和包容,并通过具体的家庭制度、契约制度及社交礼仪等制度来维系家庭和谐。
二、传统侗族社会的两性制度安排
(一)正式制度中的两性规范
正式制度是指由某个权威机构自上而下设计的,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规则[3],具有明确性和强制性。诺斯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主要指法律制度,而后者则是指合约方式[4]。传统侗族社会便是依靠款约制度与契约制度这两种正式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并促进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
1.款约制度对家庭和谐的维护
款约制度是维护传统侗族社会基本秩序的制度保障,主要表现为“款组织”和“款约”两个方面。款组织是侗族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是侗族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款约是侗族社会基本的行为规范,也是最重要的规章约法。传统侗族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款约是“阴阳款”,共有18条,分为《六面阴规》《六面阳规》和《六面威规》。其中《六面阳规》的二层二部中对男女双方从恋爱到结婚到家庭生活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旨在维护良好的社会风俗和婚姻道德秩序。如“男要换妻,女要换房。事发同处理,事起同商量。拉起队伍通路,摆起队伍同甲。枪靠禾廊,箭靠房屋。要他苦酒给喝,要他甜酒给尝”。除了阴阳款,在侗族村寨的一些碑刻文本中也有关于男女关系的规定,如清道光年间立于从江县公纳村的《公纳禁条碑记》有如下记载。
二、上等亲男女嫁娶,男自愿娶,女自愿嫁,两造父母不依,男女私约拐带,上等娘家,准吃财礼银十一两;中等娘家,吃财礼银七两。三、男女已成婚配,初则两愿,即成亲后,或三五日,男若悔亲,括女银一两六钱,饭一笠,鱼一个;女若悔亲,括男银二两四钱,男之聘金多寡,加倍退还。至三五载之后,璋琅两耳,女若悔亲,括男财礼银七两,男若悔亲,括退女银七两,土禾十二把,聘金概不准退。四、拐闺女,其女家父母不愿,退回娘家,作洗裙脚银一两,饭一笠,鱼一个,男妇私通,犯奸捉双,罚银一两二钱。[5]
公纳禁条碑是公纳村全体村民集体制定,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规范。虽不如款约效力辐射到整个侗族地区,但是对公纳村村民具有规范作用。这个碑文中对男女成婚方式及婚后破坏夫妻关系的行为做了规定,对于既违反社会公德又影响家庭和谐的行为,如悔婚、拐带、私通等,要实施一定的经济处罚。在具体处罚数额方面虽然夫妻双方不尽相同,但还是反映了侗族人民原始的平等观念,因为其规定是针对男女双方,而非女性一方。平等赋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家庭和谐。
2.契约制度对男女有别的弱化
清雍正年间,清水江流域的广袤腹地被纳入到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大规模的木材采运活动随之兴起,整个清水江流域内的人群及村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以木材种植采运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开发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当中[6]。经济的发展促使了文字契约的产生,也使妇女享有广泛的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从明清至今的500多年当中,在以锦屏为核心,包括黎平、剑河、三穗、天柱、岑巩等县,出现了数十万份纸质契约文书。在这些契约文书中,不乏有妇女参与契约活动的记载。如贵州省天柱县竹林乡梅花村吴家塖吴恒荣共同持有的祖上契约显示:
立卖竹山栢木地契人吴潘氏爱花。今因家中要钱用度无从得出,是以夫妇商议,情愿将到自己分上之业土名身小牛堂荒竹山一副,内开四抵:上抵买主油树,下抵买主竹山,左抵恒德油树山,右抵卖主油树,四抵分明,欲行出卖,无人承受,自己上门问到房叔吴会义名下承买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言定卖价,光洋二元二角八仙,其钱亲领入手,其业任从买主耕管,日后不得异言反悔。今幸有凭,立此卖契为据。[7]
这份土地买卖契约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妻子可以作为独立的立契人参与契约活动。这份契约的卖方是吴潘氏爱花,表现妇女可以作为契约当事人独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虽然这种情况在侗族社会不多见,但也从反面证明了中国传统家庭的妻并非只是在夫背后的隐形存在,即使丈夫在世,也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利[8]。第二,妻子与丈夫享有同等的经济地位。该契约中的“是以夫妇商议”表明,吴潘氏爱花在家庭的经济活动中与丈夫具有同等地位。侗族妇女在契约活动中的广泛参与及享有的契约权利,进一步强化了传统侗族社会的男女平等,弱化了男女有别。
(二)非正式制度中的两性规范
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制度,还需要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制度。[9]非正式制度是非强制性的,属于软约束,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软法”概念,软法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规范,核心是社会成员对软法的共识,其最大特点是人们对软法的接受和遵守是发自内心的[10]。
1.劳动规范中的夫妇并作
侗族作为远离中原文化的南方山地民族,在长期的水稻和林业种植过程中,劳动并无严格意义的内外之分和男女之分。侗族地区一直流传一首《十二月歌》(亦称《四季歌》),形象地描述了夫妻双方一年中的农事活动。歌词大意为:
年初正月,却看到情妹和夫耕旱地。/待到一月,却看到情妹和夫备耙绳。/待到三月耕田,他人命好,得到情妹送早饭。剩下我郎一边找柴一遍寻菜,一边摘菜一边引火草。手忙脚乱,直到日落便西都还没有早饭吃。/待到四月采秧青,他人命好,有你情妹伴山头,剩下我郎孤单一人,如同秤不平……[11]
这首歌词一方面表达了单身男性在田间劳作时的孤单与艰辛,另一方面反映了男女双方齐心协力完成田间劳作的幸福场景。传统侗族社会的生计方式被描述为“夫妇耦耕并作”[12],即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并不十分明显,也不严格区分两性的活动空间。每一个农事阶段,都是由夫妻双方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原则上是男性从事比较繁重辛苦的田间工作,女性则承担劳动强度不是很大的家务工作。如果一个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不够,女性一样要承担繁重的田间劳动。夫妻共同劳动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有助于亲密关系的培养,并进一步促进家庭和谐。
2.礼俗规范中的媳妇礼仪
侗族历史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侗族社会的历史和文化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唱歌形式来记录和传承。侗族社会有句俗语叫“饭养命、歌养心”,唱歌作为侗族先民的习惯,使每一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中,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礼俗和礼俗歌。侗族地区针对妇女婚俗和礼俗的民歌非常之多,如夸赞歌《吉日迎来金孔雀》:
新来的媳妇懂礼仪,/尊重邻里和公婆,/对老对少都和气,/满面笑容把话说/老人走路多辛苦,/先请洗脸再洗脚/老人刚把脚洗过,/她就端盆把水倒,/客人抽完一袋烟,/酒肉饭菜她已摆上来/……饭完了/她双手就把碗夺,/脸色象那十二的月亮发光,/说话象二月的太阳暖和。[13]
这首夸奖新媳妇的侗歌,既是对妻子美德的激励,也是对其失礼行为的约束。这些礼俗规范来源于传统,并代代相传。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14]
三、传统侗族女性的公共活动与个人活动
(一)款约制度对女性参与公共活动的规范和引导
款组织活动是传统侗族社会最为正式也最为重要的公共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关系到侗族社会的存续发展,具有公共性、集体性等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较之于传统儒家文化的男女内外有别,如《易经》中的“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传统侗族社会不仅不排斥女性参加款组织活动,而且还在款约中赋予她们作为正式成员的参与资格。因为传统侗族社会是一个以集体利益为中心,崇尚人人平等的社会,为保障男女老幼有序参与款组织活动,款约中对起款、立款及聚款三项活动进行了程序性制度设计,以为其提供行为指引。“起款”的意思是赶快到集中的坪子去。“立款”是订立、修改和宣讲款约,是侗族社会最为重要的法律活动。“聚款”是关于款约的执行活动,指按款约规定来审判罪犯,一般由款首聚集全村村民在鼓楼或款坪举行。在这几项活动中,虽然很少有女性作为款首来直接领导整个款组织活动,但女性可以作为款众全程参与款组织的活动,证明了女性在公共事务中的平等参与。
(二)契约制度对女性参与契约活动的激励和约束
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给人提供激励和约束。就制度激励而言,主要通过传递信息、激发热情及调动积极性,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合作;就制度约束而言,主要通过告知、纠正、惩罚等方式来限制人的行为,以保障人与人之间的良性合作。明清时期,随着清水江地区木材交易的兴起,日益成熟的市场制度和契约制度激励了女性广泛参与到契约活动当中,她们可以自由参与山林土地买卖、租佃、抵押、分家等各种形式契约的制定。在这些契约活动中,妇女不仅享有广泛的财产继承、财产支配和财产流动等权利,还可以作为凭中成为契约签订的见证人。如贵州省天柱县地湖乡岩古村宋显和持有的《山地买卖契约》中记载:
立卖房屋基地砖磉及下墱屋场基地字人杨森喜(押)、子杨发龙。今因家下要洋使用,无从得处,父子公孙商议,情愿将到土名中塖坡自己面分之业,房屋基地半座及下墱基地壹幅,其瓦片、盖果、梁柱、板壁、炉灶及岩磉以〔一〕并在内,上抵杨清松基地断,下抵卖主田断,左抵连忠,右抵陈氏碧兰墦及田断,四抵分明。在此地段内所有之天然物及人造物,以〔一〕 并要行出卖,无人承就,请中上门问到弟婿杨梁氏丹桂名下承买。当日凭中言定卖价洋柒万零玖佰捌拾捌元正,其洋亲领入手用度,领不另书。房屋基地及墦地等,任于买主子孙永远耕管为业。其花字酒席一并在内,不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此卖契字为据。
凭房族:杨书香(押)
凭中:杨眉进(押)
杨氏新姣(押)
杨金毫(押)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请代笔 杨清星(押)立[15]
明清时期的大部分契约,一般是由契约双方当事人签订契约,而由第三方来监督执行契约,即由中人作为立契的见证人以及纠纷的调解人。而这份买卖契约的中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恰好反映了侗族妇女可以作为中人对契约进行担保的事实。女性作为契约见证人和纠纷调解人,既是男女平等的反映,也是对违约行为的有效约束。
四、对当代婚姻家庭立法的启示
(一)婚姻家庭立法应追求男女和谐而不仅仅是男女平等
中国现代婚姻制度是建立在道德与法律分离基础之上的理性建构,两性关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与“平等”。婚姻自由和财产自由赋予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更多的自主权,尤其是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公布后,更是被学者们称为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式的个人财产制[16]。这种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制度安排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婚姻关系,也改变了长期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生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17]。遗憾的是,这种改变并没有促进男女平等,反而出现更多的性别歧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解释说,“男女平等”是普及了一种观念,即女性拥有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从而为女子发展潜能提供机会,但它迅速走向极端,变追求机会平等为完全平等,以致造成一种新型的、更为荒诞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家庭生活的无序、混乱与低效[18]。从立法角度而言,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我国当代的婚姻法没有真正理解并吸纳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价值,却在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父权制理论和男女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越走越远。较之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家庭关系是一种充满了个人情感、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复合关系,家庭成员的行为既有理性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婚姻家庭立法的最大公约数应该是两性和谐,而不仅是男女平等。我国的立法机关不能只是从男女平权角度赋予男女双方平等的权利,也应该强化性别角色的义务。同时司法机关不能只过分关注夫妻财产的精确分配,也应该多以调解方式来唤醒夫妻双方的责任意识和家庭意识。
(二)家庭政策应重新认识和激活传统家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家的地位和意义超越着个体,在人生中具有根的意义。传统侗族社会除了款组织之外,还有凝聚村寨和家庭的补拉组织,补拉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以父系家庭为基础,结合而成的宗法性组织[19],补拉是侗族村寨存续的基础,也是侗族团结和稳定的保障。侗族女性作为补拉组织和家庭中的一员,在生养子代的过程中发挥了生育功能、情感交流功能、教育功能;在孝养亲代活动中,发挥了赡养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在家庭生计和社会交往中,发挥了生产功能、信仰功能、娱乐功能等众多功能,她们不仅是民族的生物性再生产者,还是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者。她们常被赋予文化监护人的任务,负有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的责任,并以特有的文化方式营造一个“家”[20],这个家的核心和基础是家人之间的爱与关怀、沟通与承诺[21]。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先后经历了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及指向家庭责任的经济侵蚀三次冲击[22]。在此背景下,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解构“家”的意义上进行的,主要表现为立法者不再以亲属关系为中心来构建家庭制度,亲属伦理被国家伦理所代替[23]。国家伦理反映在家庭关系中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是夫妻关系平等,同时还指向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平等,代际平等意味着父母子女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遗憾的是,如此平等的立法并没有促进家庭和谐。为什么立法与社会实践的差距如此之大?为什么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破除了家长制却没有孕育出更多的和谐家庭?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我们立法没有认真对待中国传统家文化所致。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文化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亲情伦理与道德精神的意义系统,不仅是传统中国人生存哲学的基础,也是当下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基石[24],它们应当成为支撑当代中国法治主体性的重要资源[25]。家是培养亲情与爱的地方,我国立法应保护这种人类情感,而不是漠视甚至背离。反映在具体的家庭政策上,首先在家庭成员关系之间,应该消除平等至上论,承认保护关系的价值,以不对称保护原则来调整家庭关系,实现对家庭中的老人和儿童的特殊保护[26]。其次,应出台切实可行的家庭支持政策来激励夫妻双方的家庭照顾行为。
五、结语
传统侗族社会的女性制度存在于两性制度安排当中,其制度内容贯穿了自然和谐。因为敬畏自然,侗族先民将男女之间的“相合相生”比附于自然界的“天地配合”,将建立在血缘和婚姻基础上的家庭视为社会的自然基础,追求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基于这样的价值理念,“和谐”成为传统侗族社会的共享观念,这一观念为传统侗族社会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制度环境。侗族先民将两性制度深深镶嵌于由生育形成的血亲关系,两性结合形成的婚姻关系及孝道形成的供养关系三者共同构成的家庭结构当中[27],把家庭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在亲情仁爱的基础上,由此形成了特殊的家庭文化传统,这种家文化与传统中国孝道文化不谋而合。当下中国,在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的超载重压下,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重现眺望和复苏一种新的家庭主义,并进行孝道文化的顶层设计,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是中国人的生命真谛和生活意义之所在[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