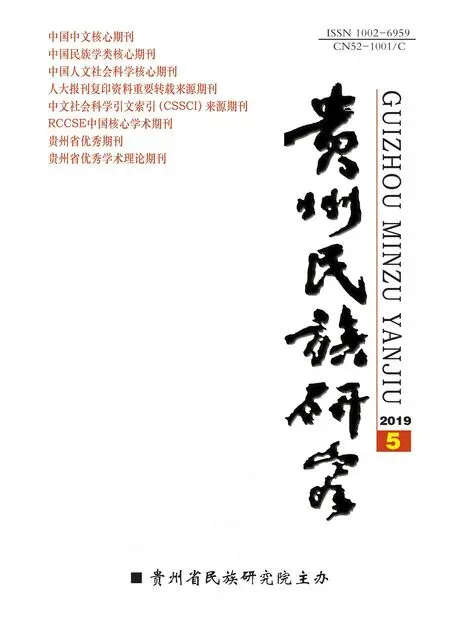论西南苗疆历史地理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王肇磊
(江汉大学 城市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56)
西南苗疆概念的形成源于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所持有的民族观。在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缺少现代人类学和民族学定义的情况下,结合西南民族历史的演变,中央王朝对西南苗疆民族聚居地区的称呼大致经历了“三苗”“西南夷(蛮)”和“苗疆”三个阶段。
一、从“三苗”“西南夷(蛮)”到“诸苗”:苗疆称谓的历史演变
西南苗疆概念的历史溯源最早可能要追溯至先秦两汉时期的“三苗”“西南夷”。苗“在湘、蜀、黔、滇、两粤之间,曰蛮人,曰夷人,曰瑶人,曰僰人,曰仡佬,曰倮倮,曰倮罗,曰倮罗夷,曰俅夷,曰仡僮,曰佯僮,曰佯僙,曰僚、曰峒人,曰革姥,名称不一,皆古三苗,九黎之遗裔也”[1]。《史记·五帝本纪》说:“三苗在江淮荆州”。为防止南方少数民族对周王朝腹地的侵袭和骚扰,周天子授权于楚以“镇尓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2](P187)可见,先秦时期“三苗”“夷越”等概念泛指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
汉代南方少数民族区域已分化出“西南夷”“百越”等具有地域性指向的民族区域称谓。《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又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2](P481~482)这样“西南夷”便成为了当时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仍以“夷”称呼西南少数民族。《华阳国志》载:“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夷乘马幡盖,巡行安抚;又画牵牛、负酒、赉金宝诣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3](P364)《三国志》则将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统称之为“武陵蛮夷”。[4](P1014)晋朝甚至还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专设了南夷府和“南夷校尉”,“统五十八部夷族”以管束地方。[3](P363)南北朝时期,南方宋、齐、梁、陈四朝亦将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视为“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氐强族,恃远擅命”的“不毛之地”。[5](P303)
唐宋时期,统治者仍习惯将西南少数民族称为“夷”“蛮”或“蛮夷”。隋梁毗治西宁州,“蛮夷感悟,遂不相攻击”。[6](P1260)唐因之,“贞观至开元,夷蛮多内属”。[7](P232)唐黔中道治黔州,下辖都督府,领充、明、劳等50州,“皆羁縻,寄治山谷”,以“式遏四夷”。[8](P1003)宋高宗云:“蛮夷桀黠,从古而然”。[9]宋人宇文常亦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地图观之,划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10](P11149)陆游则将“辰、沅、靖州”仡僚、仡偻、山瑶等土著,俱称之“蛮”。[11](P73)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也将宋所辖西南羁縻州“洞、傜、僚、蛮”统称为“西南诸蛮”。[12](P134)
以“苗”称西南少数民族自宋始,元明逐渐盛行。[13]此后,“苗”逐渐成为“蛮”的另一种称呼。[14](P32)元朝为治理西南黔、湘、鄂、川、滇、桂等六省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苗族风俗语言异于汉族。治之之法……每用羁縻政策,官其酋长,仍其旧俗,设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诸土司,及土府、土州县,并令其世袭,掌自治权”。[1]P1923“诸夷……不输税赋”。[15](P437)为便于治理苗疆地方,元政府还将西南少数民族分别称呼为苗、瑶、僮(又称侬)、仡佬、金齿白夷(又称白夷、白衣)、白人(又称僰人、白蛮)、罗罗(又称乌蛮、爨人)、峨昌(又称阿昌)、黎人等,以示区别,但仍习惯以“夷”“蛮夷”“西南番”或“诸部蛮夷”统称西南诸少数民族。[16]P194同时,元代在治理西南民族地区的过程中实行了土司制度,置路、府、州、县与蛮夷官,这为明清苗疆概念及其区域行政地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经过元代近百年的“因俗而治”,到明代,“苗”作为宽泛的民族概念,在地理范围上逐渐明确起来。虽然明代因循前代仍以“夷”“蛮”或“蛮夷”泛称西南民族区域,[17]但对“苗”的概念却日益清晰起来,并开始在地理范围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其他民族地区稍作区别。明人王士性在《黔书》中谈及贵州“苗”民族时曾说:“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贵竹地。顾清浪、镇远、偏桥诸卫旧辖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行龙家、曰罗罗、曰打牙仡佬、曰花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总之,盘瓠子孙”。[18]《黔南学政》亦指出:“若黔士之耳目,远不能越川、广,而黔中之衣食,近受窘于苗仲”。[19](P197)郭子章《黔记》亦云:“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而种类不同。自贵阳而东者,苗为夥,而铜苗九股为悍,其次曰佯佬、曰佯偟、曰八番子、曰土人、曰峒人、曰蛮人、曰冉家蛮、曰杨保,皆黔东夷属也。自贵阳而西,罗罗为夥,而黑罗为悍,其次曰宋家、曰仲家、曰龙家、曰僰人、曰白罗,皆黔西夷属。”[20](P3)“诸苗”概念遂日益固化。[21](P166)“诸苗”名称的细化,这表明了明代社会根据苗人不同区域、风俗等特征在元代基础上已经作了进一步的区域划分,对西南“苗”的社会的认知也日益深入,并据其与中央、汉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程度划分为“生苗”“熟苗”。[22](P75)
至清代,人们对西南“诸苗”的社会认知更加细致、明确,其称谓更为繁多。据乾隆《贵州通志》记载,“苗蛮”分为仲家、宋家、蔡家、龙家、东苗、西苗、九股苗、红苗、黑苗、青苗、白苗、花苗、谷兰苗、紫姜苗、平伐苗、阳洞罗汉苗、仡佬、峒人等。[23]在清代西南“苗”的社会认知深入的过程中,不同名称的苗人部族的地域性也更加明确。“都匀、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居山者曰山苗、高坡苗;近河者曰洞苗;中有土司者曰熟苗,无土官者为生苗,衣皆黑色,故曰黑苗”。[23]清平苗有“黑苗、西苗、夭苗、仡佬、仲家、佯偟七种”等。[24]
正是在对西南苗疆少数民族认知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中央政权力量在逐渐将苗疆民族纳入到有效控制、管理的过程中,为治理的方便,也将苗疆各民族与地域日益结合起来,加以固化,最终在西南湘黔鄂渝桂毗邻区域形成了一个以苗族为主体,多民族大杂居的具有典型性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政治历史特色的特殊区域——“边省苗疆”[25](P221)
二、从“藩属疆索”到“苗疆”:苗疆历史地理概念的形成与演化
“苗疆”成为一个具有特定的政治意涵的历史地理称谓,发轫于元,发展于明,成于清而渐固化,是为当时国家与社会对西南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泛称。
“苗疆”是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通过“王化”手段,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逐渐纳入到直接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疆”的含义,按《辞海》释义,即为边界、境界,如边疆、疆域、疆界等,疆域即疆土,有国境之意。[26](P965)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亦不乏疆界、疆域的表述。荀子曰:“纵不能用,使无去其疆域,则国终身无敌”。[27](P144)《史记·吴起传》:“与强秦疆界”。[28](P149)《晋书·地理志》云:“表提类而分区宇,判山河而考疆域”。[29](P261)这些表述虽与现代意义的“边疆”内涵有较大的差异,但皆指某一地域。后随着古代中国腹地观念的形成,国家和社会逐渐以北疆、西疆、南疆和海疆概称边疆地区。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根据与中国腹地的远近关系和联系程度,划分为“内边”和“外边”。无论“内边”还是“外边”,都是指传统时期王朝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治理和防范措施在国家理念上的具体反映。[30](P33)历代大一统王朝无一例外地将远离中原腹地的边疆民族地区称为“藩属疆索”。[31](P145)
为强化“藩属疆索”的控制与管理,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将其纳入到国家“版图”之内。古人所言“版图”系指登载人口、土地的图册版籍。凡人口、土地载入国家和府、州、县图册版籍的区域即是王朝的“疆”与“版籍”。在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到中央政权直接治理的过程中,这些民族区域相对于内地腹里而言便成为了“新造之疆”或“新疆”,并随国家力量的深入,将其改造而化为“旧疆”。[32](P170~172)元代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多数时期未能将西南民族地区完全纳入到国家有效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元朝统一全国后,即在西南苗疆实行土司制度。例如,至元二十年元军征服黔中、黔南九溪十八洞后,大者设州,小者设县,置顺元蛮夷长官司,有雍真乖西葛蛮等20余处,俱以土著头人为蛮夷长官,隶属于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例如,思州田谨贤“以地归附,乃置万户府”,后改思州军民安抚司,由田谨贤统之。[33]播州土官杨帮宪“以播州、珍州、南平军三州之地降”,元朝因之“许世绍封爵”,历任宣抚使、安抚使、宣慰使等职,子孙承袭之。[34](P550~554)这些土司辖区虽为元廷称之为“蛮夷腹心之地”,[15](P2558)且这些土司辖区各民族也因多不载于官府户籍图册而非朝廷编户齐民,似乎在国家“版图”之外而处于一种超然的状态,但却因元中央政府所实施的“郡县其地”“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5](P1346)在事实上成为了国家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可视为西南苗疆民族地区在国家行政地理概念确立之肇始。
明朝在承继元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在西南部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设卫所、派驻流官,以强化地区控制。明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所设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亦各异俗”,“其在黔中者,自沅陵至普安二千里,总称之苗”。[35](P324~325)在治理的过程中,“苗”日渐与特定的某一地理区域结合在一起,如“古州八万诸苗,即今黎平苗也”。[36]明实录中“黔苗”“川、湖之苗”“四川、湖广、贵州三省红苗”“播州苗”“两江苗”等称谓即是如此。[37](P416~1070)后因受国家“王化”程度的不同,又逐渐区分为“熟苗”和“生苗”。“近省界者为熟苗。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20](P8)在明代西南苗疆民族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人们也开始根据各民族的风俗而有意识地对之加以区隔。湖广“施州、保靖、永顺正当海内山川土宇之中,反为槃瓠种类盘踞”,为夷汉杂居区。[35](P288)云南则为“诸夷杂处之地”,号为“百夷”,是为夷人聚居区。[35](P322~323)“倮亻罗”则排除于苗疆之外,而限于滇境。[38]广西柳州、思恩、庆远等地则“纯乎夷,仅城市所居者民耳,环城以外皆傜僮所居”。[35](P311~312)这些西南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的宏观概括,为明代苗疆概念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本的认知基础。于是,明朝政府遂将元代所称“蛮夷腹心之地”改视为“苗界”。其文献中亦开始出现了新的地理名称明确的词汇——苗界、苗疆。《明史·地理志》云:“清水江,上流自新添卫流入,经城西,又名皮陇江,北经乘西、巴香诸苗界,而注乌江”。[39](P696)刊刻于弘治时期的《贵州图经新志》亦将黔东南黎平一带地区通称为“苗界”。[22](P76)明末郭子章在《黔记》亦云“铜仁之苗界在楚黔”。[40](P16)湘西宝庆府与鄂西南施州卫所辖“溪峒苗蛮”亦被称为“诸苗”。[21](P166)徐霞客还将西南苗人聚居区和彝族聚居区有意识地作了区分,分别称之为“苗堡”和“彝区”。[41](P1、30)明末,“苗疆”一词也出现在朝廷奏疏和文献之中。天启五年四月,工科给事中虞廷陛为平息贵州都匀、凯里、黎平、思州苗民起义,在其奏折中提议“阳许收降悬赏苗疆,阴令缚献”。[42](P8)蔡复一《抚治苗疆议》亦云:“凡此五者,皆抚治苗疆之大要也”。[43]但此后晚明文献却再无“苗疆”一词之表述。
在明代“苗界”“苗疆”认识的基础上,清代国家和社会对“苗界”的认知更加清晰明了。清初,国家和社会仍沿用了明代对“苗人”聚居区的称谓。例如,康熙《彭水县志》载:“(彭水)四邻苗界,犬牙交错”。[44]康熙《天柱县志》亦云:“清水江发源于黔属苗界”。[45]上卷,“山川”鄂尔泰在《云贵事宜疏》中说:“不禁其开垦而不来开垦者,缘荒地多近苗界,实虑苗众之抢割”。[46](P699)乾隆时,针对保甲册籍编审问题,要求“除去流寓,将土著造报”,“番疆苗界,向来不入编审,不必造报”。[47](P875)在清代承继明代改土归流,将西南民族地区施以“王化”的历史进程中,“苗界”一词逐渐被“苗疆”所代替,而特指西南以“苗人”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苗界”“熟苗”和“生苗”的基本内涵也因此随历史进程不断演变。诚如《贵州通志》所云:“古州、八寨,昔化外之生苗”。这意味着生苗、生苗界已在文献中沉淀为历史名词了,并最终消融于“苗疆”一词之中。[23]“苗疆”一词虽最早出现在明末,但广泛使用却是在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过程中。“康熙三十八年,以镇筸居苗疆冲要,改沅州镇为镇筸镇”。[48](P4087)雍正四年清世宗在给云、贵、川、广、湘五省督抚的上谕中严责其“惟边省苗疆,间有督抚自行归结之案,地方官无限期,遂生怠玩,以致案件稽迟,民人受其拖累。”[25](P221)针对官员任命问题,雍正亦屡次强调:“云贵川广等省苗疆地方,请照台湾例,令文武官弁互相稽查”,[49](P827)“稍觉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及时调换”。[50](P986)官员任命遂有“苗疆缺”之名目。据《清史稿》记载:“中国边防,东则三省,北则蒙边,西则新、甘、川、藏,南则粤、湘、滇、黔……边防与国防并重。兹分而述之:曰东三省……曰蒙边防务,曰新疆,曰西藏、曰苗疆”。其中国家任命的“云南元江、鹤庆、广南、普洱、昭通、镇边等府通判、同知,镇雄、恩乐、恩安、永善、宁洱、宝宁等州县,贵州古州兵备道,黎平、镇远、都匀、铜仁等府同知,清江、都江、丹江通判,贞丰知州,荔波知县,四川马边、越嶲同知,均为苗疆缺”。[48](P3211)乾隆、嘉庆、道光等朝亦大都以“苗疆”称呼贵州、湖南等省“苗人”聚居地区,如“楚之‘苗疆’,溯湖而西,以郡为厅,参错皆是也”。[51](P5)另据《清史稿》统计,有记载“苗疆”的条目不下60处。此外,“苗疆”也为社会广泛认知,如陆次云《峒溪纤志》、李宗昉《黔记》、檀萃《说蛮》、陈鼎《黔游记》、龚柴《苗民考》、方亨咸《苗俗纪闻》、严如熤《苗疆村寨考》、蓝鼎元《边省苗蛮事宜论》、罗文彬《平苗纪略》、徐家干《苗疆闻见录》、王闿运《湘军志》等著述均大篇幅载录了苗疆地理、风俗习惯、族群、社会经济、文化和城镇等内容。这样,经过历史时期的演化,“苗疆”在清代成为了一个类似于蒙疆、新疆、西藏等民族区域,在国家制度下具有相当政治地位的民族区域。[48](P4063)“苗疆”便成为了具有特定的政治历史意涵的以“苗人”为主体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地理名词。以至于西方传教士将其在苗疆所进行的传教活动也冠之以“苗疆开荒”。[52](P35)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界根据民族的特征对西南各民族聚居区域进行了诸多科学考察。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对湘西苗疆苗族名称的递变、地理分布、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所谓苗疆,以嘉庆二十五年严如煜《苗防备览》中之‘苗疆全图’为根据,以沅江以西、酉江以南、辰江以北,及湘黔交界以东范围以为苗疆区域”。[53](P47)王静寰、王云路则分别考察了湘西苗族分布、种族、语言和人口,指出“苗人居于湘西之保靖永绥及川黔边地,其种族共为二十九宗,言语各异”;[54](P28)“苗族同胞在湘西,以凤凰、乾城、永绥、古丈、保靖五县散布最多,约有二十多万”。[55](P11)在贵州苗疆,“苗民多接寨而居……其散布之区域既广,生活环境遂异……因天候水土之不同,语言遂生歧异。因生活习惯之差别,服饰亦随之改变,于是苗民称呼乃益烦难矣”。以服饰颜色而分,“则有青苗、黑苗、白苗、红苗”;以居住地划分,“则有山苗、高坡苗、平地苗、堤苗”;按地区划分,“则有水西苗、加车苗、潦塘苗”等。[56](P1~3)其分布“以黔东各县为中心,散于黔中、黔南及黔西各县”。[57](P1)纵观民国时期学界对苗族及其疆域的考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清代以来的“苗疆”历史地理概念,较一致地认为贵州东部、南部和湘西为近代“苗疆”核心区。同时,国民政府出于近代民族平等理念的施行和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的现实需要将“苗疆”改称为“边地”或“边区”。[58](P273)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传统的“苗疆”一词逐渐被赋予了现代民族意涵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所代替,而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或学术词汇。近来因旅游开发的需要,“苗疆”一词又陆续被湘黔鄂渝桂等省市区一些风景区或城市所援用,而重归于大众视野。
总之,经过历史的发展变迁,到明清时期西南苗疆的历史地理概念最终形成。后随着苗疆历史、地理概念的确指化,国家和社会认知上将本民族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交通等发展状况一概冠之以“苗疆”,进而阐述其特征。苗疆于是便成为了本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