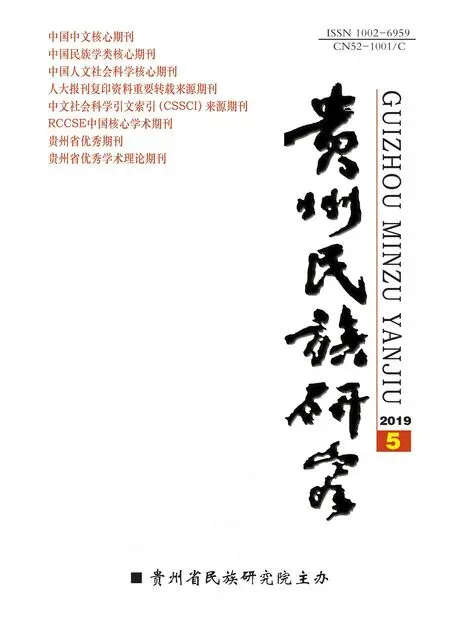基于情歌演绎透析民族传统音乐的生命力
岳明俊 金士友
(东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吉林·长春 130117)
“情”是民族传统音乐艺术主题性与主体性审美的文化结合。一方面,情歌是诉情传爱音乐艺术的囊括与概括。不同民族群体对情爱的艺术表达,折射着民族传统音乐不朽的艺术生命。比如:临夏回族、东乡族“花儿”,以相对自由的独唱将男女情爱含蓄而又直白地向大众宣泄,自由中充满丝丝情谊、缕缕爱意,继而成为妇孺皆知的情爱代名词,进而以情传递,延续着独特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民族情歌在群体直白情爱诉唱音符中不断地超脱音乐艺术本位,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在民族传统文化的镶嵌中堆塑着音乐永恒的社会生命。换言之,民族传统音乐的生命力是艺术本源生命与艺术社会价值的统一,是艺术本位、文化内置、社会映射的共同体。比如:彝族音乐《青棚里的音韵》堪称武定情歌的经典,除音乐艺术的健雅外,彝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直截了当的情爱文化,音乐线性语言的社会功能染指等构成了其独特的音乐生命体。
“歌”是民族音乐的主要艺术形式,在民族情歌的艺术历程中,歌舞是息息相关的,在歌舞艺术的框架中植入“情”的音乐主题,自然而然地倾注了民族音乐的精华。因此,立足情歌音乐艺术体的艺术脉络,透析民族传统音乐的生命力是挖掘民族音乐艺术内涵与外延的必然选择。
一、情歌——民族传统音乐艺术体的艺术脉络追溯
(一)基于民族传统音乐审视民族情歌的发展脉络
情歌是民族传统音乐的重要门类,是情爱表达音乐的综合体。同汉族音乐审美受儒道文化束缚所不同,民族情歌在艺术表达、内容承载方面与民族群体个体本位主义的价值认同相吻合,在情歌表达方面较为直白,使得民族情歌在汉族情歌“外含蓄、内直白”的挤兑中生存空间尤为狭小,但民族情歌在文化承载、社会角色定位中超乎群体固定音乐思维。比如:怒族传统情歌《求婚调》虽为情歌却是典型的怒族音乐艺术,其在表达纯洁男女情爱的同时痛斥了怒族“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婚俗文化,在传承中不少青年女性在演唱中表达了痛恨“转房婚”的心理。简单的情歌却蕴涵着丰富的怒族民俗文化。此外,《求婚调》独特的民族语调,成为探索怒族语言的重要载体[1]。
从民族情歌的基本发展脉络来看,民族情歌发展历经了“音乐萌芽到民族朴素情歌”“情歌到民族生活”“民族情歌到民族艺术”三个阶段。民族情歌的音乐萌芽源于民族群体碎片性独白音乐、说唱音乐等,大多数以歌者自我独白为基础,在音乐艺术格局与旋律方面基本处于混沌状态。一方面,早期民族情歌受中原儒道文化的影响,隐晦地多元性变相表达成为情歌通用的方式,或说或哼,或说唱相间。比如:羌族情歌《绣花调》早期以单声调的说唱为主。另一方面,早期民族情歌多游离于山水之间、乡间田野,不论独白还是对唱,青山绿水、情义朦胧,西南苗族情歌在乡野之间,诉说着阿哥阿妹别样的恋爱与厮守[2]。总之,早期民族情歌形式多变、词曲随意,与同期民族音乐相比民族情歌随意性明显。“情歌到生活”的过渡是民族传统情歌走向辉煌的黄金时期。首先,民族情歌从个体走向大众。情歌逐渐从羞涩入口的情爱唱词转向为妇孺皆知的情歌,情歌的音乐门类正式确立,且民族情歌逐渐成为群体审美认同、情歌认可的艺术表达形式。比如:佤族情歌本是群体采摘之余闲暇嬉戏的唱调,而后成为婚恋习俗“串姑娘”习俗的重要组成,“串姑娘调”“串寨子调”等情歌成为婚恋的有机组成。黔东南苗族“姊妹节”作为民俗节日,主要以情歌对唱为主[3]。其次,民族情歌超脱情爱融入群体生活,情歌被赋予了新的社会使命,民族情歌不仅仅是音乐,还是民族文化习俗的载体。再者,民族情歌实现了音乐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共生,情歌成为民族传统音乐的精灵。比如:水族情歌在重塑音乐文化之际将主旨鲜明的婚嫁文化、节庆文化等民俗文化结合,实现了音乐文化同习俗文化的共生。
“情歌到艺术”是民族情歌在现代音乐思维构筑下的全新审美,是民族情歌汇聚民族音乐精髓的关键时期。民族情歌的艺术化追溯与探讨,铸就了民族情歌超凡的艺术魅力与文化灵魂,使民族情歌逐渐成为民族传统音乐的名片。比如:羌族情歌《绣荷包》虽为后来整理,但却折射着羌族音乐艺术的全部。而佤族情歌《想你》作为现代民族情歌,从音乐表现形式诠释着民族音乐的艺术气息。
(二)基于情歌演绎透析民族情歌艺术的基本特征
民族情歌作为主题性鲜明的民族传统音乐,除富含民族音乐基本艺术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特点。一是词曲表达的直白性。民族情歌词曲表达相对中原音乐,在词曲表达上较为直白。一方面,在主题折射中,直截了当使聆听者能够快速对接,比如:德昂族情歌《葫芦笙恋歌》在歌声与器乐的交织中主题鲜明,情深意浓的恋曲格外扣人心弦。另一方面,在词曲语言表达中,民族情歌语言通俗易懂,在歌声中让人浮想联翩[4]。如彝族情歌《送郎调》的“钱文装在郎身上,拈花惹草你莫干”、《贪花闹更》的“君投妹意,情义永结合。”羞涩于口的语言在民族情歌的爱海里显得平静而又不失爱意。二是情歌形式的多元性。民族情歌从羞涩语言的表达到人文艺术的时代绽放,注定了民族情歌跨时空情境的形式多元。一方面,作为独立民族音乐门类前,民族情歌穿插于民族习俗音乐、劳动音乐等传统音乐艺术当中。比如:“阿坡翁”作为德昂族情歌对唱形式,早期发源于德昂族劳动音乐,久而久之,成为德昂族重要的情歌形式[5]。另一方面,民族情歌在类化丰富的道路上,多以山歌、调子的形式呈现。比如:东乡族情歌多以“花儿”的调子形式演绎,侗族小歌多为情歌。此外,在民族情歌的表演形式上,民族情歌的表达形式也是呈现多元化的。或说唱结合、或歌舞相伴、或声器乐并融,比如:侗族“男弦女歌”的情歌表达,成为侗族情歌的基本格式[6]。三是情歌艺术文化的复合性。民族情歌不仅是音乐文化的荟萃,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侗族情歌映射着婚姻文化和礼教文化的全部,会面歌、初恋歌、伴嫁歌等情歌通过叙事的方式将侗族婚嫁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民族情歌独特的艺术注定了其必然具有经久不衰的顽强生命力,艺术的镶嵌、文化的蕴含使民族情歌成为永恒的民族艺术瑰宝。
二、基于情歌演绎来透析民族传统音乐的生命力
(一)艺术本位:民族传统音乐艺术生命的躯体
首先,民族情歌的基本艺术形态囊括了民族音乐的基本格局[7]。情与歌、歌与舞、曲与戏,民族情歌歌舞合体、器乐歌舞并存的音乐形态同民族传统音乐艺术形态的格局大体一致,在音乐格局的塑造中民族情歌合乎传统音乐的框架。具体而言,一是民族情歌对民族音乐形态的摄入,不仅扩宽了民族音乐的艺术路径,还赋予了民族音乐的艺术发展脉络。民族情歌既有山歌的自然影子又具有祭祀音乐的仪式格局。比如:苗族情歌《阿哥阿妹来相会》在爱情的唯美刻画中,苗族山歌的曲调、节拍也融入其中。二是民族情歌情景交融、托物言情、以情喻景的表达范畴成为民族传统音乐传承与革新的艺术主线,特别是民族情歌对浪漫主题的唯美勾勒,奠定了民族情歌对群体依山傍水的自然歌颂。三是民族情歌以歌为主,兼顾戏曲、舞蹈的艺术框架同民族传统音乐歌舞多元体的艺术躯体相一致[8]。比如:怒族歌曲《哦得得》作为情歌,却超脱情歌的艺术框架,独特乐器“达比亚”的伴奏版,奏响情到深处意更浓的浪漫爱情进行曲。其次,民族情歌孕育着民族传统音乐的基本艺术属性。情爱的即兴表达,铸就了民族音乐即兴性、随意性的音乐属性,但是民族传统音乐的即兴表达,却孕育了民族音乐的自然之美。比如:藏族《砌墙歌》、蒙古族《马儿马儿快快跑》生动形象地勾勒了民族传统音乐艺术本位的原始之美。民族情歌多以4/4的节拍、词曲反复、语调折叠等音乐属性为主,在群体不断认可并传承的基础上成为民族传统音乐属性的最终格局[9]。再者,民族情歌的艺术思维是民族音乐的基本生命线。民族情歌以独特的线性思维为主,情歌的艺术思维定势逐渐转移至民族传统音乐的所有类型,圈定了民族音乐艺术属性范畴。
(二)文化内置:民族传统艺术生命的灵魂
首先,以音乐为张力和音乐演绎为基础的民族审美文化是民族传统音乐的血脉。一方面,民族情歌的审美体验汇聚着民族传统音乐审美的大体方向。民族情歌在审美趣味中侧重直白性的情感表达,独特的临摹式音乐表演涵养了民族情歌独特自在的审美文化,使民族音乐任凭岁月的摒弃和时代冲击,音乐对自然社会原生态艺术表达的审美取向,必然造就民族音乐永恒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民族情歌独特的演绎方式,凝聚着民族传统音乐独一无二的音乐文化。在情歌的海洋里,“悲而生乐,乐而生悲”的音乐演绎方式映射着的音乐文化,成为衔接民族音乐动态变迁的底线。
其次,与情歌、音乐相关联的婚庆文化是民族音乐文化主要的直接内容。一方面,类似婚庆节俗对情歌艺术的吸收,为民族情歌乃至传统音乐注入了不灭的灵魂[10]。比如:怒族“攀花”、苗族“姊妹节”等都是以民族情歌为主导的习俗节庆,民族情歌之所以世代传承,关键在于音乐艺术同关联文化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切合力。另一方面,在民族情歌的演绎中情歌对民族婚姻文化的摄列,为音乐植入了超乎艺术的生命精灵。
再者,丧葬文化、宗教文化、图腾文化等是民族情歌赖以延续的承载性文化。民族情歌通过情歌的音乐形式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使民族情歌在音乐艺术领域以超凡的生命不断传承民族文化的精髓[11]。比如:怒族“仙女节”本是祭祀活动,在祭祀过程中青年男女按照仪式,在歌舞娱乐之际,情歌成为怒族祭祀文化的最终表现形式。在情歌传承的背后祭祀文化才是音乐不断发展,持续不变的灵魂。
(三)社会映射:民族传统艺术生命的精髓
民族情歌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由音乐到生活的跨越,是民族情歌艺术性向社会性让渡的关键[12]。或者说,民族情歌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超乎艺术的生命精髓——社会映射。所谓社会映射是民族情歌跨音乐价值情境的社会价值追溯,是民族情歌社会价值的跨艺术性考量。具体而言,一是民族情歌作为特定社会符号的价值塑造。一方面,少数民族音乐长期靠口头传承的形式,将民族语言、文字以音符的生动予以承载,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二元对立的语境下,情歌乃至民族传统音乐成为洞悉民族语言的重要有声参照。另一方面,民族情歌是追溯民族文学价值的重要依据,比如:“则勒咱”和“则勒马”作为阿昌族古老情歌的重要形式,其独特的押韵、对偶形式,是挖掘文学艺术的重要素材。二是民族情歌社会化映射的历史价值考量。民族情歌的仪式性演绎是见证民族历史发展的活化石,以历史为支点,剖析民族情歌的社会价值,是挖掘民族音乐精灵的关键。三是泛艺术性价值的再追寻。民族情歌在艺术发展阶段中逐渐向规范化、民族化的轨道靠拢,以民族服饰文化为隐性的社会元素的堆积,是民族情歌不断持续发展的催化剂,特别是新时期民族文化的商业化冲击,民族情歌的市场眼球效应除音乐的演绎外,服饰文化的映射成为民族情歌、传统音乐不断传承的关键,在民族情歌的社会映射中,附带性民俗文化气息,逐渐成为民族情歌的名片。
情歌是音乐艺术永恒的典范与精髓,民族情歌从世俗走向大众,是民族传统音乐顽强生命力的写照。洞悉民族情歌的历史演变,见证民族音乐的超世永存,剖析音乐背后的民俗文化,是重新诠释与解读民族传统音乐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虽然,民族情歌在时代的洗礼与传承中脱去了裹藏在音乐背后的民俗,但是作为民族传统音乐的典范,情歌却一直书写着民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13]。毋庸置疑,民族情歌艺术价值与社会文化的合体,即音乐艺术本位、文化内置、社会映射生命体必将同个体的音乐审美相依相存,不论形式、直到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