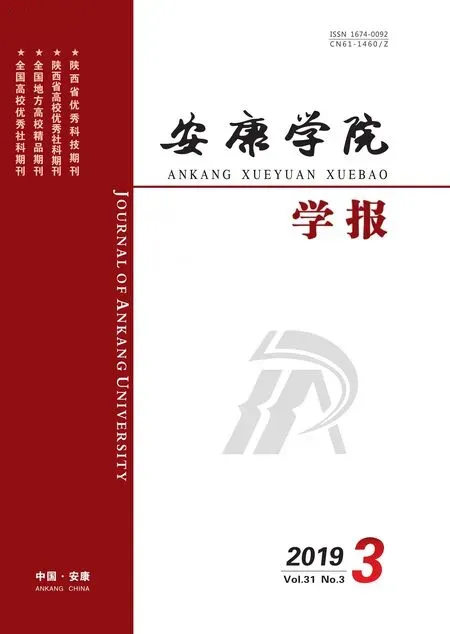论徐訏“抗战小说”中的“人性与爱”
陈 颖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在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作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但却得不到文学评论界的认可,其作品不断被误读、边缘化,他们也成了被轻视、放逐的存在。徐訏就是遭遇这种不幸的作家之一。徐訏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知名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他迁居香港,因政治、历史等原因被内地学界长期忽视,一直没有在内地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得到承认。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文学界开始清点“五四”以来的文学成就时,徐訏才重新进入内地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其小说和新诗也才得到认真的评定。在对徐訏文学成就评价的过程中,他的小说是研究的重点,但对其小说在抗战文学史上的价值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选取徐訏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抗战题材小说,从作品母题这一角度切入,探究其抗战小说的审美及艺术价值。
一、徐訏小说创作中的“人性与爱”母题概述
1966至1968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十八集《徐訏全集》,其中小说有十集。纵观徐訏一生的小说创作,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30—1936年为其作品初创期。这时期由于文坛普罗文学的繁盛,现实人生、时代的问题成为当时的文学主潮,徐訏的创作也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之后他到了法国,其思想和文学主张开始改变,创作了如《鬼恋》《阿拉伯海的女神》这类讴歌浪漫主义人性与爱的小说,初步找到了发挥自己艺术风格的题材域。1937—1949年是其创作的成熟期。这时期他的创作总体上呈现一种复杂的状态,既有以《风萧萧》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小说,又有《一家》这类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小说,还有诸如《烟圈》等带有悲观主义色调的小说,它们都表现了作者当时思想的复杂性。1950—1980年是其创作的持续发展期。他这时期作品中有着越来越重的哲学化倾向,如《江湖行》《时与光》等作品。对于其创作呈现的复杂状态,徐訏曾说:“这短短几十年功夫,各种的变动使我们的生活没有一种定型,而各种思潮使我们的思想没有一个依赖”[1]。他的创作也可被视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为追求人生真谛的苦难心路历程。
尽管徐訏的思想倾向在不断变化,但其作品中所呈现的“人性与爱”这一母题却一直存在。徐訏认为只有写人性的作品才是具有永久性的,“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文艺是由人所创造的,而人的概念中,就有一个共同的‘性质’,这就是‘人性’”[2]。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通过‘爱’的描写来折射人性,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超现实题材都离不开一个‘爱’字。”[3]二者的交织,共同塑造了徐訏的艺术世界。在徐訏的抗战题材小说中,这一母题体现得尤为特别和深刻。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史进程影响巨大,不同的作家都曾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和策略对其进行了表现。而徐訏对于战争的表现,与其同时代的那种简单、模式化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的作品不同,那些作品大多是对战争、战场等外部层面进行书写,很少深入到战争中人的内心、心理等进行挖掘和追问,缺少在人性这一维度上思考战争给个体生命和人类生存带来的摧毁,也没有自觉的审美意识。徐訏“抗战小说”的创作更接近肖洛霍夫、海明威、茨威格等世界一流作家的水准:他是在“战争”的“生与死”里面探寻“民族、人性、宗教、存在、爱与美”的关系,以及表达出在这种特殊时代里的人性,表现人们在战争的特殊“挣扎”中所放射出的“生”的光芒[4]。所以徐訏在其“抗战小说”中,对于“人性与爱”这一母题的表现,是站在一个普世价值和人性关怀的角度,思索着这场战争中个人所要承担和付出的代价以及战争中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二、徐訏“抗战小说”叙事中的两种模式:想象与真实
徐訏是一个各种体裁都精通的全能作家,他的创作贯注了其全部感情,极力探讨着人生、爱情、命运的哲理。他的作品可分为“现实”与“超现实”两类题材。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体现着作者艺术价值评判的同一母题,即人性与爱。在徐訏描写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的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现实”与“超现实”的成分存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徐訏当时也应祖国的召唤,“抗战军兴,学未竟而归国,舞笔上阵”[3]44,写了多部反映抗战的小说,展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笔者选取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进行分析,在这些小说中,作者选择了不同的叙事方式来书写:有将小说抗战背景淡化,减少生活实感,展现想象中具有浪漫情调战争的小说《风萧萧》;有一反作者固有浪漫笔调,现实主义气息浓烈的作品《一家》;还有对战争中人的复杂内心进行直观剖析的小说《灯》。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大致将徐訏抗战小说叙事分成想象与真实两种模式。
(一)想象中的理想人性:《风萧萧》中的浪漫与爱
1943年,徐訏在《扫荡报》上连载他的长篇小说《风萧萧》,这部小说当年被列为“畅销书之首”,立即使《扫荡报》“洛阳纸贵”,“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1943年也因此被称为“徐訏年”[5]。在小说中抗战情节只是副线,徐訏所展现的只是他想象中的战争,是与现实不同的具有浪漫情调的战争,主线还是表现“人性与爱”这一母题。徐訏也正是凭借着这部小说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对于小说家的艺术世界,韦勒克、沃伦曾说:“这个小说家的世界或宇宙,这一包含有情节、人物、背景、世界观和‘语调’的模式、结构或有机组织,就是当我们试图把一本小说和生活做比较时,或从道德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去评判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时所必须仔细加以考察的对象”[6]。从这样的角度来审视这部小说,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小说生动传奇的故事情节,这也是这部小说能够获得广大读者认可的一个内在原因。
《风萧萧》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上海,故事中主人公“我”是一个寓居在上海租界以研究哲学为业的独身主义者。以“我”为轴心,小说可以分为两个故事单元。第一至二十章,主要讲述了“我”偶然认识了史蒂芬,进而通过他结识了医生、白苹、梅瀛子、海伦等人,从而开始了一场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从第二十章开始,故事从传奇爱情故事转向了抗战间谍传奇。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围绕在“我”身边的各类人物开始揭开真实的面纱。经过多次误会与猜忌,“我”才知晓白苹与梅瀛子都是同一阵营的战友,于是我们三人开始合作进行抗日活动。最后白苹中弹牺牲,“我”与梅瀛子身份暴露无法正常工作,“我”只得奔赴内地开始新的生活。海伦经历了被梅瀛子利用,白苹的拯救,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向,北上求学。这部分展现了作者对于间谍生活的想象,流露出作者的浪漫心态。小说非常巧妙地将爱情与谍战融为一体,以充满悬念和陌生感的故事情节,给予了读者不同于其他作品的阅读体验。
《风萧萧》这部小说艺术世界的构成,除了故事情节曲折传奇之外,其内在意蕴也不容忽视。如果仅仅把《风萧萧》当作一部抗战间谍故事的话是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的,作品的更大价值在于超越表层间谍故事之外追求更有深刻意义的战争与人性的关系。徐訏在《风萧萧》的后记中提道:“我是一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艺术与人生上,我有同样的企慕。”[7]436小说塑造了白苹、梅瀛子、海伦等美好女性的形象,她们也是作者小说中理想化人物的代表。白苹温婉动人,具有典型东方女性的特点,她每天都过着惊心动魄的生活,但她的内心却渴望平静与安宁,这从她喜欢银色以及多次劝“我”回归书斋中能够感受到。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她没有迷失自我,而是保有着善良的人性。她想尽办法从危险境地中拯救海伦;她在分不清“我”是敌是友的情况下,还叫医生来医治受伤的我;为了夺取情报,独身一人走入了敌人的圈套,最终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和白苹性格相反,梅瀛子热烈美艳,更富有理性色彩。当白苹因轻信日方间谍的话而被害后,梅瀛子没有退缩,而是设法毒死日方间谍为白苹报仇。她身份暴露后,还依旧为“我”安排好一切退路,使“我”安全奔赴内地。而海伦是一个没有经历残酷社会磨炼的纯真少女,战争阻碍了她成为音乐家的梦想。经过一番沉沦与思考,她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回归到了永恒的艺术追求当中。在海伦身上,徐訏倾注了自己对于理想生活状态的期盼。“我”也怀着对她们三人的爱与期望,走向了更为广阔、更有意义的天地,找到了生命的真正归宿——一个使人性和个性能自由发展的地方。
在徐訏《风萧萧》这部作品的艺术世界中,“浪漫与爱”也成为解读小说精神内核的一个方向。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浪漫”的情调。如“我”的独身主义原则以及与众多女性若即若离的精神恋爱和情感沟通,就是一种浪漫心态的表现;在小说中,作者用诗化的笔触对小说人物以及环境进行描绘,使得充满危险的间谍生活充满了诗意的浪漫;同时作者在小说中淡化现实的时代环境,小说人物的间谍工作也未做详细描写,更多的是展现女主人公的聪慧与机警,对残酷的战争形式作了浪漫化处理。这些也从侧面表明,这部小说所描绘的民族战争其实是和现实战争分离开的,是徐訏浪漫想象的产物。徐訏在《风萧萧》后记曾提到自己的写作意图:“其实只是几个你我一样的灵魂在不同环境里挣扎奋斗,为理想、为梦、为信仰、为爱以及为大我与小我的生存而已。”[7]437所以,“爱”也是通向其小说艺术世界的钥匙。这种“爱”不是男女之间的性爱,而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爱”。一方面表现在“我”与几个女性之间精神上的爱恋,特别是海伦对“我”的那种哲学意义上的“爱”;另一方面表现为曼菲尔太太对海伦的“母爱”,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最崇高圣洁的爱;同时,作者还将这种“母爱”提升到“爱国”这一象征意义上,细致描绘了小说主人公对于民族、国家浓烈的爱国情怀,使作品的精神意蕴更具有现实的生命力。
总之,这部小说通过对理想人性和生命价值的多方面思考,突出了美好情感对人的精神内涵的升华,同时也展现了徐訏现代性的思想深度和哲学理念,表现了小说多维度的题旨追求。
(二)真实生命体验:《一家》与《灯》中的复杂人性
在徐訏的抗战小说中,除了《风萧萧》这类用想象构建的理想人性世界外,他还站在更为广阔的历史高度,将焦点聚焦于动乱时代中的普通人,把他们因时代压迫而变形异化的人性放大,用知识分子的理性眼光去正视战争中民众的真实心理和生存状态,为我们展现那个时代的另一面。
写于1940年的《一家》是值得注意的一篇,这是徐訏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是以沦陷前的杭州和上海为背景,叙述了一个逃亡大家庭的兴衰。在战前,林家是一个过着封闭安闲生活的旧式家庭,随着战争的爆发,林家不得不踏上逃难之路。开始便为了谁先去上海,一家人各怀鬼胎,自私人性一览无余。而后到了上海又发生了房子的分配问题、大少奶奶私吞林老太太的棺材费、二少奶奶给大少奶奶三百块钱作假等事件,展现了这个大家庭十二个成员互相之间的自私、欺骗、虚伪等丑行,将人性中的“真善美”散失殆尽。在小说中几乎所有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中,虽然他们都是在“逃难”,但从思想到行为早已将自己置于战争意识之外,毫不关注民族危亡与国家的命运,人性沦陷在自私的欲望之中。小说在现实描写中也融入了对封建家庭的思考,一方面,这个“家”是人性恶集大成的地方,集中展现了被金钱和享乐异化和扭曲的人性,作者借此也对国民性加以了批判,表现得很有深度;另一方面,徐訏通过对老四最后奔赴内地的描写,表现出青年一代的抗战意识和爱国情怀,侧面展现了他对抗战前途的乐观心态。
徐訏写于1957年冬的《灯》,是一部描写战争中人的心理承受力、人性复杂性及人的尊严的作品。《灯》讲述了主人公“我”在上海孤岛办了一个刊物,“我”和罗形累通过为刊物写稿而结识,之后才知道他是从事抗日的人。罗形累被日方通缉,“我”被当作知情人士抓去严刑问询,这之中出于“我”的道德本能,始终没有透露罗形累的行踪。之后,由于丁媚卷的天真,入了日本人的圈套,最终暴露了自己与罗形累。在这部小说中,“我”是一个很复杂的形象,既是一个“英雄”又是一个“常人”。“我”经受住了重重残酷的拷问,始终没有说出罗形累的下落。在这些被施以酷刑的拷问中,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描写“我”的心理活动。当“我”面对日本人的追问,其实打定主意想要招供,但是都被内心的道德感或是审问者的错误解读而终止,“他们一开始就把我当作决不想招供的英雄,使我很想招供的心理无法直截了当地供认”[8]467。但作者这种对于“英雄人物”的解读,不同于其他的抗战小说只是一味强调英雄人物的崇高和不怕牺牲的胆量,而是深入地挖掘到“人性”最深处,抛去道德感和英雄光环,更真实地还原一个人在面对酷刑和死亡的威胁时最“本能”的想法,尽管令人感到了人性的暗淡,但是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徐訏在小说中也将对“人性”的思考提高到了生命的层面,他借日本军官“朝信”之口说道:“你以为用你的生命换罗形累这样一个人的生命是值得的么?即以对中国来说,像你这样一个人难道不比罗形累这样一个人更值得珍贵与有意义吗?”[8]473的确,在那个时代,追寻生命价值的行为是要受到质疑的,“英雄”都是战争之外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称号,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徐訏的这一思考,将小说的内在精神意蕴推向了更高的一个层面,人们在战争的“生与死”中挣扎,战争给人带来道德与伦理上的考验,这种暴露与叙述也许才更接近当时世界的真实。
总之,从对徐訏“抗战小说”想象与真实两种叙事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徐訏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中,“人性与爱”这一渗透作家情感体验的母题贯穿其作品始终。不管是徐訏对于理想人性的浪漫想象,还是对真实人性的复杂描写,他都将这一母题当作自己艺术世界的终极目标来表现,同时对战争给人类灵魂造成的戕害,也有着富有深刻力量的表达。
三、徐訏“抗战小说”的延展性思考
(一)徐訏“抗战小说”的文学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时期的创作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峙的,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民族与阶级矛盾的激化,现实主义作品占据了主流,“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风行,“阶级性”也开始从“人性”中被抽离出来,成为被表现的主角。而徐訏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场战争的态度与多数作家不同,他不是身体力行奔赴前线支援抗战,也不是用笔墨书写宣传性和鼓动性的话语激发民众,他选择了避开主流文学,追求作品的文学性与通俗性,大胆地在作品中去描写和剖析人性。通过对人性的多层次的挖掘和塑造,对个人生存多维度的探究,来回应对那个时代的现实关注。可以说,徐訏的“抗战小说”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五四”时期以人为本的审美性文学;另一方面,对于人性与爱的追求,从文学本身的发展以及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表现来看,是有着重要意义和贡献的。
从个人视角出发,徐訏的“抗战小说”展现了更为深沉的人生哲学,极力探讨着哲学与生命的终极意义。如他的代表作《风萧萧》这部小说就有着浓郁的哲学意味和深刻内涵。笔者上文已经分析了这部小说所体现的“浪漫与爱”这一精神内核,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走入作者的哲学世界。小说前半部分写到了“我”的独身主义信仰以及对生活和爱情哲理性的思考,“我”与众多女性“有距离”的情感交流等,这俨然是作者理想的“哲学生活”。“我”对于爱情的看法,不同于普通的男女之情,是一种超越“爱”本质的情感,这里的“爱”不具有任何功利性。也许是单纯的友谊、一种生存的理想或是心灵的慰藉,还可能是对于自由的理想,总之是一种哲学家抽象意义上的“爱”。
(二)徐訏“抗战小说”研究的当代文学史意义
徐訏的“抗战小说”创作,坚持着浪漫主义的风格。他不仅在作品中减少了“五四”时期那种无节制的情感宣泄和缺少理性思考的缺陷,还有意识地加入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成分。这使他的作品“既无现实主义的直白,又无浪漫主义的滥情,而现代主义的深刻性又加强了浪漫主义的厚度。”[3]195所以后起仿效他的人很多,最出名的就是无名氏。在1989年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他将徐訏和无名氏的小说创作方法一起命名为“后期浪漫派”并称赞他们的作品“打破了艺术上的一统天下,开创了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境界”[9],他还着重肯定了徐訏在小说多样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所以,徐訏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是有其特殊贡献的。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来看,徐訏小说的文学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于徐訏作品中的“大众意识”很认可,说徐訏的小说是:“书斋的雅静与马路的繁闹融合的艺术……”[10]徐訏在《谈艺术与娱乐》一文中也说道:“文艺的本质是大众的。”[3]206徐訏对于文学创作中“雅”与“俗”的关系处理,不仅打破了传统思维中对“雅”文学的过度拔高和对“俗”文学的偏狭看法,还提供了使二者成功融合的可行经验。文学是一种人类表达需要的精神创作活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精神需求,不能用统一的文学标准将之束缚。文学中的“雅”与“俗”都是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不能将其中某一个概念放大,应多去寻找各种艺术发生的可能性,这才是文学的真正魅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徐訏的抗战题材小说创作的艺术经验,为其他作家在创作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现实超越性上有着有益启示,他的作品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
由于特殊的原因,徐訏的“抗战小说”创作横跨内地与香港两个“空间”。他1950年由沪入港,之后创作了《江湖行》《灯》等一系列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出,徐訏在创作上很少受到“政治”的影响,他延展着同时期内地创作中被割断的“五四”精神传统,一直保持着开放的文学视野,苦心营造着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些创作不仅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补充和完善,还有助于改变中国当代抗战文学史仅以内地为研究对象的单一模式,所以徐訏还是一位有着特殊参照意义的作家。
总之,徐訏“抗战小说”在人性、个体生存、哲理叙事的层面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作品中所凸显的抗战意识和抗战书写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确是一个能超越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独具魅力的作家。
四、结语
本文从徐訏小说中的“人性与爱”这一母题出发,分析了徐訏“抗战小说”叙事的两种模式,并对其文学价值和当代研究的文学史意义进行了延展性思考。他的作品是在历史、民族这一阔大的背景中,对“人性”从理想和真实多个层面进行深度测绘和思考,展现了人类面对战争危机时的人性嬗变。他还对生命意义及价值进行了具有哲学意蕴的不懈探求,营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世界。他对抗战文学所做的努力与贡献,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