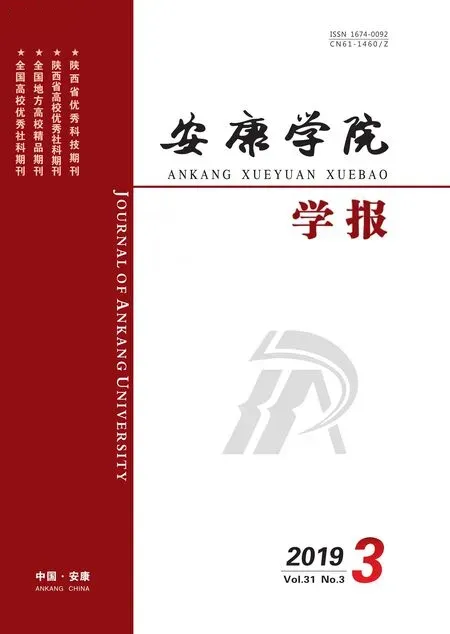唐代士族家训探析
——以柳玭家训为重点的考察
张文利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所谓家训,是指家庭或家族中长辈对于晚辈的训诫,其目的是规范家庭、家族成员言行,教化子弟,延续家族文化传统。家训的出现几乎和家庭、家族的形成是同步的①关于家训产生于何时,学界有不同观点。马玉山认为家训一类起源于东汉,盛行于南北朝。参阅其《“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第62-69页;刘剑康认为起源于上古时期普通百姓父子相传、口耳相授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伴随着家庭的形成而产生的。参阅其《论中国家训的起源——兼论儒学与传统家训的关系》,求索,2000年第2期,第107-112页;欧阳祯人认为家训起源于原始歌舞。参阅其《中国古代家训的起源、思想及现代价值》,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第36-40页。。家训的形式有韵文、散文之分,载体有纸本、石刻和木刻等之别,其内容也因为家庭、家族因素以及时代特征而不同。晚唐柳玭的家训,是唐代士族家训的代表,体现着士族的家训理念,也和六朝士族家训以及宋代的新型士族家训有所区别。本文对此略加探讨,以俟方家教正。
一、唐代士族与晚唐河东柳氏
一般认为,士族作为一种家族形态,萌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作为政治和文化高门的士族,以门阀制度为保障,形成社会的特殊阶层和特权阶层。六朝的高门著姓在家族绵延的进程中,重视家风家教,树立世代相传的家训家规,构成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堪称六朝士族家训的集大成者,也被认为是后世家训的鼻祖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为寒素阶层打开了通往仕进的大门,虽然也并未堵塞士族的仕宦通途,但是世家大族的政治、文化垄断优势却受到冲击。然而即便如此,有唐一代,门阀士族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李唐王室所属的陇西李氏本非六朝传统士族,其政治虽臻于至高无上之位,但在士族观念里,其门第族望仍不能与旧家大族相抗衡。唐太宗时期,尝令编纂《氏族志》,山东崔氏被列为第一,陇西李氏位于第三。太宗极为不满,下令重修之,明确诏令“崇树今朝冠冕”,其目的就是抑制旧家大族,抬高陇西李氏等新兴权贵的门第。唐文宗亦尝感叹说:“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1]卷172,5206唐玄宗时期重修谱牒,其修撰原则是:“取其高名盛德,素业门风,国籍相传,士林标准;次复勋庸克懋,荣绝当朝,中外相辉,誉兼时望者,各为等列。其诸蕃酋长,晓袭冠带者,亦别为一品”[2]卷560。这个既定原则,不仅抬高了“今朝冠冕”的家族门第,而且把“诸蕃酋长”也列入士族行列,这对传统士族显然是个很大的冲击,昭示着传统士族政治地位的衰落。柳芳《姓系论》曾对唐代的士族姓望有一番梳理,说: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3]卷372,3778-3779
在这番描述中,传统的旧家大族、新兴的关陇李氏和诸蕃虏姓一起,构成唐代社会的政治高门。社会阶层的新格局,带来士族生存环境的显著变化,政治、经济上的垄断性和优越感逐渐丧失。陈寅恪认为:“所谓士族者,起先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4]传统士族在政治、经济上已经不再保有优势,为了保持姓望、巩固门第,唯有大力发扬家族文化优势,整肃门风,教化子弟,以图光耀门楣,延续家族。因此,“对于士族而言,只要维护好家庭的家法、家风,文化传统不衰,其社会声望也便不会衰败,家世便会得以延绵”[5]。传统士族要保持家族文化优势,良好的家庭家族教育是必由之径。家训,作为家庭家族教育中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受到士族的关注和重视也就在情理之中。
有关唐代士族的家训资料,传世者并不多,且多数并不是撰写者有意写就的家训专文,而是因其内容关涉家训,被收录到史传文字或者后世的家训汇编之类的著述中。如姚崇、卢承庆、穆宁、皮日休等的家训类文字,收录在《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本传中;董昌龄母亲和李景让母亲的“母训”,朱仁轨、杜牧、李恕、刘禹锡的家训类文字,收录在宋代刘清之编纂的家训汇编著作《戒子通录》中。也有内容关涉家训的诗文,收录于作者的别集,如白居易《狂言示诸侄》、韩愈《符读书城南》、元稹《哭子十首》、柳宗元《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等,分别收录在他们个人的诗文集中。
河东柳氏自北朝时就是显赫的门阀士族,是河东三著姓柳、薛、裴之一。柳宗元在叙及自己的家世时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6]卷11入唐以后,柳氏亦是关中的高门望族。除柳宗元一支外,柳公绰、柳公权一支也颇为显赫。柳公绰为循吏,且以文名。其子仲郢,博学好礼,尤重义气。仲郢子柳玭,亦有文学,工楷书。柳氏家族家风优秀,家族成员品行卓杰。如:
公绰天资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丧,三年不沐浴。事继亲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绰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宫早卒,一女孤,配张毅夫,资遗甚于己子。[7]卷165,4304
(柳仲郢)母韩,即皋女也,善训子,故仲郢幼嗜学,尝和熊胆丸,使夜咀嚥以助勤。……有父风矩,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及此邪!”[1]卷163,5023
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7]卷165,4307
由上可知,柳氏家族具有优秀的家风家教,这对于家族承传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综观唐代士族,普遍重视家风家教,家族风气醇厚优良。唯唐代家训传世者不多,更显得河东柳氏家训弥足珍贵。“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7]卷165,4310,可知,柳氏家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二、唐代士族家训的基本内容
《旧唐书》卷165“柳公绰传”附“柳玭传”中,收有柳玭所著诫训子弟的文字,后世称为《家训》。《新唐书》卷163“柳公绰传”附“柳玭传”中,除与《旧唐书》所收相同的诫训文字外,另收有柳玭诫训子弟的一段文字。《全唐文》收柳玭文共三篇,其一为《大唐万寿寺记》,其二为《戒子孙》,其三为《家训》。《大唐万寿寺记》是一篇记文,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及;第二篇《戒子孙》即《新唐书》所收另一段文字;第三篇《家训》即《旧唐书》所收诫训文字。由是观之,《全唐文》收录的《戒子孙》和《家训》实则应为一篇,即《新唐书》中所收的柳玭诫训子孙的文字。本文所称的柳玭家训,即以《新唐书》所收文字为基本文本,参以《旧唐书》和《全唐文》中收录的文字。大略来看,以柳玭家训为代表的唐代士族家训,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立身
柳玭家训以立身修己为第一要务,曰:“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弃义为凶人”①《新唐书》卷163中无“以交结为末事,以弃义为凶人”两句,此据《全唐文》。《旧唐书》与此文字略有不同,“弃义”作“气义”。。“孝悌”“恭默”“畏怯”“勤俭”是他提出的做人的四个方面。百善孝为先,孝悌一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柳氏家训中,“孝悌”受到高度重视,被当作立身之基。柳玭例举崔琯祖母侍奉曾祖母至孝的故事,说明孝悌可以护佑家门昌大。在全文的结尾,更是把“孝慈友悌、忠信笃行”视作“乃食之醯酱,可一日无哉”,强调孝悌友爱之于士族家庭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在肯定“孝悌”“恭默”“畏怯”“勤俭”四者外,柳玭还指出应当戒惧的两方面:交结和弃义。在他看来,四处奉迎交结,是不足挂齿的末事;而不讲义气,做人反复无节,更是不吉利的。这两点,是对他所肯定的四个方面的反证,以更加充分地阐发所标举的立身原则。
唐代士族家训中的孝悌,不仅指对生者的孝悌友爱,还包括对逝者的祭奠葬敛。姚崇《遗训》和卢承庆《临终诫子》中,都谈到薄葬、节葬的问题,告诫子孙不要流于世俗以厚葬为大孝。恰恰相反,厚葬不仅浪费钱财,还有可能导致最大的不孝,即被盗墓,“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把薄葬、节葬的理由说透,有利于后世子孙领会遵奉。
(二)治家
“肥家以忍顺”。肥家者,犹言治家,使家业丰厚、家门昌盛之谓也。柳玭认为关键在于“忍顺”,即谦卑宽容,不义气用事,以宽柔之法,积累家业,使家庭和家族保持兴盛。唐代家训中涉及治理家业的内容很少,即便论及,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要求。苏瑰《中枢龟镜》中谈理财说:“管财无多蓄,计有三年之用。……多蓄甚害义,令人心不宁,不宁理事不当矣。”这是唐代少见的涉及钱财的家训,却提出“多蓄害义”的忠告,其钱财观念与宋代家训有很大不同。宋代士大夫家训中,有不少都谈到具体如何肥家的措施,如理财治生、发展家族产业等。
但实际上,唐代士族不善理财治家者不在少数,只是士族家庭家大业大,些微的经济损失似无足挂齿,也有士族的豪爽洒脱的个性因素在内。《旧唐书》卷165“柳公权传”谓柳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板,问遗岁时巨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笥,缄縢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所宝唯笔砚图画,自扃之。”[7]卷165,4312柳公权平素对待家资器物态度如此,可以想见,其对治家理财不会太多挂心,更不大可能将之写进家训遗示子孙后代了。
也有唐代士族谈及家产的。李德裕在其《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写道:“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人与者,非吾佳子弟也。吾百年后,为权势所夺,则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3]卷708,7267以平生之所爱对子弟谆谆教导,以保家产,其情甚为感人。然观其意,其所告诫子孙者,乃因对平泉山庄的深厚感情而不肯轻易舍弃,强调的是情感因素,而非山庄的经济价值。
(三)为官
“莅官则洁已省事,而后可以言家法,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忧与祸不偕,洁与富不并。”《旧唐书》和《全唐文》中此段文字中的“家法”作“守法”,曰“守法而后可以言养人”。三种文本文字稍异,含义基本相同。柳玭认为,做官之要仍在做人,只有自己洁身自好,才能树立规矩,有了规矩,才可以去要求规范别人。做官要“直”、要“廉”,这样才能不近祸,才不是沽名钓誉。
唐中宗朝宰相苏瑰,以子苏颋有宰相器,遂于闲暇时,将自己的为官之道和处世经验,写成二十七条文字,这就是他传世的家训文献《中枢龟镜》。《中枢龟镜》从宰相的职责、处理事务的原则、奏议的风格、与同僚相处之道、亲属子弟如何避嫌、居家宜洁而去华等诸方面,语重心长,谆谆告诫,为置身官场的苏颋提供了实用有效的做官指南。
(四)治学
“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这里的“文学”,是宽泛地指称“学问”。道德文章,历来是古人评价人物的两个重要指标,犹如今日之德艺双馨。视德行文学为根株,足见柳玭对此二者的重视。“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是说读书要有坚定的意志,要舍得吃苦。柳玭还将“不知儒术,不悦古道,懵前经而不耻,论当世而解颐。身既寡知,恶人有学”列为“坏名灾己,辱先丧家”的“五失”之一,以引起家族子弟的足够警惕。
此外,关于如何处世,柳玭认为要“保交以简恭”。谓与人交往,简捷爽直,恭敬礼让,才能交情长久。柳玭家训谈如何处世的内容不多,或许是因为士族子弟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染,于待人处世之法自然心领神会,无须多言。抑或,也有柳玭本人不甚看重处世之道的缘故罢。
三、唐代士族家训的精神内核
柳玭家训是河东柳氏树立家风家法、延续家族文化的有力手段,是唐代士族家训的代表,其所呈现出的唐代士族家训的精神内核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具有自觉的士族意识和门第优越感
河东柳氏源远流长,累世集聚,发展到晚唐,仍然是世家大族。柳玭家训中有自觉的士族观念。其开篇即言:“大凡门第高者,一事坠先训,则异他人,虽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见祖先地下。”他有清醒的门第意识,认为士族子弟比之寻常人家子弟,更要注重言行,谨遵先训,否则如有违逆家训之行为,就特别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这样,即便自己可以苟得名爵,却有何面目面对地下的列祖列宗呢?又说:“所以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①《旧唐书》此处文字作“所以承世冑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更明确了“承世冑者”的士族子弟的身份自觉。强调作为世家子弟,一定要修己为学,还把能做到这些的世家子弟称为“上智”。这种自觉的门第意识和门第优越感,既是柳玭作为世家子弟与生俱来的融渗到骨子里的气质,也未尝不是唐季时代环境下,世家子弟对士族优越性逐渐丧失的徒力挽回和自我慰藉的精神挽歌。因此,柳玭在诫训子弟时再三致意:“故世族远长与命位丰约,不假问龟蓍星数,在处心行事而已”[1]卷163,5027,“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构之重,属于后生”[1]卷163,5028。其训导子弟,延续家族统绪的心意殷切可鉴。
(二)以儒治家的基本理念
如果将柳玭家训与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魏晋六朝家训、以司马光《家范》和袁采《袁氏世范》等为代表的宋代家训相比,会看到很多共同的方面,比如对立身做人的强调就是贯穿其中恒久不变的内容。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家庭家族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自儒学创立以来,以儒治家治国的理念就得以明确。尽管佛道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也呈现出一定的作用,却始终未能动摇儒学的主导地位。“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以儒治家治国的理念几乎伴随着儒学的产生而产生。
不过,以因果报应为表征的佛教思想,在《颜氏家训》和柳玭家训中都有体现。柳玭家训中不惜笔墨,记述王涯因“不知恩权隆赫之妖”而构祸,贾餗因“卑位贪货不能正其家,忠于所事不能保其身”亦招致祸患,舒元舆因挟嫌迫害他人而最终自身也灾祸及身,说明“宿业报应”其实都有因缘。这种记述,旨在警醒家族成员要检点自省,谨言慎行,以绝祸患。虽然有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内,却是服务于修身立德的儒家用世目的。《颜氏家训》因其颇多的因果报应思想,遭到了学者的批评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其书崇尚释氏,故不列于儒家。”,足以反证士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尊崇。
(三)对修身、为学的普遍强调
《礼记·大学》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齐治平,兼济天下,是先秦儒家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在以儒治家的基本治家理念指导下,颜氏家训、柳玭家训和宋代家训中都普遍重视修身立世。柳玭指出“坏名灾己、辱先丧家”的五点过失是:安逸自私;不学妒人;心胸狭窄;从俗享乐;贪名逐誉。他认为,“五失”之害,“甚于痤疽。痤疽则砭石可瘳,五失则巫医莫及”。很明显,柳玭家训中为后世屡屡提及的“五失”,都是关乎修身立世的。
重视读书治学,是从孔子的“庭训”开始就树立的教子传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唐代士族家训,对于读书普遍都很看重。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云:“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8]卷9诗先以木材因匠人的绳削斧凿而有规矩成为有用之材,引申出读书之于人成长的重要性。然后,举出两个年齿相若的孩子的例子,因为学与不学的区别,成年以后,“乃一龙一猪”的事实,生动说明读书的必要性,谆谆教诲,勉励儿子符勤奋读书。唐代士族甚至认为,读书治学不仅是科举仕进之法门,更是终身应习之业。李恕在《戒子拾遗》中就告诫子孙“擢第之后,勿弃光阴”[9]卷4,把读书当作终生的事业。
唐代士族也颇以诗书人家而自豪。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云:“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10]卷1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位踞唐代高门的杜牧家族,教诲子弟的仍是要读书苦学,以学问立身处世。
(四)治生理财意识的淡薄
自从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此观点历经几代学人的探究,现已成为学界讨论唐宋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王水照指出:“宋代以来,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取代了六朝隋唐的门阀士族,而成为政治、法律、经济决策和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唐宋转型’的一大成果。”[11]魏晋六朝和唐代士族家训中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很少涉及家庭家族的经济问题,这一点应和他们的门阀士族的性质有关。作为世家大族,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成熟的家族经济经营模式,钱财之事既不成为问题,也就不会被放在心上。张兴武认为:“唐代‘士族’阶层不曾有过这种‘聚族而局’的家族组织形态,更不为族人承担太多的经济责任,因而他们对优美之门风的塑造全部集中在精神层面。”[12]87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唐代其他官宦诫训子弟,与传统士族相比,要“接地气”得多,会考虑到子弟后代的衣食住行等诸方面的现实生存问题。李袭誉是陇西人,尝为凉州都督。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吾近京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立身。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9]卷1这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式的家训,与农耕文化的传统相适应,亦可见出,出身陇西李氏的李袭誉以“今朝冠冕”而跻身士族行列,在家训方面与传统士族的不同。
到了宋代,家训中理财治家的经济内容则比较普遍。这个现象的出现,显然和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也和宋代崛兴的士大夫家族的性质及其经济状况有关。“宋代望族既有‘义田’‘义学’的种种负担,其做法与想法也就有了相应的改变。”[12]87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治生理财的内容堂而皇之出现在宋代的家训中。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专论,此不赘及。
要言之,处于转型阶段的唐代士族,政治优势逐渐消衰,文化传统和文化优势则仍持续绵延,家训即是其标异于一般诸姓的家族文化表征之一。柳玭家训是唐代士族家训的代表,凝聚着唐代士族家训的基本精神内核,与六朝士族家训及宋代士大夫家训既有承传,也体现出时代和家族性质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