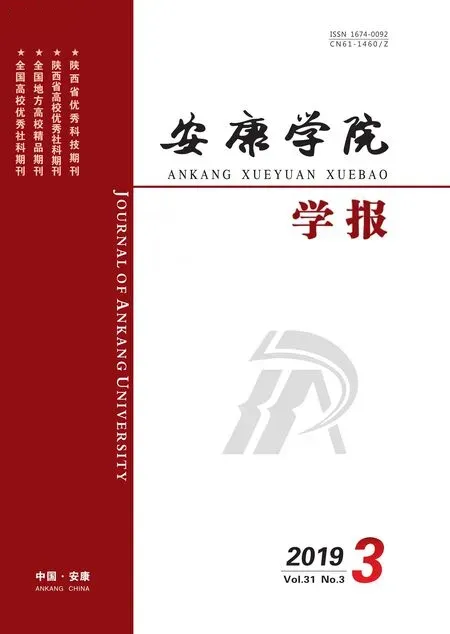中国“弥漫性宗教”的习得性特点
——以安康龙舟竞渡为例
徐彦峰,杨文思
(1.西北大学 丝绸之路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9;2.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习得性是指通过学习而增加反应强度以及对反应方式的强化。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但鲜见用其来阐释中国的宗教问题。中国有无宗教或者中国宗教的特点是什么,这是近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以来被中外学者广泛探讨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以杨庆堃先生于美国所写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一书为节点,其提出的“弥漫性宗教”(diffuse religion)与“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之经典概念基本上结束了关于中国有无宗教问题的讨论,使得中国宗教研究向着细化的方向发展,扭转了中国宗教研究的根本方向。因为中国宗教过于模糊与庞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巨大变化,更使得中国社会的宗教状况变得扑朔迷离。但是以杨庆堃先生对中国宗教“弥漫性”特点的经典阐释为基础,可以看出在中国宗教的诸多特征中,有一个特征极为明显,那就是中国宗教普遍存在的习得性。本文试以安康龙舟竞渡为例,阐释中国宗教的习得性特点。
一、“弥漫性”的中国宗教之习得性特点
中国之宗教问题,在近代以来承受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这种说法多受西方宗教的制度性特点的影响,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宗教社会,“中西宗教的存在形式和状况都有巨大差异,近现代社会忽略这些差异,以西方宗教观的有色眼镜看待本土宗教,造成对本土宗教的诸多认识误区”[1]。的确,中国社会的宗教确实没有如西方那般清晰,但是建立在制度性层面的宗教概念是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所以,面对此种研究困境,杨庆堃先生提出了经典的“弥漫性宗教”(diffuse religion)观点,用一种“特异性逻辑”去理解分析中国宗教,以区别于西方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杨先生以“功能性”作为把握中国宗教问题的主要视角,他指出:“低估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实际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寺院、神坛散落于各处,举目皆是,表明中国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2]。杨氏此种论述解释了中国宗教的基本特点,使得中外学者正视了中国的宗教问题。透过杨氏的视角看中国社会,有着太多的宗教现象,民俗、节庆等民间活动无不透露出中国的宗教文化。
关于习得性概念引入宗教社会学领域的实践,有韩恒与王瑛所作《需求性皈信和习得性皈信:农村熟人社会的基督教皈信》一文。此文在斯达克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中国农村基督教皈信类型中有需求性皈信与习得性皈信,并指出习得性皈信类型的特点:“习得性皈信并不是有目的的理性选择,而是宗教教化的结果,其中社会化的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化是通过持续性互动完成的,社会化的途径有很多,家庭影响是最重要的”[3]。依据此种习得性皈信类型的表述,可以看出中国“弥漫性”宗教也具有习得性的一般特点,“非理性”是这一特点的核心。具体可以表述为,在“弥漫性宗教”社会背景中,个人对于身处的“宗教社会”中文化、习惯的接受是一种非理性的且不得已的选择。从另一个方向来看,通过宗教社会中的每个团体成员所组成的一种集体文化,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特点同时也具备着传承性和发展性,团体内部成员在文化上表现出来一定的一致性。实际上也可以说,这种宗教的习得性特点的形成是宗教社会与个人双向互动的过程。这种选择也受这个社会团体中个人“身份认同”(Identity)之心理特点的影响。Identity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是指人格发展在少年后期所经历的一种过程,这一过程称为个人身份的意识,指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及一生趋向的一种相对一致和比较完美的意识。中国“弥漫性宗教”的习得性特点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常见的“烧纸钱”行为,就是中国“弥漫性宗教”的一种表现。这一活动的参与者从事此种活动并非是一种基于理性的思考与选择,而是身处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出于不自觉的、非理性的选择。对于此种宗教活动含义的解释,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也是有着五花八门的说法和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很多地方还出现了诸如“烧玛莎拉蒂”“烧手机”的情况,所选择的“纸钱”也是种类繁多,有类似于银票的、也有类似于人民币或美元的。中国人对于各自所处地区独特的习俗与节日的接受,无疑都是个人在“身份认同”的影响下,基于社会或家庭影响的非理性与不自觉的选择。就算身处他乡,如果法律与社会允许,个人依然会按照家乡的习俗去完成某种仪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弥漫性宗教”具有十分明显的习得性特点。
二、安康龙舟竞渡的宗教习得性特点
安康地处陕西省东南部,气候湿润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境内大小河流众多,汉江是其中最大的一条。以汉江为界,安康分为两大地域,北为秦岭地区,南为大巴山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安康独特的文化。安康居川、陕、鄂、渝交接部,具有南北衔接、东西过渡的特点,所以其文化深受南北各地的熏陶,加之安康地区人口多为历史时期的移民,多种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异彩纷呈,形成了独特的安康文化,龙舟竞渡活动正是安康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依托于端午节的安康民间传统节庆——赛龙舟,是安康地区一年一度的盛会。在这个节日里,来自安康各县区的多支龙舟队汇聚于安康市汉滨区进行龙舟竞技活动。安康龙舟竞渡可谓是安康地区的一大文化盛事,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安康龙舟竞渡的宗教面向
南宋时人祝穆著、祝洙增订的《方舆胜览》中有关于汉中府兴安州“踏石”的记载,注曰:“五月五日,太守率僚属观竞渡,谓之踏石”[4],其与龙舟竞渡有着很多的相同点,一般学者将此作为安康龙舟的起源[5]。不过此时安康地区的龙舟竞渡活动尚未形成较大规模,直至清代中期道光年间,安康地区的龙舟竞渡发展成以府治所在地为中心,拓展至辖县的大型活动[6]。民国时期,安康地区的龙舟竞渡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新中国成立后,这项活动进一步在省内拓展了其影响力,1958年的端午节,西安电影制片厂赶赴安康,专门为安康龙舟竞渡拍摄了主题纪录片——《庆丰收·赛龙舟》。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流传已久的民间活动被迫中断,直到1980年代才再一次出现在汉江水面。2000年,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龙舟搭台、经济唱戏”为主题的“安康汉江龙舟节”正式开启,每年定期举行,至今已举办了18届,并逐渐走出陕西,在全国拥有了极大的知名度,被评为“中国十大品牌节庆”。
随着安康龙舟竞渡的知名度不断上升,也引来了众多的关注,不仅是游客人数的增加,还有学术界的一些探讨。但是对于安康龙舟竞渡的讨论,大多是从文化遗产保护、体育竞技、文化传播等方面进行,对其宗教面向的讨论却未见。
那么,安康龙舟竞渡活动作为安康的文化名片,是否也是一种宗教活动呢?笔者认为它是一种宗教活动,具有宗教意义上的一般特点。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曾努力综合世界宗教的特点,得出结论:“宗教是一种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起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就是只把已有特殊发展的宗教形态认同为宗教。”[7]涂尔干的此种表述中,对“教会”一词的理解至关重要,实际上,“教会”这个词在我们研究中国民间传统宗教时可以进行一个理论转换和发展。以龙舟竞渡为例,这种“教会”是在安康龙舟竞渡活动中由其参与者和组织者组成并形成的一个“道德共同体”。杨庆堃先生的“弥漫性宗教”承袭了涂尔干研究的一般方法,沿着杨先生的思路来看,“民间信仰正是中国弥漫性宗教的主体部分,它常常通过世俗性的组织、功能性的仪式和多元化的崇拜,与外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互相嵌入、高度整合,并在传统中国的信仰系统中维持一种相当重要的主导性地位”[8]。换句话说,龙舟竞渡这种民间传统的信仰具有“弥漫性宗教”的气质。
其中,赛龙舟的仪式具有十分明显的宗教意涵。宗教仪式,一般来说,指人们不运用技术手段,而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信仰的场合时规定的正式行为[9]。祭祀仪式是龙舟竞渡活动的重要部分,共分为三项,分别为祭龙舟、拜天地和点水。这些活动一般在农历五月初一举行,目的据说是为了求得神灵保佑,消除灾难以及赛龙舟时的竞渡平安。祭龙舟,作为整个祭祀仪式的第一项,具有异常浓厚的中国民间宗教的色彩。一般来说,场地选择在寄存老龙头的寺庙,这种寺庙一般是汉江水神庙。祭祀前三天,所有的划手要洗身。祭祀仪式须在专门的道场举办,由龙舟组织者或当地官员上香并行跪拜仪式,然后游街、下江。近年来,祭龙头的仪式又多了很多的娱乐性与教育性,如2018年的龙舟节,祭龙头仪式在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三举行,参与龙舟祭祀的人群也扩大至所有来参观龙舟节开幕式的人,地点设在汉江边上,为龙头点睛的是18位安康籍名人和为安康做出贡献的人士。在祭祀大典中,18位壮汉抬着龙头,99位护卫压阵后方,走向舞台中央。主祭官高唱:“龙舟盛会,岁在端阳。承天祈福,吉祥安康。”在主祭官的引领下,百余名身穿汉服的儿童,手持祭文,齐声朗诵祭词。18位壮汉饮下寓意为平安吉祥的摔碗酒后,齐声将碗摔碎,意味着岁岁平安。随后,18位代表为龙头点睛,完成了龙头的祭祀大典。
点水也是一项较为重要的仪式,通俗点讲就是龙舟下水的仪式。在传统仪式中,当划手持龙头至汉江边时,在下水的位置摆有香案,陈列着蜡烛、猪头、羊头、菖蒲、粽子、时令果蔬等物,将龙头放置香案,奏乐,鸣放礼炮。由龙舟组织者或当地长官引领行跪拜仪式,祈求保佑平安。并宰公鸡一只,洒鸡血于汉江清流,随后将龙舟入水游个一二来回。至此,整个龙舟祭祀大典结束。
整个活动中,祭祀的对象为汉江、龙王以及屈原。在这些祭祀对象中,汉江无疑是祭祀的主体,这体现出了中国人以自然山川河流为主的传统崇拜。《周礼·小宗伯》中讲到“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10],“兆”为坛以祭的名称,说明中国人历来有以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为祭祀对象的传统。安康人民崇拜祭祀汉江还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宗教的功利性与现世性特点。汉江作为一条与安康人民息息相关的江河,可以说是安康人民的母亲河,虽然为安康人民的生活带来无穷福祉,但也常常造成洪水灾害。为了幸福安康,安康人民选择祭祀汉江,求得神灵保佑,获得现世的富庶平安。
(二)安康龙舟竞渡的习得性特点
依据前文所言,安康的龙舟竞渡作为中国“弥漫性宗教”之一种,具有中国宗教的气质,同时也具有中国这种“弥漫性宗教”的习得性特点。
首先,从传承上来说,安康龙舟竞渡活动之所以能传承至今,所依靠的不是典籍的记载和某种宗教经典的规定,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安康这个宗教性社会中的习得,不仅是操作上的习得,更是心理上的接受与认同,这与西方“制度性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安康的宗教社会背景对于安康人民接受、认可并传承这种传统活动创造了至关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条件,“宗教教化有很大一部分发生于正式的宗教组织结构之外”[11],安康宗教社会的影响毋庸置疑。从其目的上来说,现世性的目的指向非常显著,祭祀汉江、举办龙舟竞渡,为的不是达到如西方宗教那种超越性的彼岸世界,而是现世的安康,这种目的性的观念也来自于安康人民一代又一代的习得。同时也正是这种习得性使得安康龙舟竞渡的仪式与比赛年复一年的举行,并且会推出一些很有意思的创新,但是其内在核心要素与目的指向却非常稳定的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以来,安康龙舟竞渡逐渐走出安康、走出陕西、走向世界,其稳定的发展就是这一习得强化作用的重要佐证。
其次,从人们的接受上来说,受环境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接受这种宗教活动是出于非理性且不得已的选择。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作用下,当地人会选择接受此种宗教活动,并在不断习得中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没有人会很合理的、从理性的高度来解释这种宗教活动的内在理路,但是会倾向于选择相信这项活动所表达出的意涵。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作用和作为本地人归属感的影响,在端午节时,人们还是会聚集于汉江,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会。随着安康汉江龙舟节成为中国十大品牌节庆之一,其吸引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的目光,作为本地人的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而这种文化自豪感也推动了安康本地人甚至一些在安康长期定居的外乡人心中的身份认同。
最后,从仪式和内容上来说,祭祀汉江的内容是龙舟竞渡的内涵所指。前文所言,龙舟竞渡活动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汉江,关于汉江的传说很多,调查访谈一些安康老人时,每位老人口中关于汉江的认知虽存在着差异,但表现出的对汉江的敬畏却是一致的。这种敬畏,在一代又一代的习得中承袭,当地人不会过多地去思考龙舟竞渡的意义到底何在,但都在社会的潜移默化之中习得并接受。安康龙舟竞渡祭祀屈原的文化因素很有特点,屈原本身与安康关联并不大,但是在龙舟竞渡活动中却有着不小的分量,这显然与屈原的知名度以及其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的引申意涵有关,这些意涵所表现出来的无疑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知名度高的人物同时也担任了象征指涉[12]。这种具有象征指涉的文化因子以及褒义的引申意义在习得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同时,因为安康有很多古代“荆楚”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自“荆楚文化”中对于屈原这种文化符号的习得强烈影响了安康的龙舟竞渡。仪式是传统的传承,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的日新月异,人们的观念也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安康社会数代的传统依然被传承,这其中习得的作用毋庸置疑,祭祀汉江成为安康数代人的共同记忆。保平安、求安康的美好企盼成为安康人民祭祀的目标。尽管当下中国民间宗教面临着“维模”问题,安康的龙舟竞渡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虽然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关,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当地人一代又一代的习得。
三、结语
正如杨庆堃先生所言及的,中国是一个宗教社会,各地广泛存在着各种宗教活动。安康的龙舟竞渡无疑是具有中国“弥漫性宗教”特色的一个鲜明之例。本文以安康龙舟竞渡为例,承接前人的研究,认为中国“弥漫性宗教”具有习得性特点,同时这种习得性也是传统宗教得以世代传承的内在因素之一。中国的宗教,尤其是无处不在的“弥漫性宗教”是非常复杂的。近年来,社会学界围绕着杨先生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对此问题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探讨,也出现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距离构建一个中国宗教的体系轮廓尚有不少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