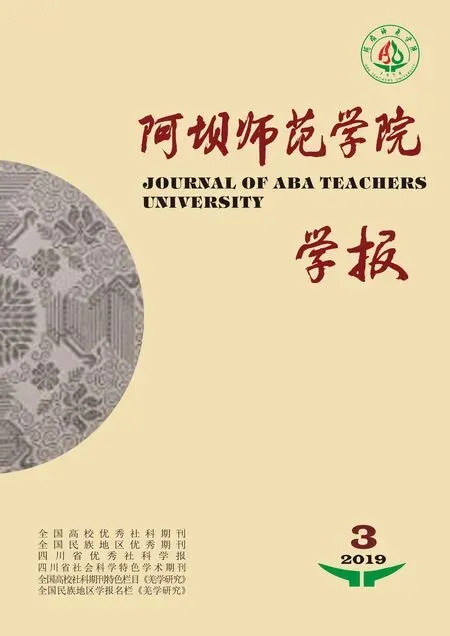灾害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
——评李朝军著《宋代灾害文学研究》
张 静
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对灾害的关注度提升,催发了探讨灾害与文学关系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陆续发表,显示出“一种较为强劲的学术发展态势,也预示了更为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1],就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说,以灾害为题材的创作蔚为大观,但学界对于古代丰富且深厚的灾害文学研究,还是关注不够、探究不深。所以,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仍是论文[2]。笔者新见李朝军教授所著的《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一书,大为叹服。该书是古代文学领域第一本灾害文学研究的系统性专著,具有开拓性与启示性意义,这本专著将中国古代的灾害文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开古代灾害文学研究之先锋
“对于中国古代典籍中大量涉及自然灾害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却没有引起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更欠缺深入扎实的细致研究。”[3]2针对这一学术实际,《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一书在中国文学史和灾害史的背景下,分类考察了两宋诗、文、词、赋中有关水、旱、蝗、疫、火、风、沙、雪、雹、地震等灾害的文学书写,对其主要内容和文学、文献、思想、文化价值作了翔实和全面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对于灾害题材创作的文学意义、社会功能、创作动机及其相关创作规律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通观学界,最早的灾害文学专著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张堂会《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民国时期的灾害文学书写,但在古代文学的灾害研究领域,还没有相关专著的诞生,《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乃是这一领域的先锋之作。该书的出版,足以证明“灾害文学”是历代普遍存在而以往学界有所忽略的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巨大存量、丰厚内蕴及其内在的统一性,足以支撑其作为一个文学分支单列出来,与人们熟悉的其他题材并立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子目。
在《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中,作者以宋代文学为中心,对灾害题材创作的文学意义、社会功能、创作动机进行总结,并由此管窥宋代文学的时代特点及其文学传承关系,最后反思灾害文学创作的得失,展望相关研究的学术发展趋势。应该说,《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一书的适时出现,及时地总结了相关研究的经验得失、探索了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制定了合理的学术规范,成为了后来的古代文学灾害题材研究绕不过去的标杆式著作。
二、拓展宋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选择灾害作品非常丰富的宋代作为本书的突破点,反映了作者对灾害文学史发展脉络的把握能力。作者指出,由于宋代官僚、文士结合的作家身份和传统灾异思想的影响,宋代诗文赋不但忧国忧民的情怀表现得强烈,而且政治批判色彩也很浓厚,所以宋代灾害题材的写作尤为明显。灾害救助是宋代一代士人的时代使命,灾害主题的写作也是一代文学的时代主题。“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主题,灾害文学映现一代文学的时代特征”,而灾害主题的写作,是“我们以往有所忽略的地方”[3]330,所以作者将宋代反映自然灾害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倾八年之力,完成了“宋代文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本灾害文学研究专著”[3]2。煌煌37万字的篇幅,展示了宋代灾害文学题材内容的广泛性、表现形式的丰富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还有社会思想、人性追问的深刻性。
这本专著,丰富了宋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开拓出宋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新空间。复旦大学中文系王水照先生曾将宋代文学与科举、宋代文学与地域、宋代文学与党争、宋代文学与传播、宋代文学与家族,称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五朵金花”,我们看到,多年来出版的优秀的宋代文学研究专著,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五朵金花”展开的。著名学者王兆鹏先生近年来又致力于将唐宋文学与数据库、大数据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推出了文学编年地图,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强烈关注,可谓是横空出世的大金花。而李著又在试图开拓出“灾害文学”这个新的宋代文学研究视域,所以南京大学卞东波教授把《宋代灾害文学研究》称之为“宋代文学研究的‘新金花’”[4],这一比喻,是恰如其分的。
而且,该书通过对宋代灾害文学的研究,揭示了很多研究界以往模糊不清的问题。例如学界通常认为唐诗的题材内容无所不包,发展得十分完备,有“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之说(鲁迅),但作者在对宋代灾害诗歌展开研究后指出:在灾害题材的诗歌写作上面,还是得力于宋诗的大力开拓。例如蝗灾诗的创作,唐代只有几首专题吟咏,而在宋代,蝗灾诗的写作数量大增、体制扩大、手法多样、主题深刻。同样,唐代的火灾诗寥若晨星,而宋代的火灾诗包括山野、都市、公共场所与私家的多种火情种类,出现了自嘲、讽世、命运悲剧、家族兴衰、生态危机等多种思想主题。宋代还有地震诗、潮灾诗、虎狼灾、山崩诗篇等等,这些都是唐诗中没有出现的灾害题材。所以作者指出:“灾害题材的创作在唐代的诗、文、赋中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或发展,在此基础上,宋代进入繁荣发达的境地。”[3]332
再者,该书虽然聚焦在宋代,但不囿于宋代。书中充分利用了宋代文学、文化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和典型性,向前梳理了各类灾害文学创作的渊源传统,有利于增进对于历代灾害文学的全局性认识。明显可以看到,作者在分析宋代各类灾害文学作品之前,总会有意识地总结其在唐代的创作概况。例如,唐代着意写火灾的诗人诗作在8人9首以上,而宋代已经达到28人40首以上。如此这般分析宋前灾害作品的发展轨迹之后,就容易考察出宋代灾害文学取的巨大成就与独特性。而且,作者这种向前联系考察的笔触,不仅仅局限在唐代,他考察灾害文学传递和嬗变关系的笔触,往往在文学史中延伸地更远。例如作者指出,与唐代火灾诗相比,宋诗恢复了陶渊明从灾民切身感受表现火灾危害和人生遭际的写法。和东汉中后期自然灾害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思潮与文人心态上不同,两宋自然灾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人的创作上,“总体来看,两宋文人对待包括疫病在内的各类自然灾害的态度不像汉末文人那样感情强烈,态度趋于理性,反映着古代自然灾害影响文学的常态。”[3]317这就显示出了作者宏观的灾害文学史观。
三、全面把握宋代的灾害类型与文体
该书对水灾、旱灾、蝗灾、疫病、火灾、风灾、沙灾、雪灾、雹灾、地震的分类论述,体现了作者对宋代文学中灾害类型的全面把握。
在学界目前的灾害文学研究中,水灾、旱灾是研究最多的灾害类型,因为这两种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最为密集,发生的地域也最为广泛。而在《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一书中,除了水灾、旱灾之外,其他如蝗灾、疫病、雪灾、地震、沙灾等,都有广泛地涉及。在宋代以前,除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5]723这句对地震的描述之外,一千多年来,地震并没有再作为诗歌的主题予以表现。而到了宋代,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搜罗出两宋的地震诗有近十首,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地动”“地震”命名的专题诗作。如苏舜钦、苏舜元的《地动联句》是诗歌史上最早专题吟咏地震的诗作,诗中以细腻的笔触、多方位的视角表现了地震灾害,“标志着地震作为独立的题材在中国诗歌中的正式确立。”[3]254此外,作者还关注到了霜灾、蟹灾、海潮、山崩、虎灾、狼灾甚至狐狸灾害等,例如作者分析了苏舜钦的《猎狐篇》,诗中讲述了盘踞城隅的老狐狸作恶多端最终被猎杀的故事,展现了宋代灾害文学书写的广阔图景。
再者,目前的灾害文学研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灾害诗歌,其他文体则不大受重视,而在《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一书中,作者还关注了灾异奏、救灾记、灾害赋、灾害词等多种文学体裁。
作者在梳理各种灾害题材的文体时,又有了新的发现。例如作者在研究宋代灾害赋时,指出宋人发扬了唐人以赋论政的做法,开创了灾异政论赋的写作。庆历二年(1042)的殿试中,仁宗以“应天以实不以文”为题,让各地的贡士就灾异直言时政阙失,其实就是用赋的形式作灾异上书,这种从上至下的推动,就开了宋代文人以赋写灾异奏疏的先河,开创了灾异赋的新门类。再者,探讨宋代的灾害文学,人们难免有这样的疑问:在宋代文学广阔的原野中,自然灾害是一类重要题材,那么,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里有没有关于自然灾害的写作呢?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宋词具有“以富为美”“以艳为美”[6]354的特质,似乎与残酷疼痛的灾害文学异趣。但作者搜罗出宋词中涉及自然灾害的内容和篇目有100多处(篇),而且将这些篇目分为了两大类,即整篇围绕灾害救治主题写作和局部的灾害意象的运用。例如作者指出释净端的《苏幕遮》是较早出现且堪称经典的灾害词:
遇荒年,每常见。就中今年,洪水皆淹遍。父母分离无可恋。幸望豪民,救取庄家汉。最堪伤,何忍见。古寺禅林,翻作悲田院。日夜烧香频□□,祷告皇天,救护开方便。[7]821
词中描写了一场大洪水淹没了田园村舍,人民流离失所、骨肉分离,他们指望不上豪民富户的救济,只好投靠佛寺,把佛寺当成救济所。身为佛教徒的词人,只能无奈地日夜祷告,祈求上苍的救护。该词暴露了官府救援失位的真相,以及佛寺因为灾害而遭遇的损失,具有丰富的历史与社会内涵。此外,作者在列举分析各种罹灾、救灾、灾后庆贺的词作之后,指出这些词作大多以灾情及其应对为中心主题,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有一定的展现,这表明单列一类“灾害词”基本可以成立,它们是宋词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应忽视的侧面[3]305。书中关于灾害词的探讨,也大大丰富了目前的宋词研究,给词学界很好的启发意义。
面对宋代复杂的灾害类型还有丰富多彩的涉灾文体,作者策略性地采用了“以文体为经,以灾种为纬,经纬交织,考镜源流,构成一套复合研究体系”[3]17,这样就利用了有限的研究篇幅,达成了多种研究目的,展示了对宋代灾害文学的全景式观照,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效果。
四、发掘了一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宋代涉灾的作家、作品甚多,但作者能够在研究中突出重点,以主带次,重点关注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灾害文学的作家、作品,为古代灾害文学的原野挖掘了一批文学精品。
历代灾害文学不是没有精品,而是缺少发现。在《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中,我们看到作为士大夫文人参政济道的重要途径和工具,宋代灾异奏疏中名篇纷纭,例如欧阳修的《上仁宗论水灾》、李纲的《上徽宗论水灾》等,其中记录灾情的文字十分生动,可以形成独立成篇的灾难纪事。程元凤的《救灾表》、牟子才的《言灾异疏》在灾难叙事的过程中,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抒发,已经突破了公文的写法,而拥有了极大的感染力。在灾害赋方面,梅尧臣的《风异赋》记录了康定元年(1040)三月发生在中原地区的一场严重的沙尘暴灾害,该赋完整地描写了这场浩大灾害发生的全过程,“在现存文献中可能是对沙尘暴天气记述最为详细的。”[3]284在救灾记方面,曾巩的《越州赵公救灾记》可谓千古名篇,明代茅坤认为“救灾者熟读此文,则于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间矣”[8]315,康熙帝评价该文云:“斟酌古法,叙次详密,可裨救灾之术”[9]卷四一,乾隆谓其“详尽明晰”,乃“司牧之臣案头必备之书”[10]卷五六。
作者关注了奏折、笔记、赋、词等多种文体,但作者也注意到了“文学轻骑兵”的诗歌关于灾害的书写篇目尤多,也最有文学价值,所以书中关注的灾害诗歌的名家名篇最多。在其基础上,作者也统计分析出了宋代写作灾害诗的两位大家——梅尧臣和苏轼。作者通过对梅尧臣的灾害诗分类考察出:其水灾诗特别能够体现出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及其官责意识;旱灾诗多歌咏君主臣民祈雨以致功德,对水旱灾害下的天人关系做过深刻的反思;风灾诗表现了诗人宦海奔波的艰难历程,使他在与风浪的生死较量中体悟到事与愿违的天人冲突;暑热诗反映诗人自己的穷困处境,揶揄热衷功名富贵的世态人情;写日食、冬雷等异常天象的诗则援灾异以规时政,影射朝政。相比之下,苏轼的洪灾诗多写灾前灾后环境与命运的巨大变化,以及劫后余生的深沉感喟;其旱灾诗则更多地表现他对天人关系的深沉思考。
灾害文学独特的题材特点,决定了其必然是艺术审美与社会实用功能统一的果实。但作者还注重在蔚为大观的灾害文学创作中,展示那些充满文学审美价值的作品,丰富了人们对灾害文学的认识。例如罗公升的《西楼火》将书房的着火,描写成火龙在火神的鞭策下匆忙失路:
祝融下省方,掉鞭鞭火龙。夜行失故路,误入书窗中。红光拂斗极,幻出琉璃宫。鱼龙沸幽壑,台观游太空。六丁摄图史,羽化茫无踪。成毁有定理,那足介我胸。造物解相补,放入山数重。此境如此心,空洞无垣墉。[11]44359
有异于传统灾害文学惊恐、痛楚的叙述,该诗的前半部分,祝融、火龙、六丁等神鬼形象纷至沓来,组成了一个神异色彩的意象群,琉璃宫、幽壑、太空等笔墨,形成了光怪陆离的新异之美。诗的后半部分又继之以轻松的笔墨、旷达的心胸,丰富了人们对灾害文学作品的理解。再例如苏籀《不雨一绝》云:“云将炮车来御敌,雨师箭镞插于房。西成一颗望千滴,跋扈朱明未可量。”[11]19634模拟雨与旱双方对垒军前的紧张场面,写出了人们久旱盼雨的强烈渴望。作者分析道:“短短的一绝,显现了强烈的雨旸对比和巨大的心理张力,有力地表现了旱势之厉害和求雨之心切,不失骏发卓厉的艺术神采。”[3]189本书中,作者注意发掘灾害文学独特的表现手法与艺术特色,表现了作者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重心。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书后的附录,一为《先秦至两宋主要涉灾文学作品编目》,一为《宋代部分涉灾文学作品编年》,搜罗统计了大量的灾害文学作品,为目前的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研究作了最基础的工作,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文献基础,创造了便利条件。
五、重视灾害文学的社会功能与现实意义
该书是作者2009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的成果之一,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作者敏锐地抓住了灾害与文学这一重要领域进行国家项目的选题与深耕,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正是作者思考了文学何为?文学研究者何为?才有了这本著作。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本书中,作者非常重视发掘灾害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
从该书的章节设计来看,作者始终把灾害文学的社会功能作为讨论的重要层面,例如“灾异奏”中设置的“忠爱之诚”的小标题;“救灾记”中论述救灾精神;“水灾诗”中的政治批判与忧责意识;“旱灾诗”中的人祸与批判;蝗灾诗中的颂歌与讽刺;“疾疫诗”中的社会疮痍与忧悯情怀;“火灾诗”中问责、劝戒、超脱与远虑等。这种章节安排表明作者意识到该研究课题的现实性、应用性相对突出,所以注重发掘宋代灾害文学中的救灾精神与道德准则,以期服务于当今社会。
通过对各类文体的层层解剖,最后作者指出灾害文学的实用救灾功能体现在:继承采诗传统,用灾害文学来反映民情,达到下情上达的目的,如郑獬写作的《淮扬大水》《临淮大水》正是他因灾上言、为民请命、以诗为谏的结果;表达忧国忧民的兼济情怀,如孔平仲《夏旱》云:“吾徒禄食固可饱,更愿眼前无饿莩”[11]10869,程俱《穷居苦雨》云:“旧雨未干新雨涨,可怜愁绝力田翁”[11]16335;发挥讽谏、劝戒,干预时政的作用,如李纲《自去冬不雨至今道傍井竭田多不耕有感》认为致旱之由就是:“东海愆阳缘孝妇,桑林谒祷本谗夫。忠魂昭雪奸邪逐,坐见为霖万物苏”[11]17730;用灾害文学作品作为救灾措施的宣传工具,如徐积的《大河上天章公顾子敦》纵论治水的方略,洋洋两千余言;表达防微杜渐、防患未然的忧患意识,如邹浩的《闻市中遗火殆尽》云:“徙薪曲突非无策,自是当时藐不闻。”[11]14947这些灾害文学功能的总结,对我们现在创作和评价灾害文学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书中还注意到了古代灾害文学中有大量的官员罪己自咎诗,例如梅尧臣为洪灾而作的《大水后成中坏庐千余作诗自咎》;周紫芝《圩氓叹》云:“救尔无远谋,每饭惭食肉”[11]17127;陈造《苦雨》云:“坐想田畴沦沼沚,忍闻升合换罗纨。纵阳援溺知无术,惭愧身为抚字官。”[11]28162作者认为这种情况是诗人利用文学进行心理调适,达到对灾难记忆的抚慰、催眠、缓解作用,属于“典型的精神救灾”[3]328。这一分析饶有新意,对于我们理解分析为何汶川地震之后,立刻出现了写作地震诗的热潮,也有一定的启发。
宋代灾害文学的创作实践,完整全面地显示了各类自然灾害的灾象、特征和治理的过程。作者通过对这些丰富的救灾防灾文学社会功能的研究,揭开了隐藏在历史中那一幕幕恢弘沧桑的苦难记忆,展现了宋代官民兴利除害、保卫家园的丰功伟绩和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再现了当时社会各界战天斗地的艰辛历程和气吐山河的英雄壮举,勾画出古人重建田园、重建生活、重建信念的民族史诗。“时虽今古同乾坤”(苏舜钦《大风》)[11]3904,自然灾害对人类的侵袭,千年以来不曾改变,灾害文学的创作,千年以来,其本质属性也一直没有改变。古代灾害文学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效用也通用于当今社会,尤其在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今时代。所以,作者在饱含深情的研究中,同时也在呼唤这种高涨的忧患意识、铮臣风骨和淑世情怀等宝贵的思想源泉能够哺育当今社会,当相同的历史情境不幸降临时,宋人坚韧不拔的优良风尚能够滋养现代人的心田。如此看来,本书对于文学史、灾害史研究以及科研和管理部门皆具有参考价值。书中这种积极将古代文学研究联系当今社会实际的学术方法,也值得后来者学习借鉴。
当然,《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与严谨之处,例如灾害文学与灾害书写的辨析与界定还需进一步明晰;各章节的安排并不均衡;某些章节的论述相对松散;附录《先秦至两宋主要涉灾文学作品编目》与《宋代部分涉灾文学作品编年》文献搜罗不全等,我们期待着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研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