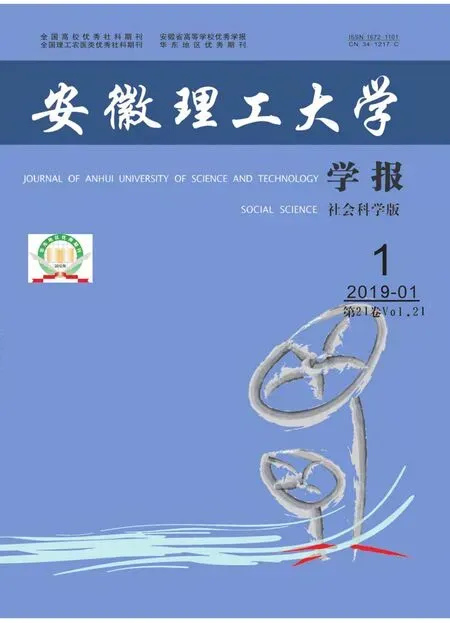论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立法缺陷
黄一鹤
(上海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201701)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流动国际化背景下洗钱犯罪涉案金额、种类急剧增加,给金融机构带来了潜在风险,也严重危害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极为关注洗钱罪的立法问题,我国亦是如此。但刑法条文相对稳定性与客观生活状态多变性之间的冲突,导致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虽历经修改取得较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一些缺陷。
一、上游犯罪主体范围狭窄导致后续行为评价不当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洗钱罪是指行为人为触犯上游七种犯罪的主体洗钱,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此处规定洗钱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的后续处置行为则主要以事后不可罚行为处理。本文认为犯罪主体部分后续处置行为,存在侵害新的法益或侵害法益程度大于原生罪侵害法益程度的情况,以事后不可罚理论处罚不适当,只有将原生罪主体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才能满足罪刑法定与保证罪责刑相一致原则。下文对各上游犯罪中超越了事后不可罚理论的后续处置行为举例分析说明。
(一)后续行为性质分析
当前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未被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对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洗钱行为一般以事后不可罚行为处理。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指在状态犯的场合,利用该犯罪行为结果的行为,如果孤立来看,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具有可罚性,但由于被综合评价在该状态犯中,故没必要认定为成立其他犯罪[1]。不可罚行为与事后可罚行为的区别就在于后行为到底是否属于前行为构成的状态犯的构成要件所预想的状态之中,是否侵害了新的法益,危害结果是否超出前行为。首先,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并不都是状态犯,因此事后不可罚存在的前提就被部分否定;其次,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在实施原生犯罪以后,部分后续行为可以被前犯罪行为所吸收,可以事后不可罚行为处理,而部分犯罪行为则产生新的法益侵害,或者侵害范围更广,需要单独定罪。下面根据此两种类型将七种上游犯罪划分并举例说明。
第一种类型即后续处置行为侵害新的法益的上游犯罪,包括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的后续处置行为。如,毒品犯罪的主体将毒赃存入银行账户使其进入市场流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主体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与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现金密集型场所的经营收入相混合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恐怖活动犯罪主体使用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各种形式投资使犯罪所得合法化,贪污贿赂犯罪主体直接将赃款汇往境外金融机构进行洗钱再汇往境内,等等。其中,毒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别侵害了我国毒品管理制度与社会经济、生活秩序,侵害的法益可以归为社会管理秩序;恐怖活动犯罪主体通过实施恐怖活动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侵害法益为社会的公共安全;贪污贿赂犯罪严重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其侵害的法益为国家廉政建设制度。而事后不论是巨额毒赃、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赃款、恐怖活动赃款,还是贪污贿赂犯罪的赃款,通过各种洗钱手段进入市场流通领域,都会对市场经济秩序以及金融安全产生严重侵害,相较于原生犯罪侵害的社会管理秩序、社会公共安全以及国家廉政建设制度而言,这些后续处置行为产生了新的法益侵害即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具有金额巨大、影响广泛、社会危害严重的特点,因此这种类型是不符合事后不可罚行为理论特征的。
第二种类型则是事后处置行为侵害法益范围大于原生犯罪侵害法益,包括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以及金融诈骗犯罪的部分事后处置行为。例如,走私罪犯罪主体将赃款转换为金融票据;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罪犯罪主体将犯罪所得收益通过投入地下钱庄、买卖彩票等方式使赃款进入流通领域或者通过赌博使其转换赌资等方式洗钱等。前后行为侵害法益程度明显加深。走私犯罪侵害我国海关管理制度,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严重侵害我国对金融秩序的管理制度,这三个罪名在我国刑法中均被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因此,从广义角度看,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罪的赃款通过事后的洗钱行为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侵害的法益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各种赃款通过洗钱的方式进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之中,波及范围广,影响速度快,破坏性强,事后洗钱行为侵害的法益的范围与侵害程度都远大于原生犯罪产生的法益侵害。因此,以事后不可罚行为处理则使超过的法益侵害逃避了处罚,有罪却无责无刑,显然违反我国刑法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罪责刑相一致原则要求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大小相适应,与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这里的“刑事责任”不是指犯罪的法律后果,而是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或者人身危险性的内容,人身危险性通常指再犯可能性。上游犯罪的主体后续处置行为侵害法益大于原生犯罪侵害法益,并且具有严重主观恶性,不处罚则必然放纵,再犯可能性升高。同时,处罚上游犯罪主体自己洗钱的行为提高犯罪成本以及刑法的威慑力,利于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侦查过程中司法机关也可借此顺藤摸瓜,查清源头,堵塞销赃的后路,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洗钱犯罪,对上游犯罪也具有一定的预防与遏制作用。
上述上游犯罪主体实施的后续处置行为明显侵害法益与原罪不同或者侵害法益范围与程度超过原罪,不能被前罪所吸收,与事后不可罚行为理论性质不同,因此应当独立定罪。
(二)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应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
如前文所述,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部分后续处置行为侵犯新的法益或者法益侵害范围与程度大于原生罪法益侵害范围与程度,不符合事后不可罚行为的理论特征,应当独立定罪。以事后不可罚理论免其处罚违背我国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因此应当对上游犯罪主体事后洗钱行为也进行相应刑事处罚。
纵观我国刑法法条列出的罪名,符合事后洗钱罪行为构成方式的只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都是以各种方式改变赃款赃物性质使其合法化或隐瞒非法化的行为。二者皆属于下游罪名,必须有上游犯罪成立为前提。但是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自己洗钱的行为并不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主体与上游犯罪主体不是同一主体,是行为人为上游犯罪主体所得犯罪收益进行掩饰、隐瞒。而本文所讨论的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事后处置行为是为自己洗钱,上游犯罪与洗钱行为是同一主体,因此不能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后续自己洗钱的行为定罪处罚。
既要坚持罪责刑相一致原则又不适用其他赃物罪罪名前提下,只有将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之内才能既保证罪行与处罚相统一又坚持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且根据国际公约的要求以及外国立法实践经验,将上游犯罪主体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是具有科学依据且满足我国国内现实需要的。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洗钱犯罪尤其跨境洗钱犯罪对国际与国内的金融秩序都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我国积极配合国际反洗钱工作,但是在国内洗钱罪立法规定上还存在缺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主体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的立法模式。例如,英国明确将上游犯罪的行为人包含在洗钱罪的犯罪主体之内,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都采取纳入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的立法模式,《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洗钱罪的规定也可以推断出洗钱罪主体包括上游犯罪主体的立法原意。国家间社会现实背景不同,故不能全盘照搬他国的立法模式,但结合我国国内现实,对于将洗钱罪上游犯罪主体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这一点,值得借鉴学习,此举有助于我国更全面预防、打击洗钱犯罪,维护我国金融秩序。
二、法律规范间逻辑关系设置不当,未能充分表达立法意图
当前我国刑法规定洗钱罪上游犯罪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七种[2],而其他犯罪领域也同样存在严重的洗钱行为,却未被列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而是主要以同属赃物罪罪名,行为性质具有相似性并且满足主体不同一性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在没有更完善的罪名法律规定情况下,此罪适用具有部分合理性。
但随着社会发展,本文认为现在某些犯罪领域洗钱行如逃税罪、赌博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涉案金额高,社会危害性严重,仅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不能充分表达立法者的意图,且有违法律规范间的逻辑关系,应将其纳入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以特殊法处罚此种帮助行为。
(一)仅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适用不当
虽然具有部分合理性,但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逃税罪、赌博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所得收益进行洗钱的行为定罪处罚仍然属于适用不当,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法益保护角度不同。两罪同为赃物罪,旨在打击侵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事后行为,但是二者对不同法益的侵害程度不同,刑法保护对象的着重点也不同。我国刑法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侵害的法益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洗钱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对金融秩序的管理。可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带来的更多是对司法机关追缴、查处赃物的阻碍。而洗钱罪则更加注重事后洗钱行为对金融秩序的冲击与破坏。
第二,有违罪责刑相一致原则。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洗钱罪法定刑轻重不同,洗钱罪的法定刑要重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刑罚。如上所述,逃税罪、赌博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三个罪名严重影响我国金融管理秩序,而当行为人实施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以外的逃税罪、赌博罪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后进行洗钱行为,造成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严重侵害时,对其却只能适用一般法条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不适当的,有违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一致基本原则。因此应当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才能保证罪责刑相适应,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避免产生司法实践中法条竞合时适用罪名不当的情况。
第三,预防犯罪功能削弱。刑法的目的除了惩罚犯罪更重要的是预防犯罪。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多为贪利性质的严重犯罪,犯罪主体之所以冒着巨大风险实施犯罪行为,就是为了获取巨大财产性利益,并利用这些利益达到各种目的,利用的过程中就使得这些财产流通进入市场,从而导致金融管理秩序的紊乱。因此,如果阻断目的,迫使犯罪分子只能将这些财产性利益囤积起来不能利用或者不敢利用,那么对于犯罪分子来说为获取利益实施前犯罪就不存在任何意义。犯罪成本降低或者刑法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降低导致犯罪率的升高。当前,仅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逃税罪、赌博罪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定罪处罚,只是做到事后惩罚,对预防犯罪未起到促进作用。如果将这三个罪名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让犯罪分子意识到犯罪成本升高,加之刑法的威严,势必削弱其犯罪的意图。例如,将赌博犯罪列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不仅可以严厉打击洗钱犯罪,还可以有效预防赌博犯罪本身以及因为赌博犯罪衍生的其他犯罪。逃税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亦是如此。
(二)适用特别法规定的必要性
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赃物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的连累犯。连累犯是指事前与他人没有通谋,在他人犯罪以后,明知他人的犯罪情况,仍故意以各种形式予以帮助,依法应受处罚的行为[3]。在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洗钱罪之前,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是以其他连累犯的罪名加以规制,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等。立法者出于严厉打击洗钱犯罪的目的将七种危害性较大的上游犯罪列为洗钱罪上游犯罪,加重处罚。因此洗钱罪罪名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赃物犯罪罪名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法条关系。刑法的产生发展与完善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中的犯罪行为需要刑法对其调整规制,而调整规制的合理性则体现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与刑法规定的罪名以及处罚是否相当。普通法与特别法原则的适用正是在解决了犯罪行为产生法条竞合的情况下,根据行为产生危害不同适用罪名轻重适当性的问题。普通法的刑法规定犯罪构成外延大,而特殊法则在普通法的基础上附加其他条件,从而缩小外延,当犯罪行为产生具有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时,原则上应当坚持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洗钱罪上游犯罪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赃物犯罪构成要件时,因为其侵害法益的严重性大大超过了普通赃物罪名的规定,因此需要适用洗钱罪这一特殊法条对其进行规制,保证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当前我国的犯罪案件中,逃税罪、赌博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洗钱行为严重侵害我国金融管理秩序,同时给我国司法程序带来诸多妨碍,与七种刑法明文规定的上游犯罪对社会产生的严重危害具有相当性,因此应将其纳入洗钱罪上游犯罪,对此类犯罪的洗钱行为适用特别法规定,才能保证罪责刑相当,更好地预防犯罪、打击犯罪。
三、上游犯罪界定过窄,与洗钱罪的立法发展方向不符
关于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问题学界争议不断。根据上文,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过窄,不能满足国内社会现实需要,且与洗钱罪立法发展方向不符,应当予以扩容,将逃税罪、赌博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纳入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
(一)国内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立法沿革与发展方向
1997年《刑法》在已有第312 条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以及第349 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基础上,增设第191 条洗钱罪罪名,规定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以及走私犯罪三个罪名为洗钱罪上游犯罪。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增加恐怖活动犯罪为上游犯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又增加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三个罪名进入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4]。根据国内洗钱犯罪现状分析以及国际公约国际立法的影响,我国洗钱罪名从无到有,上游犯罪从三个扩展到七个。纵观我国刑法规定的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扩容历程,可以发现将一般犯罪纳入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划分依据主要有以下四类:一、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刑法保障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例如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严重危及社会管理秩序,走私犯罪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恐怖活动犯罪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秩序;二、严重影响国家对金融秩序的管理。上游犯罪中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这一类罪名即符合此类标准;三、重大财产类犯罪。重大财产类案件涉案金额高,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强,因此金融诈骗类,重大走私案件被纳入上游犯罪范围;四、破坏职务行为廉洁性。贪污贿赂犯罪严重破坏了国家对职务行为廉洁制度的管理,腐蚀国家根本,因此也纳入洗钱罪上游犯罪对其强力打击。
纵观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立法变迁,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不断扩容,这是由社会物质条件发展、国内现实决定的。越来越多的犯罪符合上游犯罪划分依据,对社会产生严重影响,需要刑法加大打击力度,有效预防洗钱犯罪。逃税罪、赌博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符合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标准,不仅侵害司法工作的秩序,更产生新的法益侵害,严重冲击我国金融管理秩序。例如“金华税案”以其63亿涉案额被媒体称为“共和国第一税案”,广东“潮阳、普宁税案”涉案金额323 亿,“铁本专案”“夏都专案”“临江税案”等案件,其涉案金额至少都以十亿计;个案也不例外,北京“陈学军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地虚开地仅为北京一市,犯罪分子也仅在北京活动,但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亿元。赌博罪是一项历史久远的犯罪,危害性严重,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种毒瘤。更重要的是,赌博牵涉的资金巨大,因为赌博犯罪而实施的其他类型的犯罪也是多种多样,严重危害社会。尤其近年来“豪赌”现象严重,加之地下钱庄为赌博进行洗钱,导致我国资金流失严重、国家财政受损。此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领域的洗钱行为也危害巨大。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也增强,犯罪分子抓住消费者心理弱点以及网络等渠道缺乏监管的漏洞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牟利,近年来此罪越来越呈现出高发性、高收益的特点。例如,深圳市药监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等部门成功破获一起跨国制售假药案件,查获假冒知名制药企业的一大批知名品牌药品,货值达1.89亿元。仅一起案件数额就达到上亿元,若不对这种犯罪的洗钱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后果难以想象,且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影响范围广,社会危害性大,对消费者身心皆产生巨大伤害。
(二)国际立法趋势的导向
对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规定,国际上从1989年《联合国禁毒公约》仅限定为毒品犯罪, 到《欧洲反洗钱公约》扩展为所有犯罪的非法收益,特别是毒品犯罪、军火交易犯罪、恐怖犯罪、买卖儿童与妇女等能够产生收益的犯罪[5],《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也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展为所有犯罪的非法收益。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已成为国际立法趋势。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洗钱罪的对象范围比我国刑法规定的洗钱罪的对象范围要广得多,要求各缔约国均应当寻求将洗钱罪“适用于范围最为广泛的上游犯罪”[6],其第23 条第2 款第2 项还要求, 各缔约国均应当至少将其根据本公约确立的各类犯罪列为上游犯罪。该公约规定的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分为“最大范围”与“最小范围”,最大范围只是提供给各个公约参与国的立法导向,不具有强制力,只是作为参考;而“最小范围”则是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是公约参与国必须无条件予以规定的。尽管我国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已经扩展到七类犯罪,但是对比《公约》规定的范围,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还是较为狭窄,不仅不利于国内犯罪的预防打击,也不利于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合作,因此应适当扩容上游犯罪范围以更好配合国际反洗钱工作。
综上所述,不论是我国国内司法实践现实需要还是国际立法趋势,洗钱罪主体范围以及上游犯罪范围的立法都呈现出需要扩容的动向。本文对这两方面立法动向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其中关于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进行三个罪名的扩容建议,可能会引发不利于法律稳定性、前瞻性的争论,但是在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此立法模式是适宜的,且在出现立法修法必要时,不能为了刻板地维护法律大一统的的局面而牺牲法律明确性的要求,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